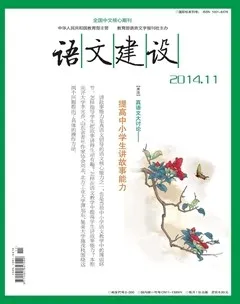第三棵樹在哪?
散文詩意濃郁,重視神韻,追求的是羚羊掛角、踏雪無痕的精湛與深意。蘇童散文《三棵樹》(本文中《三棵樹》引文,均出自北師大版《語文》九年級下冊)便有此風范,文章流淌著濃郁的懷舊與淡淡的感傷,讀后如食橄欖,余味無窮。作者以亦實亦虛的筆法,精致婉轉地描述了自己和“三棵樹”結下的不解之緣。由于“三棵樹”的意象反復出現,使之具有了隱喻象征的功能,我們也可以認為,這篇散文通篇運用了象征手法,以“三棵樹”象征自己從孩童到成年的成長過程,象征自己追逐夢想的情感歷程。
一、“三棵樹”象征不同的人生階段
《三棵樹》回憶了發生在人和樹之間的小故事,可以看作象征少年、青年和中年這三個人生階段。
弱小而嬌嫩的苦楝樹苗,成長過程是極其艱難的:它曾無處安身,“不是水泥就是石板,它們歡迎我的鞋子、我的箱子、我的椅子,卻拒絕接受一棵如此幼小的苦楝樹苗”;也曾無助可憐,“后來冬天來了,河邊風大,它在風中顫抖,就像一個哭泣的孩子”;最后是戲劇性的悲戚結局,“不會想到風是如何污辱我和我的樹苗的——它把我的樹從窗臺上抱起來,砸在河邊石埠上,然后又把樹苗從花盆里拖出來,推向河水里”。年少時的作者就似這棵苦楝樹苗。兒時的蘇童曾患過腎炎和并發性敗血癥,嚴重的時候甚至有生命危險;家里的生活也總是暗淡拮據,他不記得童話、糖果、游戲和來自大人的溺愛,“我從來不敢夸耀童年的幸福,事實上我的童年有點孤獨,有點心事重重”[1]。作者幼時成長之路的坎坷,與那棵飽經風霜的苦楝是多么相像!
要想長成棟梁之才是要經歷一番磨難的。文中寫道:“一九八八年對于我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年份,那年秋天我得到了自己的居所,是一棟年久失修的樓房的閣樓部分。我拿著鑰匙去看房子的時候一眼就看見了樓前的兩棵樹,你猜是什么樹?兩棵果樹,一棵是石榴,一棵是枇杷!”從蘇童的人生經歷來看,1986年到1988年,他在文壇嶄露頭角并聲名鵲起。此時的石榴樹像是人生目標得到跨越式發展的青年時期的作者,“石榴樹的表達很熱烈,它的繁茂的樹葉和燦爛的花朵,以及它的重重疊疊的果實都在證明這份情懷”,歷經風霜,終于小有成就,在自述中作者曾自嘲那時的自己“肥頭大耳紅光滿面躊躇滿志”[2],當時的蘇童簡直就像那棵朝氣蓬勃的石榴樹,燦爛多姿,意氣風發。
“枇杷含蓄而深沉,它決不在意我的客人把它錯當成一棵玉蘭樹,但它在初夏季節告訴你,它不開玉蘭花,只奉獻枇杷的果實。”枇杷胸懷寬廣,慈愛而悲憫,步入中年的作者更像是這棵枇杷,褪去了絢爛的色彩,在長達七年的時間里,樹凝視著作者,寬容著作者,與作者進行無數次的心靈對話、靈魂溝通。在事業迎來高峰之后,同時還兼任父親、丈夫、兒子的蘇童,多了一份成熟、一份責任。因為自己的疏忽而不知道妻子生病時,“我經常接受一種殘酷的拷問:你是人還是畜生?我當然要做人,也許我的懶惰和自私的習性從此有所好轉了”[3]。緊接著,他的母親也檢查出了癌癥,這讓蘇童非常傷心:“當我在我的文學路上‘飛黃騰達’的時候,我母親的生命卻在一天天黯淡下去,我無法確定這種因果關系,我害怕這種因果關系。”[4]經歷了繁華似錦后,步入中年的他更成熟穩重且悲天憫人,作品一改前期壓抑、冷酷、血腥、暴力的風格,變得溫情脈脈,愛與親情在作品中也得以充分舒展,他說:“沉重的命題永遠是我們精神上需要的咖啡,但我也鐘愛一些沒說什么卻令人感動令人難忘的作品。”[5]恰似那棵枇杷樹,含蓄而深沉。經過時間的累積,這兩棵果樹教會了作者很多東西,彌補了作者與整個世界的裂痕。
二、“三棵樹”象征人生夢想的不同層次
象征通常是努力尋找有聲有色的具體物象,通過暗示、聯想、烘托、夢境、幻覺等表現人內心世界的微妙。黑格爾認為:“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現于感性觀照的一種現成的外在事物,對這種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它本身來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種較廣泛較普遍的意義來看。”[6]
“三棵樹”是作者人生路途中珍貴的寶物,在這里可以看作是作者主觀情感的外化和象征,象征著作者的夢想,要用一生時間去追尋的目標。
作者幼年時懷揣著和別人一樣的夢想,他很想像“西雙版納的孩子有熱帶雨林,大興安嶺的伐木者的后代有紅松和白樺,鄉村里的少年有烏桕和紫槐”,很想擁有像其他孩子一樣的夢想帶來的快樂。然而,夢想雖然可以看見,可以想象,卻總是遙不可及,好不容易得到一株苦楝,卻終究沒能養活,但擁有樹的夢想在作者心里扎下了根。兒時的蘇童雖沒有受過正式的文學教育,但他非常喜歡文學,盡管投出去的稿子都被退回,也曾失落,但這并沒有妨礙他對文學的狂熱。苦楝象征著文學夢的種子,費盡心思為它找到花盆,本想讓它享受溫暖和陽光,卻不料一波三折。幼時的文學夢就像這棵苦楝一樣命運多舛。
后來,他迎來了生命中的另外兩棵樹:石榴和枇杷。石榴樹繁茂燦爛,果實累累;枇杷樹含蓄深沉,無私奉獻。
石榴的燦爛無疑是作者夢想之花綻放的寫照:“尤其是那棵石榴,春夏之季的早晨,我打開窗子,石榴的樹葉和火紅的花朵撲面而來,柔韌修長的樹枝毫不掩飾它登堂入室的欲望。如果我一直向它打開窗子,不消三天,我相信那棵石榴會在我的床邊、在我的書桌上駐扎下來,與我徹夜長談,熱情似火的石榴呀,它會對我說,我是你的樹,是你的樹!”石榴樹補償了作者心里的缺憾,讓作者擁有了樹,給作者憂郁的內心帶來了陽光;而擁有它們的時候,正是蘇童蜚聲文壇、夢想成真之時。當時《上海文學》《北京文學》《解放軍文藝》都發表了他的短篇。蘇童在自述中這樣說:“我看見那扇希望之門已經可以容我側身通過了”,“那些周游全國的稿件一一有了令人滿意的答復,自此上帝開始保佑我這個被文學所折磨的苦孩子”。[7]
相比石榴,枇杷含蓄深沉、穩重無私。盛名之下,蘇童卻說:“我的生活似乎非常平淡,我和妻子女兒住在南京市中心一棟破舊的閣樓上過我的日子,窗外汽車喇叭聲不斷,窗內就是我生活最重要的空間,白天讀書、會友、搓麻將,夜里寫到深更半夜,不常出門……我喜歡這種平淡隨便的生活。”[8]文學之路獲得成功后,步入中年的蘇童,多了一份寵辱不驚的心態,依舊在江南恬靜溫婉的生活之流里,做著他獨有的散發著潮濕氣息的文學夢。題材逐漸走出神秘想象與陳年舊事的狹長地帶,開始棲居于大地,更多地關注大時代里小市民的生存狀態,寫作風格也從年輕時顛覆破壞的凌厲走向保守內斂的睿智,他的人和他的創作,都像河流一樣,波瀾不驚地緩緩向前流淌,任性而優雅。
三、“三棵樹”象征追尋夢想的情感歷程
年少時,“三棵樹”小站是一個遙遠的夢,而對一個孤獨體弱的少年來說,“樹”成了他的精神寄托,身邊沒有樹是一種無法承受的隱痛。幾經周折,終于有了一棵苦楝,可是好景不長,苦楝半路夭折。對于文學的追夢人來說,這棵夭折的苦楝,可以看作是失意的寫照:“我的小說稿依然像放養的家鴿飛回案頭,這使我很沮喪。”[9]
終于天不負人愿,歲月為作者帶來了生命中的兩棵果樹,終于感受到了擁有樹的快樂。苦盡甘來,這讓作者相信自己是一個幸運的人。有了石榴,作者由“郁郁寡歡”變為“熱情”;有了枇杷,作者華麗的夢想鍍上了一層沉穩和內斂,注入了感恩和奉獻。
當然人生不止于此,“我知道兩棵樹最終必須消失,七年一夢,那棵石榴,那棵枇杷,它們原來并不是我的樹”,樹的使命只是引領著作者向前走,美夢成真后是否還會有夢?就像蘇童接受訪談時,當被認為有一個順利的文學之路時,他是這樣回答的:“聲名是一個巨大的包裹,既證明你的價值也為你增添負擔,一個年輕人如果獲得了他意料之外的聲名,有兩種可能性,一個是被負擔壓垮,一個是把這個沉重包袱里的東西減輕拿掉,越拿越少,你還可以趕路。我當然是做第二種選擇。”[10]
路途漫漫,還有更多的未知,更多的夢想在等待。“樹讓我迷惑,我的樹到底在哪里?”作者又懷想起那棵曾經的苦楝,那棵在水里向他招手的苦楝。“我一直覺得我應該有三棵樹,就像多年以前我心目中最遙遠的火車站的名字,是三棵樹,那還有一棵在哪里呢?我問我自己,然后我聽見了回應,回應來自童年舊居旁的河水,我聽見多年以前被狂風帶走的苦楝樹苗向我揮手示意,我在這里,我在水里!”“水”是一個充滿誘惑的屏障,“水”是讓樹扎根其中的生命力,水中的“樹”是塞壬的歌聲,看似能夠輕而易舉地獲得,實際卻是咫尺天涯的幻象。蘇童用樹營造了一個深邃的意境,引領讀者去探尋那隱藏在樹中的精華。“‘詩家之境,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間’……就是說藝術的藝境要和吾人具相當距離,迷離惝恍,構成獨立自足,刊落凡近的美的意象,才能象征那難以言傳的深心里的情和境。”[11]
下一棵樹在哪里呢?作者始終在尋找,那是屬于未來的,沒有定數,也許是生命無盡和奮斗永恒的象征吧!
參考文獻
[1][2][3][4][7][8][9]孔范今,施戰軍.蘇童研究資料[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71,11,12,12,11,13,11.
[5]蘇童.短篇小說,一些元素[J].當代作家評論,2005(1).
[6]黑格爾著,朱光潛譯.美學:第二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10.
[10]李杰.經典閱讀喚醒心靈——著名作家蘇童訪談錄[J].語文世界,2006(11).
[11]宗白華.藝境[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