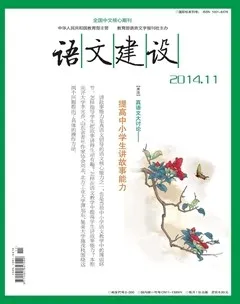民國作文教學兒童立場初探
作文一直是我國中小學語文教學的重難點。民國作文教學在實踐探索和理論研究方面均積累了豐富的課程資源,為我們破解作文教學難題提供了有價值的借鑒與參照。重溫當年國語國文的教學,給人印象深刻的是那種充盈在課堂內外的“兒童氣息”。本文初步探究民國作文教學的兒童立場及其表現,闡釋其特有的教育蘊涵,以期有俾于當下的語文課程變革。
一、兒童作文的“密碼”:外面經驗與內里情思有法度的糅合
民國作文教學致力于培養兒童的兩種習慣:“一是有所積蓄,須盡量用文字發表;二是每逢用文字發表,須盡力在技術上用工夫”[1]。積蓄源于生活中的觀察,“‘觀’是真實的受用,文章或繪畫的真滋味,要‘觀’了才能親切領略”[2]。因此,錘煉兒童的感受力和觀察力至為重要,警覺的感受力和敏銳的觀察力是作文的基礎能力。同時,作文教學還要注意進行文法的訓練,引導學生“有法度的表達”。
(一)積蓄即為作文儲備原料
生活中兒童在與人、事、物的互動中,形成豐富的表象儲備和內心體驗,外面經驗與內里情思交織糅合,用孩童方式有法度地組織語言,“主觀的情思與客觀的景物糅合,組織的方式千變萬殊,自然每有所作都成獨創了”[3]。兒童的獨特生活與感受,個性化與符合法度的表達,這樣的作文當然具有“獨創”意味。作文內容依賴于原料,需在真實生活里挖掘原料,“我們論到作文,就必須連帶地論到原料的問題。思想構成的徑路,情感凝集的訓練,都是要討究的。討究了這些,才能夠得到確是屬于正面的原料,不致枉費寫作的勞力”[4]。當然,學生需要對源于生活的原料進行個性化的加工,“思想、情感是目的,是全生活里的事情,但是,要有充實的生活,就要有合理與完好的思想、情感;而作文,就拿這些合理的思想、情感來做原料”[5]。
值得指出的是,“景物是外面的經驗,對于景物的感想是內部的經驗”[6],這里強調作者對自身經驗與情思的“糅合”,即思維加工。對外部景物,擁有獨立的見解,內部情思與別人不同,訴諸文字就是兒童本真的“作文”。作文最當緊的是真情實感,“文章是傳達自己的意思和情感給別人的東西。倘然自己本來并無這樣的意思和情感,當然不應該作表示這樣的意思和情感的文章,不然便是說誑了”[7]。“作文即求誠”,這是兒童在學習作文之初需信守的為文準則。
(二)正確與有法度的表達
任何文章都是有法的,入門先有法,而后無法,最后創出新法,自成一家之言。梁啟超說,作文教學所能教人的只有規矩。魯迅說,立定規矩,照此寫去。葉圣陶說,初學寫作,應該先學習章法。民國作文教學注重“養成正確而有法度的表述能力”[8],正確指將生活的真實感受發表出來,法度則指文章作法規范有度,行文講究思維邏輯與語言規范。法度能力的提升有賴于語言教育,要求“兒童操縱語言文字,把語言文字做發表情意的工具”[9]。在真實、具體的情境中學習語言,掌握語言規范,是提升作文能力的硬性要求,因為有法度的表達是“文章寫得好的起碼條件”[10]。與此同時,教師也應當深究文法,“要使作文教學的指導、矯正、批評、測驗等等都有一定的標準與把握,便須隨時將文法精確而徹底的研究”[11]。
原料與法度經過“糅合”形成合力,推動作文能力的提升。空有作文技巧而無原料,寫不出完好的文章,但也不能忽略法度的作用。作文內容的充實度與原料有關,原料關系到作者的經驗、修養。因為“有了優美的原料可以制成美好的器物,不曾見空恃技巧卻造出好的器物來。所以必須探到根本,討究思想、情感的事,我們這工作才得圓滿”[12]。
二、兒童作文的“驅動力”:觸發新味與筋肉運動
只有樂于表達,并體會到言說的樂趣,兒童作文的內在動機才能真正被激發,這方面,民國時期的作文教學積累了成功經驗。
(一)生活世界觸發兒童作文新味
閱讀是作文的基礎,閱讀力影響發表力,但閱讀不等于作文。作文大多源于兒童生活的觸發。“所謂觸發,就是由一件事感悟到其他的事。”[13]面對客觀的景物或生活事件,激發孩童相似的聯想與感悟,這是富有兒童氣味的情思。因為“讀書貴有新得,作文貴有新味”[14],生活體驗觸發兒童的情思,使其獲取內在的“新味”。欲達此目的,就得“留心去讀讀沒有字的書,在你眼前森羅萬象的事物上獲得新的觸發”[15],從尋常事物中體悟、發現。
但生活中的所思所感,并不一定能夠順暢地表達出來,“學童所以需要國文,和我們所以教學童以國文,一方面在磨煉情思,進于豐妙;他方面又在練習表出情思的方法,不至有把捉不住之苦”[16]。作文是發現、體悟與交流、分享交織的過程,是“發展兒童的心靈的”。一個生活豐富、體驗深刻的心靈豐盈者,自然會專心作文并最終形成個性化的表達。民國作文教學注意避免兒童與生活隔離,引導學生走進真實的生活,在親身的感受中觸發寫作新味。
(二)口語是作文的基礎
如何處理好書面語與口語的關系,是作文教學的關鍵。民國的作文教學以兒童擅長的口語入手打開寫作之門,兒童運用語言的本能和經驗比閱讀文字來得早,“話法教學實在是一切教學入手的基礎,而一切教學又處處都有施行話法教學的機會”[17]。話法即口語,語文教學若撇開口語,孤立地教文字,易造成“半身不遂”的語文,“語文教學從口語訓練入手,是順乎自然,事半功倍。放過口語練習,孤立地教學書面語,是違背自然,事倍功半”[18],口語是情意產生與傾吐的樞紐,語言是表于外的工具,“因為它最能把人與人的心連鎖起來”[19],兒童缺乏口語與思維的訓練,就會導致作文思路不清、條理混亂,因為“口語如能夠清晰流利,有結構,有組織,有勢力,有風趣,作文的技術也不過如此了。所以,口語的練習很可做作文的基礎”[20]。民國教學給予兒童講故事、演講等機會,充分鍛煉兒童口語能力。“語言發表是文章的基礎,能用語言發表情意,就不難用文章發表情意”[21],口語與書面語相互促進,統一于兒童的言語活動中。訓練兒童說話,“入手的辦法,就是要與兒童一起生活。一起生活乃是指要接觸他們的內心,而且完全了解,而且自己也差不多融合在里頭”[22]。這就要求教師要俯下身來,走進學生的生活,如此,方能真正洞悉兒童語言的秘密。
此外,兒童作文注重“能”,閱讀則注重“知”,從“知”到“能”之間有著一段距離,跨越知到能的距離需在教學中建立聽讀說寫一體化認知,即由“耳治”到“目治”,中間需經過“口治”,經過聽說讀寫的內部自循環,最終指向說話和寫作。民國時期注重口語活動作為筋肉運動的價值,剛好抓住了“語言是身體的”這一命題的要義。
三、兒童作文的“維他命”:孩童邏輯與言說方式
兒童是作文的主人。作文教學不論是訓練過程的推進,還是作為結果的文本呈現,都要包蘊、體現兒童邏輯和言說方式。唯其如此,童心、童言才可能是本真、純凈的。
(一)作文立足于兒童的實際探求
保證兒童有話可說需將寫作與生活聯系,向生活求誠。“讀物之實質固亦為種種之事物;而讀物之外,事物正多,尤貴實際探求,宜令學者隨時隨地探求事物之精蘊,且必經己之思考而得答案”[23],兒童實際探求使其心有所思,情有所感,而后有所撰作。作文教學,需引導兒童對生活中的所思所感進行加工、提煉,嘗試對事物因果做出解釋,其中“既無教師之誘掖,又無同學之輔助,各就自己之思想,以表彰其固有之能力”[24]。當然,兒童的內部加工是一個過程,“讀文好比蠶吃的桑葉,作文好比蠶的吐絲。吃了桑葉不會吐絲的蠶是沒有用的;吃了桑葉仍吐桑葉的蠶,是消化器患了病的瘟蠶。我們要看所吃的桑葉好不好,消不消化,原要看它吐絲的成績如何”[25],從吃桑葉到吐絲一是不能急迫,二是不可替代。
作文題材從兒童熟悉生活中尋找,令其有話可說,在寫作時就不至于苦咬筆頭;在兒童喜愛的讀物中尋找,喚起兒童動機的題目是與讀書聯絡。民國作文教學并非用唯一的藍本去教授,而是在生活中教授,選取切近兒童生活見聞的內容,是切生活之用的。尊重兒童實際探求,賦予其自由表達的機會,敞亮心靈。
(二)作文中的自主表達與對話
民國作文教學秉承“兒童是起點,是中心,而且是目的”的宗旨[26],教師不用成人的思維、語言強加予兒童,盡可能滿足兒童的個性欲求,還兒童本真作文的自由。兒童作文“是個人創造性的精神產品,而不是大批量生產的規格化產品,為什么在教學中非要削足適履、壓抑學生的寫作個性呢”[27],兒童是獨立的言說主體,寫作猶如寫生,文字是兒童手中的畫筆,所作之畫都是兒童個性化的表現。
兒童作文,不能局限于課堂。堂下作文是兒童自由寫作的形式,允許兒童去搜索查閱資料,調查走訪,賦予兒童時間去體驗和思考,琢磨與主題相關的素材。教學中過分注重堂上作文,令兒童絞盡腦汁去表情達意,就會封閉兒童內心,扼殺真實體驗的時機,泯滅創造性。正所謂“日札優于作文”,日札指所有課外的寫作形式。如寫日記,“日記是歲月的保險柜。通過寫日記,仿佛把逝去的一個個日子放進了保險柜”[28],日記是兒童內在的自我活動,是切合兒童心理需求的方式。由此,“教學兒童,使兒童在活潑自然的情景里,把國語科的能力,一天一天發展開來”[29]。
作文當知道寫給誰看,即樹立讀者意識。“訓練學生寫作而不給他們指示一個切近的目標,他們往往不知道是寫了給誰讀的。當然,他們知道寫了是要給教師讀的;實際也許只有教師讀,或再加上一些同學和自己的父兄。但如果每回寫作真都是為了這幾個人,那么寫作確是沒有多大趣味。”[30]因此,引領兒童心有他人,與讀者對話,養成傾聽、對話的習慣也是不能忽視的。
四、兒童作文的“潤滑劑”:自主修改與朗讀修改
語言粗糙源于思維粗糙。作文修改最當緊的是語言與思想協調、匹配。腦子里無聲的話語,寫下來就是文字,“朦朧的思想是零零碎碎不成片段的語言,清明的思想是有條有理組織完密的語言”[31],錘煉兒童語言,關鍵是理順、激活其內部思維。
(一)教師批閱與學生自主修改
養成細心修改文章的習慣,是作文教學的任務之一。因為“壞的語言習慣會牽累了思想,同時牽累了說出來的語言,寫出來的文字”[32]。
如何處理作文的自主修改與教師的批閱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作文簿的批評、訂改,是最耗教師的精神和光陰的苦事,而于兒童又實在無甚益處,因為他們只注意等第、分數或圈點、評語,至于先生的改筆如何,自己的誤點何在,能夠細心玩味的,可說是絕無僅有”[33],如何提高作文修改的成效?經過實踐探討,民國作文教學主張:一是學生自明錯處;二是自動訂正,限期改正錯誤;三是學生反復推敲,若推敲不出,教師為其細為剖析。改的工夫是教師引導下的學生自主修改,教師批語與等第判定都是服務學生自主作文的。
(二)注意修改方法的指導
民國教學倡導兒童自主訂正和朗讀修改法。批改不應只是教師下功夫,應讓兒童加入其中,“批改固非教者自己作文,乃修正學生所作之意義及字句也”[34]。兒童自主訂正作文,教師首先頒布“錯誤表”,即“字體錯誤表、文法錯誤表、事實錯誤表、思維錯誤表”[35],這是兒童修改的憑據。作文修改要旨是教師盡量少改,“其意義不謬誤而尚有不完全之處者,不必為之增;字句已通順而尚欠凝練高古者,不必為之改。意義不完,乃由于學生識力之未至,而非由于推理之謬誤”[36],以發展的眼光看待兒童的作文,著重修改生活的細節,查看觀點與材料匹配度。其間,重在啟發兒童琢磨自己的作文,掌握修改的方法。
朗讀法是修改作文的好方法。借助朗讀法修改,將口頭與筆頭結合起來,正所謂“從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詞匯,搬到紙上來”[37]。朗讀修改時,既讀給自己聽,也讀給別人聽。朗讀是對文字的深度把握,“念的人一面念的時候,一面他的思想感情就在活動了,他就把作品里的妙處一面哼出來,一面哼進去,不懂的人覺得可笑,事實上都是很有滋味的”[38],通過朗讀,文中的真滋味不斷涌現,活的情思不斷更新,作品便不斷優質化。
熟悉民國語文教學的人都知道,當時的教學主要是作文取向的,不論是平時的訓練重心,還是各類考試,都體現了這一點。這一時期的作文教學貫穿始終的是對兒童生活的關注,對童心的珍視。教學注重引導孩子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世界里,表達所思所想和愛恨情仇。兒童的世界,兒童的視角,兒童的表達,常常讓人怦然心動,作文的過程即是孩子思考與成長的過程。我們認為,這就是民國作文教學中的兒童立場。重溫昔日學者的研究,傾聽當事人的回憶,今天,我們仍能依稀見到民國作文教學的情形。
民國作文教學啟示我們,教學中要切實保證“兒童立場”,對教師而言,一是要將兒童當兒童,二是自己童心未泯。事實上,確保“兒童立場”得以實現的策略大都是“常識性”的,關鍵在于我們必須謹記,兒童是自己作文的主人。
參考文獻
[1][4][5][12][23][31][32][34][36]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下冊[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0:433,353,353,353,346,448,449,350,350.
[2][6][13][14][15]夏丏尊,葉圣陶.文心[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262-263,9,111,111,116.
[3]葉圣陶.怎樣寫作[M].北京:中華書局,2007:7.
[7]夏丏尊,劉薰宇.文章作法[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3:3.
[8][20][25]阮真.中學作文教學研究[M].正中書局,1929:15,11,2.
[9][21]李學.吳研因語文教育思想初探[A].教育史研究學術研討會編.紀念《教育史研究》創刊二十周年論文集(2).
[10]張志公.張志公語文教育論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82.
[11][33][35]黎澤渝,馬嘯風,李樂毅編.黎錦熙語文教育論著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505,504,567.
[16]葉圣陶.小學國文教授的諸問題[J].教育雜志,1922:14(1).
[17]張鴻苓,李桐華編.黎錦熙論語文教育[M].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8.
[18]鄒賢敏,王晨編.重讀呂叔湘走進新課標[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3.
[19][22][38]鄒賢敏,張定遠編.重讀葉圣陶走進新課標[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4,10-11,77.
[24]范祥善.綴法教授之根本研究[J].教育雜志,1919:11(4).
[26]趙祥麟,王承旭編譯.杜威教育論著選[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1:77.
[27]潘新和.語文:回望與沉思——走近大師[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242.
[28]周國平.周國平論教育[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113.
[29]趙欲仁.小學國語科教學的三種新趨勢[J].中華教育界,1930:18(12).
[30]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朱自清論語文教育[M].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21-22.
[37]朱泳燚.葉圣陶的語言修改藝術[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2:77.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身體與智慧——具身認知視域內的教師學習研究”(09YJA88005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基金資助項目“教學學術性與大學教師專業發展研究”(JURSP311A05)的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