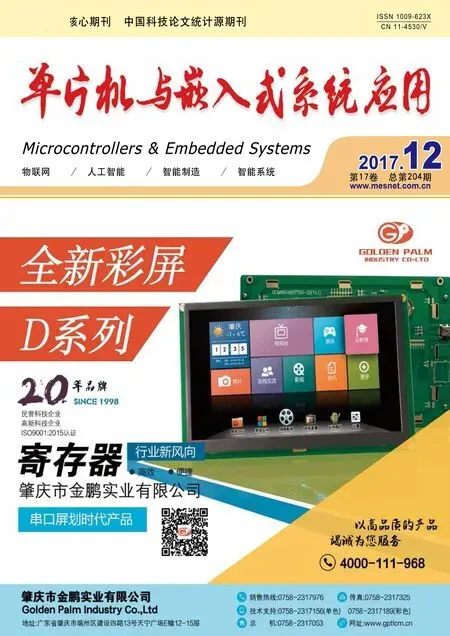Cadence攜手Arm交付基于高性能Arm服務器的SoC驗證解決方案
2017-04-17 06:23:01
單片機與嵌入式系統應用 2017年12期
Cadence攜手Arm交付基于高性能Arm服務器的SoC驗證解決方案
楷登電子(美國Cadence 公司)與Arm聯合發布基于Arm服務器的Xcelium并行邏輯仿真平臺。作為Cadence驗證套件(Cadence Verification Suite)的產品之一,Xcelium仿真平臺憑借優化的單核仿真和多核仿真技術創新有效提升了運行效率。較之前的仿真軟件平臺,Xcelium的單核性能提高2倍,多核仿真性能提高3到10倍,縮減了長周期SoC測試程序的時間,縮短產品上市時間。在基于Arm的服務器上運行Xcelium仿真平臺可以幫助系統和半導體廠商高效利用服務器核心,滿足高階節點設計對快速驗證的需求。另外,Xcelium仿真平臺自動分離設計和驗證測試平臺代碼,可在多核服務器上快速并行執行。
猜你喜歡
儀器儀表用戶(2022年4期)2022-04-01 03:17:14
閱讀與作文(英語初中版)(2021年8期)2021-09-13 02:16:29
現代裝飾(2020年7期)2020-07-27 01:27:42
流行色(2020年1期)2020-04-28 11:16:38
藝術啟蒙(2018年7期)2018-08-23 09:14:18
海峽姐妹(2017年7期)2017-07-31 19:08:17
Coco薇(2017年5期)2017-06-05 08:53:16
數字通信世界(2015年10期)2015-12-21 12:22:54
母子健康(2015年1期)2015-02-28 11:21:44
自動化博覽(2014年10期)2014-02-28 22:3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