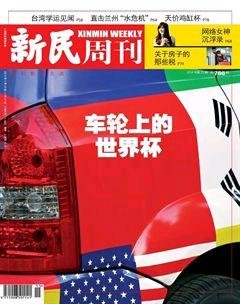“過氣”了的再“打氣”也沒用
蘇堅
旅居法國的華裔藝術家朱德群于2014年3月26日逝世,享年94歲。我希望這篇短議不至于產生不必要的誤會。我認為國人對族裔的情結、對逝者的忌議,嚴重影響了對某些時刻、人物、事件的客觀判斷和評價,而這種效應又往往泛濫為一種維護、愛戴的情緒進而掩蓋事實、真相、本質。很顯然,對朱德群及與其逝世事件一起打包張揚的“留法三劍客”之趙無極、吳冠中,無論藝術評價或是藝術市場估價,從相關歷史和現實因素考察,都有高估的嫌疑。
一般讀者、觀眾,甚至包括很多專業人士,可能很迷戀于像“法蘭西學院院士”甚至“華裔第一位”這樣的綴稱,有“勛章騎士”想象,至而容易被“藝術大師”、“國際名家”等彈性很大的級別稱謂所迷惑。但是,一個失去昔日“藝術中心”輝光的,意在推廣法國文化、藝術影響力的虛稱,不應該影響大家回到朱德群、趙無極、吳冠中們的作品本身:對現代主義的遺續和部分完善,此“經典現代主義”有其價值和貢獻,但也是“過氣”了的。
事實上,其時趙無極、吳冠中、朱德群前后遠赴留學的法國,無論曾經的“藝術中心”巴黎,或是作為見證者的諸多現代主義名家,都已處在光輝終結的臨界點,“畢加索們”仍在招搖過市,但也感知得到離“過氣”不遠,就像那里的人們二戰期間一直體會著的乏力感。而在因二戰接上了“生氣”的美國以及正“打造中心”的紐約,即使同是現代、抽象,已經不僅僅局限于“純粹形式”,而糅進觀念、行動乃至消費社會的時代因素。所以,本意要在巴黎尋找和實踐現代主義的趙無極、朱德群,即使知道身邊有畢加索、馬蒂斯等人,也不得不轉而借鑒美國“抽象表現”,受波洛克、德·庫寧等人影響,將筆觸、肌理、色澤的運動和節奏運用起來。最關鍵的是,由于現代主義“補缺”的機制自律,在現代主義的“普適原則”之外,強調中國傳統元素——筆墨、書寫、意韻等等——現代轉化的理念,多少起了些作用,讓他們算是抓上了現代主義拖延著的長尾巴。要對朱德群、趙無極、吳冠中等做學術、藝術史地位修理,還需要時間,畢竟他們剛剛過世。依有限信息和世界標準看,他們很難取得輿論渲染所意欲達到的學術地位。而藝術歷史發展的態勢是,絕不會永遠依據單獨一個“中國結”、“華人圈”來做學術預算和決算的,族裔“打氣”的招數沒有用。藝術史也早已越過聯結現實有缺的“畫意現代”階段,甚至,“畫意唯美”的追求在巴黎更早的沙龍藝術時期,已被“雅集階層”玩過氣了。
其實,就算觀察市場跡象,也多少能窺其一斑。據80年代末90年代初嘗試從臺灣開始推銷朱德群的畫商介紹,單幅折合人民幣10萬上下的畫價,都很難賣出。趙無極的推廣情形大同小異,差別僅在于,趙無極“早識時務”,不但市場策略有備、先行、應時,甚至因親自“歸國”辦繪畫講習班授徒,無意間在另一個“外交”領域、主要的華人圈推廣了自己,政治正確名分、知名度都好于朱德群。大家想想,80、90年代,西方藝術界對現代藝術的學術評價、歷史定位幾乎早已成型,專業藝術史書里已經有各種版本的專門篇章,如果他們的“中國式抒情抽象”真有那么高的學術和藝術史地位,何以會只價值10萬還在西方銷不開、跑回港臺也銷不開?當然,此后的情形,同樣的藝術家、作品,學術評價、歷史定位不會有什么根本的改變,但“市場狀況”卻天翻地覆了,就像此后本國經濟騰飛、國內“土豪涌現”——這幾乎就是有目共睹的唯一原因!
藝術領域的整個生態體系,都或多或少存在“過氣”現象,我們一直都有“打氣”追趕的緊迫和無奈心態,這之中,包括朱、趙等藝術家所謂的“傳統現代化”的努力。跟朱德群、趙無極生活在同一時代、同樣是法蘭西學院院士的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持有一種“場域理論”,他試圖解釋、揭示“藝術場”中的權力、資本、傳播等生效邏輯。毫無疑問,就像布爾迪厄對依托于“收視率”、“暢銷書”邏輯的“電視場”、“文學場”的批評和擔憂一樣,藝術生態體系中如果哪一個環節有嚴重的“打氣”跡象,各生產要素之間缺乏真實的互文關系,藝術離本真就一定愈行愈遠。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