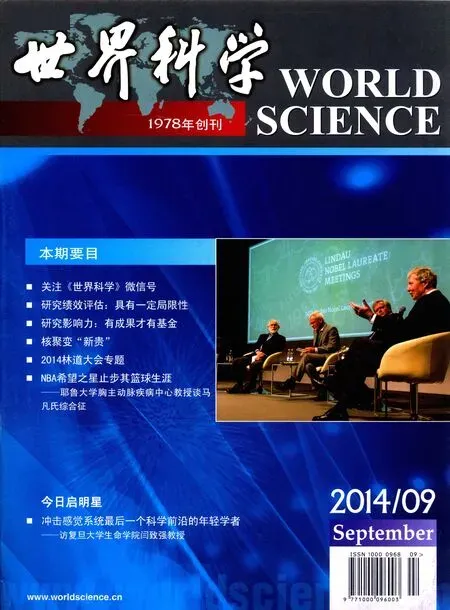沖擊感覺系統最后一個科學前沿的年輕學者
——訪復旦大學生命學院閆致強教授
沖擊感覺系統最后一個科學前沿的年輕學者
——訪復旦大學生命學院閆致強教授

復旦大學生命學院閆致強(見圖)教授因果蠅聽覺傳導機制的研究入選本年度啟明星計劃,成為今年啟明星A類50位入選者之一。通常我要到每年第四季度啟明星入選人授證會后才會開始對入選者的采訪報道,今年搶先了一點時間是因為一個機緣巧合。二周前我參加了上海科教出版社為《饒議科學Ⅱ》在上海書展的首發搞得一個饒毅、江曉原對話活動。與我鄰座是一位帥氣的年輕人,一交談得知他是饒教授的學生兼好友,進一步交流知道他是本年度的新科啟明星,今年剛32歲的閆致強已是復旦大學生命學院的教授,就這樣因為饒毅的原因,我和小閆有緣相識,當下我們就約定幾天后在復旦江灣校區見面。
大一就拿“曾憲梓獎學金”
1982年出生的閆致強是山東新泰市人,他有三個姐姐,49年出生的父親要撫養四個孩子自是擔子不輕,但閆父聰明好學,學得一手泥木建筑施工手藝,80年代末就帶著一幫工友承攬建筑施工的活。
小閆把自己日后學業上的順利歸結為從小就有想做事就能做成功的自信心,而這正是受了家庭氛圍的影響,盡管在家比較受寵,但他的衣服都是自己洗。在學習這件事上,和一般家庭父母總是叮囑孩子少看電視多看書不同,閆家大人是鼓勵他看電視的,經常提醒他學習不要太累。小閆13歲時父親因病去世。家庭的這一重大變故使得小閆較一般的同齡人懂事早熟。為讓母親少操心,原本學習很少讓父母操心的他在學習上更努力了,高中時還因為表現好當了班長。
小閆說他讀書從來不覺得很累,考試一點不緊張,這與他的學習方法是有關系的,他比較會總結、會琢磨出試題人的想法。平時他愿意花時間在知識的學習上,而不愿意多花時間在應付考試、做各種模擬題上。學習方法加上心理素質較好,2000年參加高考的小閆,以物理化學基本滿分的成績如愿進了復旦大學生命學院。
剛進校時擔任過一年的管5個班的年級長。回味復旦那些年的學習生活,已是復旦教授的閆致強最傾心的還是母校自由寬松的學習氛圍,“有時偶爾學生缺課,老師比較寬容,也容易交流。好的大學就是不一樣,有好的老師、好的同學,都很優秀。”進校不久,生性活潑的小閆就和一批志同道合者創建了復旦大學自行車協會。大一時因各方面表現優異,他拿到了曾憲梓獎學金。
大二起毛遂自薦進實驗室實習
大二那年,他開始對腦科學感興趣,就自己去找老師,聽聞楊雄里院士帶了團隊來復旦建了腦科學研究機構,小閆就慕名找了李葆明、楊雄里,壽天德等前輩,去了李老師他們的實驗室,李老師讓他先看有關的教科書。大三時小閆聽說國際神經科學界大牛蒲慕明先生來上海辦神經科學所,他立即向學校提出想利用暑假去那里學習,學校自然同意他去。這樣在一個多月時間里,小閆每天很早就騎自行車去岳陽路,晚上10點騎回學校,路上只花了28分鐘。
這段跟著蒲老師做(神經發育生物學)實驗的經歷雖然只有一個多月,但對閆致強今后的學術生涯意義重大,首先這是在中科院正規實驗室做實驗,其次是跟著當今世界最頂尖的神經生物學家蒲先生做 (某種意義上小閆也可以算蒲先生的學生了),其實還有一層意義是當時正是作為中科院自主創新試點之一新組建的中科院上海神經科學所剛開始運作不久,這個改革試點的意義在于首次引進一位外籍知名科學家出任所長,而且引入全新的科研管理方式。這段歷史應該是要寫進中國科學大事記的。能親歷這段歷史,哪怕如小閆這樣短暫的時間也是彌足珍貴的。
在小閆印象中,蒲先生很隨和,他喜歡穿牛仔褲,做事非常認真,往往是一下飛機就做事,不倒時差,有次因低血糖暈過去,至于他為別的實驗室以及自己實驗室學生論文親自改稿更是經常的事。除了蒲先生,小閆在那段時間還有幸認識了饒毅等一些在神經科學領域做出漂亮工作的大牛,“我和饒毅教授是在神經所就認識的,饒毅是中國改革開放后首個以中國大陸學者的身份在《細胞》上發文章的人,后來他在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做小鼠的行為分析課題時我幫他設計軟件和硬件。當時學生很少,和這些老師交流就很多,關系也就熟絡起來。”
有了這段經歷,到了大四下學期,小閆再去神經所參與具體課題,而他的畢業論文也是在那里做的工作。當時整個復旦生命學院本科生中也就小閆一人自己聯系在外面實習。
在國內最好的研究所完成博士學位
本科臨近畢業,小閆得到很難得的學校推免(推薦免試入讀研究生)的機會,他自然首選到中科院神經所碩博連讀,而神經所也因為對他比較了解愿意接受他,經過溝通小閆選了實習時曾帶教過他的羅敏敏老師做自己的導師。羅老師的背景是北大心理學本科,后到美國念計算機又讀了神經科學的博士,也是一位已在美國《科學》雜志等頂尖刊物上發表多篇論文的牛人。很快羅老師就給了小閆一個嗅覺方面的題目,讓他做嗅覺初級神經元到次級神經元的信息轉換機制研究。難能可貴的是在做這個課題的過程中,小閆發現了新的東西,和導師商量后他就放下原先導師定的課題轉向自己發現的新東西的研究上,而且用了一年多時間就完成了。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令小閆的研究經歷又多了一頁。也就是在神經所讀了一年多一點時間后,羅老師就帶著小閆等幾個學生離開上海神經所加盟到了彼時剛組建的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簡稱北生所)。北生所與神經所有異有同,相同的是都是由國際著名科學家親任所長,北生所的所長為中國改革開放后大陸赴海外留學者中首位入選美國科學院院士的華裔學者王曉東,不同的是神經所是隸屬于中科院系統,而北生所則是由國家多個部委以及北京市地方財政撥款等組合而成的董事會性質的研究單位。
到北生所后,小閆繼續做他的課題。這個工作2005年就做好框架了,06年完善補充,07年撰稿修稿,正式發表在神經科學領域頂尖雜志《神經元》上是2008年5月。小閆告訴我,他是文章的第一作者。最終他也以這篇文章作為博士論文順利畢業。
閆致強在北生所呆了三年多,見證了這個被很多人寄以希望的新體制科研機構初生和發展,在小閆看來,王曉東的特色是管大局,細節不管,只要看中的人,就滿足你的硬件、資金需求,具體你怎么做他完全不管,而蒲先生是完全不一樣的風格。“說起來我很幸運,在中國最有活力的兩個研究所呆過。”小閆這有感而發的一句話其實在聽者的我內心是起了波瀾的。可能讀到這篇文章的人不一定都能了解十年前中國科技體制改革中的這一段 “傷筋動骨”式的改革的前后經歷,我不是親歷者,但因為一直在做科技報道,所以也時有所聞,不管日后會對這些當年的改革做出怎樣的評價,但我對這些改革的先行者們是心懷敬意的。
在世界一流實驗室學習做事做人
博士畢業前,小閆就聯系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和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的詹裕農教授,希望到他的實驗室做博士后研究。詹裕農教授與他的妻子葉公杼為美國科學院院士、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在國際神經科學領域有很高的聲望,也培養出了眾多杰出的科學家,饒毅、駱立群等都曾受教于他。也因為饒毅、王曉東兩位的推薦,小閆順利得到了這個職位,在詹先生的實驗室呆了四年半。這樣,閆致強又得到了一個在世界頂尖實驗室學習的機會。
在小閆的描述中,詹先生是這樣的風格:“只要看中的人,加上你已有的工作能力和經歷,不管你做什么,他都信任你。這個實驗室先后出了80多個教授,這在美國也很罕見。”“到實驗室后,方向讓我自己選,而且讓我隔幾個月后再確定方向。這個過程中你即使問他,他也不提具體意見,他認為你建自己的實驗的過程也是你自己選方向、建立能力的過程。通過自己看文獻并且和同事、博士后們討論后,大約一年后我定了自己的方向,在向詹先生報告時,他還再三問我是不是真的喜歡這個題目,是不是確定了。他不是來審查這個方向好不好,而是來確認你本人對這個題目是否理解和喜歡。他覺得他認為好不好是次要的。現在回想起來,感覺這確實是培養獨立科學家的一種可取的做法。”
閆致強選定的方向是利用果蠅幼蟲做觸覺和聽覺傳導機制方面的研究,這也是詹先生實驗室的新方向。“我選這個題目是因為觸覺和聽覺分子的轉導機制一直都不清楚,成為感覺系統中分子的轉導機制的最后一個前沿。聽覺的聲音振動以及觸覺的壓力,需要轉化為電信號才能被中樞神經系統所感知。機械力感受,即把機械力轉化為電信號的過程,是聽覺和觸覺的生理基礎。”
通過小閆的描述,我明白了當時他選這個題目的深意:觸覺、聽覺和視覺、嗅覺一樣是動物最基本的感知功能,所以是相對基礎的,但又因為一般人很容易理解,而且如聽力方面的任何問題都和大眾密切相關,所以能引起更多人的關注。
具體實驗時,小閆選了果蠅的幼蟲來做,因為“這種幼蟲聽覺的結構與人比較接近,而且這種模式生物獲得容易,資源多,加上幼蟲是透明的,做起來很便利。”另外,講起為什么果蠅幼蟲的聽覺細胞和人類似時,小閆相信“生物學上決定某種功能的結構一定有進化上的原因,或是同源的,或是存在方法上的有效性。”用了差不多三年時間,閆致強在2013年就發了一篇Nature文章,他是第一作者。緊接著在PANS上又發了一篇聽覺方面的文章 (第二作者)。這些文章表明,閆致強和他實驗室的同事就把這個以果蠅幼蟲為模式生物的系統構建起來了。“這個方向現在國際上已經有人在跟進,但我們有自己的優勢。”
到詹先生實驗室的第二年,一個國際知名的支持基礎科學的機構——國際人類學前沿科學機構——給了閆致強一個項目基金,這是一個專門支持博士后的基金,得到這筆基金意味著在2010至2013年每年小閆都能獲得5萬美元的資助。小閆事后了解,申請到這個基金是很難的,這是一個所有國家的博士后都可以申請的項目,申請者都很優秀,而通過率只有5%。小閆說他還是基于以前的工作,加上詹先生的推薦,才得到這份很難得的基金。
學成歸國,復旦啟航
2014年2月,閆致強學成回國。處于對氣候、環境等因素的考慮,加上很想去大學,再加上復旦給他的條件不錯,給教授,給啟動經費,這樣閆致強就正式進入復旦大學生命學院,成為目前該院最年輕的教授。從小閆的介紹中,我再次感受到國內重點高校在引進重點人才方面的力度和實力。復旦當然是“劃算”的,引進了一個馬上就能帶起一個方向的學術牛人。做出這個決定并不難,只要看閆致強已有的工作,包括發表的文章,研究方向及前景,當然他博士后老板的知名度也是至關重要的。
盡管到復旦只有半年,但組建實驗室、招募人員這些事情都在一件件落實中。一回來后正逢啟明星申報,校方馬上讓他申報,“啟明星項目是我回國后拿到的第一個科研項目,希望啟明星帶來的好運能不斷延續下去。”小閆告訴我,到復旦后他的方向仍然是聽力和觸覺,模式生物上有可能從果蠅幼蟲擴展到小鼠。小閆說他正在申請國家青年千人項目,目標仍然是希望為聽力障礙者,特別是新生兒聽障的臨床治療提供科學依據。“我國新生兒的聽力遺傳缺陷的比例達到千分之二左右,目前每年新生兒聽力遺傳缺陷兒童約有3.5萬人,因此聽力研究在我國有重大的需求。希望通過我們的研究篩選出聽力相關的關鍵基因,揭示聽力轉導的基本機制,并且為耳聾等疾病的預防、診斷和治療提供更多的科學依據。”
對閆致強的這次訪問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饒毅教授牽的線,盡管他可能完全不知情。我也很有幸,通過這次訪問能結識一位正處在最好科研狀態中的年輕科學家,我也因他的介紹勾起了對滬京兩個中國科研體制改革樣本機構及那段歲月的回憶,真的很難得、很珍貴。
[江世亮采寫自2014,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