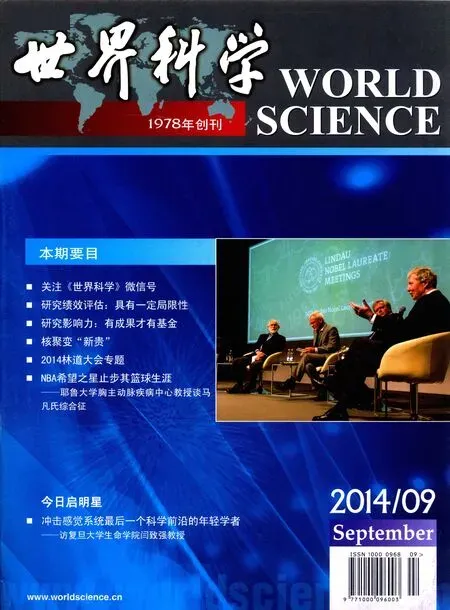鑄造中國特色的航天材料
——記上海交通大學吳國華項目組的鎂合金應用研究
本刊記者/李輝
鑄造中國特色的航天材料
——記上海交通大學吳國華項目組的鎂合金應用研究
本刊記者/李輝
項目名稱:高強耐熱鎂合金材料及其在航天航空領域應用技術開發
完成人:吳國華 丁文江等
完成單位:上海交通大學
機遇從來只給有準備的人們
2011年4月的一天,中國航天一院某國家重大專項的總指揮和總設計師來上海交通大學座談。作為座談的一部分,輕合金精密成型國家工程研究中心的吳國華教授按照校方安排做了關于鎂合金研究進展的簡短匯報。由于座談會設定的主題并非鎂合金,所以吳國華的匯報只有5分鐘。然而出乎校方意料的是,在會后,兩位客人對上海交大開發的高強耐熱鎂合金材料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他們試探著尋問是否可以用該鎂合金材料來制作某航天重大專項型號的大型復雜部件。這個部件原本設計用鋁合金材料制作。
現場,航天方沒有明確說用也沒用明確說不用,只是反復和吳國華溝通。從交大離開后,他們開始馬不停蹄地調研,在接下來大約5個月的時間里,他們陸續調研了國內有影響的一系列鎂合金科研機構及生產單位,尋求可行性上的建議。然而各方的回應都不樂觀。航天方要求的鎂合金需高強度而且耐熱,技術指標比所有國內外現行手冊上的鎂合金標準牌號高出近一倍。幾乎所有單位都認為無論從鎂合金材料性能要求角度,還是從材料成型的角度,研制航天方需求的高強耐熱大型復雜鎂合金部件均沒有可行性。
吳國華卻堅持認為可行。
航天方的躍躍欲試并非只是看到新研究成果時的一時興奮。我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師昌緒院士曾經說過,在材料領域中,還沒有任何材料象鎂那樣,潛力與現實有如此大的顛倒。
潛力,是因為鎂合金是目前實際使用中最輕的金屬結構材料,純鎂的密度只有1.74g/cm3,而鎂合金的密度通常也就1.8 g/cm3左右,約為鋁的三分之二,鋼鐵的四分之一。在常用金屬結構材料中,鎂合金的比強度排第二位,僅次于鈦合金,而比剛度則排第一位。不僅于此,鎂合金還具有較高的導電導熱性能及機加工性能,是公認的二十一世紀綠色工程材料。這些屬性,使得人們早就看到了鎂的應用前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就將其用于研制武器裝備,“二戰”及戰后,大部分發達國家也開始發展鎂的應用,尤其在航空航天領域。上世紀50、60年代,鎂的應用可以說已經風生水起。
而反差在于,在中國,直至1980年代中期,上海交通大學的年輕研究人員丁文江才在一次偶然的機緣下,從零開始研究鎂和鎂合金的屬性以及應用。“當時國內沒有人研究鎂,而人家德國人早已經用在汽車制造上了。”已由于對鎂的開拓性研究入選中國工程院院士的丁文江院士如是說。(“丁文江的鎂世界”,《浦江縱橫》2014第6期)
航天方當然知道上海交大在鎂合金方面的開拓與積累。事實上,交大鎂研究團隊曾經完成過多項重要的鎂合金科研項目。2002年起,輕合金精密成型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即開展了有關高強耐熱鎂合金材料的基礎研究,2005年到2009年,他們承擔了國家安全973項目計劃項目,之后又承擔了國家863重點計劃項目,等等。憑藉這些重要項目,交大鎂研究團隊取得了一系列鎂合金基礎研究成果,并在實驗室里做出了新型鎂合金試樣產品。
而且交大的輕合金精密成型國家工程研究中心也是國內實力最強的鎂合金研究基地之一。100余人的研發團隊,加上100多名工人和實驗人員的實驗基地,最近幾年不斷購置的裝備,這里已經建設成為了我國目前唯一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產品開發全鏈條服務的鎂合金基地。
如果有滿足要求的成熟鎂合金產品與鋁合金產品供選擇,航天方毫無疑問會選擇鎂合金產品。然而問題在于,交大開發的新型高強耐熱鎂合金材料,彼時還處于“三無”產品階段:沒有國家標準,沒有應用先例,更沒有在軍工型號產品上應用過。在對失敗容忍率極低的航天航空領域,嘗試使用一種新材料,是不管誰都必須慎重考慮的巨大冒險。
無論吳國華如何強調他們已有的研究基礎,所有的設計師都不愿意簽字。用還是不用的討論一度陷入僵局。關鍵時刻,一位曾經主持過多項重大專項因此在航天領域享有極高聲譽的權威總指揮決定簽字。他的決定,給設計師們減輕了壓力,設計師們簽字后,經過多次嚴格的質量體系認證,該新型鎂合金材料終于列入了該航天領域的供應商目錄,成為了名正言順的需求產品。
塵埃落定,總算可以上路了。

吳國華教授(左四)為航天系統領導介紹研制情況
挑戰新的70%的難題
然而,“大型復雜薄壁高強耐熱鎂合金部件研制開始后,才發現難度遠超出我們的想象。”吳國華說。“雖然我們曾經做出過該鎂合金的試樣,但了解成型過程的人都知道,做小試樣與做大型復雜部件是有天壤之別的!”
由于結構原因,航天方需求的大型復雜薄壁部件只能通過鑄造方法研制。鑄造是通過熔煉金屬,制造鑄型,并將熔融金屬澆入鑄型,凝固后獲得一定形狀、尺寸、成分、組織和性能鑄件的成形方法。然而這個過程對鎂來說卻是極難實現的。
鎂的一個特點是燃點低,活性強,非常容易燃燒。在其高溫熔融狀態下,如果不采取一定措施,鎂很容易就燒起來。在鎂合金材料制備過程中發生燃燒、爆炸并不少見。
再者,鎂極易氧化,一旦氧化就會產生夾雜物,麻煩在于,鎂很輕,其夾雜物也很輕,兩者密度差別不多,夾雜物通常懸浮于鎂熔體中,很難分離。而鋼鐵產生氧化夾雜物的話,由于其夾雜物比鋼鐵的密度低得多,夾雜物易于上浮,方便通過扒渣而去除。如果鎂合金中的夾雜物不能有效去除,將會大幅度降低材料的力學性能與耐腐蝕性能。尤其,吳國華團隊使用的是鎂與重稀土元素釓(Gd)、釔(Y)合金化而成的高強耐熱鎂合金材料,稀士元素的活性也很強,也易于氧化燒損,如此該鎂合金材料的熔煉凈化就更難了。
這還只是該新型高性能鎂合金成為航天方合格可用材料所遇到的最基本問題。將材料鑄造成大型復雜部件的工藝是更大的難關。在實驗室做兩三公斤的樣品,只需要一個小爐子,而大部件300多公斤,需要的熔煉爐僅從尺寸上就要大很多。材料制備過程控制更是復雜的多。“按材料研究工作量比例來說,材料開發只占到工作量的20-30%,把新材料推廣到實際應用階段而進行的技術開發,其工作量至少要占70%。”吳國華如是認為。
這70%以上的工作量,要求他的團隊在項目規定的時間內必須補上。
航天項目有嚴格的時間節點。在吳國華團隊面對一系列工程難題一籌莫展之際,北京的航天方更是著急,一段時間里,航天一院、航天科技集團與總裝備部等與此項目有關的領導及設計師們,一批批帶著焦慮的心情接踵而至。“我們前期是一個月匯報一次,后來改成一個星期匯報一次,再到后來,每天匯報一次。白天研制,晚上匯報進展情況,”吳國華說。但這樣并沒有讓航天方放心,“有時候還派人來蹲點,跟著你,你去那里他去那里。了解研制過程中每一個環節遇到什么困難,進展怎么樣。”
“有時航天方的領導急得直接拍桌子的,”吳國華說。航天項目不同于一般的民用項目,自上而下的層層壓力,不容許任何環節有影響全局的拖沓延誤。
“有一次會上,我說我豁出去了,少活十年,也要給你們研制出來。”吳國華仍然記得自己這句破釜沉舟的話。不過現在再說出口已經淡然很多,似乎全然忘記了自己曾經累得病倒數次,每次都躺在床上兩三天里幾乎不能動彈。作為項目負責人,沖在第一線是肯定的。吳國華被輕合金精密成型國家工程研究中心的師生們稱為拼命三郎。“我沒有星期六星期天,也沒什么節假日,而且一般晚上11、12點才離開辦公室。我長年累月都這樣的。”他如是說。
做出承諾不單單是遵守簽訂合同所必需的契約精神,更重要的,是吳國華從來都是一個對“玩真的”感興趣的人。“我很想知道,從理論到實實在在的產品,到底怎樣才能實現。”在我追問他這種氣質最早來源的時候,他回想起了他的父親。
吳國華的父親是一位中學物理老師,在小的時候,他看到父親曾經制作過滅蟲燈,一種放在稻田里,晚上飛蛾蚊蟲看到亮光便飛撲過去然后被電死的裝置。少年的吳國華也繼承了父親的基因,他曾經為修理好一臺收音機而高興許久,后來學工科,吳國華更加喜歡上做成一種產品的成就感。碩士期間他就曾經開發過一種成效顯著的鑄造涂料。“這種實在的東西給我的心理滿足感很強烈。”吳國華說。
然而,就在他迄今難度最高、挑戰最大的航天產品的研制過程中,他產品思維的啟蒙老師,他的父親病危,在醫院搶救過程中,吳國華竟沒有抽出時間趕到父親病榻前。“醫生說再晚兩個小時就不行了,”吳國華談及此事仍有愧疚。在父親經搶救度過病危的半年后,吳國華回家探望了三天。“當時就是想把這個部件研制成功,愿望非常強烈。”
吳國華的這種強烈意愿,既來自他與生俱來的做實在產品的基因,拼命的個性,也來自于他多年研究積累的自信。
從2002年起 ,他已經開始帶領學生做關于鎂合金材料的理論基礎與應用基礎研究。在2011年接手這一項目之前,他在鎂合金組織性能、熔體復合處理、液態精密成型、熱處理及腐蝕行為等方面開展了大量研究工作,研究課題分別與真實產品研制過程中的各個環節相關,并且在研究過程中已帶出了5名博士和6名碩士。這些博士論文和碩士論文課題,“沒有一個是我拍腦袋拍出來的,都與實際工程中遇到的關鍵難題有關。”吳國華說,“沒有這些鋪墊,我也不敢接這么重大的項目。”
而他自己也主持或參與了國家973計劃、863計劃、自然基金、攻關計劃、軍工配套、上海市優秀學科帶頭人計劃、航天基金等30余項鎂合金相關的科研項目。雖然都不是直接上天的高強耐熱鎂合金型號產品,但都屬于鎂合金的基礎和應用基礎研究范疇。難能可貴的是,在他所有主持的項目中,驗收成績幾乎都是優秀,“我做科研十分認真,沒有做砸過一個項目。”他說。這既是對以往成績的自豪,也是其理論基礎扎實的證明。

然而,產品研制的成功,除了興趣、堅持與基礎,還需要全新的突破。
吳國華教授(居中)在鎂合金部件研究過程中已帶出了5名博士和6名碩士,圖為吳教授與兩名新鮮博士合影

吳國華教授在試驗現場
跨越鴻溝
為了充分挖掘鎂合金材料性能的潛力,該鎂合金部件鑄造成型后,還需要進行熱處理。因零件尺寸太大,學校的熱處理設備滿足不了要求。在上海只有上海航天院第800研究所具有滿足要求的大型熱處理爐。他們得到了800所的鼎力支持。
然而原先在實驗室基于小試樣開發的熱處理工藝卻存在巨大的挑戰。在實驗室因為制備的是小試樣,而且形狀簡單,熱處理過程中產生的應力小,不易出現試樣開裂問題,所以一般采用的是固溶水淬熱處理工藝,以便獲得最佳的材料力學性能。
但由于此鑄件屬于大型復雜薄壁框架類結構,經過前期分析,熱處理過程中應力一定很大,極易出現熱處理開裂問題。若采用已有的熱處理工藝方案,便是將鎂合金部件從500℃以上的固溶處理溫度下直接淬入冷水中,但這樣的話,零件激冷作用太強,極易在應力作用下開裂。為降低開裂風險,吳國華團隊想到降低固溶處理淬火時的激冷作用,讓溫差不那么大,讓水達到極限的沸騰溫度,也就是100度,以減少水淬時開裂的風險。為了滿足這一新的工藝要求,800所關掉了所有其他車間的水蒸氣供應,將鍋爐房的水蒸氣全部都用于給吳國華團隊所需的大型熱處理水槽中的水進行加熱,一直將水槽中的淬火用水加熱到100℃沸騰狀態。然而,即便如此,鎂合金部件經水淬后依然開裂的一塌糊涂。這條路行不通……再后來,吳國華改用固溶處理空冷熱處理方案,即將鎂合金從固溶熱處理爐中取出后直接在空氣中冷卻,部件開裂情況有所好轉,但力學性能依然達不到要求。
工藝的復雜,不僅僅在于技術的難以突破,還在于團隊的協調難度。“光試制工序就幾十道,必須要一系列人馬的參與,”吳國華說。他所帶的博士碩士團隊,以及專職研究人員及工程技術人員,因此也都必須各司其職負責相應的環節。
作為工程研制必不可少的一批成員,車間工人也被吳國華特別提及。他認為充分發揮工人的積極性與創造性非常重要,一些工人師傅在工廠里有幾十年的經驗,諸如解決鑄件開裂、尺寸不合格問題,有些就是由工人提出了創造性的解決方案。
當我問及帶領這么大一個團隊是不是需要花費很多管理組織的時間時,他說,不多。我本來就在一線現場,一旦有問題,很快就解決了。
一系列的攻關之后……吳國華團隊開發出了一種熱處理方案,通過一系列熱處理優化試驗,攻克了熱處理開裂難題,并達到了航天方的性能要求。這一在本文必須一帶而過的細節,包括了無數的心血,從材料制備、液態精密成型、再到熱處理的20余項專利。
吳國華說,可以自豪地說,我們研制出了真正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材料”。因為他們研制的稀土鎂合金部件。最主要的原材料是鎂和稀土,都是中國特色材料。中國的稀土產量占國際上90%以上。而鎂,中國的儲量產量出口量都是世界第一。更為重要的是,在國際上目前所有公開的報道中,還沒有看到任何地方研制成功吳國華團隊所研制的這一大型復雜薄壁高強耐熱鎂合金航天部件。“中國特色”因此也包含了“中國獨有技術”的含義。
不過,“要早知道研制難度這么大,我恐怕就不敢承接這個項目了。”吳國華心有余悸地說。但更多的還是慶幸自己曾經那么的堅持。“有段時間也有很多人勸我放棄,我還是選擇了堅持,主要還是希望大力推動新型鎂合金材料的發展與應用,尤其是高強耐熱這種高性能鎂合金材料在航天航空領域的應用。”“不管怎么說,也要對得起自己20多年在科研戰線上的奮斗。要說我在國內外重要學術期刊上也發表了一百幾十篇文章,但幾乎都是基礎研究與應用基礎研究方面的,高端型號產品應用研究較少,我總覺得是個欠缺。”這是吳國華對自己之所以堅持的解釋。
這項國家重大專項最終圓滿成功。他為之耗費心血研制的部件,在試驗成功后已經被國家航天部門收藏。有一次應邀參觀,“看到自己研發的產品的那一刻,心情實在太激動了,有種強烈的精神滿足感。 ”他說。
在國家重大專項成功之后,今年3月的一天,負責該重大專項的總指揮一行人,從北京趕到上海虹橋機場,然后趕到交大材料學院,正式而鄭重地宣讀了國家航天部門的感謝信,并對吳國華團隊表達了最誠摯的謝意,旋即趕到虹橋機場趕回北京。一趟專門的致謝,誠意至此,榮幸之至!
記者手記:
在采訪吳國華教授之前,記者在別的選題下有機會采訪到中國鎂合金領域開拓者之一的丁文江院士。據丁院士介紹,在其初出茅廬的1980年代中期,中國在鎂合金領域的研究幾乎是空白的。而經過30年的努力,以上海交大輕合金精密成型工程中心為代表的中國鎂合金研究力量已經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在感慨開拓工作之艱辛的同時,筆者也迫切想知道,30年后的今天,我們的鎂合金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究竟如何。恰好,在上海市科委今年評選出的2013年度上海市科學技術獎獲獎名單中,以輕合金中心骨干吳國華教授為第一負責人的 “高強耐熱鎂合金材料及其在航天航空領域應用技術開發”項目,赫然出現在技術發明獎排名第一的位置。這顯然是鎂合金領域最為前沿的成果。于是經丁院士引見,就有了本次對吳國華教授的采訪。
對吳國華教授的訪談持續了5個多小時。他帶我重新回顧了從接到項目到完成項目,幾乎片刻不停的攻關歷程。一路上的風景,在吳教授邏輯清晰的說明和不善修辭的表達中,被濃縮為“玩真的”三個字。這一通常被指代扎實工作態度的常用語,在他的談話中更指代另一層含義,從基礎研究到產品應用的跨越。在技術創新的理論界,這一跨越又被稱之為“技術創新”。
而這正是這個時代經濟領域里最關鍵的命題之一。經濟轉型升級的壓力促使從政府到公眾,對基礎研究向應用產品的轉化都格外關注。但正如吳教授所言,這兩者工作量是20%和70%的對比。我們知道也許不能簡單的厚此薄彼。但是在當下,成果轉化,可能是最迫切也是最實際的需求。“論事易,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或許只有真正經歷過的人,才會有最真切的感悟。也正因此,成果轉化、技術創新中的劈荊斬刺鮮少為外人所知。而吳國華團隊的案例,則為我們提供了一例極佳的典范與詮釋。
再聯想丁文江院士那一批科學家自1980年代從幾近空白開始的篳路藍縷。這30年的歷程,不也恰是中國科技一路奮起直追的一個縮影嗎?
●相關鏈接●
上海交通大學輕合金精密成型國家工程研究中心成立于2000年3月,是由國家發改委批準組建、上海交通大學承建的國家級工程研究中心,現任中心主任為丁文江教授。經過十年多的發展,中心目前已經成為我國重要的鎂合金材料研發基地,同時也是世界范圍內最大最先進的鎂合金研究團隊之一。
中心的前身是上海交通大學材料學院有色合金教研室和鑄造研究所,教研室早在50年代就已經開始從事有色合金的相關研究,從50年代到80年代初,教研室的研究重點是鋁合金材料及其成型技術,這一時期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即為后來在國防產品上廣泛應用的“交大鋁”。到了80年初期,教研室開始從事鎂合金相關的研究,并逐步將研究重點從鋁合金轉移到鎂合金上,經過十多年的積累,于2000年初在國家發改委和上海交通大學的共同支持下,成立了輕合金精密成型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從50年代黃良余、余滋璋、翟春泉等老一輩研究人員、到丁文江教授、再在到現在30歲到40歲的青年研究學者,輕合金研究團隊已經歷了三代人的沉淀。
——摘自輕合金中心主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