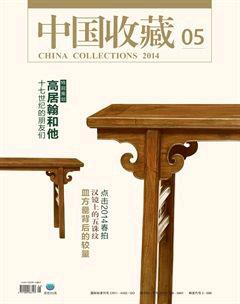歸家 復雜情緒交織
王菁菁



闊別家鄉多年的銅罍終于要回歸了,與它的“另一半”完整合一,這對于向來崇尚美滿的中國人來說,無疑是一件值得稱贊的快事。也許,不能說話的器物無法向人們傾訴它的感受,但就在其受到矚目的同時,有關海外文物回流的種種,卻又一次成為輿論的熱門話題。
兩面之緣
“這次在紐約佳士得預展中再見皿天全方罍,真讓我有種難以言喻的感慨。”這是原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流散文物處處長、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上海博物館研究員許勇翔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的第一句話。
在他的私人相冊中,一直珍藏著這樣一張照片,那是2001年,同樣的3月、同樣的紐約佳士得拍賣會,他與這件銅罍的合影。而十幾年后,當他再次與銅罍一道站在鏡頭前時,“你看,我的頭發都白了不少呢。”盡管是打趣,言語中卻掩飾不住對這份重逢之緣的激動。
其實,在當年那場拍賣會上,上海博物館也有意購藏這件珍貴的青銅重器。“當時馬(承源)館長還在,我們手上也有征集費,但沒那么多。讓我們沒有想到的是,競拍會是那樣熱烈,一下子就超過了300萬元美金,我們根本連舉手的機會都沒有啊。”許勇翔嘆道。
據悉,當年爭奪銅罍的主要是臺灣藏家與境外藏家,彼時,國內藏家走出海外參與競拍的情況還比較少。而講究競拍“策略”的上海博物館事先對于有意購藏銅罍一事也是絕對緘口。“后來有人問我,聽說你們也想買這件東西,我感到很驚訝,反問對方‘你是怎么知道的?因為當一切沒有成形的時候,我們都會將意向視為機密。”
當年拍場那看不見硝煙的戰爭似乎還歷歷在目,時間一晃而過,這一次的紐約佳士得拍賣,上海博物館沒有出手,“它能夠洽購成功,回歸湖南省博物館,我們也感到很欣慰。可以說,無論是已出土的還是傳世的,這件器物都堪稱是罍中的極品,重器中的重器。一定要好好保護,不要再讓它淪入拍賣的命運了,它是無價的。”許勇翔出示了兩張小小的合影照片,無聲地釋放出這位老文物工作者的強烈心愿。
據資深文博界人士透露,上世紀90年代初,是國內文物流失的一個“猖獗期”。而公藏機構對于海外流散文物的關注、搶救,自此之后一直未曾間斷。仍以上海博物館為例,在業內人士看來,其對海外流散文物的搶救回流,稱得上是走在業界前沿的。據了解,2001年以前,上海博物館主要是從香港購買回流文物,包括一些珍貴的青銅器。據悉,當時該博物館里的很多人,身兼上海文物鑒定委員會與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雙職,既是委員,又是專家。事先,大家都會從各自擅長的領域出發,去探尋、發現那些海外流散文物。對于每年館藏征集經費的使用,該館的規矩也非常嚴格:信息收集回來后,專家們先要進行內部商討,判斷這件藏品是不是館中真正需要的,能不能對現有藏品進行有效補充等,只有看法一致方會考慮購藏。如果確系特別珍貴的文物,要向上級政府部門進行專項申請。
“這種征集工作感覺有些像‘情報員,”許勇翔笑稱,“之前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在社會上密不漏風,假如大家都知道是博物館要買,那我們反而不一定會買了,通常都是事后才會對外公布。現在回過頭來看,當年我們征集的很多藏品,價格肯定是比較便宜的,包括瓷器、玉器、青銅器等等都有。”
“文物工作者都有一種職業病,好像搶救流失文物比什么都重要。”他說。
受制約的現實
投身購藏海外流散文物的還有上海圖書館。首當其沖的例子則莫過于翁氏藏書。這是已知海外惟一數量最多、保存最完好的私家藏書,也是當年所知清代以來流存海外的最后一批中國古籍善本收藏。
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主任黃顯功向記者介紹,當上海圖書館確定要購藏這批藏書后,立即向上級部門進行了專項申請,很快就通過了審批并且得到上海市政府的專項資助。隨后,有關場外交易的相關事宜,上海圖書館全權委托中國嘉德拍賣公司負責辦理。2000年2月,雙方達成協議,塵埃落定。上海圖書館以400余萬美元的價格購得翁氏藏書而轟動一時。
盡管時隔多年,對于當時的“驚心動魄”,曾親自參與過此事的相關人士依然記憶猶新。據說,想購買這批藏書的除了上海圖書館,還有北京的文博機構,在這場“爭奪戰”中,審批的快慢與否成為了決定性因素。以致后來有不少業內人士感嘆,上海在這方面的反應,的確顯得更加“開明一些”。
事實上,在公藏機構搶救海外流散文物的諸多行動中,除了政府的反應,外界最為關心的當屬價格。該不該買,怎么買,投入是否給力?錢,在人們眼中是一種最直接的體現。
記者了解到,為了搶救流散海外的珍貴中國文物,2002年,國家財政部專門設立了“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專項經費”,由財政部和國家文物局共同實施項目管理,具體工作由國家文物局所屬的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承辦。例如2002年以近3000萬元的價格購藏的北宋米芾的《研山銘》、2006年從日本購藏的商代子龍鼎等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之作。而這些珍貴文物征集回國后,文物部門將以是否需要、是否合適的原則分配給相應的國有博物館。相比之下,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這樣的國內大型博物館明顯更占優勢。
另一方面,作為公藏機構,根據等級、大小之分,每年國家都會撥付一定的征集費用。
“以前國家博物館尚未合并的時候,中國革命博物館每年的文物征集撥款大概在幾十萬元左右,歷史博物館要稍微高一點兒。以我的經驗來看,對比意向,在征集的時候感覺財力有限。”中國國家博物館原顧問夏燕月這樣告訴記者。
確實,錢不夠用。以2002年為時間節點分析,自2013年為止,十余年來,全球文物藝術品的市場價格漲幅有目共睹。更進一步放眼望去,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權威數據,2002年,我國的GDP突破10萬億元;到了2013年,我國全年GDP達到56.8萬億元。顯而易見,與市場和經濟的高速發展相比,無論是5000萬元的專項征集經費,還是國有博物館每年的征集費用,用“杯水車薪”來形容實不為過。
即便是在上海這種經濟發達的一線城市,國家財政對于公藏機構的投入依然比較有限,甚至有業內人士認為,基本上僅夠“館藏資源的日常維護”。而就拿此次銅罍回歸來說,據相關媒體報道,洽購成功后,湖南省博物館相關負責人在接受采訪時曾坦言,博物館“資金薄弱”。
由此可見,資金有限,依然是國有博物館所面臨的一種不爭現實。
國家的態度
針對國家財政投入文物征集的話題,記者發現,諸多討論中人們的看法不一。有人認為,當前國家提倡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海外文物回流也是當中的一部分,應該繼續加大力度;也有人表示,文化的傳承中,文物是否能得到最好條件的保護才是置之首位的,沒有必要完全因為“民族熱情”一頭熱;而北京一位長期關注博物館發展的研究人士的話則更加耐人思考——國家撥款有限,反而從側面提醒了各大公藏機構,財政撥付,花的是納稅人的錢,因此在征集工作上應當慎之又慎,尤其是像文物藝術品這樣比較特殊的門類;另一方面或許還說明,有關部門對于國有博物館以競買的方式購藏海外流散文物,態度上并不是全然贊同的。
采訪中,一些文博機構相關人士的表述也一定程度地印證了上述觀點。“如果拍賣的金額比較小,在館藏征集撥款范圍內可控,博物館也許能自主;但如果數額比較大,需要專項撥款,現在國有博物館向政府上級部門申請一般就很難通過,就算有戲,也不是短時間內能完成的。”
在文博研究學者看來,有關部門不大主張、鼓勵以拍賣的方式回購海外流失文物并非沒有考慮。一是為了抑制和打擊文物走私,二是如果一件文物的流失經過、原因不同,對于回流的處理方式也不一樣,這關系到國際慣例和相關國際公約,以及一個國家的形象和尊嚴。再者,市場價格攀升得厲害,盲目拍賣可能讓國家蒙受損失。
“假如一件流散在海外的文物要被拍賣,又有據可查它確實是通過非正常渠道流失的,國家一般不會贊成拍回來,我們也不會這樣做。”幾位受訪的文博業內人士紛紛表示。
記者注意到,在已公開的“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專項經費”購藏過程中,這些回流文物要么是直接從海外機構或私人藏家手中征集,要么是由國內拍賣行征集回來后再進行定向拍賣給公藏機構,直接從海外拍賣會上購得藏品的事例鮮少。
“所以海外文物的征集、回流實際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工作,很多因素都能決定它的成敗與否。”一位在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任職多年的人士如此說。
比買更重要的
當然,盡管以參加公開拍賣的形式來搶救海外流散文物不是主要渠道和主流方向,卻并不意味著國內的公藏機構會忽略于此。
不過,比起買家的頻頻舉牌,他們更像是以一種“觀察員”的身份參與。即便有意向,事先保密是首要原則,原因在于一旦高調公開,等于是在無形之中為該拍品又增加了附加值。事實上,他們的目標往往是那些既有意向最后又流拍了的文物藝術品,試圖尋求機會能夠通過場外協商以合適的價格購回。據透露,在公藏機構這種場外協商的方式中,比起個人購買價格上經常會優惠一些。
此次湖南藏家購買銅罍捐贈湖南省博物館的消息被媒體廣泛報道后,有人呼吁,國家應該建立相關的基金會制度,幫助國有博物館購藏海外流散文物。與此同時,迎接海外流散文物回國,應該給予一定關稅優惠的呼聲同樣很高。
“北京已經出現了基金會性質的民間組織,據我所知到目前為止效果卻并不理想。”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朱鳳瀚說,“購買是種經濟行為,成立基金會所使用的是基金的利息,如果沒有大企業、大資金的注入很難做。我想,隨著認識的逐步提高,相信將來會有更多的企業愿意投身其中,但這個過程的培育與完善需要不少時間。”
黃顯功則告訴記者,為了便于操作,當前公藏機構購藏海外回流文物,往往會委托給國內拍賣公司等第三方機構。比如2010年上海圖書館從瑞典買回來一批西洋古籍,共千余種,是由上海圖書進出口公司來辦理相關手續;而前不久北京大學圖書館從日本大倉集團回購的一批中國珍貴古籍,則是通過上海博古齋來買的。“以我們的體會,如果國家公藏機構購買海外回流文物是用于研究的,在稅收方面會有一定減免。譬如我們從瑞典買回古籍,進關時就免收了部分關稅。”
更有相當一部分公藏機構資深人士建議道,搶救海外回流文物,當前比起購買,相關研究、整理工作以及形成專門機制才是當務之急。
“非正常途徑走出國門的,應該由國家出面追索,這是行業慣例。從經驗來看,就以流失海外的玉器為例,業內通常的參照標準現在依然是多年前陳夢家先生編著的目錄,雖然權威,但這些目錄里面對于文物到底如何流出去的也缺乏相應記載。我們現在的文博界、公藏機構能不能做好這些研究、考證工作,是決定搶救方式一個重要的前提基礎。”許勇翔直言。
與此同時,對于追索,記者發現,至今官方在專門機制的啟動上表現仍不明顯,缺乏相應的機構與人才來專注于此。甚至在某些時候,地方政府對于海外回流文物的態度也是模棱兩可。“現在反而是民間機構在做這些事,文物回流一味依靠民間力量不是長久之計。作為國家文化戰略的一部分,對此確實值得深思。”有評論如此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