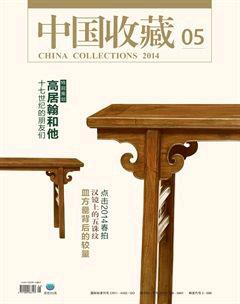三問文物回流之路
王菁菁+王曉旭

問題一:收藏家或企業出資購藏回流文物,并捐贈給國有博物館,對于這種新形式,業內人士如何看待?
許勇翔:不要總是以利益的眼光質疑海外文物回流
像上海博物館屬于古代藝術博物館,但在有些省份的博物館,相關工作人員是考古專家,卻不是文物鑒定專家,這兩者是有區別的。因此,這些地區的博物館陳列主要以考古為主,是一種反映當地歷史文化的陳列,所以往往他們的工作重心,征集不是主要的。
我個人認為,作為一座反映古代藝術的博物館,征集工作是應該加強的。從中央到地方,應當下工夫搶救,不要總是以利益的眼光去質疑海外文物回流。
黃顯功:民間力量支持公藏機構豐富了館藏
我覺得此次湖南銅罍回歸這種方式非常好,說明這些收藏者、企業家有社會責任感。實際上,國有博物館依靠民間捐贈,這在國外比較常見,不過像此次這樣的回流新形式中國目前還沒有形成慣例。
說到民間力量支持公藏機構豐富館藏,以上海圖書館為例,無論是質量還是數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堪稱是一個接受捐贈的高潮。早些天我們還去看望了上海的一位捐贈者,當年他捐獻了4萬余冊古籍,現在上海圖書館的古籍編號從001開始,而“001”的古籍就是這位人士捐贈的。相比之下,如今就批次來說,上海圖書館接受捐贈仍然比較普遍,但從藏品本身的珍貴程度而言,比起當年肯定是弱了很多。
朱鳳瀚:應當不遺余力地去搶救和保護
有人說,現在國內的文物破壞現象依然普遍,在這種情況之下,關注海外流散文物有些多余。我認為這種觀點有失偏頗。坦白說,現在我們的保護條件比起早些年要有所好轉,盡管流散海外的文物數量龐大,不可能全部收回,但是對那些特別重要、珍貴的文物,只要價格合理,我們應當不遺余力地去搶救和保護。
林明杰:我們應該有輸出文化的想法
此次皿方罍的購藏有著不同意義。首先這件青銅器在中國青銅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它傳承過程中帶有傳奇性;其次,皿方罍的器身與蓋子一物二分,從普世價值來看,人們希望它們合二為一,能夠“完璧”。博物館承擔著傳播文化、歷史、藝術的普及教育責任,通過皿方罍的回歸,想必湖南省博物館對公眾的吸引力會劇增,也會吸引更多人想了解中國青銅文化。由于目前對購藏價格不得而知,所以,如果皿方罍是以合適的價格購藏的話,那么這確實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然而,總體上我并不鼓勵國人將流失在海外的文物都買回來。過去被侵略被壓迫的歷史讓國人懷有一種民族情結,希望通過一件件文物的回流來證明國力的強盛,這可以理解,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中國的形勢在變化。隨著國力的增強,民族感情也要與時俱進,我們的意識應該轉為輸出文化的想法。新中國建立以來,中國的考古技術已經有了長足進步,也出土了許多令世界震驚的文物,可以說現在國內博物館的館藏文物已經相當豐富了。因此,不論現在流失海外的文物曾是合法出境還是非法出境,讓其他國家花著他們納稅人的錢幫我們養護文物,在各大博物館展示中國文化,也不失為一件好事。
龔繼遂:民間集資購藏是完全合理、有效的
首先,我們要認清這次皿方罍的回歸是一個個案,在這個個案里,由民間集資購藏是完全合理、有效的。這件事的特殊性在于:一是皿方罍極其特殊,它在歷史、美學方面的價值是處于國寶級的地位,與圓明園獸首、齊白石或者張大千的畫等是完全不同的;二是皿方罍的價值難以估量,雖然目前購藏價格被各方保密,但在預想的價格范圍內購藏我認為都是值得的;三是如果政府參與其中,可能會因為審批嚴格、過程復雜、耗費時間而錯失這件重器。因此,我認為藏家個人集資購藏皿方罍是一件非常精彩的事情,做得也非常得體,像這樣的稀世之珍是很難遇到的。但是我并不鼓勵藏家個人或者企業毫無選擇性地購藏流失在海外的文物。
問題二:有關政府部門是否需要給予這些幫助文物回流的收藏家或企業一些政策扶持或獎勵?
林明杰:前提是健全法律法規
如果參照西方國家慣例,是不會對這種回流文物征收進口關稅的,并且在經過嚴格考察后,也會給企業或者個人的一些稅收予以回報,但是這種辦法在中國執行起來有難度。畢竟目前國人的守法意識、文物意識還不太高,即便藝術圈內的有些人素質都有待提高,一旦有了這樣的政策,恐怕有人會鉆空子。尤其是在當前國內法律法規還不夠健全、藝術市場又十分復雜的情況下,有些人利用此騙取稅收優惠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如果希望國家給這樣的個人和企業提供一些優惠扶持,首先就要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健全審查、監管制度。
龔繼遂:需要視情況而定
國家需要根據當前的歷史發展階段、文化政策,以及財政稅收狀況來確定稅收調整。什么樣的藏家購藏捐贈行為能夠得到獎金、稅收優惠,或者什么樣的企業購藏文物、建立帶有公眾教育意義的企業博物館能夠享受到減稅優惠,都需要視情況而定。其實,如果國家為回流、收藏文物的企業制定減免相關稅收的政策,也會有稅務部門不執行的情況,因此這是需要上層各方協調的事情。
李米佳:重要的是精神上的鼓勵
這要分情況來看,對于不同經營范圍的企業應該有不同的扶持政策。但有一個前提是,很多企業和藏家個人在購藏回流文物這件事的時候,并不將得到國家回報當做出發點,他們可能只是單純出于愛國主義情懷,單純地對皿方罍器身與器蓋不能合一感到遺憾。
另外,國家有既定的稅收法律、法規、政策,不能僅因文物回流一點而改變。因此,我認為國家能給予這些企業和藏家個人最重要的一種回報是榮譽上的獎勵,這種精神上的鼓勵是目前社會中應大力提倡的。例如故宮博物院的景仁宮,其中展出的藏品都是他人捐獻的,我們就會在宮中建一個“景仁榜”,讓來往游客都能看到這些善舉。
夏燕月:可以考慮給予一定的獎勵
像湖南此次回購的銅罍,其文物的價值在國內都是很少有的。我想,碰到這樣的“鎮館之寶”,不管是哪家國有博物館都想將其收入囊中。現在,國有博物館財力有限是事實,海內外的有識之士有能力購買并且捐贈,這種行為本身來講國家可以考慮能給予他們一定的獎勵。
問題三:在文物回流方面,除了國有文博機構和民間力量購藏之外,還有哪些回流模式可以選擇?
朱鳳瀚:主要有三種方式
現在海外文物回流主要有幾種情況,一是以集資的方式參加拍賣,一般政府在這種情況下不會出面,像湖南這次的例子,過去也不多見;二是一些企業開設的博物館,財力雄厚,從海外購買后帶回國內;三是國家出面進行追索或回購。
林明杰:國家不參與出資文物回流是正確的選擇
此次皿方罍的回歸是由湖南藏家集資洽購,國家并未對此撥款,我認為這是國家成熟的一個標志。因為目前中國的藝術市場太過復雜了,一旦開了國家出資回流文物的先河,就可能會被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借機哄抬物價。所以,在我看來,除非關系到民族尊嚴、國家顏面等“要命”的條件,國家不參與出資文物回流是正確的選擇。
其實,博物館的文物承擔的是一種文明的印證、文化的傳承與教育責任。我們的博物館可以與國外博物館溝通舉辦借展,讓一些珍貴的中國文物回國展出,其教育意義也是一樣的。或者我國政府可以與其他國家交流達成一種協議,類似于文物的所有權歸我國、使用權歸他國的形式。我們可以用友好的高姿態推動文物的回流,或者說文化交流。
龔繼遂:在國內,基金會成效不佳
通過商業方式購回與政府交涉追討文物都是可行的途徑,應該齊頭并進。但是追討文物涉及到文物能否追討回來的問題,如果能回歸當然非常好,但如果不能,那么對國人的信心也會有一定程度上的打擊。在追討文物方面,很難操作的是對證據的收集、操作這件事的成本,以及對預期結果的考慮。此外,國內可以幫助回流文物的基金會很多,有些公司就曾提出過這種想法,但是成效都不太好,沒有像西方某些基金會做得那么好。
李米佳:國際話語權逐步增強
回購的方式來回流文物是與國家經濟發展、國力強盛相對應的。當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好”而西方各國的經濟又“不太好”的時候,只要他們愿意,我們有能力出錢買回來也不是件壞事。當然,如果我們的國力在軍事、經濟、文化方面強盛起來,有了國際話語權,能夠不花錢也可回流文物就更好了。另外,換個角度來說,多年來我們的文物在其他國家得以展示,讓更多外國人了解中華文明,也是一種中國文化的輸出。
夏燕月:主要依靠外交途徑
我認為海外文物回流,主要的渠道應該還是通過外交途徑,依靠法律。除此以外,現在國內文博機構間比較常見的借展也是一種方式。無論如何,我認為國家應該把搶救海外流散文物作為一項長期工作,堅持不懈地關注,這是一項不可或缺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