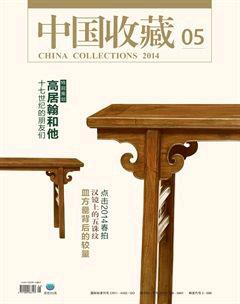盛茂燁 走一條自然主義的路
倪夢婷

到了晚明時期,代代相傳的作畫成規已經越來越失去活力,同時也成為畫家沉重的包袱,正如高居翰所說,如何脫此困境成為了晚明畫家們思考的基本問題。
較早期的畫家為了擺脫畫風的拘于一格,在畫作中嘗試形體較大、較厚重的造型,并賦以較簡單的構圖,同時也是為了避免吳派繪畫常有的瑣碎感,然而卻給人留下了強烈的矯飾主義傾向。
而這一點在時代稍晚的盛茂燁畫作中已然不復存在。這個被高居翰稱贊能夠深刻運用自然主義手法的畫家,他所描繪的景色表現出來的柔和感常把觀眾的注意力引向迷蒙的幽境之地。高居翰眼中的盛茂燁在當時的晚明繪畫中是起到承上啟下、帶動后期繪畫轉變的重要作用的。在高居翰看來,盛茂燁離給觀者營造身臨其境的大自然更近了一步。
盛茂燁是一個看不到任何有關他的出身線索、也沒有任何有關他為謀取功名而赴科舉的記錄的畫家,發現他的特殊存在可以說有一定的困難,而高居翰在眾多試圖改變格式化畫壇問題的晚明畫家中獨到地注意到了盛茂燁的不同。盛茂燁在其山水畫中利用了光和面的轉換,避免了平庸化;他沒有像之前很多畫家那樣垂直構圖,而是用形體之間的不同來相互遮掩;他沒有刻板地勾勒物體的外形,而是用模糊又清晰的輪廓線塑形,以輕重不均的筆觸處理明暗,來反映現實大自然的霧迷。在他的筆下,人們感受到的地表是變動不拘的,皴法用筆塑造的不同的傾斜變化,好似使巖石具有了方向感。這一切在當時都是驚人的,他確實運用其出色的自然主義手法描繪著大自然的景致,讓人們駐足體驗自然中的隱居生活,到山間漫游,感受那些景色聲響。
晚明的許多畫家拒絕簡單解讀的創作能力,這些可以被認為是畫家本人的微妙觀念,也可以說是為了給觀者留下解構并重構其含義的余地。盛茂燁以直接身臨其境的實感使人聯想到各種視覺現象,令人感覺煥然一新,貼近了視覺,打動了觀者。
然而高居翰眼中的盛茂燁也是優點與不足并存的,他辯證地認為我們也必須承認盛茂燁非常多產但卻也比較草率這一點,他畫了太多相同題材又很草率的作品,以至不能充分超越世俗和程式化繪畫的水平。盛茂燁也過分迷戀于分解山水的形體,極力地想要使其如沐浪漫煙云一般,為的是能夠免去悉心構圖的要求,以及擺脫那些往往顯得很膚淺詩意效果。
對盛茂燁的看法足以表達出高居翰先生在看畫方面的另開途徑。
值得一提的是,高居翰先生眼中盛茂燁的不足也真的導致了盡管他以及與其目的相似的畫家雖在當時擁有相當的市場,卻幾乎沒有被后來的藝術家所繼承。這也是因為他們有悖于董其昌及其圈子所倡導的占支配地位的學說和風格傾向。晚明的蘇州畫家雖對批評家的意見有較強的容忍性,但這樣精美的意境卻被后期像董其昌那樣有影響的又被大眾所接受的批評家歸入了另類,且在觀者中影響深遠。
因此由于多重的原因,盛茂燁等人的成就在中國和外國著作中并未得到普遍認可。而高居翰對盛茂燁等人具有前瞻性的探索研究,使他們做出的這類努力更完整地浮現于世人面前,在中國繪畫的后期歷史中構成了一段重要的插曲。
所以說高居翰是獨到的。他看到了盛茂燁獨特風格背后的話語;他探知他的創作原意和情感寄托;他一方面用視覺化的語言描述作品,一方面又引導人們在歷史的大問題中體味他的理論;他讓我們不應以賞析為滿足,必須了解畫家為其所創作所賦予的層層意念聯想及內涵;同時又教給了我們新型的看畫方式;還敦促我們不要被一己的專業領域所牢籠。
/ 高 居 翰 和 他 17 世 紀 的 朋 友 們 /
當時復興宋畫風格的風氣可能提供了盛茂燁一些新(或傳統)的方式,使他能夠從吳派創作的公式窠臼中跳脫出來。當時,新的風格方向固然開啟了種種新的創作可能,盛茂燁卻也未盡全力,半途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