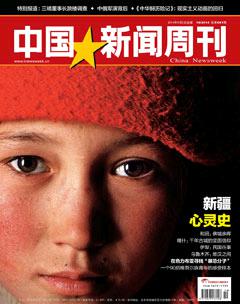金融創新不能脫離監管
王全寶

對于在銀行系統工作了30多年的銀行家張燕玲來說,近幾年層出不窮的影子銀行業務(以下簡稱“影子銀行”),的確令其“眼花繚亂”。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影子銀行開始成為國內外金融界關注的焦點。在國內,各方對影子銀行的界定眾說紛紜,對其規模也有不同版本的預測,更有觀點認為影子銀行是潛在中國經濟背后的巨大風險。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著經濟周期下行、金融脫媒、利率市場化和互聯網金融興起等一系列挑戰。如何以改革的眼光看待當下的影子銀行顯得尤為重要了。
為此,本刊專訪了中國銀行原副行長張燕玲,詳解影子銀行在中國發展的情況以及該如何監管。
張燕玲于1977年加入中國銀行,先后擔任中國銀行營業部總經理、米蘭分行總經理及法律事務部總經理、行長助理、國際商會銀行委員會副主席;2002年3月起,張燕玲擔任中國銀行副行長同時兼任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中銀飛機租賃公司董事長等職務。2010年7月23日,張燕玲主動申請辭去副行長職務。
張燕玲認為,目前影子銀行的創新,實際上是繞開監管,賺更大利潤,也承擔更大風險,“也許是無知無畏”。
要警惕美國次貸在中國重演
中國新聞周刊:在中國,影子銀行業務大概是什么時候出現的呢?
張燕玲: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的影子銀行業務開始興起。但他們刻意回避了“影子銀行”這個詞,而是用銀信合作、銀證合作、銀保合作等字樣。影子銀行的產品,基本上用于資產管理、理財產品、非標資產等。其產生的原因主要是:一是客戶需求高回報的理財產品,也需要超出授信規模的融資產品;二是金融機構追求業務發展,一筆影子銀行業務可幫助資產和負債業務同時增長;三是為了迎合和滿足監管指標如存貸比要求等。
總的來說,我國的影子銀行發展甚快,不夠規范,大部分產品是政策套利,監管缺失。如果管理不好,真可能會產生美國次貸危機那樣對經濟和社會的強大殺傷力,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這些產品都是我國金融機構的相互債務,如果一家出現問題,可能會產生多米諾效應;而美國則是將其衍生產品銷售到全球的金融機構和主權基金。
中國新聞周刊:影子銀行業務出現后,業界褒貶不一,在你看來,我們應該如何正確看待出現的影子銀行業務?
張燕玲:首先應先理清褒和貶的概念。我覺得褒貶所指內容不一致。影子銀行是經濟發展的需要,直接融資必須要有影子銀行的服務,如美國、英國當年都取消了嚴格的法規,讓投行發展,來促進直接融資、資本市場發展,盡而推動實體經濟快速發展。
褒的是真正的資產證券化及直接融資業務,股市和債市融資;貶的是目前的銀信、銀證等跨界合作,都衍生于銀行信貸。如信托業因渠道式融資,已成為金融業老二,總規模已經達到十幾萬億。券商通道式資產管理余額,約6萬億元,通道業務代理、代銷混淆,資產錯配。
中國新聞周刊:影子銀行因為自身的業務特點,可能積聚一定的系統性風險,影響金融體系的安全,你認為體現在哪些方面?
張燕玲:的確如此,不規范的影子銀行業務會影響金融系統的安全,如不透明——影子銀行的產品表現形式多為信托計劃、理財產品,背后還是銀行貸款,幫銀行資產偷偷走出表外。有些影子銀行的產品,只是金融機構過橋或通道,如買信托產品或券商資產管理產品,實際上是直投,法律權益關系不清晰,風險承擔不明確。
國外當年亦有這種情況。上世紀70年代,西方金融自由化浪潮下,影子銀行直接融資,使傳統銀行業務受到擠壓。銀行把資產證券化后再出售給投資者,催生了金融機構投資者,主要購買商業銀行的證券資產。
中國新聞周刊:影子銀行對傳統銀行體系的影響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張燕玲:正常的影子銀行機構(即從事金融業務但不叫銀行的金融機構),會幫助投資人做直接融資,如IPO、擴股、發債等。這些業務都要吸走銀行的存款,也要減少企業對銀行的貸款需求,所以對銀行的存款貸款業務,即銀行盈利的主要來源(存貸利差)產生影響,那么就會促進銀行發展中間業務,服務型業務,如貿易融資、SME貸款、結算、清算、擔保、各類卡、咨詢等業務,促使金融產品創新,而不是現在的主要為了規避監管要求的創新。
目前的創新實際上是繞開監管,賺更大利潤,也承擔更大風險,也許是無知無畏。很多創新產品,存在固有風險,與此同時還埋下很多隱患。
中國新聞周刊:影子銀行的出現,對我國宏觀經濟發展產生了哪些影響?
張燕玲:黨的十八大提出,要發展現代金融體系,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即直接融資的股市和債市。股市是高效的、市場化的資源配置機制,如美國納斯達克,培育出了微軟、蘋果、Facebook。他們能讓年輕人白手起家,讓創意和資本無縫對接,減少資源錯配成本,改善創業環境。
我國股市市值很大,但很壓抑,先天畸形,后天不足,好在“滬港通”將要出臺,但規模有限,兩地共800多支股票(香港開放266支、內地開放560余支),額度限制在5500億元。
我國債市世界第三,規模達27萬億(多數是銀行理財),最熱的是國債,海外有熊貓債、點心債,現在又有地方債、中小企業集合債、中小企業私募債。但發展很慢,新產品少,規模小。
中國新聞周刊:在資本市場發展方面,影子銀行體系面臨著機遇與挑戰并存的局面,能否具體介紹?
張燕玲:我覺得機遇很多,為什么這樣說呢?我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原因:一是十八大及三中全會給出了明確的發展方向;二是國際上已經有成功和失敗的經驗和教訓可參考;三是實體經濟和企業翹首以待。當前排隊上市近千家,準備發債的更多。
以國家準備發的信用債為例,近期就聽到鐵路債券、住房金融專項債券等等。如國家準備投資80%支持鐵路投產新線6600公里,發鐵路債券1500億;而住房金融專項債券,重點用于棚戶區改造及城市基礎設施等相關工程建設。2013年到2017年,國家要推進1000萬套棚戶區改造,至少需要資金2.5萬億。
有人總結,我國資本市場十多年來原地踏步,金融創新脫離了本意。所以,美國投行因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是值得借鑒的。
中國新聞周刊:在你看來,影子銀行的出現對于金融監管的挑戰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
張燕玲:在銀行系統工作這么多年,我的感受是金融業是高風險行業、高杠桿、高信息不對稱、高關聯、低容忍度。金融機構自己是控制不了自己追求利潤的欲望的。這對監管提出了挑戰。
因此,我的建議是:首先,要保證相關政策的一致性,不能厚此薄彼。直接融資管理嚴格,間接融資管理更嚴,但搞一個“創新”就可以比較容易的繞過監管。這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的。
第二,產品政策要一致。信托業經過了整頓再整頓,業務規模很小,但得益于信托法(人稱信托業的特權法),使它可以提供通道業務,從而導致銀信合作爆炸式發展。這個渠道將信貸、股權和債券外的融資方式合法化,讓所有金融業眼紅。
隨后證監會也擴大了券商資產管理的投資領域和品種,銀證合作來的更猛烈了。券商既無資金,也不需要對項目負責,只收取通道費,比信托更優惠。不到三年,券商通道式資產管理余額達到近6萬億元。
第三,監管政策要清晰,監管要到位。現在我國金融是分業監管,這種模式的基本特點是,主營業務不交叉,資金不互通。而影子銀行的兩種渠道業務,則把金融業資金渠道徹底打開。過去資產管理業務特指證券公司代客理財業務和公募、私募基金管理業務,現在金融各業都要做大做強資產管理業務。銀行、證券、信托、保險、基金競相擴大此業務,好像誰投資范圍廣,誰創新力度就大。
從資產運用方看,分業監管模式已被顛覆。各種金融機構都在構建全產業鏈,金融各業的投資業務已沒什么區別。分業監管僅體現在按資金來源方式或負債方式劃分。一些金融機構資產管理規模已達幾百億,但投資和研究機構卻沒建立起來,只為滿足理財需求,還成了表內轉表外的工具。
更可怕的是金融機構相互投資、相互提供通道、相互搭橋。如果有人有項目,有人出資金,有人出通道,一筆業務就完成了,各賺一部分利差和費用,說白點,其本質上是制度套利。
中國新聞周刊:當前,金融理論界、實務界和監管機構等各方面對影子銀行的范圍及其主要交易形式的認識并不一致,對此你如何看待?
張燕玲:的確如此,中國影子銀行至今沒有一個明確的概念界定,不僅概念并不清楚,而且對其范圍和交易形式的認識并不一致。
現在有個比較一致的概念,是指“游離于一行三會監管之外的變相金融機構,其金融交易難以納入金融統計和被監管。這些機構包括擔保公司、地下錢莊、民間借貸、委托貸款、小貸公司、典當行寄賣、期貨配資、融資租賃等八種形式。產品包括融資票據、理財產品、代委托資產證券化、網上洗錢、私募股權、Q幣等”。這些影子銀行機構及業務都沒在監管之下,這是否有點可笑?
中國新聞周刊:那為什么沒人管?
張燕玲:不能因為老鼠改個名,貓就不管了!現在管理模式不改會更亂,所有的金融機構及其產品都不能沒人管,也不能亂管,流程中不能漏管,制度不能缺失。
十八大及三中全會確立了明確的目標。但要認真細化,做好頂層設計,用智慧來加強監管,用責任來推動創新,只有以高度的使命感才能實現很好的監管。
我建議考慮以下三方面問題:國外影子銀行衍生產品出事后,我們才大發展,而且走的是不太正規的政策套利之路。當然,它們沒有必然的聯系,但要引起足夠注意。
國外影子銀行及其衍生產品是在金融自由化政策下發展的,開始時是支持直接融資,促進了經濟發展。我國目前的政策是分業監管,但金融機構利用產品創新已打破了分業監管制度,應加強跨業監管機制建設。
我國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大力發展直接投資、融資,非銀行金融機構作用大有可為,監管機構有責任使其回到良性發展的軌道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