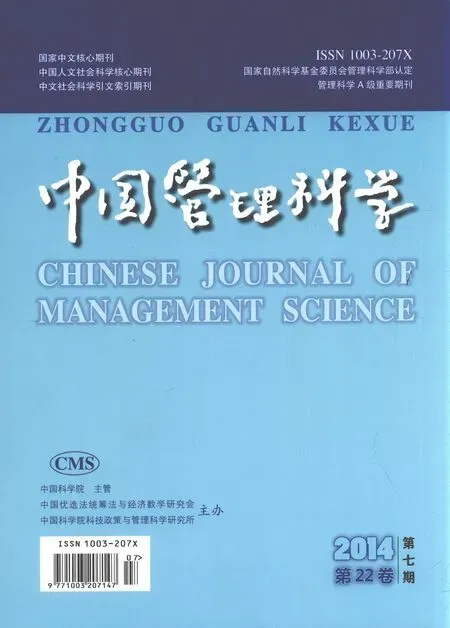CAFTA產業集聚與平衡發展效應實證研究
龍云安
(西華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四川成都610000)
CAFTA產業集聚與平衡發展效應實證研究
龍云安
(西華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四川成都610000)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是在中國主導下成立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CAFTA),積極推進自由貿易區內部成員國的產業集聚與產業發展,并通過經濟一體化效應,促進東盟各成員國產業升級和平衡發展,本次研究在空間經濟學理論基礎上,應用產業集聚常用的H指數和模型分析,實證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產業集聚效應和產業集聚到平衡發展路徑。研究結果表明:有效協調的一體化機制成為自由貿易區的平衡機制;協調加速產業轉移;產業集聚的最終結果將走向產業平衡。
CAFTA;產業轉移;產業集聚效應;平衡效應
1 引言
中國主導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的正式成立,意味著中國在推進世界經濟一體化和全球貿易自由化進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自從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2002年簽訂以來,日益復雜的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使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一體化挑戰。為此,為了進一步推進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國選擇了“10+6框架”[1]。de Grauwe[2]認為深化發展自由貿易區,不得不充分重視一體化過程中帶來的運作成本及相應的風險,并且,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深化和發展,必然導致區域內產業集聚和不平衡發展,使各國的現實需求不對等,而且還會增加協調成本,風險治理難度加大。由此可見,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深化,中國政府必然會承擔越來越多的社會責任,必須采取對策,盡力消減一體化風險,促進成員國之間產業集聚與平衡發展,實現良性循環[3]。因此,本研究問題的提出,源于中國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自由貿易區內產業集聚的最終結果實現成員國產業平衡發展,為此,重點研究“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深化發展過程中的產業集聚及平衡效應,進一步推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順利發展,為成員國在一體化過程中作出正確的戰略選擇提供幫助,實現成員國產業集聚最終走向平衡。
在經濟一體化的產生、發展、演進過程中,逐步形成了許多有關產業集聚理論。這些研究成果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空間經濟學和新貿易理論學派,他們研究經濟一體化過程中成員國產業集聚的原因、產業轉移規律、產業集聚和投資轉移路徑、福利變化及其對策等,而且,在研究自由貿易區產業集聚與平衡效應時,還應用了自由資本垂直關聯模型(FCVL)和自由資本模型(FC),以及產業集聚的區位選擇、空間集聚力與分散力、產業集聚對成員國經濟的溢出效應。所以,對于自由貿易區產業集聚和平衡發展的研究采用空間經濟學理論是最為合理的。自由貿易區的成立與發展,會給成員國帶來生產轉移效應,并出現本地新興市場化、而且還會使自由貿易區內部產業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4-5],Krugman[6]研究發現,隨著自由貿易區的深化,后期加入的成員國會在原始成員國先發基礎上,形成“輪軸”效應。在此基礎上,空間經濟學研究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他們的共同觀點是,隨著經濟一體化的深化發展,區域內部的貿易、投資和金融必將日趨自由化,進而改變區內成員國的投資方向和投資流量,在自由貿易區內形成一股產業集聚的浪潮;由于各成員國市場規模存在明顯差異,出現了顯著不同的產業集聚效應。在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由于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自由貿易區的成員國獲利較多的激勵效應,必然會產生以“輪軸”中心的“多米諾骨牌”效應。Granovetter[7]提出政策協同方案,由市場規模大的國家負責提供公共產品;Buckley[8]提出個成員國從單邊主義出發對貿易自由化政策作出戰略性控制;Meyer和Gelbuda[9]認為自由貿易區內具有產業集聚和產業轉移效應。
綜上所述,有關CAFTA的研究,多數學者一般把研究重點集中在貿易效應及投資轉移效應上,基本不涉及系統研究產業集聚和平衡發展趨勢等相關問題,因此無法準確解釋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的新問題[10]。本研究應用H指數和模型分析,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產業集聚和發展規律作為重點,實證分析產業發展不平衡的原因和最終實現平衡發展的對策,成功應用模型分析,解釋自由貿易區形成的三種模式,準確測算“CAFTA”在不同條件下的經濟效應和產業集聚效度,得出相應的結論,為中國與CAFTA的深化發展提出政策建議。
2 指數設置與模型分析
2.1 選擇產業集聚的測定指標及其應用
為了準確測定產業集聚效應,通常需要選擇適當指標體系,一般研究中,同常選擇兩個常用指標體系,即行業集中度指標和赫芬達爾指數(H指數)。由于不同成員國的行業標準不同,精確的行業數據難以獲取,因此,本研究不考慮采用行業集中度指標而采用“H指數”,用“H指數”從宏觀的角度來研究“CAFTA”各成員國的產業集聚情況,并在此基礎上展開實證分析。本文中H指數的得出,主要依據WDI數據庫,以美元為計價貨幣,依據中國—東盟各國當年產值計算。見圖1。

圖1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主要產業的H指數變化情況
應用H指數對農業、工業、制造業、服務業進行測定(見圖1),從各產業數據和變化趨勢觀察發現,在國民經濟各類產業中,農業的H指數初始水平最高,而且較為穩定,表明CAFTA各國農業生產的集中度高,在自由貿易區內,基本形成了較為穩定的國際分工體系,同時,由于自由貿易區內各成員國資源富裕度存在差異,加之各國歷史背景與自然條件不同,農業生產長期保持相對穩定的狀態,專業化水平亦高。可是,在成員國各類產業中,服務業的H指數變化最大,1985年的H指數是0.356482,而2009年上升到0.532648,可以看出,與其他產業的比較,服務業的產業集聚速度最快、力度最大,在各產業中,服務業的產業集聚效應也最明顯。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起步階段,各成員國服務業水平大體相同,但是,在自由貿易區內的部分成員國,人力資本優勢顯著,市場規模相對較大,它們的服務業集聚最快、集聚效應最強。這一現象在中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成員國的產業集中度表現為最高。與農業服務業不同的工業及制造業,初始水平H指數較高,增加速度也快,與其他工業相比,制造業的H指數上升最為明顯。在1998年前后,東南亞金融危機,使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各成員國的產業體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并形成了新的國際分工體系,在自貿區內部出現了產業集聚的浪潮,產業集聚的同時,也出現了產業發展的不平衡,各成員國的農業、工業、制造業、服務業的H指數變化均為明顯,表明必須加強國際協調、促進平衡發展。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應用H指數研究一體化過程中產業變動規律,能夠較為準確反應自貿區各成員國產業集聚和自由貿易區深化發展的各種現象。
2.2 假設模型與分析
2.2.1 模型假設
假設,世界是由兩類國家組成,即自由貿易區內部成員國家和非成員國。所有國家都具有農產品(A)和工業品(M)兩個生產部門;它們都使用兩種生產要素,即資本(K)和勞動力(L)。農產品市場完全競爭,而工業產品市場為壟斷競爭。資本要素允許在各成員國之間按照市場規律自由流動,而勞動力要素不能再成員國之間自由流動,只能停留在國內市場。初始狀態下,各個成員國的貿易開放度(Φ)基本相同,與WTO的非歧視原則保持一致;當自由貿易區建立之后,各成員國均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于是貿易開放度大大提高。假設,一國的對外貿易是由冰山成本τ(τ<1)決定的,即貨物在運送途中有1-τ部分貨物被“融化”掉,當貨物到達目的國家后,就只剩貨物τ部分;在自由貿易區內部成員國之間的冰山成本系數τFTA,一般比它們與非成員國家之間冰山成本系數τWold要大,即τFTA>τWold。采用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數:

上式中,C為消費,P為價格,I為總收入,μ為常數,0<μ<1
假定,工業品消費函數是:

消費者對第i種工業品消費總量為c(i),世界工業品總類數為nw,成員國任意兩種不同工業品之間的相互替代彈性用σ表示,假設消費者對工業品的需求變化,是隨替代彈性的變化而變化,則一階條件得到:

如果生產環節屬于線性函數,總成本:

式中,固定成本F,工人工資wM,單位產品勞動支出αM。以利潤最大化為前提,計算出工業品的價格指數:

公式看出,消費者消費的所有工業品價格(P)相同,表明產品價格與產品種類無關。由于各成員國市場缺乏自由度,屬于完全壟斷競爭,工業品從一國出口到其他成員國,用τ輸表示輸出價格與輸入價格之比,為了實現價格均衡,必須考慮冰山成本,才能使不同國家的工業品價格趨于一致[11]。在自由貿易區內,把成員國廠商j之間的工業品定價、以及它們與非成員國產品之間的定價表示如下:

由于資本自由流動,各地利潤相同,本國及其他成員國所分別占世界總的工業份額表示如下:

2.2.2 產業集聚與不平衡發展
根據自由貿易區成立之前后區域內產業份額的比重差異,還能夠計算出從區外產業轉移來的凈值:

從自由貿易區產業轉移最后結果來看,自由貿易區產業轉移效應IC總是為正,區域一體化的深化,必然出現區外產業向區內成員國轉移;而且貿易開放越大,產業凈移入量就越大,反之亦然;自由貿易區成立前后,成員國消費支出占世界比重恰恰相反。但是,如果只分析自由貿易區內部一個成員國,那么本成員國所得到的生產轉移效應IC1為:

意味著,自由貿易區內,生產轉移效應由一成員國的消費支出與區內其他成員國的消費支出之間的差額決定。如果消費差額為正,那么該成員國會有凈投資移入,有正向生產轉移效應;如果兩者之間的消費差額一樣,該成員國任然有凈投資轉入,依然存在正向生產效應,只是相對于第一種情況較小。如果一國消費支出小于它國的消費支出,即消費差額為負,該成員國則缺乏生產轉移效應。一般來講,自貿區成立不可能使一國生產轉移小于零,在自由貿易區內的小國,偶有發生這種現象,也意味著各國在自由貿易區內部產業發展不平衡。
在上述研究中,如果充分考慮自由貿易區成立過程中的諸多因素,各成員國加入自由貿易區的時間存在先后差異,各成員國的生產轉移過程具有很大的差異性。由于自由貿易區從產生、發展到壯大,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先后加入的時間間隔,使后面加入的國家融入自貿區的時間變長,在初期階段,它們一般很難獲得自由貿易區給它們帶來的益處。分析自由貿易區的形成模式,可以概括為三種形態:第一種,由兩個水平相似的國家,作為原始成員國,組成自由貿易區的初始形態,之后,其他國家通過相應的程序相繼加入;第二種,一個強國和一個較為弱小的國家,作為原始成員國組成自由貿易區初始形態,之后其他國家也按照一定的程序相繼加入;第三種.即強國模式,指兩個實力相當的強國,作為原始成員國組成自由貿易區,而后其他地理上相鄰的國家按照預定程序相繼加入,現實中這種模式只是理想假設,尚無現實案例,因此將前兩種模式的數據模擬結果呈現出圖2、圖3所示。

圖2 兩個水平相似的國家組成自由貿易區模式下產業集聚進程
從通過比較上述三種自由貿易區形成模式,可以看出,第一種模式較為普遍,屬于各國最容易支持的一種小國模式,小國模式下的產業變動規律見圖2,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的組建正是按照第一種模式發展起來的。開始階段,弱小國家可以按照統一大市場模式結為同盟,以抵消強國加入所帶來的生產轉移負效應,當然,在開始階段,強國會將生產轉移到弱小國家,因為,它們自身市場能力,還不足以應對由弱國組成的統一市場,圖中從t1到t2時間段內,自由貿易區的產業集聚主要集中在弱國。當后入者強國已經完全融入到自由貿易區,即到達圖2中所標注的時間t2后,由于統一市場的作用,生產轉移又逐漸回到強國,這種現象的直接結果是將“核心—邊緣”模式的不平衡效應減弱了。實際上,如果自由貿易區的原始成員國均為弱小國家,國內生產缺乏規模效應,在自貿區的初始階段,它們首先可以快速擴大生產規模,培育強大的市場作用力,增強應對后加入的強國沖擊,促進自由貿易區內部成員國產業最終趨于平衡。

圖3 強弱兩國組成自由貿易區模式下產業集聚進程
然而,從圖3的趨勢來看,按照第二種模式組建的自由貿易區,即由一個弱國和一個強國作為原始成員國組成,之后,其它國家按照既定程序相繼加入。在開始階段,該模式由強國主導,弱小國家在一體化內只能聽從強國的安排,由于市場規模太小,基礎差,強國的低端產業向弱國轉移,弱國的高端產業向強國轉移,這種畸形的轉移結果必然會成為更加不平衡的“核心—邊緣”格局,最后必將出現“單極”世界。
3 實證分析與結論
通過對“CAFTA”的研究,實證分析自由貿易區產業集聚和平衡發展過程。對“CAFTA”給自貿區各成員國帶來投資流量進行測度,研究對外直接投資轉入、產業集聚路徑,進而研究產業集聚的國際分工效應、成員國企業的規模擴張效應。通常“CAFTA”促進了各成員國專業分工不平衡,導致不平等和畸形的“核心—邊緣”經濟格局,這樣只有通過付出更高的協調成本,推動自由貿易區向前發展;但是,如果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帶來了成員國市場產品多樣化,那么自由貿易區內各成員國之間的產業發展必將趨于平衡,此時“CAFTA”所需支付的協調成本較少,即可以達到自貿區成立的原始目標,按照圖2模式發展與深化。
3.1 產業集聚效應
產業集聚效應可以通過測度直接投資來驗證[12]。為了提高投資效應的測量精度,可以把時間因素和控制變量引入估計模型[13]。從自由貿易區產業集聚的過程來看,把生產、消費指標作為控制變量集,模型表達為:

式中,FDIit為投資流量,表示i國在t時期的投資流入量,它反映該成員國的在自由貿易區的投資效應大小。di、dt表示虛擬變量,自由貿易區內的成員國假設為di=1,或者取0值;在自由貿易區成立之前,dt取0值,成立之后取1。控制變量集分別為人均投資I、人均消費C、勞動效率L、人均政府購買G、人口數量P。殘差項為εit。除虛擬變量以外,計算時對指標的數值取對數,以確保模型測度準確,消除指標單位的差異性干擾。
樣本區間選擇1981~2011年年度數據,將控制變量滯后一期,即1980—2010年,以體現內生化。從WDI數據庫中選取FDI數據,以1980為基期,把FDI流量視作存量。在PTW7.0數據庫中選取控制變量數據,再按照不變價格進行調整,定為數據源。在原始組中,為了保證觀察組和對比組成員的對稱性,選擇東盟原始成員國為樣本;在東盟吸引外資的總量中,東盟原始成員國所占比重最大,超過85%,可以代表東盟產業轉移水平現狀。因為截面單位數量和時間序列的多少基本一致,設面板模型為混合模型。估計方法采用面板數據的最大似然值(LS估計)估計法,以無相關回歸(SUR)作為估計權重,這樣可以消除截面異方差與同期相關性問題。假設,在各時期初始狀態下,各要素彼此互不影響,達到倍差法對貿易協定效應中的基本要求,這樣,一國加入自由貿易區之前后,除控制變量外,其他各因素作用的時間基本一致。表1為計算結果與穩健性檢驗。
表1各參數估計結果顯示,除勞動效率指標之外,其他解釋變量的方向和顯著性完全相同,即使變量組合與對比組完全不同,在兩種對比組的結果中,模型R值都接近0.70。由于面板數據D-W值本身容易被低估,所以D-W值有些偏低,均小于1.5,但是卻與模型的擬合度較好。另外,在6個對比組中,D-W值在消除變量后依然略有增加,說明各變量之間確實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相關,由于本研究意在預測產業集聚后的發展趨勢,D-W值低,但相互之間并不具有明顯的干擾性。分析結果證明,計量結果是穩健的,并且很好的詮釋了“CAFTA”的產業集聚效應。
在6個估計值中,最不穩定的是變量勞動效率系數L(-1)。在分析兩國對比組的勞動效率時,其勞動效率系數為正值,可在分析四國對比組勞動效率時,則勞動效率系數為負值。表明勞動效率的高低,對投資流入量的影響程度,在估計上出現波動現象,許多情況下由于人力資源優勢及較高的勞動效率,該成員國會輸入大量的FDI;然而也因為這些國家勞動效率高,要素成本相對來講也高,必然會阻礙投資的大量轉入,但由于這種阻礙作用是不確定的,勞動效率對投資轉入的影響也只是暫時的。
從各估計系數的方向來看,除去不穩定的勞動效率指標外,解釋變量投資集聚效應(di×dt)、政府購買、人口數量及資本總量四個指標均為正值,均具備實際意義;雖然人均消費指標系數為負值,但也可以作為解釋變量。模型估計結果表明,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那些資本總量大、政府購買較多、人口數量多、人均消費最小的國家,獲得最多的的產業轉移,由于自由貿易區一體化機制作用,可以帶動大量的產業轉入,也就是積極的產業轉移效應。不過,在考察10+3模式后,結果顯示人均消費和產業轉入表現為負相關,可是,依據空間經濟學的基本思想,在產業集聚力的作用下,人均消費與產業轉入之間應該表現為正相關。其原因是,凈投資國人均消費較高,投資流出量超過流入量;在世貿組織的推動下,隨著全球貿易自由化的深化,必將提高自由貿易區的開放度,降低貿易成本。規模生產和規模效應為成員國帶來的產業集聚效應,將遠遠超過消費帶來的產業集聚效應。

表1 “CAFTA”產業集聚效應和穩定性檢驗
通過分析“10+6”模式后,自由貿易區投的資集聚效應數值最高,投資集聚效應好,顯著性高,表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有著很好的正向產業集聚效應,不過這種效應比生產規模及消費規模的產業轉入效應要小得多。東亞經濟體之間,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實現了產業重組和深化,沒有明顯的生產轉移效應;大量投資轉入東亞經濟體內各國,加之相互之間的貿易自由化程度高,加入自由貿易區后,他們并沒有明顯拉動外部投資;貿易自由化成為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要形式;由于中國、越南、泰國更具有相互需求空間,其投資轉移效應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各成員國的比較來中,效度最明顯[14]。

表2 CAFTA產業集聚路徑與檢驗值
3.2 產業平衡發展路徑測度
通過實證測度自由貿易區的貿易結構變化,來描述CAFTA產業集聚和平衡發展的具體路徑。選取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文萊、越南、柬埔寨和泰國作為對比組,測量自由貿易區各成員國貿易結構的變化效應,并在SUR設定條件下作LS估計和穩健性分析。有用普適度高的Grubel-Lloyd指數解釋貿易結構的變化,各國相似度指標作為各類解釋變量,包括政府采購相似度、投資相似度、消費相似度、人口結構相似度、勞動效率相似度等。
樣本區間選擇2001至2010年的年度數據為控制變量,應用HS92貿易數據庫中的相關數據,測算被解釋變量,計算出對比組國家的相似度指標,其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表2所示,盡管對比組在同一商品種類中存在差異,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深化,使區域內成員國貿易結構變化方向和變化幅度卻大體一致;同時,在估計結果中,由于R2值和D-W統計量滿意度高,說明估計結果是正確和可靠的。估計結果的差異的主要原因是:越南和泰國在東盟自由貿易區內關系密切。由于原始組四國與對比組成員數量對同,表2中第四欄數據反映了自由貿易區的產業集聚效應。樣本中19個商品種類中,有14類β3系數為負值,說明“CAFTA”使產業間貿易在成員國之間加強了,自由貿易區使成員國內部專業化分工不斷深化,進一步加強了各成員國的產業集聚效應,使各成員國經濟發展的出現不平衡,通過深化發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必須降低不對稱沖擊的風險。而且,成員國在不同商品種類中增加了產業內貿易,促進了區內產業的規模效應,強化了區內產業的集聚效應,同時,自由貿易區的深化發展還將促進區內產業轉型升級,逐漸消除區內產業發展的不平衡。
4 結語
通過對“CAFTA”的產業集聚效應與平衡效應的實證研究,結果顯示產業集聚最終將走向產業平衡。自由貿易區必然會使區外產業轉移到區內國家,出現內部產業集聚效應,在自由貿易區一體化機制作用下,區域內部產業發展的不平衡逐漸消除,使產業集聚的不平衡開始趨向平衡;必須通過協調加速產業轉移。可以通過協調和完善區域機制,可以快速推進產業集聚和平衡發展;有效協調的一體化機制成為自由貿易區的平衡機制。“CAFTA”加速了成員國產業間貿易,并具有明顯的產業集聚效應。只要深化“CAFTA”一體化機制,增進溝通和協調,最大限度地降低不對稱性沖擊的風險,最終促進各成員國經濟發展走向平衡。
通過對“CAFTA”產業轉移效應的研究,CAFTA不僅可以帶來成員國的產業轉入,同時也會造成成員國之間的不平衡發展,為此,本研究提出相應的解決措施:(1)完善一體化機制,充分發揮一體化的平衡機制,不平衡發展向平衡發展轉移,在自貿區內建立一體化的結算機制、共同風險基金、公共產品緩存機制等各種應對措施,消減不對稱沖擊。(2)強化微觀經濟管理,通過品牌戰略,快速實現產品的規模效應。在自由貿易區強化傳統產業內貿易,加強產品多樣化,強化品牌意識,擴大市場占有率,實現規模效應。(3)政府積極引導,加速產業間貿易,加快產業轉入,積極促進內部化分工體系的建立,為自由貿易區成員國在一體化過程中獲得更多的便利,促進自由貿易區快速邁進新的全面一體化階段。
[1]李靖,蔣士成,費方域.戰略聯盟與一體化:多渠道研發外包背景下的組織比較[J].研究與發展管理,2012,24(1):26-34.
[2]de Grauwe P.The economics of monetary integratio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3]李亞敏.發展中國家間區域經濟一體化問題研究[D].鄭州:鄭州大學,2012.
[4]Baldwin R E.Trade polic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M]//Jones R W,Kenen P B.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Amsterdam:North-Holland,1984.
[5]Baldwin R E.The cause of regionalism[J].The World Economy,1997,20(7):865-888.
[6]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3):483-99.
[7]Granovetter 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6,(3):481-510.
[8]Buckley P J,Cross A R,Tan H,et al.Historic and emergent trends in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J].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2008,48(6):715-748.
[9]Meyer K E,Gelbuda M.Process perspective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in CEEI[J].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2006,46(2):143-164.
[10]戴卓.國際貿易網絡結構的決定因素及特征研究—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為例[J].國際貿易問題,2012,(12):71-83.
[11]曹慶林.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的貿易效應分析[D].濟南:山東大學,2009.
[12]Baldwin R E.Investment creation and investment diversion:simulation analysis of the single market progress[R].NBER,Working Paper,1995.
[13]Tekin-Koru A.North-south integration and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0,18(4):696-713.
[14]龍云安,基于中國-東盟自由區產業集聚與平衡效應研究[J].世界經濟研究,2013,(01):80-86.
Empirical Study of CAFTA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Balance Effect
LONG Yun-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of Xihua University,Chengdu 610000,China)
Based on the Chinese leading establishment of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CAFTA),CAFTA actively promotes free trade zon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balance development,and promotes Asian member countries industrials upgrading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economy.On the base of spatial economics theory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commonly used H index and model analysis are applied in this paper.With Empirical study is carried out in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to balanced development path.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a)the effective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of integration is just the balance mechanism of the free trade area;(b)coordination speeds up industrial transfer;(c)the final results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will be towards the industry equilibrium.
CAFTA;industrial transfer;industrial agglomeration;equilibrium effect
F752.733
A
1003-207(2014)07-0100-07
2012-07-03;
2013-04-05
四川省軟科學資助項目(2014ZR0094);四川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重點課題(14sa0055);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07BJY081)
龍云安(1965-),男(漢族),四川成都人,西華大學經濟貿易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世界經濟、金融投資、國際貿易、跨國公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