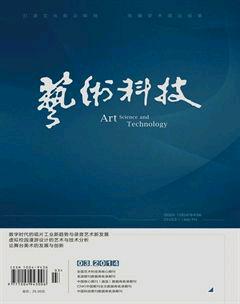試論中國傳統畫論中的休閑智慧及其當代意義
摘要:在經濟發展水平、物質水平極大提高的當今時代,休閑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休閑既是指休暇時間的人類活動,也作為一種人生態度浸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休閑方式并非都是健康的,不良的休閑方式無論對休閑者自身,還是對社會與生態都造成了不利影響。繪畫是我國重要的傳統休閑方式。在繪畫理論中蘊含著的豐富的休閑智慧,對推動休閑文化良性發展意義重大。
關鍵詞:休閑;畫論;心性修養;自主創造;生態休閑不僅是個人“自由和幸福的關鍵所在”,[1]更體現了社會的整體精神面貌和價值取向,是一個對社會發展都有著重要價值的課題。就整體來看,健康積極的休閑方式正在養成,但一些不良的休閑方式也是方興未艾。當前經濟高速發展,但同時現代人也背負起更大的精神壓力。功利主義價值觀的強化使人際關系趨向復雜化。精神家園的失落,信仰的缺乏和整體社會信任度的下降,進一步導致各種社會問題的出現和精神疾患發病率的增長。這些問題反映在休閑生活中主要表現為外傾刺激性休閑,被動、符號化休閑,環境破壞性休閑等。不良的休閑方式對身心健康、社會和諧、生態平衡都造成了不利影響。而傳統休閑方式中蘊含的人生智慧有助于推動不良休閑方式向心性修養型、自主創造型和生態友好型休閑轉化。
1外傾刺激性休閑轉向心性修養型休閑
從精神旨歸來看,休閑大致可分為心性修養型休閑和外傾刺激性休閑。心性修養型休閑是對自我身心發展有益的休閑方式,其意旨既是回歸本源之域對心性的涵養,又是對道德人格的提升。外傾刺激性休閑則是離開了生命本源而濟濟于外在感官或者情緒刺激的不健康的休閑方式。在社會競爭不斷加劇,精神壓力持續增大的狀況下,很多現代人陷入了外傾刺激性休閑的迷霧之中。比如受大眾文化娛樂化的影響,一些青年人陷入了無厘頭娛樂和虛幻的游戲世界。一些媒體不負責任的信息傳播,如新聞傳播的三俗趣味、影視傳媒的癲瘋搞笑、廣告的失真宣傳,更是加劇了社會的浮躁風氣和社會信任度的下降,人們在難得清醒的同時又難得糊涂,失落了生命本真在本源之域的涵養。在某種斷裂、紛擾的人生境況中維系生命境域的整全就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而對休閑進行合理引導的價值正在于此:通過健康的休閑尋回安頓心靈的精神家園,涵養身心,滌蕩性靈,恢復靈魂本然的高尚與清明。
如西方理論家們所言:“休閑提供的不是一條現代意義上的逃避之路,而是一條回歸之路,即返回到一種崇高而和諧的狀態上來。在這種狀態中,每個人都會真正地成為自我并因此而變得‘更好和更幸福。”[1]在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回歸本源之域、提高個人修養的智慧。老子說:“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莊子的“心齋”“坐忘”功夫都是對本源境域的回歸。儒家更強調在實踐中實現生命境域的圓滿,提出“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進修層次。這正是中華民族精神根基之所在。作為蘊含著豐富中華文明智慧的傳統畫論,也體現著對本源之“道”的感悟和回歸。
休閑的文化生命在于寓于其中的精神追求,而中國傳統繪畫就體現出修養心性,回歸精神家園的旨歸。“靜”在心性修養中有著本源性意義,在靜的狀態中人更容易接近性天本具的真實與通明。道家很強調靜的修養:“致虛極,守靜篤”,儒家也講:“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歐陽修推崇“蕭條淡泊”“閑和嚴靜”的畫作意趣,“淡”正于“靜”中得其真味。莊子說:“淡然無極而眾美從之”,這正是由靜而淡的一種放心于大化自然的人生境界。秦祖永也在《桐陰畫訣》中強調作畫時要有“靜氣”,他說:“畫中靜氣最難,骨法顯靈則不靜,筆意躁動則不靜,全要脫盡縱橫習氣,無半點喧熱態,自有一種融和閑適之趣浮動丘壑間,正非可以躁心從事也。”“靜氣”的養成是通過繪畫所需要的“滌除玄鑒”“澄懷觀道”的精神修行,掃除了心靈蕪雜的遮蔽而顯發出心光的澄明。
所謂“學畫可以知師弟子行己之道。”(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繪畫在中國傳統理念中作為一種人生修養的方式,對道德人格的培養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宣和畫譜》中有言:“志于道,據與德,依與仁,游于藝。藝也者,雖志道之士所不能忘,然特游之而已。”正因為“藝”以“道”為本源依托,根植于“德”“仁”的精神修為,故而古人于此“特游之”。清代王昱在《東莊論畫》中說:“學畫者先貴立品。立品之人,筆墨外自有一種正大光明之概;否則,畫雖可觀,卻有一種不正之氣隱躍毫端。文如其人,畫亦有然。”可見中國古代繪畫本身就含有對品格的要求,所以才有“人品不高,用墨無法”的說法。在宋元時興盛的“梅蘭竹菊”四君子圖,之所以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睞就是因為這些意象可比于君子之德。文同是畫竹的大師,曾賦詩道:“虛心異重草,勁節逾繁木”。又王冕題《墨梅圖》詩曰:“吾家洗硯池頭樹,個個花開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這都是以繪畫彰顯人文精神的佳作,所以說“畫直一藝耳,乃同于身心性命之學。”(《芥舟學畫編》)。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講作畫時必須“注精以一”“神與俱成”“嚴重以肅”“恪勤以周”,不可以輕慢之心待之,并奉之為“進修之道”以教子。郭熙對繪畫的莊敬由此可見,他就是把繪畫作為人格修養的途徑來對待的。
席勒在《審美教育書簡》中說:“只有當人是完全意義的人的時候,他才游戲;只有當人游戲時,他才完全是人。”繪畫作為休閑游戲,正是游于人之為人,性天澄明的自由之境。米芾稱繪畫為“墨戲”,作畫惟求其平淡天真處,在這種游戲之中獲得一種“游”的情態自由。郭熙說繪畫不止于“可行、可望”,更喜其“可游、可居”。“可行、可望”是一種外在的觀照,而“可游、可居”則引人融身于山水之中隨其俯仰,暢然自得,產生“物我合一”的精神愉悅。只有在這種“游”的精神境域中才能“下筆如有神”,揮灑出生命歸復于本源境域的無盡妙用。宗炳說:“閑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不違天勵之叢,獨應無人之野。峰岫峣嶷,云林森渺,圣賢映于絕代,萬趣融其神思,余復何為哉?”[2]這正是在山水畫中進入了道境的神游,可見中國古人在休閑之中對自由曠達、神與物游的生命狀態的向往和自覺追求。
2由被動符號化休閑到自主創造型休閑
在大眾娛樂、崇尚消費的文化氛圍之中,現代媒體的華麗宣傳之下,美好的生命體驗似乎真的可以復制粘貼。一些現代人正是在對這虛浮的快樂體驗的盲目追逐中失去了厚重、豐富、真實的生活大地,迷失了自己。一方面,休閑在現代人快節奏生活方式中成為某種可供選擇的經濟快餐,計之分秒,去之匆匆;另一方面,休閑成了某項任務,某種概念化的符號,時間促迫之下,旅游也變成了平面化的浮光掠影,以至衍化為一種對財富、身份的表證。休閑就這樣變得淺浮和功利,失去了它真實的內涵,從而產生了休閑的被動性和符號化的問題。
美國休閑研究教授杰弗瑞·戈比是這樣定義休閑的:“從文化環境和物質環境的外在壓力中解脫出來的一種相對自由的生活,它使個體能夠以自己所喜愛的、本能地感到有價值的方式,在內心之愛的驅動下行動,并為信仰提供一個基礎。”[3]休閑被認為是“以自己所喜愛的、本能地感到有價值的方式”進行的。其目的是讓每個人都能在其休閑生活之中各得其所,成其所是,讓生命意義隨之充盈,而不是讓它成為新瓶裝舊酒的乏味生活的復制品,因此休閑應該具有很強的自主性和創造性。休閑中出現的這一被動性、符號化的問題,正如莊子所言是“是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自適其適”是一種我之為我的真實存在,在繪畫中就是本真的表達,表現為對前人的法則的揚棄和富有意義的新畫風的開創。繪畫需要師法古人,但不能因循古人。石濤在《苦瓜和尚畫語錄》中就反對以古人之法為牢籠,而不知自創新法的繪畫風氣。“古人未立法之前,不知古人法何法?古人既立法之后,便不容今人出古法。”他推崇“師古人之心”而非“師古人之跡”,強調“我之為我,自有我在。”這就是繪畫思想中對“我法”的要求,不拘于古人之法而放乎天真,妙寫大化。潘天壽講:“學畫時,需懂了古人理法,亦須懂了自然理法;作畫時,須舍了古人理法,亦須舍得了自然理法,既能出人頭地而為畫中龍矣。”將所學化為己用,不為古人拘,亦不為自然所拘,得其自適,這樣的創作才會是真正優秀的創作。郭熙說:“予以為大人達士,不拘于一家者也。”(《林泉高致》)“不拘于一家”才不會以人之“肺腑”,安入“我之肚腸”,實現“我法”創作的自由。所以說,休閑不該是被動的隨波逐流,要合于本心地去積極的創造,綻放出生命本真的魅力。
自主意味著創造,但創造不意味著無所遵從。休閑如果失去了本性之心的原初體悟,失落了對道德的本然信仰,其魅力就會黯然失色。本源意義上所謂“創新”是主體于無待境域之中進行的合境域的創作,是對“存在”之真的敞顯,具有呈現本真、優游自得的特點。布顏圖在《畫學心法問答》中說:“無法者非真無法也,通變乎理之謂也。”這個“理”就是依天道之理,順乎自然而彰顯境域之真。石濤有言:“山川脫胎于余也,余脫胎于山川也”便是深會山川之“理”而歸乎大造的自在之所。倘若失卻理境,落入物我隔絕的對待之中,其作品就不免會因為生命整全體驗的缺失而出現拼湊造作之感。“法于何立?立于一畫。一畫者,眾有之本,萬象之根”。中國畫的精神乃是“無法生有法”“一法貫眾法”,這個“一”便是自主創新的精神內核之所在。而境域作為超越性的境界體驗,就是順乎“理”而達到“一”的生命存在的圓融。以一畫融匯萬有,“深入其里,曲盡其態”才能把握中國山水畫之真精神。休閑也需要回歸本源才能綻放出燦然的生命光彩。中國傳統繪畫這種回歸生命本源境域“自適其適”的自主創作觀對當代自主創造性休閑是足資借鑒的。
3由環境破壞性休閑轉向生態友好型休閑
不管是不良休閑方式對資源的嚴重浪費,還是過度消費產生的環境污染,對生態的破壞都是不容忽視的。從消費品來看,不管是珍稀動物制品的銷售、還是一次性筷子的普遍使用,都對生態帶來了很大的破壞。消費背后化學肥料的大量使用、汽車尾氣的過量排放、大型化工企業對化學污染物質的排放,對生態的破壞更是不可估量的。人與大自然本是同構而生成的關系,自然就是人類生息繁衍、代代相承的家園。而工業導致環境惡化的進程不斷加速,動植物大量滅絕,生態平衡受到嚴重威脅,我們正在失掉自己的家園。美國大片《阿凡達》風靡一時,而其劇情幾乎就是對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對自己家園暴行的再現。由法國楊恩亞瑟導演執導的紀錄片《家園》更是對這種地球家園破壞境況的痛心不已的集中展示和對人們生態良知的深切呼喚。在這個家園中每個人都不是一座孤島,對家園的不負責也就是對人類自己的不負責。面對這樣的境況,現代人保護環境的責任意識急需提高。
不同于西方傳統二元對待性思維中強調人對自然的征服,中國古人推崇天人合一的生命狀態,自然就是人類生命的一部分,與文明相生相成,是一體不可分的。《中庸》有言:“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物之性就是人之性,自然世界就是人生的世界,它們在根本上是相通的。鄭板橋喜歡畫竹,不是專為畫竹而畫竹,他作詩道:“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由于人與天地自然的這種同體的關系,人類對待自然就應該是“民胞物與”“與物為春”“與物有宜”,自然對人來說則是“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鳥山花好弟兄。”
中國傳統繪畫與西方油畫取材上的不同之處在于國畫以山水自然為主,而西方傳統油畫以人物事件為主。國畫的這一取材特點并不是由于民族傳統對人的不夠重視,而恰恰反映了中國人休閑生活的智慧。人是自然中的人,只有依于自然這個本源才能實現真正的人的整全和完滿。所以孔子會對曾晳“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生活理想欣然頷首。
“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園素養,所常處也;泉石嘯傲,所常樂也;漁樵隱逸,所常適也;猿鶴飛鳴,所常親也……然而林泉之志,煙霞之侶,夢寐在焉,耳目斷絕。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窮泉壑;猿聲鳥啼,依約在耳;山光水色,混漾奪目。此豈不快人意,實獲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貴夫山水之本意也。”[4]可見中國傳統山水畫精神所反映的人與山水自然的這種斷不開的血緣關系。南朝王微在《敘畫》中描繪他在自然之中的感受:“望秋云,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雖有金石之樂,珪璋之琛,豈能仿佛之哉。”人在自然之中俯仰自得,暢釋胸襟,怡然忘我,這是中國傳統休閑智慧的超然展現。
所謂“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內外向映,才能與天地造化相參贊,動而為筆墨,生而為山水,無不靈秀,無不合于自然之道。人類文明不斷接受著自然世界的涵養和孕育,乃生成于自然。以文明之心體觀自然,自然亦成一人文。由此筆下之山水,安可以內外辨之,必然是通透渾然,一體萬化。董逌在《廣川畫跋》中對于李成的創作經歷有這樣的記載:“咸熙蓋稷下諸生,其于山林泉石,巖棲而谷隱,層巒疊翠,嵌欹崒嵂,蓋生而好也。積好在心,久則化之,凝念不釋,神與物忘,則磊落奇蟠于胸中,不得遁而藏也。他日忽見群山橫于前者,累累相負而出矣。嵐光霽煙,相與而上下,漫然放乎外而不可收也。”[4]也只有在這種人與自然一體涵容的狀態下,精神才能完成向本源的回歸,作畫才能得山水真精神。德國學者皮珀就認為:“一個人只有內外一致,并且與世界保持和諧,才有可能休閑”。[5]這與我國人與自然一體涵容的思想也是相通的。這種“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天人合一”的存在觀對生態友好型休閑有著本源意義上的奠基作用,同時也是建立環境友好型社會所需要的思想基礎和根本保證。參考文獻:
[1] 托馬斯·古德爾,杰弗瑞·戈比.人類思想史中的休閑[M].成素梅,馬惠娣,季斌,馮世梅,譯.昆明:云南出版社,2000:11,119.
[2] 朱良志.中國美學名著導讀[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65.
[3] 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閑[M].康箏,譯.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14.
[4]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M].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285286,291.
[5] 皮柏(德).節慶·休閑與文化[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117.
[6] 葛路.中國繪畫美學范疇體系[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7] 李益.近年來學術界關于休閑問題的研究綜述[J].廣西社會科學,2003(1).
[8] 朱良志.論儒學對中國畫學涵養心性理論的影響[J].世界弘明哲學(季刊),2001(9).作者簡介:王仲凱(1988—),男,山東臨朐人,山東大學藝術學院碩士,藝術學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