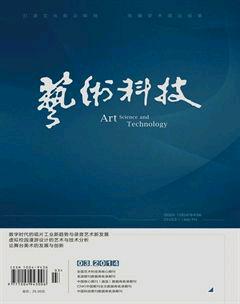簡述朱珪對乾嘉政治學術的影響
邱爽 李小娟
摘要:朱珪,字石君,與其兄朱筠并稱“大興二朱”,著有《知足齋詩文集》。作為嘉慶帝師,官至安徽巡撫、戶部尚書、太子太傅,體仁閣大學士的要職,是集銓選、財政、文化等大權于一身的朝廷重臣,對嘉慶朝政施加了重要影響。又歷任福建、浙江學政,會試考官,選拔和影響了一大批有學之士,推動乾嘉經學走向極盛。
關鍵詞:朱珪;石君;嘉慶帝師;己未會試;乾嘉經學朱珪(1731~1807),字石君,號南厓,晚號盤陀老人,順天大興(今北京)人。與其兄朱筠(1729~1781)并稱“大興二朱”。乾隆十三年(1748)戊辰進士,官至太子太傅,體仁閣大學士,謚文正。著有《知足齋進呈文稿》二卷,《知足齋文集》六卷,《知足齋詩集》二十四卷。
1朱珪的政績及影響
朱珪受乾嘉兩朝眷寵,歷任福建糧驛道,福建按察使,湖北按察使,山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侍講學士,文淵閣直閣事,福建學政,內閣學士,禮部侍郎,浙江學政,兵部侍郎,安徽巡撫,廣東巡撫,兩廣總督,左都御使,兵部尚書,吏部尚書,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體仁閣大學士等要職,于政治上頗有建樹。[1]擔任地方官員的時候,朱珪非常注重發展民生,并且能夠較好的應對天災。在山西時,“免土默特蒙古私墾罪,以所墾牧地三千餘頃,許附近兵民認耕納租,歲六千余兩,増官兵公費;又太仆寺牧地苦寒,改征折色,以便民除弊;皆下部議行。”兩次擔任安徽巡撫時,都遇上皖北水災,朱珪“馳驛往賑,攜仆數人,與村民同舟渡,賑宿州、泗州、碭山、靈壁、五河、盱眙余災,輕者貸以糧種。筑決堤,展春賑,并躬蒞其事,民無流亡。”[1]擔任中央官員時,堅持減輕百姓負擔,令曹司凡事近加賦者皆議駁。無論是長蘆鹽政請加增鹽價,或是廣東請濱海沙地升賦,或是倉場請預納錢糧四五十倍,都予以駁回,駁曰:“國家正供有常經,名實關體要。于名不正,實必傷,斷不可行。”[1]
更重要的是,朱珪是乾隆帝任命的皇十五子顒琰(嘉慶)的師傅,朱珪以其學問、品德影響了嘉慶,與他建立起很深厚的感情。“持節南疆。仁宗在書房,常頒手札,積一百三十九函,歸朝繳進。上亦書數年懷公詩數十首為二冊,題曰《蒹葭遠目》,曰《山海遙思》,以示公。明良之契,稽古之榮,古今所罕覯。”[2]嘉慶四年正月初三,就在乾隆帝逝去的那一天,嘉慶帝即召朱珪來京供職。朱珪聞命即起,“見星奔路”,在途中就上疏說:“天子之孝,不專以毀形滅性為奇,而以繼志述事為大。親政伊始,遠聽近瞻,默運乾綱。……刻刻以上天之心為心,祖考之志為志。思修身嚴誠欺之介,于觀人辨義利之防。君心正而四維張,朝廷清而九牧肅,身先節儉崇獎清廉,萬物昭蘇,天佑民順,自然盜賊不足平,而財用不足阜也。”[1]朱硅的這段陳說,實際上成為嘉慶初政時的施政綱領。在嘉慶朝,朱珪是集銓選、財政、文化等大權于一身的朝廷重臣,以其政治理論、治國原則對嘉慶朝政施加了重要影響。[3]
2朱珪的詩文及其對乾嘉學術的影響
第一,朱珪本人的詩文,“奧博沉雄。國家有大典禮,撰進雅頌、詩冊、文跋,乾隆皇帝必親覽之,以為能見其大頌不忘規。”[4]徐世昌《晚清簃詩匯》:“其詩探源漢魏,參以昌黎,博大雄深,直吐胸臆。承平臺閣中,固當首屈一指也。”[2]符葆森《國朝正雅集·寄心庵詩話》:“賦《前后易水行》兩篇,縱橫破碎,雖翻案文章,實千秋至論。其‘當筵不惜美人手,此舉竟負將軍頭奇險語,令人心駭。”[5]朱珪的學術,“學兼漢宋,曾與孫淵如寫信論學曰:‘四科之四,則文學亦不悖乎上三者,又謂考據非詞章之上乘,又謂正心誠意或短在不能致知格物,又謂不講格致則雖有仁心廉操何從著手以察吏治獄安民,又謂偽尚書無損益于人心風俗,又謂今之耆學以為高出前賢。”[6]阮元在《神道碑》里說道:“于經術無所不通,漢儒之傳注、氣節,宋儒之性道、實踐,蓋兼而有之。”[4]王昶也說:“參政兄弟少入翰林,即以高文典冊,照耀蓬萊華蓋之間,為藝林所仰垂三十年。然其尚名教,敦清節,世或未盡知也。”[7]
第二,朱珪先后擔任山西布政使,福建、浙江學政,又多次擔任鄉試、會試主考,是一時學林、文壇領袖,對乾嘉之際的學術、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符葆森《國朝正雅集·寄心庵詩話》:“文正愛才如命,孤寒八百,無不揚眉,今之李平泉也。其學問精醇,人品和粹,尤為近今罕匹。”[5]王昶《湖海詩傳》:“愛才下士,士以此望而趨之。昔韓忠獻為中正所歸,而于元祐諸賢,未嘗偏徇;葉文忠為清流眉目,而于東林君子,亦無私好。參政蓋深的此意者也。”[7]在擔任山西布政使,朱珪“匠成人材甚眾。在閩則鰲峰書院,在晉則晉陽書院。而晉之俊髦從游者,如裴學士謙,朝夕聞業,裴亦念德不忘,后官京師,一二日輒來屬晨夕也。”[8]在擔任福建學政時,朱珪立志改變福建“士子好高者矜言博洽,陋者至本經不能誦,經義相沿草率”[8]的情況。通過鰲峰書院,召集了一批有志于經史考據之學的學人。謝章鋌說:“國初吾閩不矜淹洽經書,時文以外多置不理。自朱石君珪督學,以通博倡庠序……列郡靡然從風,而俗習一變。”[9]在任糧道觀察使時,朱珪曾以糧儲觀察身份管理鰲峰書院(據院志,糧道負責書院院產及經費,并參與課士),在諸生中“拔時髦二十八人,令聯一社,曰讀書社,授以治經作文之法”。[9]朱珪倡聯讀書社,在閩省傳統的飲酒作詩之會中,融入經史考據之學,使文會成為學人研習交流學術的處所。在讀書社內,社人各就其性情所近,“或好宋儒言性命之學,或好求經世之務,或耽考訂訓詁及金石文字。”讀書社中人才輩出,孟超然是乾隆年間閩省最有名的程朱學者。鄭光策則以開創嘉道以后閩省經世致用之學著名。龔海峰、林樾亭既以詩文聞于時,也長于經史考據之學。讀書社“打破了康熙以來復興理學的樊籬,不同學術見解,自由爭辯”。士人學風轉變可見一斑。[10]
第三,在擔任科舉主考時,朱珪通過左右科舉考試評判標準的途徑,使考據風氣的影響達到了最大化。朱珪“取士務以經策較四書文,誠心銳力,以求經學,經生名士,一覽無遺,海內士心,向往悅服。佳士之文,未薦被落者,讀而泣之。才士黃景仁、張騰蛟死,稱悼之。通人寒士,必揚其名于朝。《秦誓》‘一介臣之心,公斷斷有之。公領試事,不受外僚贈遺,不留貧生銀。”[4]
朱珪左右科舉考試評判標準的做法主要表現在:(1)對二場經義、三場策論的重視。例如,阮元在《揅經室三集》卷五中言:“乾隆丙午秋,朱石君師典試江南,合經策以精博求士”。《揅經室二集》卷三中言:“乾隆丙午科,大興朱文正公典試江南……公搜落卷,得其經文策……及拆卷,得君(孫星衍)名”。阮元在《隱屏山人陳編修傳》中又言:“會試闈中,(陳壽祺)其卷為人所遏,元言于朱文正公曰:‘師欲得如博學鴻詞科之名士乎?閩某卷經策是也。遏者猶摘其四書文中語,元曰:‘此語出《白虎通》。于是文正公由后場力拔出之”。(2)衡文標準改變,尤重對經書及漢唐人注疏的征引。例如,昭梿《嘯亭續錄》語:“今日自朱石君講論古學,時文中試者,多以填砌經典為貴,文體為之一變。”姚鼐《惜抱先生尺牘》卷八亦言:“自朱石君先生閱文不辨佳惡,只要人用書,成一種鈔撮之陋習,而夾帶之病彌深。”“嘉慶己未,典會試,阮文達為之副。所得士如姚文田,王引之,湯金釗,程同文,張惠言,胡秉虔,陳壽祺,許宗彥,張澍,劉臺斗,郝懿行諸人,皆一時經學之選,人才之勝空前絕后。”[6]朱珪選拔和影響了一大批有學之士,推動乾嘉經學走向極盛。朱珪在學術史上的意義由此可見。附:朱珪歷任鄉試、會試主考情況簡表[11]
朱珪對于研究乾嘉時期政治環境和文化背景有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朱珪也是乾嘉學術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人物,通過研究朱珪,能夠更好地把握乾嘉時期的政治社會面貌,也能夠更加系統地理清乾嘉經學的興盛與發展。參考文獻:
[1] 趙爾巽.清史稿[M].中華書局,1977:11085.
[2] 徐世昌.晚清簃詩匯[M].中華書局,1990.
[3] 張力,史謙.一代帝師朱珪述論[A].故宮博物院八十華誕暨國際清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2006.
[4] 阮元.揅經室集[M].中華書局,1993:419.
[5] 錢仲聯.清詩紀事[M].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5324.
[6] 徐世昌.清儒學案[M].中華書局,2008.
[7] 王昶.湖海詩傳[M].商務印書館,1958.
[8] 朱錫經.朱珪年譜[M].嘉慶十年本.
[9] 謝章鋌.圍爐瑣憶之一[A].賭棋山莊全集·筆記[C].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
[10] 陳忠純.鰲峰書院與近代前夜的閩省學風——嘉道間福建鰲峰書院學風轉變及其影響初探[J].湖南大學學報,2006(01).
[11] 朱寶炯,謝沛霖.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