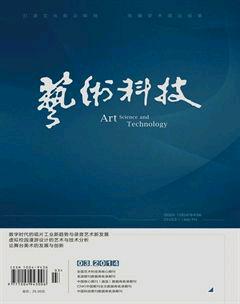由詩歌空間的涂畫想象漫談藝術
喬治
好像是零九年入秋的一天晚上,大學畢業的我賦閑在家,考研又不順利,為點兒什么瑣事跟媽大吵一架,翻來覆去睡不著覺。昏暗的燈光下忽然閃過一個念頭,就像層層烏云在不經意中被陽光撒上了一道金邊,細微但極閃爍……抓住它!就這樣,我踏上了詩歌之旅。
幾年里,伴著波動,她始終為我釋放平復,讓我有話能說出口,在非現實的夢境中營造文字的幸福;她讓我在迷霧中得以呼吸,甚至為薄弱的伸張沾沾自喜;她是一幅沖向自由的圖畫,在吶喊中希望,在馳騁中接近飛翔,她告訴人們,逆境中用奮力燃燒可以成就自己;她留戀時間,愛憎分明,敏感周圍人世的變化,習慣在熟悉的環境用陌生的節奏訴說生活常識,用放任記憶來經營渴望;她簡短而漫長,平實又華美,往往是某個擦肩的觸碰讓心頭一震,繼而在平淡的律動中捕獲鮮奇。就像漫步河灘,白茫茫中你被一粒寶石的迥異所吸引,哪怕微弱,但足夠定位。發現的這刻,你開始變得手舞足蹈,慌躁中用非常的手段急速記錄,似乎某些東西很早以前就堵在那,時機一到,像開閘的洪水噴涌而出,顧不得排隊。你明察于此時的混亂,并用足夠的耐心在語感和反復中尋找邏輯。你自說自話,計較某個字的多少甚至標點的得失……最終,虛無里,跨越的秩序被建立,一切互成唯一。
中國自古就有詩畫一體的傳統。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但是要明確一點,這里的“詩”“畫”并非簡單意義上的內容疊加,而是基于意旨和趣味相同基礎上的精神共通。“詩”寫字外之“畫”,“畫”畫“畫”外之“詩”。二者要共同達到的是一種不可言說,但確實存在又百轉千回的意境。或者我們理解為尼采學說中“酒神精神”的“日神表達”。他們都是給觀眾或讀者傳遞一種直通心靈的想象,不同的是前者依靠文字引述進而在讀者的腦海中形成印象,因人的性情,見識和理解的不同而異;后者呈現則更加直觀,至少在最初的視覺感官上是明確統一的,甚至是可觸摸的。相對前者,后者更具物理屬性。當然,無論哪種形式,他們都是藝術家最本真的生活感悟,因而都能引起受眾在精神上的共鳴,在不同方面和程度上拓展人們對生存的認知。但需注意一點,此處的精神共鳴與單一的視覺夸張不同,她并不是單一感官上的詫異,而是發自內心對未知領域的無言。以維米爾的油畫作品《倒牛奶的女仆》為例,畫幅很小,用筆平實,但絲毫不影響她流傳千古的光輝。一代代觀眾在這幅畫中領略到生活的愜意與安適,好像畫中的場景就發生在身旁,畫中的陽光和自家窗外的陽光是同一處。反觀當代的一些作品,作者只是破碎復制西方的某些觀點,采用照片寫實的方法羅列人像,哪怕借用反叛為名,哪怕使用的材界尺度非凡,除了引起人們一時的指點外,絲毫沒有其他可循,更掩飾不了內容的空洞蒼白和創造的無力。這樣的畫作即使再有累牘的文字解讀進行搭配,也到底逃不了被丟棄的最終。各行業中,唯藝術最冷酷又最可愛,最不能騙人但又往往是最騙人的行當……
真誠是對每個有志藝術創作的人最大的考量,判斷其中與否的標準可以在當事者愛心中的藝術還是愛藝術中的自己這個命題中尋找答案,也就是通常說的“毋自欺”。首先,一個很現實同時也經常被人誤解的問題擺在面前——藝術家既不是一種身份,也不是一個職業。它只是對創作者蓋棺定論后所取得成就的一種囊括稱謂。其次,藝術的從事很可能是沒有回報的。因為她只涉及自我探求,換句話說,她只是一種活動方式或習慣,僅此而已。藝術的創作需要堅實的物質基礎作保障。這一點在它發展的過往中也不難看出,藝術大多隸屬有閑階級。不可否認,不同藝術門類或流派因表達方式和內容的差別而存在不同程度的接收認知。但不能就此根據受眾的多寡而把不同方向的結果粗略成等號或大小。更不能無知的根據字面或畫面的視覺工作量去評定作品價值的好壞和高低。一百萬字的小說一定比三言五語的律詩絕句高明嗎?獲獎的大型歷史題材一定比齊白石的花花草草金貴嗎?答案恐怕未必,有時越看似簡單的招數越難修煉。
藝術家真正的艱辛是絕不故意留給外人窺探的。他們心中都有一桿標尺的敏感,一份自信的孤傲,和一份悲憫的嬌羞。但恰恰是這敏感,孤傲和嬌羞,因人類的狹隘和無知,在歷史上留下了太多的遺憾和誤解。不同于欺世盜名輩的投機,真正的創造者會用全部生命去踐行和拼搏。強烈的專注使他們容不得有一絲毫雜質的侵擾,在瞬間他們聚集強大的力量于一點,敏感準確地抓住時機,成就非凡。他們對真正的創造懷有無限的愛和敬仰,但正是這無限的愛和敬仰讓他們不屑并極度摒棄與己無關的紛擾。天生的倔強讓他們寧可背負世人的誤解也必不屈從妥協,在孤獨、堅韌中,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尋找歸屬。就像凡·高,也許他在別人眼中有很多不易,甚至不能容忍的缺點,但他真實勇敢地面對,憑一己之力問答天地,最終,在向日葵的昂揚和星月夜的璀璨中收獲了綻放……古今中外,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可以說,他們是一群背負神性的使者。之所以稱呼神性是因為在他們的認知維度中,生命的擴張在最大程度上超越了常人,這種特質不因時間流轉或人世變遷而黯淡,相反,會歷久彌新,甚至在時間和地域毫不相干的幾件事或幾個人身上相互印證。這正是藝術的魅力,人性的光輝和創造的偉大。中國道家講求“比于赤子”,可以說,只有純潔的靈魂才具備偉岸的力量。
以上由詩歌的創作經驗漫談開去講藝術,東拉西扯,林林總總似乎說了很多,其實我很慚愧。一來文章受篇幅限制,這些所謂的見識缺乏詳實體系和論據支撐,可謂漏洞百出。二者其中很多意想都沒有創新,大抵可拿陽光底下無新事作敷衍塞責吧。還是回到初衷,一個從小沉默又喜歡語出驚人的孩子,相同的意思非得別著勁兒說,不特殊那么點兒總覺不過意。現時想來,這應該是創作的最初萌發吧。日子告訴我,青春就是在不停尋找。對于曾經的不平,直至潦倒,我從未有過念頭要放棄。走來的路上,除了相信和堅持,因為寫作的緣故,現在更多了份坦然,我感謝這一切。
霞光碰撞,鶯歌曼天,這樣的情境是在等待中收獲的。只要留心,生活中處處都充滿著奇妙——黃昏中的飛鳥,村莊邊的樹梢,霓虹,夜晚,車流,汐潮……萬家燈火有萬千故事。只要記住一點:詩歌是一種態度,一切與他人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