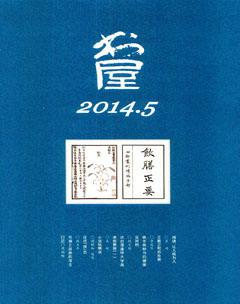《無字》與《青狐》
劉心武++張頤武
張:關于莫言,我們有很充分的對談。現在能不能說說你們那一代,我指的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們。
劉:我們這一代雖然有的作家淡出了文壇,有的不那么活躍了,邊緣化了,但也還有不少人保持創造力,還在寫作,所寫出的文本,基本上還是屬于現實主義范疇,當然像王蒙,他借鑒一些像意識流啊,時空交錯啊,等等傳統現實主義里頭沒有的技巧,但就整個文本而言,它是寫實的,也就是現實主義的。那么在莫言那樣的文本大得其道的情況下,我個人認為,現實主義的文本現在確實遇到了困難。有一個個案,我覺得有一些詭異,你是文學評論家,我想請教你,你來詮釋,就是在中國有一個作家,兩次獲得了茅盾文學獎,就是張潔,按說她兩次獲得茅盾文學獎,應該是中國當下最重要的作家,就算讀者還不夠多,起碼評論界應該熱鬧起來,但是很奇怪,我沒有看到任何評論家就這個事情來做分析,特別是她后來獲獎的三卷本《無字》,在評論方面非常稀少,非常空缺,對吧?參與那屆茅盾文學獎的評委,似乎也都悶聲不響,獲獎名單出來后,張潔二次獲獎,你知道這個獎中國作家們還是很看重的,中國一般讀者也是很看重的,但是也沒有哪位評委寫出文章來,告訴大家他為什么投這個作品一票,告訴人們這個作品好在哪里,以及張潔在中國文學界是多么重要的作家。而且,一些文學圈內的人士都知道,那次的茅盾文學獎,張潔的《無字》和王蒙的《青狐》都入圍了,王蒙不消說是中國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在海外的聲望也非常高,而他在那以前的歷屆茅盾文學獎評選里都沒有能夠獲獎,他的《活動變人形》,我個人認為非常精彩,應該得獎,結果落選。當然絕不能僅以獲獎論英雄,沒得獎王蒙依然是出色的作家。但是整個事情還是有點奇怪。張潔此前因《沉重的翅膀》得過茅獎,《無字》還要再給她一次,王蒙此前沒得過茅獎,《青狐》卻依然落榜。王蒙本人可能無所謂。但是我覺得這個現象值得探究。更有意味的是,《青狐》本身就是對《無字》的撥亂反正。
張:兩者互相隱喻,互為文本。
劉:倒沒互相,張潔應該是自己寫自己的。《無字》面世不久,王蒙就在《讀書》雜志上發表一篇長文,《極限寫作與無邊的現實主義》(載《讀書》雜志2002年第6期),是針對張潔《無字》寫出的評論。王蒙對《無字》基本上持批評的態度,認為張潔書里寫到的那個共產黨高級干部的原型已經故去,張潔這樣進行“極限寫作”不厚道。王蒙設問,如果那個原型仍然活著,并且也行使話語權,也以張潔為原型來寫部小說,又該如何?大致是這樣的意思。王蒙文章里提到的“無邊的現實主義”,跟法國文學理論家加洛蒂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提出的“無邊的現實主義”似乎沒有什么關聯,他那批評文章的總體意思是,現實主義的寫作還是應該有邊界的,應該把握一個度,“極限寫作”不可取。那篇文章發表不久,2006年王蒙出版了長篇小說《青狐》,這個長篇小說,似乎有替已經故去的那位《無字》中的男一號原型行使話語權的意味,那原型大體上跟王蒙是一代人,是“少年布爾什維克”。《青狐》是對《無字》的一個回應。這是一次認真的回應。查閱百度上關于《青狐》的詞條,可以看到這樣的說明:“《青狐》是王蒙最新的長篇小說力作。這部小說寫作歷時三年,又花數月時間精心打磨,終于奉獻于讀者面前。王蒙從事寫作五十年,出版了七部長篇小說,《青狐》是他第一次以女性為主人公,描寫她的愛情、性格、欲望,描寫她的理想、才華、熱情與她的環境、教養、歷史角色之間的巨大的不平衡,刻畫了一個可愛可笑、可敬可悲的女性形象。”“不平衡”、“可笑”、“可悲”這些考語值得注意。
張潔寫《無字》用了十二年,王蒙寫《青狐》用了三年,他們都是認真的。茅獎給了《無字》,似乎是對《無字》的充分肯定,但沒有后續的聲音,沒有什么評論家來分析,告訴讀者《無字》的文學價值究竟體現在哪里。而且似乎也沒有什么媒體就此采訪張潔,發表出有相當篇幅的采訪錄來。我覺得這不是“此時無聲勝有聲”,是“緣何此事竟無聲”?王蒙的《青狐》倒還有些評論,但是似乎都忽略或者是回避了它是對《無字》的一個反撥。王蒙關于“極限寫作”和“無邊的現實主義”的論述值得重視,但我沒有看到就他這些文學理念的回應與討論。為什么?這是一個很怪異的文化現象。我現在就要請教你,你對這個問題怎么看?
張:您提出的這個問題有意思。《無字》這本書呢其實寫了很久,篇幅也很大,它等于是一個自傳,但是這個自傳呢按照王蒙的想法,對與作者生活中有過關系的某些人士,造成了很大的傷害。這個書確實是把寫實主義推向了極致,涉及私生活,下筆很猛。
劉:實際上張潔這樣一個長篇是很難得的。日本很早就有一個關于小說類型的概念,叫做“私小說”,中國好像沒有。你看包括莫言的作品里邊,文本里似乎沒有什么他個人私生活里的東西。
張:中國白話文學早期有,1949年以前有,其實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就是“私小說”,但是還不夠強烈,沒有這么猛。張愛玲有的小說也可以劃歸到“私小說”范疇里。在中國大陸“私小說”斷檔很久,但是二十一世紀初張潔出版了《無字》,她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就很猛。張潔很有意思,就是《無字》其實是把《沉重的翅膀》解構了。這兩部書如果互為參照的話,你看當年《沉重的翅膀》中那個男主角真是非常了不起,那個副部長簡直就是一個渾身發光的改革家。《沉重的翅膀》那個書當年其實正好展示他的正面,后邊的《無字》則把《沉重的翅膀》里的那個角色給解構了,拆解了,否定了,把他私生活里那么下作、低級、不堪的狀態無情地描寫出來,把生命的骯臟不堪寫到極限了。這樣的寫法在中國文學領域真的很少,她后邊的作者也沒有這么寫的,后無來者。
劉:為什么評論家集體沉默呢?
張:這個事可能是它太具有挑戰性,太兇悍,許多人都難于接受。
劉:具有挑戰性才更有評論的價值啊。
張:它又很長,涉及的家族史又很復雜,沒有人去仔細評論,可能是因為難以下手吧,這確實很可惜。這本書這種寫法在新時期以來的文學里面獨樹一幟,這么狠地把自己的私生活曝光,這種寫法是很罕見的。endprint
劉:正因罕見,更需評析。評論家怎么能怕麻煩呢?這是你們的專業啊,難下手也應該下手。特別是作為茅獎評獎委員的評論家,你為什么把票投給《無字》,或者你為什么不把票投給《青狐》,在塵埃落定之后,無妨寫出文章,對作家、對讀者、對中國文學的發展都是應盡之責嘛。如果說是怕得罪王蒙,那又為什么讓張潔二次獲獎呢?其實張潔本人可能對二次獲獎也沒多大興趣。
張:你對評論界的質疑有一定道理。《無字》這個作品也并沒有得到廣泛的閱讀,這個作品很怪,寫私生活十分生猛,“極限寫作”,但影響有限,沒產生轟動。仔細想真的很值得玩味,《沉重的翅膀》里作為改革家形象的,和《無字》里在私生活里寡廉鮮恥的,兩個男子的原型,其實是同一個“少年布爾什維克”。這個現象似乎很少有人關注。
劉:張潔是以《森林里來的孩子》出道的,但那篇作品似乎只不過是她步入文壇的敲門磚,她真正想書寫的,還是她自己,從短篇小說《愛,是不能忘記的》開始,到中篇小說《方舟》,到后來的長篇小說《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走了》,到《無字》,她作品里的自傳性、家族史性質越來越凸顯。《愛,是不能忘記的》里面的那個令女主人公愛慕的男子,原型就是“少年布爾什維克”,在那篇小說里,以張潔自己為原型的那個女子,對“少年布爾什維克”還只是遠望,連手都沒有拉過,后來寫《沉重的翅膀》,就把那“少年布爾什維克”的副部長作為改革家謳歌,從遠望變成近觀了,那么到《無字》,就“極限寫作”,寫到肌膚之親了,一路寫下來,層層扒皮,是個幻滅的歷程,是“私小說”,也是女權主義的書寫。《無字》這么一個龐大規模的文本,好像大家都在冷落它的時候,我覺得在我們的對話當中要把它提出來加以強調。
張:張潔這個人現在也不在公眾視野中出現,我覺得沒有聽到她的聲音。
劉:好像也不是她有意躲避傳媒,似乎也沒有傳媒專門關注她。
張:沒有人關注這個事情,得了獎以后也沒人關注。因為茅獎的作品其實得了獎以后還是有助于它獲得關注的,但這個作品真的是沒有人關注。這個倒是一個新發現。
劉:別人不關注,我們要關注。而且我們基本是肯定性的關注。張潔《無字》的被冷落,折射出純文學里寫實作品面臨的困境。其實王蒙從1992年到1999年陸續推出的“季節系列”,即四部內容相接續的長篇小說《戀愛的季節》、《失態的季節》、《躊躇的季節》、《狂歡的季節》是他本人最重要的著述,我以為也是非常精彩的結撰,雖然還不到史詩的程度,卻也算得上為一代人,為共和國一段歷史立傳的宏偉卷帙,出來以后有些反響,也有大學里的教授、研究生寫出學術論文,但是卻被排除在茅盾文學獎外,傳媒雖然對王蒙的報道采訪很多,但把重點放在“季節系列”并在社會上引起反響的報道采訪卻似乎缺席,以致就讀者閱讀而言,“季節系列”還得算是“冷書”,這也是很遺憾的事情,也折射出寫實文學的窘境。現在似乎只有莫言那種拉大與寫實的距離,搞魔幻、搞復雜隱喻的小說文本,既容易被國內寬容,也容易被西方接納,但是你嚴格地寫實,可能就會被認為敏感。現實主義文本的書寫如何走出困境,需要有志向的作家做出新的努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