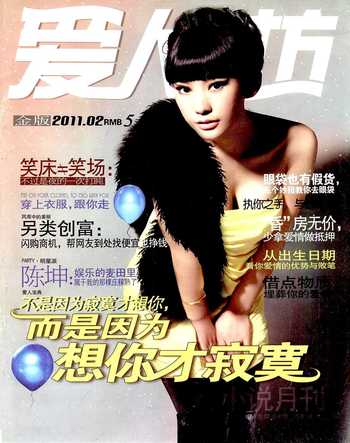《愛情公寓》爆笑臺詞大全
一菲:現在你的眼神很像梁朝偉;眉宇間有點金城武的味道;拿啤酒的動作乍一看像吳鎮宇,就是臉長得像曾志偉。
心理醫生:又一個戴綠……帽子的,你們那綠化不錯。
展博:屁股長在臉上的家伙,整天放屁。
宛瑜:我看到了你腰不酸了,腿不疼了,連心臟也不跳了耶——
展博:那還是我讀高中的時候,有一天我夢到自已在考試,后來我一下子就驚醒了。更恐怖的事情發生了,原來我真的在考試!
關谷:那時候天還是藍的、水也是綠的、雞鴨是沒有禽流感的、豬肉是可以放心吃的。那時候照相是要穿衣服的、欠債是要還錢的、丈母娘嫁閨女是不圖你房子的、孩子的爸爸也是明確的。
一菲:鄙視你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
關谷:小龍女真是太漂亮了!只可惜楊過心里只有他姑姑!!
小賢:小龍女就是他姑姑!
關谷:啊?怎么能這樣呢?那他姑父沒有意見嗎??
小賢:事實上,沒有姑父這個人……
關谷:那楊過自己做了自己的姑父!小龍女自己做了自己的外甥媳婦!!!
宛瑜:師傅,我們現在離市中心遠嗎?
公交車師傅:剛才不遠,現在挺遠的。
展博:我看起來很不開心嗎?
一菲:切,你把郁悶倆字兒都寫臉上了,不識字兒的還真看不出來。
展博:姐你養過狗嗎?
一菲:沒有,不過……你是我養大的。我以前養過很多動物的,鳥、兔子、魚、松鼠、發財樹,不出三天……全都死了,展博你真幸運!
一菲:寫詩么也就算了,還寫的狗屁不通、又臭又長,結果那女生一看,好不容易激發的雌性荷爾蒙瞬間……全變成膽固醇了。
子喬:你的眸,清澈動人;你的手,溫柔細膩;你的心,晶瑩剔透。
美嘉:你的臂,孔武有力;你的胸,寬廣偉岸;你的皮,刀槍不入。
展博:先來五份“強……暴雞米花”!
宛瑜(對服務員):那我們要五份“強……暴雞米花”
一菲:兩位神童,人家那是“勁暴雞米花”
展博:哦,是嗎,改名啦?
小賢:大家好,歡迎收聽《你的月亮我的心》:他們問我有什么理想面。我就說:我想擁有一幢小房子,但我的房子跟別人的不太一樣。我理想中的房子啊,屋頂是杏仁糖片、煙囪是烤豬肉卷、床是蜜糖紅棗糕、枕頭全都是水晶蝦餃、下雨下的是葡萄干、下雪下的是棒棒糖、屋外隨處可見小籠灌湯包、河里流的全是皮蛋瘦肉粥、河里游的天上飛的都是熟的。我哼一聲它們就自動排著隊往我嘴里跳,天上的云是棉花糖,地上的石頭是紅燒肉。
(責任編輯 花掩月 xuxi2266@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