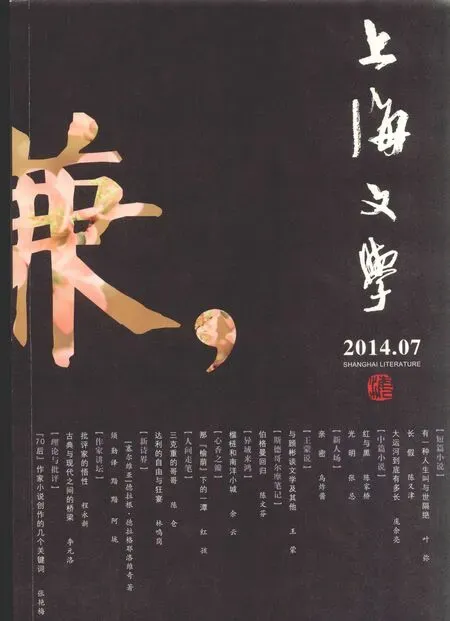榴蓮和南洋小城
余云
每個人首次進入一個城市,都是以自己的一種獨特方式。但回想那個晚上,從燈火通明的怡保火車站大廈拾級而下,朝黑暗的停車場走去時,我們并沒想到會這樣走進怡保。
8點45分,我們已經如愿住進誘人的白色火車站旅館,下一步,要去獅城友人介紹的宏圖酒樓吃他所謂“此生最美味的生蝦面湯”。
不見計程車的蹤影,步行或許也可到達?但四周正如友人描述的一片寂靜。前方不遠處的停車場似有點動靜,趕緊向已發動了引擎的車子走過去,叫住正在拉開車門的婦女。
華人婦女嚇了一跳,等她看清是兩個問路的外鄉女子,臉上仍驚魂未定。不過她和駕駛座上的男子說了幾句廣東話,就轉頭告訴我們,她丈夫說,可以載我們去“宏圖”。
啊?
擠進已有兩個少男少女的車子后座,發現是張全家福:中年父母和小兒子,到火車站接從吉隆坡回怡保度周末的大學生女兒。他們說,宏圖酒樓在舊街場,不遠,但在怡保,兩個女子是絕對不能走夜路的。
車子駛過的大街小巷,果然門窗緊閉杳無人跡。早知山城怡保曾從繁華錫都一夕沒落,但對夜晚的怡保如同一座死城,還是意外。說話間車子拐入一條斑駁舊街,暗街上唯一燈影人聲的酒樓,像夜航中的燈塔散發溫暖。
素昧平生的一家人,就這樣把我們帶進了怡保城。
酒樓的年輕老板娘過來招呼,白皙清秀讓人記起此地盛產美女的名聲。她溫柔的建議不可抗拒:生蝦面湯外,還嘗了炸魚滑、網油春卷、伊面。是家老店,傳到如今已第三代,三十出頭的阮姓少東穿著廚師圍裙,頭上卻綁一條帥氣頭巾,墻上的剪報顯示他作為攝影發燒友的勇氣和成績。要回旅館時,他為我們電召來計程車,對怡保治安的說法和那對夫婦一樣,還囑咐我們有任何問題都可打電話給他。
治安不靖?有點吊詭,怎么在馬來西亞一路盡碰到好人?
相比夜晚的死寂,早晨的怡保像在陽光里活了過來。依著少東夫婦指點,一早就直奔舊街場去喝著名的白咖啡。十字路口,望去都是兩層老店屋,一字排開的三家茶室新源隆、新源豐、新源峰和對街的南香,構成了城中咖啡香最濃郁的街口。
在最擁擠的新源隆檔口坐下,同桌的兩個阿叔見我們面對那么多美食不知所措,就幫忙叫來沙河粉和新鮮叉燒。不一會兒,新源豐的豬腸粉、新源峰的海鮮米線也由兩家的伙計送來了,對面“南香”的小伙計捧著湯碗穿梭小街——一瞬間竟有些感動,想起在獅城看慣了的硬邦邦告示:“非本店食物飲料,一律不準在此食用。”
兩個阿叔互相倒不多話,大約每天一起喝咖啡吃早餐的。他們走后又坐下一對老夫婦,白發圓臉的老先生要了看來很美味的云吞面,一份《星洲日報》遞上來,他接過、付錢,一切理所當然。熱情健談的老先生和賢惠太太也每天到這里早餐。他退休前做玻璃貿易生意,兒女如今在吉隆坡新加坡成家立業。他說富山茶樓的香港點心好吃,怡保城外有很多山洞景點,如果我們多留一天,他可駕車帶我們去玩。
飄著新鮮白咖啡香的街口,和老先生一直聊到預約的計程車司機來接我們去華都牙也的凱利古堡。
真是一個太美好的早晨。
十年前,到過怡保的上海好友敘述他們一家如何在黃昏的怡保城里尋找芽菜雞:他們要去吃最有名的芽菜雞,在街頭問了幾次路,然后,整個舊街場的店家似乎都知道了有一家新加坡來的中國人在找“老黃芽菜雞”。吃完了往回走時,還不斷有人唱歌一樣地問:“找到了嗎?找到芽菜雞了嗎?”
位于盛產錫米的近打河流域的怡保,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急速發展成“銀光閃耀之城”,各路人馬涌至,戲院、酒吧、沿街攤檔,入夜仍熱鬧非凡。昌盛幾十年后,怡保隨著錫價崩潰、礦場關閉而沒落,年輕人紛紛到別處謀生。寫小說朋友描述的情景饒有意味:盛極而衰的怡保,是個居民善良,都是熟人,但已變得空落落的小城。
今天的怡保努力推行許多發展計劃,試圖恢復昔日繁華。然而它讓旅者和文化人眷戀的,卻正是充滿懷舊氣息的老街道,還未被現代化摧毀的場景。它是從怡保出發的作家黎紫書筆下的“州府”——深邃幽暗愛恨情仇的背景,它是阿牛鏡頭下純真少年情懷的底色,也是生于怡保的留臺作家陳大為的詩句:
我把族譜重重闔上
仿佛訣別一群去夏的故蟬
青苔趴在瓦上書寫殘余的館史
相關的注釋全交給花崗石階
南洋已淪為兩個十五級仿宋鉛字
會館瘦成三行蟹行的馬來文地址
后來在網上看到有年輕怡保人抱怨城市發展停滯薪水太低,連車都供不了,但也有人寫道:既然繁榮不了,就讓我的家鄉保持寧靜吧,反正我就是愛它。
我們來遲了嗎?只看到一個“沒落”之城。但有時,幸與不幸,好與不好,其實在于你用什么眼光去看。
落日般的城鎮,落日般的歲月,自有一份文學之美,歷史遺韻。
星期五,亭亭打來電話,召集我們星期天傍晚六點到馬里士他路吃榴梿。說已在阿玲那邊預訂七個榴梿,但不保證一定能吃到,因為“等候名單很長”。
六點?就是晚餐了。雖然我已會吃榴梿,以榴梿當正餐倒還是第一次。
果然在阿玲的攤位,“損友”五人只嘗到四只風味絕佳的“牛油”:干包果肉苦甜,回甘醇香,最后那個香氣馥郁如酒。賣了三十年榴梿的阿玲,把她認為不夠好的榴梿都斷然棄之。
意猶未盡,轉移陣地再吃。幾步之外這攤名為“空軍”,因堅持賣極品榴梿剛得亞太品牌大獎。攤邊燈火通明,排開近十張桌子,伙計還在不斷翻下桌面,這景象恐怕南洋獨有——親朋好友圍桌不為吃飯喝茶,桌上主角只有榴梿。
五女又分食個大肉厚的“貓山王”兩只,飽腹不在話下。隔壁的“亞順”,榴梿筐里插著“黃肉苦甜,扁種子,包好肉”的牌子,無本事再吃,精神卻提起來了,和攤主聊天,說是“每天可賣兩三百粒,六點開檔,九點就賣光”。
到獅城二十年,吃榴梿只是近年的事。雖然聽說只要嘗試幾口,度過最初的“適應期”,便很容易為榴梿著迷,之前十八九年,味覺經歷慢慢本地化的過程,與南洋人引為驕傲的熱帶果王卻是無緣。聞其味必躲得遠遠,走過榴梿攤碰到小販兜售,總一句“對不起,我不會吃榴梿”后疾步走開。友人盛情下勉強嘗過,捏著鼻子囫圇而吞。直到一年前老板招待中國學者,陪吃了螃蟹后移步實龍崗體育場邊一榴梿攤,兩只“金鳳”上桌,果殼打開,第一次好奇怎么這黃黃果肉并無臭味?抓起一囊,入口甘香,好味呀!神奇的跨越瞬間完成。
同事聽聞我終對榴梿開竅,包車組織榴梿團北上,在新山榴梿大巴剎見識了名稱千奇百怪的馬國榴梿:D24、紅蝦、葫蘆、趙傳、意難忘……“小紅”不算風騷,還有喚作“林鳳嬌”的呢。一口氣品嘗了五六種,大快朵頤。
榴梿確是讓人愛恨極端的水果。“榴梿出,紗籠脫”,有人愛它滑似奶脂,齒頰留香,嗜之如命;有人嫌它臭如貓屎,不堪入鼻,繞道而行。當年孫中山“惡之”,其紅顏知己陳粹芬“喜之”。郁達夫的形容是:“有如臭乳酪與洋蔥混合的臭氣,又有類似松節油的香味,真是又臭又香又好吃。”苦甜,臭香,怎樣的水土孕育如此奇異的果實,將沖突的兩極融于一體?記得有一年影星陳沖來此,記者問她對新加坡的印象,她答得感性:整個島國的空氣里彌漫著一股有點腐爛的香蕉的味道。想一想,南洋水果不都有似臭實香、大香若臭的芬芳?香蕉、芒果、木瓜、黃梨、菠蘿蜜……滿身硬刺的榴梿,只不過特立獨行,異香更濃烈而已。
讀到馬國美食博客林金城的《榴梿送飯》,寫他幼時一家大小席地食榴梿,穿唐衫孖仔裝的外婆蹲坐不便,總以高姿態坐在圈外參與,遇到對味的便以東莞鄉音嚷說要留些送飯。他那時無法想像甜食的榴梿與白飯配搭是多惡心的吃法,而外婆一邊吃得津津有味,一邊不忘探尋他驚疑的目光,喚他“過嚟吃啦,幾好吃架”!他外公以賣榴梿為生,外婆則嗜吃榴梿出名,有次為了把整攤榴梿吃光,竟被外祖父一氣之下扔出門外……“有人說,早年南來的華人都迷信榴梿有股魔力,一旦吃了便流連忘返,落籍南洋,不愿歸去!如此推想,當年外婆不僅著魔成癡,甚至還扮演公然惑眾、推銷南洋的角色呢!”
飲食習性,實為一代人的故事。“一只榴梿三只雞”,榴梿性溫滋補,物質匱乏的年代,南洋老祖母似乎都愛死榴梿也偏好榴梿送飯。而能欣賞“榴梿配飯”的,才是最高段數的榴梿迷?從網友對林文的回應中,我抄下“榴梿送飯”的三種食譜:馬來人的,早期華人的,峇峇娘惹的,口味和做法有微妙差異。
如林金城說“歷史虛虛實實,榴梿可具象可抽象”。東馬大詩人吳岸有著名的《榴梿賦》:“在潔白的子宮里/孕育著稀世的醇膏/披著盔甲/戴上自由女神的桂冠/伴著八月驟雨的節奏/悠然降臨人間”。對“榴梿是鄭和大便”的說法,獅城的王潤華教授一定很憤怒,在他眼中榴梿是一道“后殖民風景”,《榴梿滋味》一書中,他將“吃榴梿的神話”作為一種“后殖民文學的文本”來分析。
在南洋,榴梿的種種皆成新聞。近年焦點與中國崛起及全球化有關:馬國榴梿大量出口中國大陸及香港,新馬人反而要吃貴價榴梿了。
唉,說不盡的榴梿!無論如何,下月初要去柔佛的榴梿園吃一趟榴梿,因為組織者的話太誘惑:直接到園里吃,可嘗到有機種植的榴梿;剛掉下的新鮮榴梿,和運到本地的有很大不同。榴梿最好一落地馬上吃,很“粘喉”,不能馬上也要在掉下后六小時內入口!
和我一樣最近才迷上榴梿的朋友說,來新十多二十年后能幡然醒悟愛上榴梿,實在太好了,仿佛終于拿到一張“生活永久簽證”,可以自詡為南洋人了。
與這兩個檳城男的相識,很像一篇小說的開頭。
來到喬治市當天下午,我和女友站在街邊,為了要問去海邊怎么走,揚手去攔一輛從不遠處駛來的電單車。載著兩名男子的電單車在馬路上打了個漂亮弧線轉到面前,還沒停穩,長得像謝霆鋒的騎手已笑了起來:
怎么又是你們!
大家都笑了。半個多小時前在打銅仔街路口尋找孫中山住過的“莊榮裕”時,為問路招過一次手。駛過小街的這輛電單車停下來,后座的圓臉男好心告訴我們,孫中山紀念館在前面不遠,不過這時候已關門。當時友人就說,那束馬尾的騎手很酷哦,輪廓深邃眼神深沉。
再次偶遇,很奇妙地就有了幾分熟悉感。你們要去哪里?海邊,City Hall那邊。那有什么好看?“謝霆鋒”微笑時露出整齊白牙。殖民地老房子,旅游書上都介紹的呀。圓臉男對同伴咕噥了句什么,然后認真地看著我們:“我們可以載你們去,不過你們要到葉氏宗祠——就是你們之前走過的那路口,等我們二十分鐘。”
他們要回住處多騎一輛電單車來嗎?
椰腳街、大統巷、打銅仔街和本頭公巷構成一個十字路口,位居喬治市古跡區中心地帶。街邊有家看起來蒼老的“華民茶室”,走進去發現,除了我們兩個游客,其他人都是熟絡的老街坊。稍歇,向老婦叫來“茶烏”喝了,就到街上等我們的騎士。
街角的大樹下有一輛三輪車,幾把木椅,很像一幅靜物。我們走進畫中坐下,看著四周布景一樣的百年老店屋。黃昏慢慢降臨,行人寥寥,陽光把對街的白墻染成燦燦明黃,無聲地,像一出戲序幕的情景。坐在十字路口的淡金色世界里,兩個外鄉人一時不知身在何處。
有人過來搭訕,在“華民”見過的。他坐上三輪車,一直絮絮說著什么,要說服我們第二天包他的車?聽不清這車夫的話,只覺有人在遠遠地念繞口令。
好像過了很久,兩個熟悉的身影驚醒了夢中人:他們真的來了,開了一輛小車!
這次是圓臉男駕車。大家都有些興奮,很快交代了各自的姓名身份。海邊天色已開始暗下來,匆匆拍過照片,車就往回開了——比起那些殖民地大廈,這兩個當地人的生活顯然更加引人。原來他們是好友兼鄰居,馬尾男單身三十出頭,圓臉男已四十多歲有上小學的女兒,兩人各自開了家小古董店,都在本頭公巷街邊,緊挨著大伯公廟福德祠。每天他們都一起出來喝兩次咖啡吃一餐飯,所以似乎永遠在小城里晃悠。
圓臉男姓陳,他的店其實是老檳城有名氣的腳踏車店。各款老爺腳踏車,或高吊樓板下或掛在墻上——這畫面上過不少媒體。從小喜歡老舊事物,他把多年收集的古早物品擺在店里:牌匾、歌星明星舊照、如今少見的大光燈、時鐘、熨斗、玩具、黑膠唱片、鳥籠、茶壺……古色古香塞滿一屋。
馬尾男姓蔡,他的店里也林林總總,但多了字畫、面具和自己用舊物設計的燈盞,更文藝氣息。屋子中間還布置了閑坐的沙發小幾,幾張好萊塢碟片顯示主人的另個喜愛。很有意思,蔡帥哥應是自覺能吸引眼球的那種,舉手投足都有明星架勢,我們也干脆把他當明星猛拍了一輪。
這結合了愛好的生意足以維生嗎?答案是肯定的,盡管不能算富裕。帥哥說不幾天要去巴黎跳蚤市場淘貨,他店屋樓上,也一直租給洋人朋友住。憨厚的陳男呢,當其他腳踏車店紛紛捱不下去關門大吉,繼承父業的他守到了人們追求健康生活,腳踏車又復興的日子。
那晚的本頭公巷,在茱迪·福斯特拍過一星期《安娜與國王》的店屋前,我們意外窺見了綺麗一幕:夜色和暴雨一起到來前,夕陽奇異地迸發最后的光亮,烏云的醞釀讓暮色的暈染如此絢爛,把對街一大面山墻照得金黃金黃,雕花的黑色屋檐像蜿蜒的鑲邊,精致小窗嵌在墻中央,真可以拍一張明信片。
雨止了,陳男的老母凝坐廊下竹椅一動不動,一身南洋花衫褲的側影,疊印著五腳基外冰藍夜空。絕好的光線畫面,可誰忍心驚動仿佛坐了一個世紀的老婦?
小說也不會寫得如此巧合,逗留檳城的兩天里,我們竟然和這輛電單車、這兩個檳城男遇見了五次!除了上述兩次,一次是在夜食攤檔碰上,一次是臨走那日中午我們特地前去道別。可告別后回旅館取行李前,我們匆匆去找一家朋友介紹的“咖啡電影”喝了杯卡布基諾,出來走在小巷里,那輛電單車又迎面馳來!
這回,大家倒都有點不好意思了。
回到獅城上班,那個籠在淡金色陽光里,桃花源似的街口不斷擺蕩回來。記得有人論述“人行道的幸福生活”,認為小城才是最人性而適合居住的。寧靜純樸,居民互相認識,沒那么多壓力、計算的小城人生,是更自在美好的人生。
離去那天在陳男的腳踏車店門口喝茶,一名靈秀女子騎車載著男友飛馳而過,一路留下銀鈴般笑聲。陳男邊揚手回應她邊說:這對戀人是在后巷開咖啡座的,每天這時候都關了店自己去喝茶逍遙,你看,他們多快活呀!
頸椎僵硬地坐在電腦前的我,走了一會兒神。
這時節已是榴梿季的尾聲,十一月下旬和十二月初,損友們開過兩次榴梿派對后,已相約明年六月再吃邱家榴梿園的有機榴梿。可偏偏北方來了友朋,總要獻獻寶,賞味種種本土美食后,仍覺缺了什么,是的,如果沒嘗過榴梿,遠方來客怎算到過了南洋?
自從去年六月某夜臨時被友人召喚去赴邱家的榴梿派對,味蕾被每只榴梿里僅有一瓣果實的“極品紅蝦”寵幸過,我們吃榴梿的段數猛升了幾級。
俗話說“人無癖不可交”,榴梿是身為銀行高管的邱先生和太太唯一的共同癖好,不過二十年前他們在柔佛買下一塊地種下二百棵榴梿樹,并非只為飽己口福,不然無法理解,為何他們每到周末就開車奔向對岸,辛苦得家務都荒疏了;為何他們舍得投下超過百萬新幣,一次次砍掉不夠優良的果樹重新種植耐心等待(一棵榴梿樹長成結果至少五年)。
不知經歷了多少次失敗,當兩人都被熱帶陽光曬得黝黑,邱先生終于和技術員一起研制出黃梨(菠蘿)制成的天然酵素,不施化肥農藥的有機榴梿——枝頭的夢想之果日漸成形、成熟。近年他們開始將自家榴梿園的少量產出與親友分享,試者無不“驚為天果”。
友人向邱太嘗試可能性,回話是:有沒有得吃,要看今夜有無足夠的榴梿從樹上掉下。晚餐時我們向客人說:一起為榴梿祈禱吧!
等著榴梿從樹上掉下的感覺很新奇美妙。正巧那夜翻到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的《馬來群島自然考察記》,這位英國博物學家、探險家、地理學家、人類學家與生物學家,為了發掘和采集西方世界不曾知悉的動植物種,從1854年3月開始用八年時間游歷了馬來群島的無數島嶼。他筆下有大花草科的巨花、“蝴蝶中的王子”大型綠翼鳥刺蝶、酷似人類的紅毛猩猩、絕美的天堂鳥、美得難分軒輊的各色昆蟲、風俗各異的島民和奇特自然地理景觀,書中竟還有整整一節專記榴梿。
華萊士寫道:“……砂拉越河夾岸果樹遍地,是戴雅克人的倉儲。這一帶盛產山竹、蘭撒果、紅毛丹、菠蘿蜜、蓮霧與楊桃,但最多也最貴重的是榴梿。這種水果在英國默默無名,但在馬來群島則不論土著或歐洲人都奉為無上珍品。”
來自19世紀中葉的第一手記錄中引用了16世紀荷蘭旅行家林索登(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1599年的筆記:“據吃過的人說,這水果香甜味美,堪稱人間水果之最。”另有林索登游記的編纂者帕魯達努斯(Paludanus)博士的補充:“這水果潤熱,對于不曾吃慣的人,乍聞有爛洋蔥般的臭味,繼之入口,即尊為果中之后。土著推崇,贊美有加,并為之作韻賦詩。”
和林索登不同,華萊士是“吃過”榴梿并成了發燒友的:“它的臭味常常十分嗆人,有些人因此無法忍受品嘗它。這正是我初次在馬六甲試吃榴梿的寫照,但后來我在婆羅洲拾得一顆掉落地的成熟榴梿,就地嘗之,一嘗就愛它終生不渝。”
從樹到果,這位植物學家的記錄頗仔細:“榴梿長在高大的喬木上,樹形像榆樹,但樹皮較光滑、多鱗片。果實圓形或稍橢圓形,大小如大椰子,表皮綠色,密布短硬的木刺,刺腳相連形成六邊形,刺尖強韌銳利……它的外皮厚而韌,即使從高處墜地,依舊完好如初。從果臍到果尖隱約有五條直紋,直紋旁硬刺略彎,這些直紋是外果皮的接合線,可從此處用一把結實的刀或有力的手將之剖開。五瓣內襯為白緞色,每瓣有一團飽滿的奶油色橢圓果漿,最里面有兩三顆大如栗的種子。”
來到果實的滋味,華萊士似有少許為難:“果漿可食,其稠度與風味難以形容”,但還是努力形容一番:“像濃郁的奶油蛋糕加了濃濃的杏仁味,卻又帶著一絲絲像奶酪、洋蔥醬、棕色雪莉酒香,以及其他種種不可名狀的氣味。此外,這果漿有種黏稠的順口感,真是美上加美,這也是其他水果缺乏的特點。榴梿不酸澀,不甜膩,也不多汁,卻又讓人覺得它樣樣皆全,簡直完美無瑕……”
合上書頁,禁不住開始想像邱家寂冥無人的秘密花園,撲通……撲通……青綠色的幻夢在半島的夜霧晨風里有節奏地離枝、墜落,靜待一雙歡欣的手珍惜地拎起它的青蒂。真是熱帶獨具的幽秘景象。那夜睡夢里,榴梿墜地的砰然之聲該帶著幾百年的回響吧。
第二天上午不到十點,好消息從柔佛傳上了擺滿肉骨茶的桌面:經理報告撿到八只榴梿!客人和我們一起歡呼。
榴梿宴在損友之一家舉行,泳池邊,朦朧光影里橙金色果肉格外誘人,貓山王的滋味完美得如華萊士說的難以形容。有人也嘗了主人怕不夠喂食客人而特意從城中名攤買來“備吃”的榴梿,直說立見高下,前者的回味清新馥郁,后者的甜香似存僵硬的糖精味。我為自己沒有“續貂”而得意,只強烈地感到詞窮。
不久前推出以臺灣茶葉史為背景的長篇新作《幸福之葉》的作家陳玉慧說:最難的是寫感官反應,你如何描述一碗好茶入口時的溫潤?
榴梿的味道是更復雜難言的。想起張愛玲曾說,沒有何種感覺或意態形致,是她所不能描寫。突發奇想:如果這位文字高手在場,會怎樣描述這頓榴梿大餐?
忘了告訴我們的客人華萊士的這句話——“事實上,光為了體驗榴梿的美味就值得一趟東方之旅了。”
星期天晚上,我們坐在獅城廈門街的“茗香”吃福建菜。這個“我們”是蠻有趣的構成——幾個上海來的“新移民”,一名本地女子,一對短期居新的美國夫婦(華人教授與白人太太)。大家都說中文。白人女子的普通話太標準,竟引得安娣(阿嫂)侍應生不斷進包房倒茶水換碗碟——輪流來聽這洋人說的好聽華語。
漸漸地情形更有意思了,新移民們開始教美國夫婦如何在本地的“Kopi店”點咖啡——
Kopi O, Kopi Si, Kopi O Kosong, Kopi Si Kosong, Kopi O Siew Dai, Kopi Si Siew Dai……
唱歌一樣的音調里,唯一的本地女子笑了:這些朋友,已徹底淪陷在了南洋飲食里。
很自然地,“新移民”們憶起了和本地食物的情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一個說,為了吃,哭都哭過呀。剛來時夫婦倆在咖啡店不知吃什么好,先生隨便叫一碗面給她,浸過堿水的面黃黃的,一看就沒法下咽,她皺眉埋怨,也來自上海的男人急了,當眾斥她嬌氣。看她委屈得眼淚汪汪,小販安哥(阿叔)同情地走過來,端回黃面,重新燙了碗米粉給她。二十年了,難堪又感動的一幕一直留在心里。
一個說,兒子剛來時,總想著老家對面菜市場里的砂鍋雞湯餛飩,剛出蒸屜的滾燙小籠包,惦著以前飯桌上的紅燒肉、蔥烤鯽魚甚至一盤清炒雞毛菜。有次大人談著生活的改變,他在一旁幽幽說:“我也不容易呀。”“你有啥不容易?除了上學什么都不用管。”少年人嘆口氣:“唉,這里的東西都那么難吃!”幾年過去,兒子再次遠行留學,午夜夢回,惆悵的已是叻沙和雞飯。后來在那北美城市的郊外發現了一家“獅城餐廳”,他興奮莫名,每月一趟,和同樣在島國念書長大的女友巴巴地坐一個半小時巴士前去,吃過其實并不地道的蝦面、河粉,再心甘情愿坐一個半鐘頭的車返回。回獅城度假,天天出門尋食,必得把雞飯、鴨飯、炒福建面、炒米粉、魚丸湯、沙爹、咖喱魚頭、Nasi Lemak、Riti Prata……通通掃過一輪。
嫁給了獅城男的女子說,那時和老公剛戀愛,他總帶她去吃心中的最美味:小販中心的黑醬油炒粿條,芽籠的豆豉蒸魚頭……地方通常悶熱,吃得她滿臉油汗。后來她的表情終讓男人讀懂了:吃什么不重要,先要有冷氣!不知那些長相平凡味道有點奇怪的小食有什么魔力,歲月悠悠,已是兩個滿口Singlish(新加坡式英文)兒女之母的她,早可充當島國美食導游,某些癮頭,比土生土長本地人更甚:幾天不喝基里尼路的咖啡,不吃某攤肉骨茶,渾身不舒暢。
如果說,香料是埋藏在南洋食物里的秘密,本地小吃中,口感層次豐富的叻沙最是撩人?想起一個移民舞蹈家朋友,從島國又輾轉去了外地工作,每次回來探親,女兒都從機場接了他直奔“加東叻沙”,讓他在舌尖上的溫柔鄉里飽足了,才載著人和行李回家。
一直沒忘的還有一幅圖景:剛來不久,曾在一座小販中心外偶遇一本地詩人帶了位長發女孩來用餐,有幾分姿色的蘇州女孩筒狀長裙及地,望著有些油膩的水泥地邁不開步子,見了我們立刻嘟噥:我都不吃小販中心的!
嗲氣的蘇州女孩還在新加坡嗎?當年,另一個朋友倒真為故鄉的鮮美小餛飩作了歸人。這朋友拿美國文憑美國護照在獅城有高薪工作,卻執意要放棄一切回家鄉杭州去。臨走時他告知,起先家人都激烈反對,直到他說了這么一句話——“你們想一想,我每天都在吃著至今不能習慣的食物!”東坡肉西湖醋魚龍井茶養大的家人,聽了這理由都默不作聲,不再堅持。
舌尖上的記憶究竟是生理還是感情的?這也是吊詭之一:有人放棄了在移居地的嘗試,只因住得還不夠久?而有些味道,離開了才會在想念中濃烈起來。不就有這樣的老外,走了又回轉來,干脆娶了本地女子久住,只為習慣了熱帶的天氣,熱帶料理的辛辣刺激。
從凡常小食到國菜辣椒/黑胡椒螃蟹,到最華麗濃郁的娘惹菜,顏色艷麗香氣誘人的南洋之食,最終會抓住中國新移民的胃。他們從擁有八大菜系、悠久飲食文化的文明古國而來,但同樣“回不去了”。情感融入之前,味蕾已開始異變。一片水土,一座城,一個國家,有時就濃縮于方寸,含在口里。
有人說得好:所有的美食感受,都離不開情境體驗;所有的美食故事,其實都是一個人的成長史。
童少的滋味還是在的,只是舌尖上已堆疊起兩個家鄉的記憶。
辭職返鄉的馬國前同事阿珠忽飛來獅城“公差”,見面才明白,休整一段時日后她當上了印度尼西亞棉蘭某地有三十多員工的華文報的總編輯。呵,眼前立刻一派古樸的南洋小城風光。她說那里薪水自然不比這邊,剛上手的工作也還蠻忙,但小地方生活簡單民風淳樸沒有壓力,看她輕松的樣子,確像過得十分怡然。
是和京小姐同去會阿珠,交談沒幾句,京小姐便頓悟般宣稱找到了“人生下半場”的活法:屋子的貸款供完之后,就可以開始在南洋小鎮蕩來蕩去的日子!遐想即刻展延:印尼和馬來西亞?哪些小鎮,可以悠然住上幾個月?
其實朋友中早有人在南洋小鎮晃悠了。也供職于獅城的華先生,近年似乎故意在邊境的兀蘭租房,一有空就邁過關卡往馬國小城小鎮跑,居鑾、麻坡、芙蓉、怡保、江沙、金寶、文冬……僅有一個周末,就去近的地方,多幾天假期就走得稍遠。坐火車或巴士,一處處漫游;散漫的晃蕩,好就好在沒什么特別要做的事。街頭欣賞一下各有來歷的老建筑,經過有趣的老鋪子進去望望。更多是在茶餐室里耗著,看會兒書,和東主或每日坐在同個座位的茶客聊聊天。餐食是不用愁的,每處總有些聞名美食,歲月留下的味道,價錢也叫人驚喜。“高高的屋頂、悠悠的吊扇、馬賽克地磚、友善的老人、攤開的《星洲日報》、香濃的咖啡、移動的光影,(有些還配置)龍腦木椅、云石圓桌,仿佛一頭扎進了過去的老歲月里。就這樣以一個外鄉人的身份孤立于南洋的語境里,卻其樂融融。”
純樸滄桑人情味濃,對華先生而言并非魅力的全部,他說再微型的南洋城鎮也有幾棟殖民建筑和老店屋,加上基督堂、回教堂,各色人種,這中國小城沒有的景象,對新移民太誘惑了。
我走過的南洋小城名單上,怡保和太平,是從幾十年前的繁華城市逐漸“沒落”。尤其怡保,昔日堂皇的規模仍在,年輕人奔往大都會后棄留的父輩和老屋舊巷,已被五腳基竹簾篩過的陽光雨水,斑駁成另種風韻。走過這黃昏般的落寞之城,你會覺得自己變得柔軟,一種溫情慢慢在心里滋生。
與上述兩城不同,由新山北上火車的第一站居鑾,從來就是個散淡在熱帶炎日下的小山城。去年三月首次抵達,只知最著名的是“火車站咖啡”,曾為當地文化人聚集點,不料正逢星期四休息。失望間遇到個開輛舊車賺外快的老人家,載我們去吃了肉骨茶,看了會館聚集、屋檐雕飾奇異的老街,又在大路口新店里找到“火車站咖啡”老板——小城人都互相認識。老板請吃炭烤軟面包、牛油炒的黑咖啡,話頭一扯開就是家族三代移民故事。半個月前和一伙同事去柔佛吃榴梿,又意外停留居鑾,這回小城最美妙的款待,是那碗加入十多種藥材烹成,好味之極的“東甲牛肉面”。
當然,如果認識一兩個當地文化人,讀過些文人的敘述,小城故事會更歷史和文學。已落幕的怡保老酒吧“東華”,秾艷又纏綿的往事,由當地人李永安那本《情人的午后》流播。民國時期外交部長陳友仁之妻、曾執教獅城南洋美專的傳奇女畫家張荔英,當年常駕一部粉紫色小車到馬國城鎮覓景寫生,她的后印象派南洋靜物,筆筆情深。董橋書里格外古典的南洋,都蒙著一層淡紫色月光,熱帶色澤鮮明的人和事,被他織成文字錦緞。上個周末和友人到了以美食著稱的麻坡,白天做了貪食街的饞貓,入夜跟著資深報人張先生的車在總共六條馬路的城里轉悠,“同盟會重鎮啟智會堂”,“二戰時畫家劉抗和妻兄陳人浩經營的巴黎風咖啡館舊址”——寥寥幾句像魔棒點睛,眼前的畫面立刻有了景深。白天我們坐過的茶餐室仍亮著燈,三兩茶客身影依稀。也有真假難辨的按摩院和夜店,一家“有中國妹來才開”的酒廊名喚“夜夜逢”,那晚沉默在幽暗里。文化名城的風月,也比別處多點墨水?
說不盡的南洋小城,回想讓自己剎那動過遷移之心的,有一處是老撾北部的瑯勃拉邦。因那寺廟處處的古城有前消費時代的質樸笑容,也因幾千美元便可在湄公河畔建一棟小樓。人總在尋找適合自己棲息的地方。不曉得生活消費的廉宜是否列入“宜居城市”指標,卻知理財專家告訴新加坡人,需百萬新元才能過理想退休生活。這天文數字令許多中老年人沮喪,也讓年輕人剛開始工作就被“養老”捆住手腳。然而誰說非得有百萬儲蓄才可退休,如果目光轉向那一個個南洋小城,在麻坡,月房租五百令吉已是中等價位。
歐洲和北美的小城小鎮更漂亮古意?對多數亞洲人來說,那些“天堂”都太遙遠。華先生說在老南洋茶餐室里,“時間似乎有了另外的意義,我也似乎變成了另一個自己。”反過來說,只要你愿意變成另一個自己,愿意踏上“回歸”之途,在南洋小鎮悠閑地蕩來蕩去,實在并非遙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