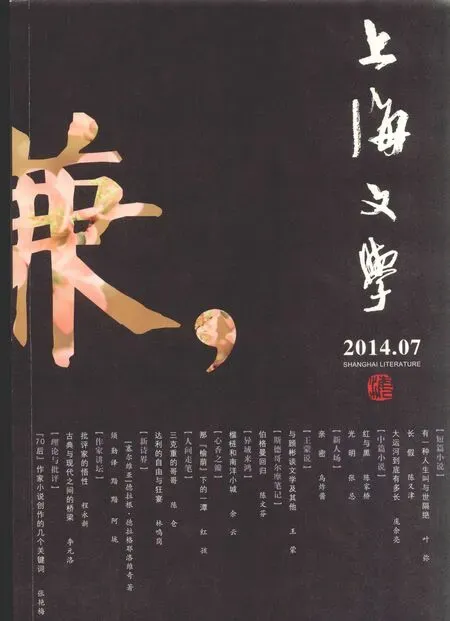“70后”作家小說創(chuàng)作的幾個關(guān)鍵詞
提起“70后”作家,我們可以列出長長一串名單,而研究“70后”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我們常常會用“山東女作家群”、“山西新銳作家群”、“甘肅八駿”、“河北四俠”、“新生代”、“中間代”之類的概念,不過,這些地域論、題材論、風(fēng)格論等話語,對于這個豐富而復(fù)雜的群體來說,并不十分有效。整體上,“70后”作家是具有藝術(shù)氣質(zhì)的一代,是關(guān)注精神信仰、靈魂存在和內(nèi)心世界的一代,是思想駁雜、風(fēng)格多樣、藝術(shù)觀念比較先鋒的一代,是充滿疑問、進(jìn)退兩難、泥沙俱下的一代,他們在自我和社會之間、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鄉(xiāng)村與都市之間、童年記憶與中年感懷之間,不斷搖擺,很難簡單定位。因此,深入剖析這一作家群體的創(chuàng)作心理和意識形態(tài),顯得很有必要。
一、時代與自我
1970年代,是一個什么樣的年代,親歷者,后來人,可能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jié)論。“70后”作家,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群體,也不是三言兩語可以簡單概括。已有的研究,無論是整體觀照,還是個體解析,不乏真知灼見,也難免有研究者自說自話。那么,我們寫了那么多評論文章,與作家的寫作初衷究竟有何關(guān)聯(lián)?我們這些研究者,又在多大程度上,了解自己對面那些或沉默或饒舌的寫作者?這些寫作者出生于城市或是鄉(xiāng)村,來自知識分子家庭或是農(nóng)民家庭,他們的寫作傾向和思想意識有很多不同,至于出生在70年代初期或是末期,甚至近乎于兩個時代了。當(dāng)這一群人慢慢進(jìn)入中年,開始有意無意回首往昔時,那段歲月雖然算不上驚濤拍岸,但面對1980年代出生的后來者,還是難免有些滄桑感懷。畢竟,出生在“文革”時期,成長于“后文革”年代,經(jīng)歷了社會格局和生活氛圍的劇變,可以說,1970年代,及此后的三個十年,每個十年幾乎都是迥然不同的社會形態(tài)。雖然十年“文革”與后來的撥亂反正,對于尚處于童年時期的“70后”來說,談不上什么切膚之痛或是由衷歡喜,但是歷史的影子,總會在一個年代留下深淺交錯的痕跡。作為后革命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經(jīng)歷了理想主義的青春歲月,然后是面對極端物化的后青春時代,兩個時代的斷裂,無疑對這一代人的精神底色和思想構(gòu)成,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及至新世紀(jì)十余年來,社會問題日益尖銳,漸漸成熟的“70后”寫作者自身也經(jīng)歷了新的分化和轉(zhuǎn)型。
在進(jìn)行當(dāng)代文化反思時,我們應(yīng)該看到1990年代社會變遷、人心動蕩、欲望漫漶之間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這個話題其實很有意思,當(dāng)代中國的標(biāo)簽實在不少,真正反映社會本質(zhì)和問題根源的不多。經(jīng)濟(jì)上的跨越發(fā)展,政治上的偏于保守,形成了特別強(qiáng)大的兩種力量。“70后”就在這兩種力量糾結(jié)作用下,以相對滯后遲緩的姿態(tài)成長起來了。這使得他們對物質(zhì)書寫,有著天然的本能和特別的敏銳,對于文化裂變,則保持了一種比前后兩代人都更為激烈的態(tài)度。客觀地看,衛(wèi)慧、棉棉被炒作那個階段,欲望書寫背后,藏著的是對大時代的恐懼和惶惑,看似沉湎于物質(zhì)和感官世界,覆蓋了思想和生命的任何深度,其實在那種夸大的自我放縱和張揚里面,還有一種與感官世界相對抗的力量,這種力量既貌似天真的犬儒姿態(tài),又有著某種毫不在意的破壞力。等到新世紀(jì)開場,那股摧枯拉朽的頹廢虛無之氣,漸漸消散,“70后”作家仿佛一夜間改頭換面重新出場了。細(xì)細(xì)分析,除魏微等個別作家屬于從時尚寫作轉(zhuǎn)型為嚴(yán)肅寫作外,這一撥“70后”與之前的那些,幾乎沒有任何關(guān)系了。所以最早期“70后”高調(diào)包裝炒作的市場意識,或者后現(xiàn)代語境中的身體寫作之類等等,這里就不準(zhǔn)備作為研究對象了。
那么,“70后”作家的自我意識里面,都包含哪些精神指向呢?以徐則臣、李浩、張楚、弋舟、路內(nèi)等人為代表的這一作家群體,近十年來,帶給我們廣闊而深邃的文學(xué)世界。他們的生命觀照與世界視域,體現(xiàn)在對生活的觀察視角、對人性的深刻把握以及多樣性的藝術(shù)追求之上。整體看,這一代作家是從自我出發(fā),建構(gòu)屬于個人的文學(xué)博物館。有研究者認(rèn)為,“50后”作家寫自己以外的世界,“60后”作家寫自己眼中的世界,“70后”作家寫自己的世界。這么說雖未免失之簡化,多少也有一定道理。正因為這一代人的寫作常常是從自我出發(fā),又回到自我,使得他們既要面對精神禁閉的囚徒困境,又要接受世界范圍的無限敞開,比起前兩代作家,具有更強(qiáng)烈而鮮明的自我意識。這種意識與部分“80后”作家的自我膨脹自我消解,又有所不同。這一代寫作者始終關(guān)注個人生存尊嚴(yán),關(guān)注世界存在的合理性,不斷探索精神世界的邊界。追問世界本質(zhì)的徐則臣,挑戰(zhàn)文學(xué)極限的李浩,專注于精神追問的弋舟,把小縣城灰色人生寫得活色生香的張楚,在青春敘事里不斷強(qiáng)化自我的路內(nèi),偏執(zhí)而又憂傷的阿乙,執(zhí)著于靈魂敘事的鬼金,帶著南方潮濕陰郁氣息的朱山坡,有著飽滿的生活和土地溫度的李駿虎,回歸民間充滿傳統(tǒng)文化憂思的劉玉棟,還有溫潤的魯敏,犀利的喬葉,諳熟大上海小市民文化的滕肖瀾,擅長虛構(gòu)和想像的王秀梅,在精神世界里自由游弋的李燕蓉,等等,他們小說中的精神世界,充滿了時代的、人生的、哲學(xué)的各種疑問,不僅關(guān)注人的現(xiàn)實生存,更關(guān)注人的精神困境及靈魂依托。
朱山坡寫過一篇小說名為《靈魂課》,城市中的高樓大廈,埋葬了多少鄉(xiāng)村年輕人的夢想、生命和靈魂?那些鄉(xiāng)村中遙望孩子的母親,滿頭白發(fā),受盡煎熬。一個靈魂旅館,一只白色氣球,兩個甚至無數(shù)年輕的生命,一個垂垂老矣心無所依的母親,靈魂保管者的視角,無法歸鄉(xiāng)的魂魄,小說在有限的篇幅里拓展出繁復(fù)的精神空間,對現(xiàn)實的反思,對人世的彷徨,對生命的體恤,對靈魂的追問,都充滿敘事的質(zhì)感和彈性。鬼金則寫過《除非靈魂拍手作歌》。作為“70后”寫作者中的一個,鬼金的文學(xué)世界里既有“70后”那個群體的共性,也有屬于他自己的文學(xué)個性。那種自敘傳色彩,不是成長經(jīng)歷的復(fù)制,而是深藏的精神烙印。朱河,一個穿越理想與現(xiàn)實、穿越精神與物質(zhì)、穿越生存與死亡的小人物,一個對生活有疑問的主人公,他有著打破舊世界的渴望,又有著破壞一切的暴力傾向,甚至對親人也會產(chǎn)生殘殺的念頭。灰茫中的暴力,絕望中的反抗,這就是草泥湖的噩夢人生。這些審視生死關(guān)注靈魂的文字,正是“70后”向自己所屬的時代、所經(jīng)歷的生活,以及自己的內(nèi)心發(fā)出質(zhì)疑和追問的表達(dá)。這一代作家中,張楚有他獨一無二的審美品質(zhì)和精神追求。他的寫作容納廣闊,富饒豐沛,體現(xiàn)了深厚的生命意識和對心靈的內(nèi)省,對自我感知到的世界,他懷抱著冷靜的激情。他不僅在無意義的生活鏈條里找到了斷裂的那個最重要的環(huán)節(jié),而且因斷裂而形成的傷害和痛苦,也被他逐一挖掘出來;他不僅關(guān)注存在本體,也關(guān)注存在自身的陰影,在詩意的悲傷里,不斷展開被時代、生活和命運折疊的人性。李云雷評價張楚是一個“黑暗中的舞者”,的確很形象;而另一方面,張楚又是一個“晨光中的歌者”,站在黑白交界處,冷靜描繪他眼中的世界,一半是悲涼,一半是摯熱。相較于一些作家喜歡從外部書寫人的生存狀態(tài),張楚更關(guān)注人的精神境遇,即使是現(xiàn)實批判,也是貼著人的心理和精神困境展開的,他揭示的是精神的深度,尤其是對某種處境中人的精神世界的凝神審視。“70后”作家靈魂關(guān)懷中的主體意識呈現(xiàn),讓我們看到了處于文化一體化及完全市場化中間狀態(tài)的一代人的思考和存在。如果說“50后”作家擅長宏大的社會體系和歷史語系建構(gòu),“60后”作家喜歡文化色調(diào)雜陳的生活場景鋪敘,“70后”作家的哲學(xué)氣質(zhì)則更為突出,他們執(zhí)著于靈魂敘事,反復(fù)探問人的存在意義、存在形態(tài)及存在維度,給出了當(dāng)代小說創(chuàng)作新的話語空間和精神視野。
二、漂泊與尋找
“70后”作家的成長小說與“80后”的青春寫作有所不同。這些成長小說,往往是作家在青春逝去后,回溯那種漫長的成長歷程,記述一代人經(jīng)歷的時代波瀾和精神創(chuàng)痛。對于自身所經(jīng)歷的時代,有著深刻的體認(rèn),尤其是對1980年代的記述,有文化氛圍、政治激情、社會風(fēng)氣、時代精神、日常生活等各種不同視角。那一代年輕人對遠(yuǎn)方的向往,對理想的追求,對文學(xué)的狂熱,與早期“70后”作家純粹個人感官主義寫作,形成了兩種不同的敘事風(fēng)格。“70后”作家的漂泊意識,包含著文化的無根感、生存的碎片化,以及時代的動蕩感。與上一代作家相比,他們的成長空間,具有更多的不確定性,青春時代經(jīng)歷的時代劇變,人到中年的各種焦慮困擾,都不同程度影響著他們對世界的理解,不僅拉長了成長的視線,而且放大了這一主題之下的各種敘事指向。包括追問、疼痛、理解、寬宥、舍棄與堅守、迷惘和尋找。這種漂泊感的形成,一方面是外在世界的變化、時代轉(zhuǎn)型和心理焦慮帶來的不穩(wěn)定感,一方面是這一代人的寫作更具有哲學(xué)維度,往往超越了生存的表象,去探究生命和存在的哲學(xué)依據(jù)。
2013年,“70后”作家有幾部長篇小說引起了普遍關(guān)注。包括徐則臣的《耶路撒冷》、李浩的《鏡子里的父親》、喬葉的《認(rèn)罪書》、路內(nèi)的《天使墜落在哪里》、田耳的《天體懸浮》、柳營的《我之深處》、李鳳群的《顫栗》、弋舟的《蝌蚪》、王秀梅的《藍(lán)先生》、王十月的《米島》等。路內(nèi)、弋舟和喬葉這三部長篇,都有著成長小說的影子,又同時超越了成長敘事的局限,路內(nèi)放大了某個時代側(cè)面,弋舟拉長了生命鏡頭,喬葉寫出了歷史幽暗處的人性裂變。這一代作家,正在緩慢告別成長,開始對歷史和時代發(fā)言,這種表達(dá),嚴(yán)肅尖銳而又真誠。這幾部長篇小說,或多或少都隱含著孤獨,絕望,漂泊,懺悔,救贖等主題。那種內(nèi)在的焦慮感,到底意味著什么?為什么在“70后”作家的意識里,有那么強(qiáng)烈的負(fù)罪感和漂泊感?這種負(fù)罪感來自于對父輩的審視和追問,也來自于自我身份的存疑和焦慮。漂泊感則來自于他們對世界的疏離和對自我的回歸。李浩和徐則臣都寫過《在路上》。徐則臣特別喜歡寫火車。他有一本集子就名為《夜火車》。還有葛亮的《無岸之河》,楊遙的《奔跑在世界之外》,以及李浩和徐則臣寫過的《如歸旅店》。徐則臣最初引起文壇和讀者廣泛關(guān)注的就是他的“京漂”系列。為什么他們在自己的小說中,會不斷地書寫那種在路上和旅途中的漂泊狀態(tài)?對此,徐則臣說:“一個作家最初的寫作可能源于一種補償心理,至少補償是他寫作的重要原因之一。現(xiàn)實里得不到的,你會在虛構(gòu)中張揚和成全自己。……人是無法自證的,也無法自明的,你需要他者的存在才能自我確立;換一副嗓子說話,你才能知道你的聲音究竟是什么樣。出走、逃亡、奔波和在路上,其實是自我尋找的過程。小到個人,大到國族、文化、一個大時代,有比較才有鑒別和發(fā)現(xiàn)。我不敢說往前走一定能找到路,更不敢說走出去就能確立自己的主體性,但動起來起碼是個積極探尋的姿態(tài);停下來不動,那就意味著自我拋棄和自我放棄。”(《我們對自身的疑慮如此兇猛——張艷梅對話徐則臣》,《理論與創(chuàng)作》2014年3期)徐則臣對城鄉(xiāng)文化差異,對漂泊孤獨的生存處境,對這個時代的人心人性,具有敏感的洞察力。他以冷靜的目光,熱誠的情懷,正面呈現(xiàn)社會轉(zhuǎn)型期不同階層的生存處境和心靈境遇。無論寫生命痛感,抑或生存反思,在倫理、文化和情感的各個側(cè)面,徐則臣小說總能給存在以更深刻的理解和關(guān)懷。《小城市》與《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在精神結(jié)構(gòu)上一脈相承,出走,回鄉(xiāng),兩種不同的行為方式,指向的是同一精神視野,即心靈漂泊者的困擾和思考。小說通過不同視角回顧了彭澤年輕時代的選擇和心靈煎熬,又通過夢境和現(xiàn)實的對照,拉長了時空的線索,給出了超越個人的思索和追問。痛苦嘶喊的原野上,燈紅酒綠的夜宴中,彭澤是一個充滿精神焦慮的個體,也是徘徊在兩個世界的所有渴望安寧的心靈的象征。小說提供的不僅僅是生活狀態(tài),也不僅僅是城市與鄉(xiāng)村之間的心靈徘徊和游蕩。在生活背面,有一種關(guān)于愛的永恒追問,在心靈背面,有一種對存在的終極反省。
弋舟的“劉曉東三部曲”《等深》、《而黑夜已至》、《所有路的盡頭》從個人、到時代、到歷史,精神漂泊的履歷,追問和尋找的執(zhí)著,寫出了一代人隱約著懷舊情緒的精神突圍渴求。《懷雨人》以青春回溯的方式,記述了大學(xué)時代的一段獨特經(jīng)歷。與李師江的《中文系》比較,同樣是兩個男孩和一個女孩的故事,同樣有著中文系的影子,同樣隱約著一個成長的主題。如果說《中文系》是氤氳著感傷情調(diào)的抒情詩,《懷雨人》則是蘊含著宗教意味的哲理詩;如果說《中文系》是背對成長的離歌,《懷雨人》則是直面存在的寓言。弋舟把一個關(guān)在自己世界里的人,把一種埋葬在心靈深處的記憶,把一種生命里不斷凋零不斷重生的情感,寫出了神性。李師江的小說與其他的“70后”作家相近,大都以個人眼光和經(jīng)歷反觀時代,即以小敘事及邊緣生存觀照社會小人物的人生遭遇、細(xì)碎的日常生活,無限切近一種黏滯的真實,努力表達(dá)一種個性的聲音,語言風(fēng)格收放自如。《中文系》的敘事依舊飛揚靈動,流暢舒展,那些青春的碎片,悉心撿拾,輕松幽默的口吻,濃淡相宜的筆墨,一切游刃有余,又恰到好處。我們跟隨作者一起蹚過往昔之河,曾經(jīng)的夢想,寂寥的遠(yuǎn)行,孤獨的對抗,心靈的悸動,喜悅和渴求,煩惱和疼痛,都在這一幅成長的長卷中,略帶感傷地緩緩展開。魯敏的短篇小說《謝伯茂之死》微有荒誕的寓言色彩。每個人都是孤島,渴望尋找到連接大陸的狹窄土地,但是漂泊感始終都在。對于李復(fù)來說,尋找是工作的一部分,而這種毫無意義的行為,與他心中的人生價值和生活意義緊密相連,這雙重背反之間的荒誕性,是這篇小說獨特的思想價值之一。對于陳亦新來說,寫信本身也是毫無意義的,只是他的一個游戲,而這種毫無意義的游戲在重復(fù)了多次以后,由形式變成了一種儀式,當(dāng)他發(fā)現(xiàn)另外一個人也加入游戲之后,游戲宣告終止,這其中的背反,同樣是對意義的消解和重新確認(rèn)。在這樣的一個離散的時代,每個人都陷入了意義和無意義的糾纏。因為沒有信仰,也就看不到溝通存在與虛無之橋,注定找不到涉渡之舟。小說結(jié)尾處,陳亦新的嘲諷,李復(fù)的自嘲,算是這個世界給我們的最后一擊。小說給出了當(dāng)代人生活的無聊和無奈狀態(tài)。每個人都在尋找寄托,只是有的人寄托于實存,有些人寄托于虛空。在哲學(xué)意義上,我們今天面對的是一個離心力越來越大的時代,社會生活缺少穩(wěn)定感,確定生存坐標(biāo)變得很難,別人的存在成為一種尺度和鏡像,當(dāng)我們不能夠在現(xiàn)實中找到心靈的依托和有效的溝通,就只能以虛構(gòu)的生活,虛構(gòu)的人物,給自己提供微薄的樂趣。
在生命哲學(xué)建構(gòu)中,漂泊意識隱喻了現(xiàn)代人失鄉(xiāng),找不到歸宿的哲學(xué)母題。近年來,“70后”作家的成長小說還有徐則臣的《水邊書》、劉玉棟的《年日如草》、李云雷的《父親與果園》和《舅舅的花園》、李駿虎的《慶有》等。知識分子精神還鄉(xiāng)始終是新文學(xué)的一大主題。緬懷和批判則是面對故鄉(xiāng)的兩種糾結(jié)的情感立場。《父親與果園》敘事接近回憶性散文,悠悠往事,淡淡憂傷。只是寫到父輩的離去和傷病,寫到果園的今昔對照,有隱隱的凝重和深深的眷戀。小說結(jié)尾與魯迅的再次離鄉(xiāng)不同,穿越時空的自我對視,找到自我,找到最初的、也是最終的家園,在這個混亂而又迅疾的世界中,其實非常艱難。由此可見,李云雷的理想情懷和赤子之心。《慶有》里有溫暖的鄉(xiāng)村成長烙印,和萬物生長的原野風(fēng)情。小說沿著慶有和學(xué)書的成長,慢慢展開蛙聲燈影里的鄉(xiāng)村生活畫卷。春種秋收,那些鄉(xiāng)間的光陰,平常細(xì)碎,歲月的變遷,同樣波瀾不驚。慶有慢慢褪去乖戾頑皮的少年之心,成為一個專心、踏實、能夠自得其樂的莊稼漢,他生機(jī)勃勃,樂在其中,并且顯示出終生擁有這一切的強(qiáng)烈渴望。學(xué)書則對土地上的勞作抵觸而且絕望,渴望通過知識來改變這一切。這兩種對待土地的態(tài)度不僅隱含著個體人生方向的差異(留下來還是走出去),其實也是鄉(xiāng)土中國面對現(xiàn)代化的兩大路徑(鄉(xiāng)土重建還是鄉(xiāng)村改造)。人世更迭,滄海桑田,永遠(yuǎn)不變的是大地的沉默和溫柔。楊遙的《從滹沱河畔出發(fā)》是第一人稱的成長記錄。既有現(xiàn)實的思考,也有人生道路的探索。小說有意呈現(xiàn)了城市和鄉(xiāng)村的差距,理想與現(xiàn)實的矛盾。一些細(xì)節(jié),包括捉魚,野炊,放風(fēng)箏,喝酒,還有樹上的塑料袋遮住了月光,父親生病,母親枯瘦,父親在“我”的手稿上留下了漆黑的指印,等等,都給人以情感的沖擊。生活如流水,唯有青春一去不回頭。
三、反思與重建
其實無論“文革”也好,還是更早的歷史,對于“70后”來說,并沒有親歷者的切膚之痛。不過,這一代人開始思考?xì)v史,給出了他們不同于上兩代寫作者的歷史敘事眼光和立場。徐則臣、李浩、喬葉等人不僅寫出了歷史感和命運感,而且寫出了在場感。還原歷史,反思?xì)v史,追問歷史,漸漸成為近年來這一代作家的寫作自覺。而這種出生和成長的時代烙印,讓“70后”寫作者,成為思想意識和精神世界極為復(fù)雜的一個群體。對于他們來說,青春歲月,是個人意識的張揚,也是時代意識的投射,具有后革命時代的典型特征。這是伴隨著中國社會體制轉(zhuǎn)型而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他們在回溯成長經(jīng)歷的同時,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歷史反思的個人化視角。前面談及的罪感意識,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自覺疏離等,都是這一代人歷史觀的橫截面。對于現(xiàn)實生活,無論是鄉(xiāng)村題材還是都市題材,無論是現(xiàn)代人的生存掙扎還是精神困境,“70后”作家同樣表現(xiàn)出了少有的耐心,站在現(xiàn)實生活的前沿。相對于近現(xiàn)代中國歷史的風(fēng)起云涌,我們今天面對的的確是一個小時代,1980年代之前社會意識是閉合的,之后是敞開的,1990年代之后,社會意識不斷瓦解和裂變,在這種支離破碎的觀念世界和現(xiàn)實世界里,寫作者如何找到自己的思想坐標(biāo),找到那個恒定的精神尺度,的確很困難。人,不僅僅是負(fù)載著社會屬性和道德屬性的群體,還是無所依憑的個人,好的文學(xué),首先是對個人的關(guān)懷和關(guān)注,然后才是對人類和世界的洞見和思考。對現(xiàn)實與夢想、生存與存在的呈現(xiàn),對幽暗意識的探尋,對理想的執(zhí)著,在這一意義上,“70后”作家的寫作,不僅體現(xiàn)了重新闡釋歷史的自信,而且具有重建生活的勇氣。
李浩在這一代作家中,有著無可替代的重要意義。不僅因為他的文學(xué)修養(yǎng)、他的藝術(shù)追求,還因為他自覺的知識分子立場。他對中國社會現(xiàn)實和歷史,都有著清醒認(rèn)識和獨特思考。《鏡子里的父親》是當(dāng)代長篇小說的重要收獲。《鏡子》是塔可夫斯基靈魂熬煎的表達(dá),關(guān)于精神探索,心靈追問,關(guān)于世間因果,以及生命真相,在他的影像世界里,被反復(fù)強(qiáng)化,通過鏡子,呈現(xiàn)出我們的生活困境和局限,把瑣碎的個人世界逐漸擴(kuò)展到更廣闊的歷史視野。《鏡子里的父親》與之可謂異曲同工。這部小說是父親一生的記錄,是父親的生活史和生命史。這種個人簡史,相對于民族家國宏大歷史,只能稱之為小敘事。在有關(guān)父親命題的小敘事中,蘊藏著李浩思考?xì)v史命題的大視野。比起同類題材,這部小說的獨特性在于李浩進(jìn)入歷史的路徑,表現(xiàn)歷史的角度,剖析歷史的策略,雕刻歷史的意圖。小說以自述方式,強(qiáng)化了真實感,在把寫作者帶入文本之中的同時,不斷提示讀者,關(guān)于父親的記憶還有很多變形和虛構(gòu)。而這種變形和虛構(gòu),與多年來我們接受的歷史形態(tài)的扭曲和虛構(gòu),剛好構(gòu)成了彼此的背反。
李浩對歷史的濃厚興趣,以及闡釋歷史和重建歷史的野心,在《鏡子里的父親》中,一覽無余。徐則臣對生活的深刻理解,以及闡釋生活和重建生活的野心,在長篇小說《耶路撒冷》中,同樣清晰可見。《耶路撒冷》寫出了一代人的生命和精神歷程。從花街到北京,漫長的時空里,纏繞交織著各種社會問題,各種生活經(jīng)歷,各種生命體驗,徐則臣以冷靜而熱忱的文字,記錄這一切掙扎、惶惑、尋找和夢想。耶路撒冷,對于秦奶奶,或是初平陽,并沒有本質(zhì)的不同,信仰,始終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最重要的人生問題。小說講述的是初平陽、楊杰、易長安、秦福小的出走與回歸,負(fù)罪與救贖的故事。這幾個人共同經(jīng)歷了花街的童年少年,然后走上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作為一代人的心路歷程和命運走向,小說涉及到的歷史與現(xiàn)實、思想與文化、宗教及信仰等,都值得我們深入思考。葛亮喜歡有根的異鄉(xiāng)人,《朱雀》寫到了“南京大屠殺”、“反右”、“文革”。關(guān)于歷史反思與歷史建構(gòu),葛亮說:“青年人對于歷史,是一個不在場者,所以沒辦法以自己的文字作為見證。但是,這賦予我們一種想像的權(quán)力。就如同我前面所說的,歷史是一種敘述,這種敘述有見仁見智的一面。同時我覺得,對于歷史的個性化的認(rèn)知與態(tài)度,是一個作家內(nèi)心強(qiáng)大的途徑。”(《上海壹周》“葛亮專訪:我城與他城”)《泥人尹》中,尹傳禮經(jīng)歷了三個時代和三次家庭變故,先是舊時代由家業(yè)豐厚的“尹半城”,到父親尹團(tuán)長眾叛親離家道中落,他被托孤到藝人世家朱家,學(xué)會了泥人手藝;二是“文革”時期,革委會主任強(qiáng)暴了他的未婚妻,留下一個殘疾孩子,妻子死后,父子相依為命;三是市場經(jīng)濟(jì)時代,泥人成為熱銷的藝術(shù)品,帶來大筆財富,可惜被兒媳脅迫,尹師傅勞累致死,兒媳最終席卷而去。小說不是按照尹傳禮的人生經(jīng)歷展開敘事的,時空交錯,世間百態(tài),經(jīng)受那么多磨難,這個始終活在舊時代,活在自己的藝術(shù)世界里的人,內(nèi)心有種不為人知的力量。小說結(jié)尾那一箱端端正正的泥塑毛主席像,既是一個時代的反諷,也是一個人命運的巨大回聲。
對于現(xiàn)實生活,“70后”作家表現(xiàn)出了鮮明的反省和批判立場。楊遙的《唐強(qiáng)的仇人》中,主人公唐強(qiáng)是個本分農(nóng)民,他的仇人王二是地方一霸。一弱一強(qiáng)構(gòu)成鮮明對照。小說主要情節(jié)有六:賣豬,理發(fā),挨打,逃亡,報仇,懸賞。那么,除了對生活在底層的小人物的同情以外,這個普通的生活事件是否具有更復(fù)雜的敘事意義呢?小說中寫到被打以后,唐強(qiáng)自我質(zhì)詢“他和豬越來越一樣了。被人趕,被人打”,所以,唐強(qiáng)反抗的不僅是王二,也不僅僅是王二所代表的暴力和壓迫的生活,而是自己的豬一樣的“被生活”的命運。“人”的消失究竟意味著什么呢?“活下去,像畜生一樣活下去!”這是《芙蓉鎮(zhèn)》里秦叔田對胡玉音喊出來的,在那個混亂的時代,一個人要活下去需要多大的勇氣啊。被巨大的苦難淹沒在最底層的人們,以超乎想像的堅韌頑強(qiáng)地生存。可是還有一個問題,索爾仁尼琴認(rèn)為,人是要活下去,但是要有尊嚴(yán)地活下去。那么,究竟是什么把人變成了畜生呢?這個問題才是隱含在這篇小說背后的追問。這就是楊遙選擇的策略。寫底層,寫被侮辱被損害的小人物,即使走投無路,也很少直接控訴,而是以人物的行動作為一種緊張的釋放和回應(yīng),那些弱者的反抗,不是慘痛的結(jié)局,就是自我安慰,并不具有真正的力量,這才是生活的本來面目,我們遭遇的是無從反抗的陰影和暴力,小說的悲劇意識得到了巧妙的滲透和拓展。《春天》延續(xù)了阿乙一貫的風(fēng)格,揭示幽暗的人性空間,表現(xiàn)低處的人生和小人物糾結(jié)的心理世界,調(diào)子略顯陰郁和壓抑。小說結(jié)構(gòu)是用了心的,逆敘事、插敘、正敘交替進(jìn)行。人物正面筆墨不多,卻呈現(xiàn)得飽滿有力,給人幽冷寂寞處開出似錦繁花的驚喜。春天,一個可憐的女孩子,從小父母離婚,沒有關(guān)愛,沒有溫暖,沒有幸福,后來做了小姐,還偷東西,慘遭毒打。最終這個備受生活摧殘、傷害和侮辱的女孩子,在陳慶誘導(dǎo)下,喝了敵敵畏,掉進(jìn)護(hù)城河,雖經(jīng)萬千掙扎,終于悲慘死去。春天的幽閉恐懼癥,陳慶的心理強(qiáng)迫癥,都是一種精神疾病。這個世界很冷漠,即使此刻置身陽春三月,可是那個充滿愛充滿溫情的春天,究竟在哪里呢?阿乙筆墨冷靜,對于這個相干不相干的世界,我們,都是有病的人吧?
“70后”女作家小說寫作大體沿著兩個方向,一是鄉(xiāng)村記憶懷舊與現(xiàn)實社會問題關(guān)注;二是都市情感婚戀與人性深度解析。付秀瑩有著輕盈靈異與凝重冷峻兼具的筆墨,無論是“芳村”,還是都市,付秀瑩的中國故事講述得曲調(diào)悠揚而又豐饒沉靜。她的《愛情到處流傳》、《舊院》、《花好月圓》都頗受好評。《六月半》描繪了初夏的鄉(xiāng)村,一場未來的婚禮的籌備。婚嫁習(xí)俗寫得豐饒且富有生氣,人物心理也是百轉(zhuǎn)千回鮮活細(xì)膩。包工頭的奢華霸道和俊省一家的艱難窘迫;燠熱的天氣和冷酷的命運;瑣碎鋪陳的細(xì)節(jié)和出人意料的結(jié)尾,形成了鮮明對照。小說沒有正面批判,俊省的心事是主線,從期待和憂慮,到默默隱忍和痛徹心扉,既寫出了命運感,又通過一個人的命運寫出了時代的痛感。結(jié)尾兵子的意外死亡是點睛之筆。在猝不及防的震撼中,付秀瑩完成了一個無聲的悲劇。肖勤是近年來頗引人注目的一位女作家。她的基層干部身份令其小說中的中國敘事更接地氣。中篇小說《霜晨月》更加沉重。父愛無聲湮沒在兒子精心呵護(hù)的花墳,那些盛放的花朵里沉睡著生死兩茫茫的隔絕,是寄托了作家復(fù)雜情感的精神隱喻。與其他女作家的文化倫理立場相近,這篇小說仍舊表達(dá)了“唯一的救贖是愛”這一主旨。《暖》對小等內(nèi)心情感的表現(xiàn)相當(dāng)精彩。孤獨,恐懼,對愛的渴盼,入木三分,悲劇結(jié)局的詩意書寫尤見鋒芒。《云上》通過對鄉(xiāng)村日常生活的精微書寫,表達(dá)了作家深切的現(xiàn)實憂患和底層關(guān)懷。肖勤小說有種亮烈的精神追求,又因女性作家特有的細(xì)膩情懷和詩意追求,從而形成了溫婉與鋒利兼容的風(fēng)格。
滕肖瀾擅長寫市井故事,平實老練,追求現(xiàn)場感。《小么事》中那條小街,小狗,顧長榮,街頭巷尾的小人物,都是一樣的處境和命運,生活的漩渦吞沒了沒有反抗能力的“小么事們”。小說把愛情糾葛放在商戰(zhàn)的大背景下,從顧長榮被天花板砸中,到美容店火災(zāi),房產(chǎn)商草菅人命,居戶搬遷,顧怡寧報復(fù),再到最后顧怡寧被天花板砸中,故事獲得了超出敘事所指的自足性,對現(xiàn)實的批判終于消解在情愛糾纏之中。王秀梅是“70后”作家中創(chuàng)作成績斐然的一位女作家。她的小說擅長虛構(gòu),細(xì)膩溫婉,又不失大氣深刻。《去槐花洲》、《再去槐花洲》、《坦克》、《李不易》、《躺椅》等篇,對于城市男女的感情世界,都有著清晰的透視。同為山東女作家常芳的中篇小說《阿根廷牛排》語調(diào)從容、生活感強(qiáng),開頭結(jié)尾回環(huán)照應(yīng),密閉的敘事里有敞開的生命痛感。圍繞歷史學(xué)院院長的競爭,布告欄不斷刷新的小字報,副院長邊明古在妻子的壓力和女友的溫暖之間游蕩。常芳對這個人物命運的安排顯示出了女性作家的某種隱秘的立場,邊明古患癌處于生死臨界,愛與生活的思索沉重而不乏蒼涼,隱約透視出女作家特有的精神線索。盛可以的小說時代氣息鮮明,對于復(fù)雜的生存狀態(tài)與情感危機(jī),筆墨犀利,眼光獨到。短篇小說《白草地》講述的是武仲冬和藍(lán)圖、瑪雅的故事。作家對武仲冬的生存掙扎描述得相當(dāng)高調(diào),而對兩個女子內(nèi)心世界的映照則不動聲色。瑪雅的報復(fù)是毀掉別人的幸福,藍(lán)圖的報復(fù)是毀掉自己的丈夫。在女作家里面,盛可以的文字比較凌厲,常能見他人所未見,思他人所未思。這篇小說對女性命運的關(guān)注依舊銳利,不見血淚卻力透紙背。張惠雯的《群盲》小說場景集中于一個廣場,人來人往,一條被車壓傷的小狗,一個寫小說的年輕人和他的女朋友,一個等著無名女子出賣孩子的女士,一個被不懷好意的老板引誘的女工,一個被脅迫在路邊乞討的殘疾男孩,一個同情傷狗和乞討者的過路女孩,一個遭遇家庭暴力的小女孩……這篇小說采用了全知視角,很像清明上河圖,畫面一點點展開,各色人等紛紛登臺;也近乎電影搖鏡頭慢慢掃過,聚焦點是那個廣場,有瞬間的定格,也有長鏡頭的緩慢推進(jìn),沒有貫穿始終的人物和情節(jié),但是有個內(nèi)在的東西,就像張惠雯自己說的,那就是生活觀察者的視角、心理和潛在傾向,對具體時空中生存狀態(tài)的考察,以及借助襲擊傷狗的孩子、冷漠的路人,還有內(nèi)心不安的年輕男子、他的女朋友、那個夾克女孩,呈現(xiàn)出來的面對弱者的態(tài)度。小說標(biāo)題不乏精英主義的味道,不過看得出年輕的寫作者對待生活的嚴(yán)肅立場。
無論面對歷史,還是現(xiàn)實,“70后”作家的闡釋和建構(gòu)意識都相當(dāng)明確。正如陸憶敏所說:“身臨絕境的不是我,而我與身俱在。”這種在場感的強(qiáng)化,背后是一種歷史和生活的參與意識,不愿意完全邊緣化,也不甘心輕易被生活捕獲。對父輩的審視與自我審視同時發(fā)生,批判意識與救贖意識同樣鮮明,審美超越與道德回歸,來自于自我身份的存疑和焦慮,那種內(nèi)在的自罪和自證,那種基于現(xiàn)實和歷史的自我背負(fù),到底意味著什么?這可能是值得我們?nèi)ニ伎嫉牧硪粋€重要話題。總之,“70后”作家為我們提供了很多新的文學(xué)質(zhì)素,他們對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刻探察,對于歷史和時代的敏銳觀察,對于小說審美藝術(shù)的執(zhí)著追求,都是非常有意義的。這一代作家還有無限未知的成長空間,每個人都正走在漫長的自我超越的路上。
- 上海文學(xué)的其它文章
- 與顧彬談文學(xué)及其他
- 親密
- 光明
- 大運河到底有多長
- 長假
- 有一種人生叫與世隔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