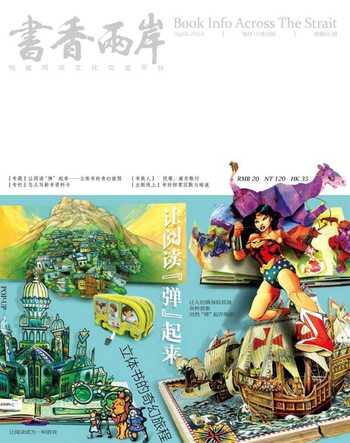祁立峰:我非記錄下這座城市不可
神小風


斯文人。這是祁立峰給我的第一印象,戴著細長眼鏡,身穿筆挺襯衫,走進露天咖啡館里的他態度熱切,一派書生模樣,坐下來的第一句話卻是“我真的不是文青”。否定一件事之前,總該有個定義吧?于是他開始細數“文青”應該要有的標簽:看藝術電影、泡咖啡館、會用單眼、讀文學書籍……說得頭頭是道,令人想起他在書里對于“好人”“犀利”等一些熱門詞匯的剖析,想必他也曾如此分析了自己一番吧。在中文系擔任助理教授的祁立峰,鉆研六朝文學,是頗受期待的年輕學者,但骨子里卻是個地道的“鄉民”,網絡上的許多笑點和時事梗都能朗朗上口。不斷自言“很宅”的他,擅于觀察各種網絡現象,城市的地景變遷,不斷變換的流行文化,他一一透過自身的情感予以記憶、書寫,收進散文集《偏安臺北》里。這是他出版的第一本書,是紀念,也是對過往青春的憑吊。
不文青的一本書
“我沒有那種駱以軍所言的,文藝青年的教養。”談起寫作之始,祁立峰說得坦白,他崇拜紙本,對鉛字印刷自小就有種莫名的迷戀,卻不是那種極早就對文學“開竅”的寫作者,高中時躍躍欲試,想投稿校內的文學獎,卻連初選都沒通過,“事后國文老師還叫我到辦公室,送了我一本類似解釋怎么寫小說的書……”這類聽來有點好笑的經歷,形成了祁立峰書寫的基調。如他不停強調他真的“不文青”這件事,也搞不懂為何自己仍持續創作:“除了寫作之外,我的生活極端的不文青,沒有單眼、不看影展,不會剪齊劉海,電影只看爽片,聽的是什么Popu Lady……”談起自己,祁立峰說得直接:“所以這本書,也不是什么純粹的文青之書啦。”現在大學任教的祁立峰,生活和普通人沒兩樣,原本喜愛的學術工作在繁雜的事物消磨下,難免也變得無趣起來。但研究已經是工作,不得不做;他說人本來就不能把興趣當成職業,“那樣就沒有興趣了。”他選擇將散文、隨筆等文字創作當成個人興趣,是嚴肅學術生活的調劑,卻也為他開辟了一條異于同代人的寫作之路。
他擅以城市固守回憶,讓流行記錄青春。《偏安臺北》里寫了許多臺灣人熟悉的時代記憶,廣告片、歌詞、日劇、跨年煙火,從中森明菜到周杰倫……都是祁立峰成長的腳注,也是歲月的痕跡,文字中難掩感嘆,讀得出作者的多情,但因為敘事者的人稱都是“你”,又隱隱有種與時間面對面的距離感,仿佛對著茫茫人海中,曾一同度過這些歲月的人說話。書中收錄的文章,多是曾發表在報章雜志上的集結,篇幅皆不長,多寫現代生活所見所感,熱門話題或網絡流行語。問他會不會怕這樣的文章無法“恒久遠”?祁立峰說創作對他而言,僅是作為一種標記,一個抒發;無法寫進論文里的想法,就歸于簡短的散文:“況且我也真的就生存在這個新世代,硬要寫些很宏大的東西,只會落入虛構的套路里。”他認為寫作應該從自身出發,不該特別避諱那種輕薄、日常的時代產物,而是將它們容納進作品里,“并且呼應自己所處的當下。”這種姿態,其實也正是祁立峰所謂的“偏安”美學。
偏安臺北城
在學術界里,祁立峰專精六朝文學,對“偏安”這個歷史名詞也有個人的見解。“中國第一個偏安的朝代就是南朝,因為版圖比較小,文人所能看見的世界也比較狹窄,文章里面關注的都是一些瑣碎細物;他們集體寫詠物,詠的都是屏風、蠟燭之類的。而以我們這個島嶼來說,似乎也受限在這個地方。”祁立峰也坦言,這本書所指出的“偏安”觀念,讓很多人聯想到臺灣的情勢,“我覺得確實也不能說沒有。臺灣就是一個狹小的世界觀,我們生于斯長于斯,會有著偏安的美學也是理所當然,例如現在流行的微電影、小清新、小旅行等等,其實是對應到所謂的壯游、史詩片。”祁立峰說:“但‘壯游最初是誰起的頭呢?是少年時的司馬遷,他跟著漢文帝第一次到泰山,受到當時壯麗的風景所感動,覺得整個世界都開闊了。但可能在臺灣,我們不是也不適合走這個模式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跟謝旺霖一樣去‘轉山,寫一本很偉大的書。如我就是比較宅,可能就是去了一個沒去過的、很近的地方,像走到溫州街,就已經算是我的‘轉山了。”祁立峰也強調,“偏安”仍是一種美學,就跟“肚臍眼文學”同樣是這個年代的標志,有種小小的堅持和任性,是屬于新時代的態度,更是一種妥協的藝術。
讀這本散文,不難發現祁立峰投注了相當多的心力在書寫臺北城。即使這座充滿現代感且不斷流動的城市,早已被大多數人熟悉,他仍以自己的方式予以捕捉。臺北對他而言究竟是什么?“是我的青春記憶。”從陌生到熟悉,那樣一來一往的過程,時間在此流逝:“跨年、第一次戀愛、中正紀念堂、新公園;接著是我開始認識西門町、貴陽街,在那和女孩第一次牽手。然后赫哲數學,然后才是東區,還有第一次在信義區跨年,看煙火……”
他的青春,其實也正是這座城市的成長史,“就像評論家王德威說的:時間往往是空間的,而歷史也會成為地理。臺北是我很重要的青春地景,而更重要的是許多時間軸上發生的大事件,可能有點國仇家恨或創傷經驗,但都因為我們用無限青春來看待它,讓它成為另外一種面貌。”祁立峰說:“小歷史批注了大歷史,也記錄了我們曾經存在的意義。”
宅男的逆襲
不知是否因“經驗豐富”,祁立峰在書中對男女關系的描述也頗有趣味。無論苦情或自嘲,都將這時代的網絡戀愛關系寫得相當到位,也因過往遭遇使然,他開玩笑地以網絡用語“仇女”自稱,意指仇視女性。這類“仇女”的男性族群在BBS上相當多,祁立峰自認和這些BBS的“鄉民”有些共通點,也善于在文章里使用這類網絡用語:“但我可能不只是加入鄉民的隊伍里,在陪著他們走了一段之后,也會站到外面來觀察他們的樣態。”談到這,他忽然沒頭沒尾地補了句:“其實這是本怨念之書。”表情認真,看來背后大有一段辛酸往事之勢。其實書中幾篇文章,如果不是全盤虛構,便從那情節里可瞧見端倪:曾被當成呼來喝去的“工具人”使用、追求過程的失敗、共同養了兔子卻無法增進感情、女孩移情別戀等等戀愛血淚史。那么,將這些聽聞的、網絡上看來的、親身接觸的戀愛故事書寫下來,是否也可以說,這是種“宅男的逆襲”呢?
祁立峰稱兩性之間,不善交際的男孩們若想一親芳澤,只得阿腴吹捧、力求表現、漫天胡謅……最終可能還是落得失敗的下場。而他筆下的女孩一貫的古靈精怪、易感善變卻又極具魅力,“利落的金發,白皙的后頸散發淡淡檸檬草香……”這些詞匯太過美好,明知只是資本主義包裝下的陷阱,卻叫人忍不住想和她們演一場偶像劇。祁立峰將那種笨拙的男人心事寫得如此真實,帶點無奈或自嘲,但仍是浪漫的,“到底要怎么樣,才能只憑愛與勇氣──甚至不用拿出護照機票,就可以闖進登機門?”在他心中始終有個單純的男孩,即使明白世界如蔡明亮的電影般孤獨,仍在愛情的世界里一試再試。書中也有一些篇章以“妳”為敘事者,是他的一種嘗試:“希望可以回避主體,甚至扮裝、變裝,享受不是‘自己的自己那種快感。且逃避主體,更可以在文章中調度一些不敢說的經驗,就像變裝派對,在那里人們才敢做自己平時不敢做的事。”這或許也是他揣測女性心理的另一種方式吧。
人是忽然就變老的
“如果說人類平均年齡是七十歲,那么三十五歲這樣的年紀,就像是游泳池畔的轉身時機,不好也不壞,有些疲憊卻也還能再游下去。”對于時間的一種界線,村上春樹的“轉身”隱喻相當精準。跨越青春,緊跟著來到而立之年,書中也不乏這類面對時間的困惑與心境。在《三十自述》里,祁立峰形容那是一條“起跑線”,殘忍、沒得商量地逼近自己:“墜落,退化或衰老,本身并不可怖,惶恐的在于從壯盛到頹圮的轉戾點。”不同于村上春樹,祁立風相當古典地借了唐朝盛世,安祿山被任命平盧兵馬使,風風光光地穿過繁華的市街,大量商隊出入,販賣高級器皿、貴重金屬,那些極講究的瓷器陶俑被人一一賞玩,盛大的豪奢場面卻是敗壞的前奏曲──以后人的角度看來,也只能給出“由盛轉衰”此一成語,來捕捉這美好卻脆如薄翼的“瞬間”了。這是時間毫不留情的巫術,而祁立峰自己呢?已跨越30歲的他,又怎么去面對“由盛轉衰”的時刻來臨?
“我覺得人好像是忽然長大的,忽然就變老了。我上次讀到一篇網絡文章,作者說他大學時期的女友,原本最喜歡穿星星帆布鞋。出社會之后,她跟男生的話題變了,不再是哪個女生很賤或考試很難,換成了日本的客戶、工作的業績之類。下班后,她穿了高跟鞋跟那男生約會,男生發現穿著套裝、坐在小綿羊機車后座的女孩,好像真的長高了,心煩和不安都丟到另一個世界了。”祁立峰說:“但后來男生就發現,女孩跟自己的話題越來越少,她不想出去玩只能坐機車,不想生日收到大眼怪、史迪奇的玩偶;而是想要香奈兒的提包,不再是二十、二十一歲被單純的驚喜而感動的女孩了……”這樣一個隨處可見的故事,卻觸動了祁立峰心底的某個角落,“大概是這個故事里的男孩還在‘偏安的國度,女生卻已經長大了。這件事告訴我們——我們是突然長大的,突然就變老了,所以那一瞬間很難承受,甚至很難察覺。我要怎么應對呢?其實我更希望自己干脆就不要察覺,那樣更好。”
電影《黑客任務》(大陸譯作:《黑客帝國》)里,基諾·利瓦伊(Keanu Reeves)掙開了虛擬的牢籠,選擇吃下藍色藥丸,在一無所有的現實里化身英雄與機器搏斗。但祁立峰的選擇卻截然不同:“我寧可相信一切的虛擬都是真實,選擇在那里面,當個繼續茍延殘喘的角色。”于是我們發現,一直躲在“偏安”國度的男孩或許就是他自己。但即使消極,即使虛假,祁立峰仍是提起筆,“在它如預言般墮壞之前”將這座城市紀錄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