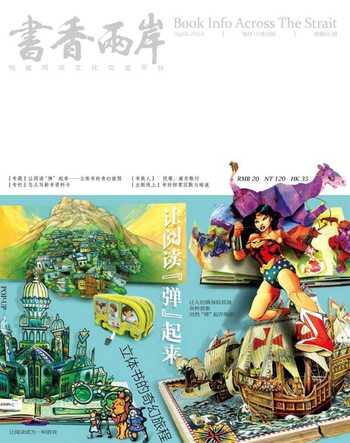城市就是我們的文學經驗
彭礪青
我們經常聽到一句老話說:“語言是我們的居所。”但我們所居住的城市呢﹖它不也構成了我們生活中的語言場景嗎﹖我們每天工作、吃飯、休憩,都涉及我們生活其中的地方,無論它是城市還是鄉鎮,我們都不能脫離,即使這城市天天在變,而在我們成長或衰老過后,往往忘記了它所失去的許多細節,但往往就是失落的記憶片斷,讓我們去追撫昔今,重塑我們的童年記憶。
如果有人認為這番話涉及了文學的意義,那么他應該大概對香港文學多了一重了解。正如陳智德這本《地文志》試圖回溯的記憶,這既是作者的個人成長史,也是涉及城市風物書寫的香港文學史,而作者的詩文在其中穿針引線。全書一開始便以九龍城展開這段文學旅程,以前清遺老流落九龍城、以古體詩吟詠宋王臺故事,展現了香港的離散歷史,其與中國的前朝今世關系,后面一章《旗幟的倒影》所談的國民黨將領居留地調景嶺,也可算是這種前朝的記憶所系之處。
地方記憶有不同性質的層面,有官方色彩的宏大記憶,也有專屬于香港某一代人的記憶,作者寫的大多屬于后者。像七十年代成長并深愛搖滾樂隊的一代青年,對當時作為國際音樂節的半露天場地而建成的高山劇場,就無法忘懷;還有七十年代的維園,是左翼愛國青年學生日后回憶“保釣運動”的重要場景,在鐘玲玲、辛其氏的小說中,讀者仍能找到舉行“保釣”的維園現象。這就有如拆卸的皇后碼頭原址,也活在八零后一代的回憶之中,這種記憶是封閉性的,一旦這代人紛紛謝世,又沒有被記錄下來的話,就因為對下一代人沒有意義而不復存在。
這大概就是文學超越時代,而又局限于時代的特質。一如《包法利夫人》這類作品有專屬于時代的特質,也有永恒的意義,但如果文學作品的意義僅只對活在該時該地的個人有效,那么下一代讀者較難欣賞。或許以后研究香港文學的人會想到這一問題,即使他們仍會欣賞作家筆下的時代特色、地方風物和生活方式。但如果香港文學真有一種超越時代的意義,那么這可能就是以書寫作為抗爭(即使是一種姿態)的堅持,呈現真實民間生活(它不一定是苦或樂)。這是本土的經驗,也是人安居于地上最實在的記憶。根據作者的說法,“本土經驗”是成長以至更大范圍下的共同體社會經驗,它不一定是歌頌,卻讓我們認清我與非我的真幻。也許從事文學創作,就必須選擇接受、肯定或批判自己的在地成長記憶,而那些感動我們的詩歌、小說,都是從時空的局限性萌芽,以至超越它。
《地文志》既是地方志和地方文學史的綜合,也是一部交織著個人成長史的文學作品,這無疑是最吸引讀者的“賣點”。對于讀過陳智德詩集《單聲道》、《低保真》及《市場,去死吧!》,還有《抗世詩話》的讀者來說,《地文志》的文學理念及對地方記憶的眷念都可以一一在上述作品中得到證實,如果這位讀者認同這種“反建制”“反市場”的文學立場,并且認為作者的文學立場確實如此的話。更難能可貴的是,作者以其研究、整理香港文學作品的經驗,將關于同一地區的不同作品加以對比。例如在《我的北角之夜》一章,作者將馬朗的《北角之夜》、也斯的《北角汽車渡海碼頭》和自己的《北角之夜》作對比,從作者的不同背景、時代等因素,映照出地區的時代嬗變、文學風尚的變遷等。這些對比有很多時候是印象式的,但作者以其文學鉤沉的根柢,加上文學刊物編輯的經驗,和對香港一代人的觀察,寫出其他沒在香港成長、沒有從事詩歌創作和香港文學研究的人,所無法寫出來的見解。
這些視角無疑是屬于文人的,它未必能被普羅大眾所理解。在本書上卷《破卻陸沉》中的《黃幡故事探源》一章,讀者固然找得到灣仔平民百姓掙扎求存的身影,但下卷《藝文叢談》卻是全然屬于讀書人的書店緣。作者當中提及的二樓書店,有不少曾活躍于七十年代,然而即使是活躍于八九十年代的書店如青文書屋及后來的東岸書店,也大多逃不過結業的命運。這固然與租金上漲有關,但對于普羅大眾來說,書店亦不過是眾多生意之一,在百事維艱的香港市場里,這種邊緣事業沒有被特別照顧的特權。然而作為一種都市經驗,作者娓娓道來的筆觸的確吸引讀者,對于成長于七八十年代的香港讀者,就更有味道了。再者,如果有一個地方,你可以沿著街道,記起街頭巷尾的店鋪曾經擁有過的歷史,還有你在那里的成長記憶,而且能援引詩文的話,那么這就不只是一個地方,而是孕育你、你所歸屬的世界,就像父母和兒女的關系,它的景觀變遷也反映出你在成長經驗的變化,或者,它塑造了你的精神面貌。這就是香港和陳智德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