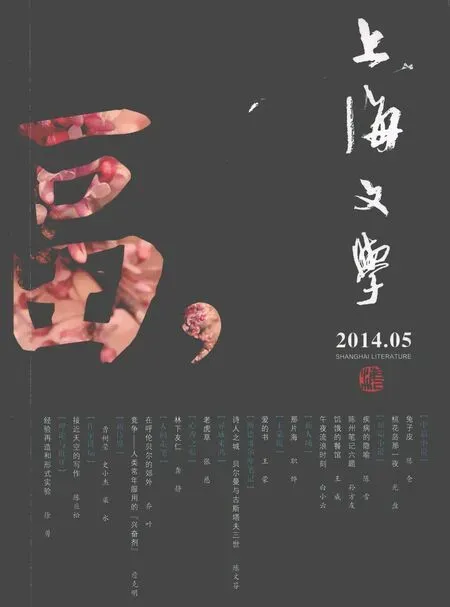詩人之城:貝爾曼與古斯塔夫三世
陳文芬
斯德哥爾摩由七座島嶼相連而成,當你來斯京攬游,你雅好山水,肯定讀過旅游指南,指出東南邊的優戈登是古時瑞典國王狩獵的園林。西邊的王后島是現任國王的住居,宮殿的花園是法國式的花園,島上有18世紀古斯塔夫三世國王(1742—1792)創立的歌劇院,是世界上維持至今最老的歌劇院且長年演出,因為有這“活古跡”,導演伯格曼拍出電影《魔笛》。中國旅客樂意看宮殿花園里的“中國宮”,里頭的擺設中國人看了或許不怎么經心,卻是北歐最早“想像中國”的經典證物。
1753年7月24日,羅薇薩·鄔麗卡王后三十三歲生日,她收到一份大禮:國王悄悄地在王后島夏宮為她建造了一座“中國宮”。王后系出丹麥國王與德國貴族的聯姻家庭,美麗聰慧,對歐洲的知識潮流十分敏銳,對中國文化也很感興趣。國王安排的生日晚宴上,法國的劇團演員穿著中國戲服模仿演出中國古典戲劇。這一天,羅薇薩·鄔麗卡王后主持了皇家人文歷史考古學院(The Royal Academy of Letters History and Antiquities簡稱為皇家人文學院)的成立儀式。受邀與會的五位紳士之一、財政大臣舍費爾(Carl Fredrik Scheffer,1715—1786)剛在巴黎出任公使十年回來,他與法國的重農主義者米拉波侯爵(Marquis de Mirabeau,1715—1789)是好友。米氏認為農業是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而中國在世界上實現了政府重農的理想。舍費爾后來當了王儲的御用教師,他抓住這個機會對王儲施加影響,啟發了古斯塔夫三世國王日后的作為。
我要帶你看老城,那是古代斯京的全部。王宮面對內海,背靠著老城。老城“大廣場”有諾貝爾博物館與瑞典學院,你必得看看環繞瑞典學院的建筑,酒館,餐廳,樓房,教堂。古斯塔夫三世國王建立瑞典學院,跟他同一個時代的吟詩唱人貝爾曼就是在這些洞穴般的酒吧吟唱,以酒館的生活為靈感創作。老城的地景建筑民居皆十分奇特,適宜漫游與晃蕩。這是我說的“詩人之城”。詩人貝爾曼對瑞典語文學的影響等同于莎士比亞之于英語文學的貢獻,他的創作與生活靈感都在老城。
跟瑞典其他大城市烏普撒拉、隆德相比,斯德哥爾摩是座晚生之城。有一則建城傳說:一名漁民不愿將一條珍貴的魚上稅給主教,遂沿著海岸線來到此地。一條魚創造一座城市似不可信,倒像是一則重稅賦國家的歷史隱喻。可靠之說是,古代首都Birka沿海水域岬灣越來越窄,為了登船的便利,轉到斯京附近,漁民沿著海岸居住,工匠、手藝小販就上了岸,住進“老城”。
老城的商業是德國人、芬蘭人引進來的,城市里許多名詞看得出德語的根基。從王宮往老城走,可從瑞典學院背后一小園穿進,到“大教堂”有一座瑞典最偉大的木質金漆繪雕像——圣悅然(瑞典語的“悅然”即英語的“喬治”)屠龍。“大教堂”不很大,與三百步之遙的“德國教堂”相較,大教堂的園庭簡直小得不起眼。大教堂內部造型堂皇可觀,拱頂一層層,木雕金漆裝飾與燈光相稱,圣悅然面貌俊美,舉劍屠龍之際做凝神沉思之態,舉止與神情是一種強烈的對比。北歐的古木雕神像面貌秀氣,容似書生,與維京人海盜的歷史形象對照,天上地下,較之歐土教堂神像,則顯氣宇仙風,樸質無華。
幾年前維多麗亞公主大婚,以手工擦拭金漆修復重現大教堂的金光,大主教證婚,各國王族圍繞而坐,盛典的燈飾與燭光,印證了瑞典歷史上一張重要大畫:古斯塔夫三世于大教堂登基,主教正將王冠舉在國王頂蓋,大堂平整寬闊,光線有如冬末圣誕光始現,金色光芒在遙遠的天邊,余燼的折射足以照見滿朝文武,暈眩的光線與朝臣的絲綢袍子將許多人的神情攬進另一度空間的恍惚。這張畫之所以偉大,是因為畫師來不及畫完,尚在草圖狀態的肖像布局、設色,像是一種從未發生的“印象畫派”,呈現超越時光的現實感。
斯德哥爾摩的歷史必須進一步,退三步,把時序錯落了參差對著看,才能看出歷史的詭奇與宏闊的格局。
遲至17世紀所謂的斯京僅在老城,以后緩慢延伸到南區。海島的群居建筑緊挨著,抵御嚴寒的海風。老城街巷以逼仄著稱,最窄僅有九十三公分,居民人口過度密集,為舉世之最。那時商住一體,底層屯貨,樓上住家,樓窗洞開就是開市的鋪面。律法嚴格,入夜后家畜不可在外游走,豬睡在底層會凍死,跟人同住臥房或廚房最合宜。犯罪的人可受刑責,甚至被街道眾人鞭打致死。醫療條件很差,少數的貴族有醫生看診,百姓只能去藥房抓藥,藥物大約是曬干的蛤蟆之類巫藥。衛生環境惡劣,初生兒童死亡率為歐洲之冠。瑞典經年累月處于戰事,男人多半戰死,苦力工作留給女人,老城的糞肥靠人力挑到南區,地勢原來就高的南區填成更高的巖坡。老城有大量的孤兒,有能力逃出去的少兒冬夜臥靠糞堆,靠糞肥冒出的熱氣度過寒夜,活存下來。老城商人,如擔心肉臭的肉販或者擔憂失火的貨商,逐步往南區移動,南區遂成理想的新住區。
我再把歷史退一步回述。古代戰事頻繁,從海上登岸攻城最迅速,16世紀丹麥國王殺進斯德哥爾摩,在王宮登基,廣邀瑞典貴族餐宴。鴻門宴散席浴血屠殺,數十名貴族在大廣場行刑人頭落地,血流三天三夜。沒過多久,瑞典的瓦薩國王(當時的太子)領兵從陸路堵截反擊丹麥軍隊,趕走丹麥人,成為瑞典建國始王。瓦薩國王要瑞典人民矢志不忘丹麥人屠城的恥辱。瑞典宗教改革于立國之始,削減天主教會房產,采路德教派宗義,治理首都卻容忍德國教堂立于大教堂咫尺之內。德國教堂等同德國國境,象征著斯京的歐土文明,花園曲徑幽深,門口的金飾題字以德語贊頌上帝,教堂內部的光線是嚴峻的深色光影,暗色的木紋講壇,壯觀的管風琴,著名的作曲家巴哈的哥哥有段時日曾在此演奏管風琴。德國教堂也是某種階級的象征,音樂無國境,雅麗動聽的樂聲很容易就飄進老城小鋪商店人家。老城的樓房多為德國商人所建,17世紀以后的樓房樣式堅固結實,門面疏朗巧麗,每種不同年代的建筑物以不同的鐵鑄紋飾為記。
瑞典現在有淳良的飲水質量,古代的水質卻惡劣得幾乎不能飲用,以酒代水,酒不上稅,價格也低廉(這個情況一直維持到1925年,20世紀瑞典的禁酒令極為嚴格,買酒只能在國家體系的酒鋪)。當時的瑞典人從兒童期就喝啤酒,老城的酒館之多,三步五步一家。18世紀的老城,入夜都進入酒神的狀態,街上常有爛醉如泥的行人。此時橫空出世一音樂家——吟唱詩人貝爾曼(Carl Bellman),他是一個十二弦琴的演奏家,他還能以人聲摹仿大提琴、笛子等樂器。他吟唱歌謠的內容假托一個名叫斐德曼(Fredman)的鐘表匠,以“歌詩”與“信件”兩種文體來演唱,還有一個以煙花女子塢拉(Ulla)為名的系列,是他歌詞里的維納斯女神。貝爾曼的音樂風格深受德國音樂文化與名家莫扎特的影響,用現有的德國歌謠創作瑞典語的歌詩,更精確地說,他是一個詞人,用歌詞敘述有形的故事,二三百年來還為瑞典最有名的聲樂家跟歌手傳唱不斷。
貝爾曼(1740-1795)生在南區,在私塾讀書,他的老師教他音樂,也是他爸爸的老師,爸爸在王宮當秘書。論身世,他出身不凡,祖母與母親都是貴族。1757年貝爾曼寫了一些圣經式的歌謠,也當了翻譯(可能是德語翻譯)。以后他謀得一個稅務員的閑差,1760年代他開始受邀在宴會上演唱。游走一些高尚人家的俱樂部以后,他自己創辦了一個“酒神俱樂部”,只要是在街上酒醉臥倒兩次以上的人都能當會員,看來是很挖苦當時高尚人士的俱樂部。1770年春天起,貝爾曼發表以“斐德曼”鐘表匠寫給酒鬼朋友的信件為形式的歌詞體。貝爾曼的歌謠幽默感很強,敘事力量深刻,常能引發強烈的感染情緒,詩歌里頭最重要的人物是酒鬼跟酒友,妓女在詩歌里化身為神祇。他也是斯京最好的山水詩人,常常描寫到哈咖或優戈登的園林野餐看四季景物之變化。
古斯塔夫三世國王1771年登基,他是一位戲劇家,英挺俊秀,風度翩翩,在文治武略上確實與他心儀的中國乾隆皇帝有些相像。他擁有瓦薩王朝的血統,有強烈的愛國情懷。登基以前他訪問巴黎,感受到啟蒙思潮的影響。古斯塔夫三世對啟蒙思潮感興趣,可是他非常害怕革命,他后來將推崇中國作為一種政治工具──因為中國有一位仁慈而智慧的國王,這是一些耶穌會傳教士與探險家傳遞回來的消息所聚合出來的形象,他藉此來抑制貴族們的政治勢力。
瑞典國會保守派與激進派的爭執由來已久,當國王登基以瑞典語演說時,瑞典國會已有一個世紀之久沒有人在國會以母語演說,國會成員的貴族勢力有的親近于俄國,也有芬蘭貴族的力量。國王決定自己發動一次革命,1772年夏末的一個夜晚,國王騎上御馬巡城,左手臂扎上白手帕,沿途熱烈擁戴他的官員都在手臂扎上白布,宣誓效忠國王。國王進城受到群眾擁戴。此時,貝爾曼寫了一首歌《為古斯塔夫干一杯》在城里的酒館傳唱,感染鼓舞首都人民擁護國王的感情跟力量。以后樞密院首長遭到逮捕,這次不流血的和平革命訂立了新憲法,撤除了對國王的種種限制,史稱“自由時代”由此展開。
詩人貝爾曼支持國王,以后國王也支持他,兩人惺惺相惜。1775年貝爾曼從稅務員的閑差退休,得到一百銀元。次年,他出任彩券秘書,一年一千銀元,收入頗豐,以后一度又做了王宮秘書。貝爾曼一直有經濟上的困難,后來有一段時間他逃到挪威躲避債務,國王出面幫助,才回到斯京。1777年貝爾曼終于有足夠的財力結婚,住在王后街,婚姻是否美滿不甚清楚,妻子一直不大滿意丈夫是個酒鬼。1780年起他發表宗教性的詩歌,為寫作而寫作。
政權穩固以后,古斯塔夫三世積極考慮人文與藝術、學術各方面未來的發展,母親羅薇薩·鄔麗卡王后創立的皇家人文考古學院停滯了好長的時間,需要重新整頓。1786年的4月5日,古斯塔夫三世國王同時創建了“瑞典學院”、“皇家科學院”與“皇家人文歷史考古學院”三個學院,其中兩個學院冠有“皇家”的名稱,各自在科學與歷史哲學領域,開學術研究風氣之先。唯獨“瑞典學院”的建制名義上還要高于皇家,故刻意去掉了皇家之名,院士的座席僅十八席,瑞典重要的詩人作家與戲劇家、語言學者同列院士,共同維護瑞典語與瑞典文學的純凈,瑞典學院院士也必定是瑞典人。
瑞典史家認為,古斯塔夫三世固然是深受法國文化影響而有了創建三大學院之舉,他建制瑞典學院的思維更顯見他是一個強烈的愛國主義者,才會認為瑞典學院要超越皇家之上。國王自己設計了瑞典學院每年12月20日舉辦年會的典禮儀式,這個儀式沿用了二百多年,是每年冬天圣誕節以前瑞典最重要的文化活動。古斯塔夫三世讓瑞典學院的運作完全獨立,他以立法的法源賜給瑞典學院擁有內政與郵政公報的權力,這是一份歐洲最古老的報紙,當國家有新的法案成立時,必須在此報刊登廣告,收入屬于瑞典學院,用來編輯《瑞典語字典》這套龐大的語言數據庫,它至今一直在進行收錄瑞典語言的工作。
古斯塔夫三世用了很多心力保證瑞典學院的產權穩固,確立瑞典學院的院士是一種榮譽職,在制度設計上力求周全。十八名院士是終身制,每一位院士有編號座椅,彼此開會時必須尊稱對方的姓氏,不能直呼其名,十分注重禮儀。合宜的榮譽也宜低調,比如收到瑞典學院的郵件,收信人寫的是“十八人之一馬悅然先生”。院士的職責是每星期四開會,每次領一枚銀元,換成一百元克朗,約等于同值港幣,需繳稅。盡管事事嚴謹,古斯塔夫三世在設計制度時也留下一點宮廷的趣味痕跡,比如,他規定,瑞典國王可以出席瑞典學院的院士會議(其實他沒參加過),外國的國王不得參加院士會議,外國國王的兒女可以出席(那些國王的兒女也沒來過)。
至于皇家人文學院的院士也是終身制,分為兩組,一組歷史與考古,一組思想與語文哲學,每組二十五人,每組院士每當有一名年滿六十五歲時,就可再推薦一名新院士加入,如此逐漸擴增。2010年以后約有一百三十名國內院士,外籍院士有四十一名。院士是榮譽職,不支薪。每月頭一周的星期二開會,院士可以自由決定去不去開會。皇家人文學院著重的是人文研究,瑞典學院則貴在創新與語言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法國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1694—1787)當年獲皇家人文學院選為外國院士。伏爾泰對瑞典歷史是有貢獻的,他欽佩與俄皇彼得大帝打仗的瑞王卡爾十二世,著有《卡爾十二世》傳記(1682—1718在位)。
皇家人文學院的第一位外籍中國院士是馮至(1905—1993),1980年選進學院。馮至的推薦者是馬悅然,通過院士們投票選進。1979年4月,馬悅然擔任總編輯編選歐洲漢學協會《1900—1949的中國文學指南》,曾拜訪馮至。馮至指出一個為人所遺忘的事實,即韋叢蕪1927年的詩作《君山》,共一百四十頁的長詩,可能是中國現代文學里最長的情詩。馬悅然欽佩馮至的文學見解與研究,1980年馮至夫婦受邀來到斯京,在學院做了一場德國詩人里爾克的專題演講。
讓我們回到貝爾曼的故事來。1790年貝爾曼發表了鐘表匠“斐德曼”篇章的新作,著名的詩人、瑞典學院的常務秘書Kellgren把貝爾曼的新作捧得很高,這對貝爾曼應該有很大的幫助。在此之前,Kellgren一直不甚欣賞貝爾曼作品里頭太多酒鬼的敘事腔調,這一年Kellgren改變了看法,支持貝爾曼。可惜的是,貝爾曼的經濟狀況越來越糟,常常搬家,越搬越差,1792年他搬到國王島的住處,鄰居就是在化妝舞會上開槍暗殺古斯塔夫三世國王的安卡斯特倫,一個沒落貴族。3月16日,國王在皇家歌劇院舉辦化妝舞會,當日國王跟朋友晚餐時已收到威脅信,國王以前也收過類似的信,故而不加理會。國王走進舞會,雖然戴了面具,安卡斯特倫跟他的同黨從佩戴的勛章認出了國王,遂以法語說,“晚安!俊美的面具客。”從左后方開槍擊中國王。國王也以法語呼喊救援,“我中槍了快救援!抓住那個人!”國王中槍以后還活著,仍然治理國事,直到3月29日因傷口發炎而駕崩。古斯塔夫三世所害怕的革命終究沒有發生,開槍者是一名對他不滿的貴族。他所留下的深遠影響,是瑞典在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之外,保有一種古典文化世界的終極理想。要是世上真有所謂“瑞典文化”模式,他的貢獻最值得書寫。
1793年貝爾曼獲選為皇家音樂學院院士,他的音樂才華終于得入學院的大雅之堂。比古斯塔夫三世國王中槍駕崩更加戲劇性的發展是,貝爾曼第二年因為債務被捕,關進設在王宮底下的監牢,這只能怨嘆支持他的守護天使古斯塔夫三世上了天堂,自此無人呵護。以后有朋友來幫助他還債,總算出了監牢,獲得自由。這段牢獄生活使他原來就不大好的健康情況更壞,貝爾曼過世時年僅五十五歲。他的遭遇應和了他自己傳唱與命運和死亡主題有關的歌:“你干你的杯子。/看,死亡等著你!/稍微開門看看,關起來,也許過些時候回來。”
當我還不能意會貝爾曼歌謠里頭的詩意時,馬悅然說他的歌謠的涵義和意境要跟中國的古典詩人相比,反而容易理解些,比如辛棄疾“杯汝來前”那種幽默自況吟歌豪邁流露的情感,或者如李白的揮灑,以及陶淵明的田園抒情,這些詩人氣質都跟貝爾曼是比較接近的。貝爾曼死時凄涼,埋在窮人的墓園克拉拉教堂。1840年有人重整墳冢,在北邊的墓園下葬,1851年瑞典學院在克拉拉教堂的原墓地替貝爾曼立碑,紀念這名永遠的詩人。
貝爾曼對瑞典文學的影響如此深遠,日后他的文學地位越來越重要。在往后的一百年,老城的酒館一直有個“貝爾曼詩人會社”流傳著貝爾曼的歌謠,人們稱呼他為“國家詩人”,卻未及時選入瑞典學院,成為十八人之一,可說是滿遺憾的。貝爾曼吟唱詩人酒鬼的形象太深刻了,在那個時代也許難于登上高雅之堂,卻給瑞典后世留下最好的歷史敘事,得知老城酒館與庶民的生活。若是沒有貝爾曼的歌聲,老城現存16到18世紀那些傲人的古老建筑、民居群落式的島嶼,就漏失了很大的趣味與審美情感。
跟貝爾曼一起永垂不朽的是老城留下最古老的酒館“黃金和平”酒吧,后來由富裕的畫家安德斯·左恩(Anders Zorn)買下產權捐贈給瑞典學院,成為學院的財產,也是老城著名的高級餐館。現在學院院士每周四開院會以后,步行到“黃金和平”餐館聚會,就在貝爾曼演奏的房間吃晚飯,房間里供置著一架據說是貝爾曼彈奏過的十二弦琴。
冥冥之中,貝爾曼終于跟古斯塔夫三世國王遺留的功勛有了一線之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