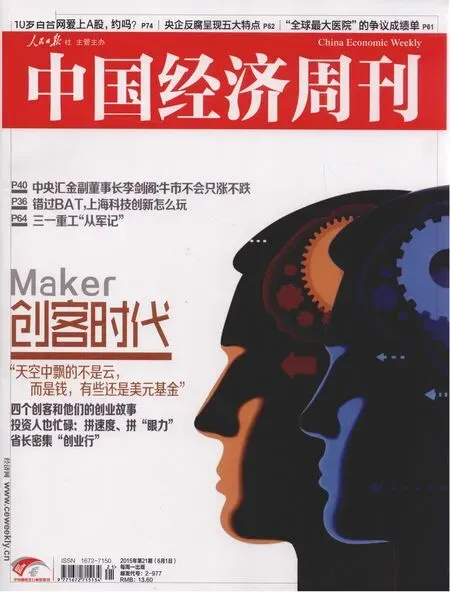修訂我國 《國家安全法》,把軍事、外交、情報統籌為“一盤棋”
趙宏瑞
5月6日,由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編寫的《中國國家安全研究報告(2014)》在京發布,其中明確提出“我國需要一部名副其實的《國家安全法》 ”。同時有消息稱,美國總統奧巴馬近期要發布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我國亦已將修訂《國家安全法》的工作納入了高層視野。因此,抓緊預研我國“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理論內髓,前瞻評述我國在《國家安全法》修訂工作中應當堅持什么、借鑒什么、改進什么,這對于強化我國全球局勢的應對機制,預設預調相應的政經決策,就顯得尤為必要。
美國首部《國家安全法》制定于1947年。二戰以后,美國政府反思了戰時指揮混亂、安全體制錯位、戰后對外安全事務激增等事實,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及時創立該法,整合了美軍、外交、情報三大部類,構成所謂“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劃”一道,開啟了“冷戰”,開創了意圖增強美國世界領導力的美式“國安”時代。而我國于1993年制定的同名《國家安全法》,僅是旨在國務院內部并列設置國家安全部和公安部,在本質上并不能有機地整合軍事、外交、情報三大國家資源于一統。
國家安全,事關公民權利和社會發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確立了“穩定、發展”兩大政治訴求,緊緊地依賴國際安全環境賦予我們的戰略機遇期。1981年中共中央決定恢復“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2000年又組建“中央國家安全領導小組”,該兩“小組”合署辦公,兩塊牌子、一套機構。在對外安全戰略上,該兩“小組”緊緊盯住美國“無暇東顧”所帶來的戰略機遇;其對內功能,旨在“維穩”。
世易時移,伴隨著深刻發酵的國際金融危機,美國安全戰略調整為“重返亞太”、我國經濟總量崛起至“坐二望一”。黨的十八大又重新評估國際戰略環境,決定設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下稱“國安委”)。時至2014年4月,以國安委第一次會議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標志,對內推進“國家安全立法”,對外伴以“溫和醒獅論”,從而開啟了我國的新“國安”立法時代。當然,此前的“穩定、發展”兩大訴求,在政治上已讓位于“安全、崛起”的國家治理模式;修訂《國家安全法》的工作,已成重中之重。
“和諧世界”理論,應是獨具中國特色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宗旨
安全是最基本的國民需求;國家的“安全、崛起”,需要在戰略上知己知彼。修訂我國《國家安全法》,應當首先審視自詡“世界領導者”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需要找準我國的國家利益定位。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0年5月27日發布《國家安全戰略》時,在字里行間闡釋出了美國“武力三段論”,即維護美軍優勢、追求全球領導地位、增進美國國家利益,此三者在理論上具有內在的美式邏輯;當然,該文中還混雜著諸如普世權利、民主自由等美式價值觀。中國在政策上從未宣稱過謀求全球領導、軍事優勢、增進利益,所以,中國的“總體國家安全觀”,無法復制美式“武力三段論”。
我國總體安全應當堅持什么?如何確立我國“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總基調,是當前修訂我國《國家安全法》的政治前提。在經濟全球化發生以前的時代,印度總理尼赫魯(Nehru)曾推行不結盟運動(Non-Alignment)、曾提出“五項準則”(Panch-sheela),這也曾是中國贊賞的國家安全行為準則。但自經濟全球化、特別是新世紀以來,中國對內提出“和諧社會”方略、對外提出“和諧世界”理念,這已經超出了且不限于“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等非全球化時代的國際行為規范。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經濟全球化新時期,中國的國家安全實踐,囊括了諸如“非戰”協商國際爭端、反對任意使用武力、不主動使用核武器、擱置爭議、“政冷經熱”、“不挑事、也不怕事”等諸多對外政策和安全戰略元素。概括這些軍政外交現象,可以發現中國確實沒有追求美式的世界領導地位、軍事霸權、全球爭利。所以,“和諧世界”理論,便是中國區別于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獨具中國特色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宗旨;“和諧世界”理念,便是修訂我國《國家安全法》時所應當堅持的理論內涵。
借鑒美國,
把軍事、外交、情報統籌成“一盤棋”
借鑒先進,修訂我國《國家安全法》,就需要把軍事、外交、情報統籌成為“一盤棋”,這確實是客觀存在的急迫需求。我國軍事與外交部門奉行的具體政策偶有脫節,我國的情報系統雜陳于多個機構之中、因而難以統籌;外界看中國,例如美國就認定中國“戰略不確定、軍事不透明、外交不負責”。反觀我國學術界,掃描當前中文學術資源,就會發現鮮有能把軍事、外交、情報三大部門統籌起來進行研究的學術成果。雖然可以說中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并不謀求領導世界,但研究借鑒美國領導世界的 “一盤棋理論”(A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 研究借鑒美國“增強國家能力”(Strengthening National Capacity)的“國安”立法,研究借鑒美國統籌其國內外安全與防護平衡的結構性設置,從而將我國的軍事、外交、情報三大體系都協調地納入“一盤棋”統籌立法,這就是借鑒先進經驗、改進我國“國安”立法的良好學理視角和研究選擇。
應設立國家情報局
改進舊識,就會發現我國《國家安全法》的諸多過時之處。例如,實體部門層級過低,國安部并列于國務院內部的公安部,這就無法真正地統籌軍事和外交;又如,對情報統籌的重視不夠,重復地強調適用《刑法》罰則、粗糙地兼用公安系統的偵查拘留預審逮捕等公安職權;再如,籠統強調“一切義務”,空談一切國家機關、武裝力量、社會團體、組織個人的“國安”義務和保密義務,這其實與《憲法》和《保密法》等構成立法重合;其強制措施的立法設定也簡單粗陋。因此,要革除這些老舊條款,就需要改進立法的根本之處,就必須在立法上明確提升當前國家安全的統籌級別,擯棄原有國務院部門法的立法層級,將傳統的對內安保立法,上升為能夠統籌我國軍事、外交、情報三大體系的“大安全觀”立法。具體而言,應確立我國國家元首的安全統籌授權、撤銷或改造原有的國家安全部、進而設立國家情報局,以求強調情報統籌的先導作用與決策價值,強調國內外“反恐”行動的軍政聯動;這些條目,都應當是修訂我國《國家安全法》的立法關注點與目標改進點。
總之,堅持“和諧世界”宗旨,借鑒“一盤棋”統籌,改進我國情報統籌的決策價值,以實現我國軍事、外交、情報三大體系的相互協作,進而組成有法律支撐的“大安全格局”,這些都是我國步入新“國安”時代所需增強政府治理能力的立法要義,都是我國《國家安全法》修訂工作中應予重視的學理探究。其中,尤其需要強化構筑“和諧世界”理論,它不同于美國“武力三段論”所脫胎的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等西方國際關系傳統理論,因它擁有著中國五千年豐富的安全實踐與和平思想的歷史淵源,在理論立足點上絕不能妄自菲薄。當然,中國進入了新“國安”時代,同樣需要平衡和保障公民權利,以求切實地實現“以國安促發展”的長遠國策。
(作者系哈爾濱工業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中國民主同盟中央經濟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