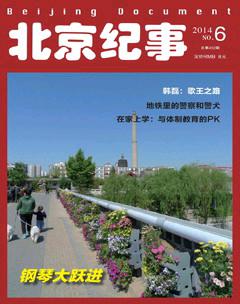鋼琴大躍進
馬多思



在北京南六環的亦莊開發區,住在這里一套大房子里的鋼琴天才沈文裕,被粗暴的父母管教得失去自我的故事被多家媒體報道,成為中國不少音樂愛好者津津樂道的談資。為了讓沈文裕早些回國賺錢,沈的父親甚至以死相逼,讓他放棄了繼續向德國鋼琴教育家凱沫林學習的機會。沈在中國目前不是十分成功,與沈同時代的郎朗與李云迪都已經身價千萬甚至上億元,而沈文裕的一場演出出場費還不到前兩位鋼琴家的一個零頭。
距離沈文裕80公里的北京北部最大的社區天通苑,6歲的北京小姑娘夢涵停掉了已經學習了三個月的提琴課,被母親金女士送到一所私立雙語小學去學習。夢涵很高興,因為她根本不喜歡難學的小提琴。但是她不清楚的是這所雙語小學有一門必修課——鋼琴演奏。金女士說,現在北京好一些的私立學校幾乎都設置了鋼琴和小提琴課,公立學校開設這門課程的也不少,“如果學校不開鋼琴課,就很難吸引到生源。”
就在夢涵開始改學鋼琴后三個月的2014年1月,北京上萬家長帶著孩子爭搶北京市少年宮5700多個培訓名額,其中主要課程是藝術課,包括鋼琴培訓。最終所有名額在下午4點被搶光,預計4天的報名時間變成了一天。為了能搶到一個名額,有些家長排了一夜的隊。少年宮鋼琴老師的技術保障和只是私人授課三分之一的價格,無疑對工薪族家長有著巨大吸引力。
面對中國的古典音樂熱和西方古典音樂逐步走向低谷的現狀,“中國據說有3000萬到1億的兒童在學習鋼琴、小提琴或者是兩者”,“古典音樂正在蓬勃發展”以及“古典音樂的未來在中國”這樣的說法,早已在中外媒體間廣泛傳播,西方的古典音樂從業者們也把希望寄托在了中國。
中國到底有多少琴童?從事鋼琴教學幾十年的中國著名鋼琴家劉詩昆本人也難以估計,“鋪天蓋地,根本沒法統計。誰要說出一個確切的數字,那肯定是在胡說。”
出生于1939年的劉詩昆,曾在“第一屆柴可夫斯基國際鋼琴比賽”中獲亞軍。在中國鋼琴熱還沒有興起,鋼琴只是資產階級的玩意兒的時候,中國三代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江澤民等,就專門聆聽過他的演奏,并分別不只一次同他長談。改革開放后,劉詩昆曾在許多“偏遠得都沒聽說過名字的城市”舉辦演奏會。他驚奇地發現,中小城市對鋼琴的熱情比北京、上海有過之而無不及。當他坐在簡陋得需要話筒擴音的場子里演奏時,“臺下全擠爆了”,周圍黑壓壓站著的盡是帶著孩子的家長。
興起
“中國千萬琴童學琴,已經成了全球關注的現象。當西方的孩子們在無憂無慮地玩耍時,我們的孩子在鋼琴前埋頭苦練;當國外的孩子們夢想著成為足球明星、政壇名人、法律高手時,我們的孩子在憧憬著鮮花和掌聲簇擁的舞臺生涯。我誠心呼吁,請各位不要在逐夢路上迷失;請家長們在完成硬指標的同時,別忘了關注孩子們內心的幸福含量。”肖荻把這種現象比喻為“鋼琴大躍進”。肖荻是旅英女鋼琴家,她在自己不久前為英國著名報紙《金融時報》寫的《鋼琴大躍進》的文章中不無擔憂地說到。
但是,肖荻自己可能都沒有意識到的是,她本人就是一名在鋼琴熱中脫穎而出的佼佼者之一。肖荻,廣州人,生于音樂家庭。4歲始習琴,兩年后在廣東省珠江杯少兒鋼琴比賽中獲獎;1992年至1998年就讀于星海音樂學院附中;1998年肖荻以全省最高分考入中央音樂學院鋼琴系,2002年以全院專業及學術最高分考取中央音樂學院鋼琴系研究生;2005年,肖荻到英國留學并獲得博士學位。如果沒有開始于上世紀80年代的鋼琴熱,肖荻很可能至今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人。比肖荻更著名的是18歲就獲得波蘭肖邦鋼琴大賽金獎的李云迪和如今紅遍全球的鋼琴家郎朗,他們倆無疑是中國鋼琴熱催熟的兩顆最大最成功的果子。緊隨他們的是劉颯和王羽佳。有著鋼琴家夢想的琴童和他們的家長,為了能一睹這些明星的演奏,不惜花費幾百甚至上千元人民幣買一張票,而這個價格是中國普通人月收入的四分之一。
據上海音樂學院的資料記載,上世紀80年代,隨著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帶來的文化生活的需求, 出現了家庭購置樂器的社會現象,掀起了一陣鋼琴熱、小提琴熱、電子琴熱等,家長們不怕勞累地通宵排隊購買鋼琴、小提琴、電子琴等樂器。1985年, 為了與國家形勢相適應, 提倡不僅要發展經濟, 也要發展文化。教育部下了一個文件,提出高等院校的大門應該向社會敞開, 向社會輻射。于是,社會上的音樂教育培訓開始廣泛出現。當時公開在報刊披露的抽樣統計數字顯示, 僅上海市區就有鋼琴、電子琴和手風琴琴童十萬;1987年,上海和廣州率先出現鋼琴考級。
目的
難道中國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為鋼琴家或者音樂家?中國的家長們一切都是從實際出發。有用的東西就信,沒用的就不信。面對鋼琴和音樂,中國人最看重的并不是音樂,而是考大學,只有書讀得好,才能有望當公務員和出國,如果學習鋼琴能有利于高考,那么必然成為熱潮。
從90年代中期開始, 中國部分地區出現土政策——中考和高考可以根據考生高級別的鋼琴考級證書予以不同程度的加分, 最高可以加50分,還有個別的高校開始招收藝術特長生,加分和藝術特長生無疑給已經開始的鋼琴熱又添了兩把火,鋼琴考級熱也自然迅速升溫。1998年,鋼琴熱重點地區的北京,考級考生人數超過7萬人次;到2000年,北京考生人數已超過10萬人次。上海后來居上。據上海市音協統計,從1988年8月至2007年8月,參加上海鋼琴考級的總人數已超過25萬人次。發展至今,中國每年參加各類音樂考級的琴童已號稱“百萬大軍”,規模龐大而壯觀。
鋼琴熱還帶來了鋼琴培訓、鋼琴學習教科書和鋼琴制造業的發展。2001年中國已成為世界頭號鋼琴生產與消費大國。全國鋼琴生產量為26.5萬臺,國內市場鋼琴銷售量達到22.5萬臺,均居世界第一。珠江鋼琴廠成為世界第一大鋼琴廠。
這其中的弊端不言而喻。2002年開始,文化部規定:藝術考級不得與升學掛鉤。2007年,教育部出臺的《關于加強和改進中小學藝術教育活動的意見》中再次聲明,“各類社會藝術水平考級的等級不得作為學生升學、獎勵的依據。”自此考級與升學的關系終于結束,“現在讓孩子學鋼琴的家長還是很多,但是不如以前那么多,畢竟和升學無關了。”上海城市交響樂團團長曹小夏說,但是鋼琴熱的冷卻過程卻仍然漫長。
在北京東直門一家名為蘇菲的畫室,五六個孩子正在認真地畫著石膏像,他們其中有人也即將參加美術考級。一家餐廳的老板潘東來畫室接自己的女兒回家,他說:“我女兒也曾經練鋼琴,學了三年,孩子自己實在對鋼琴不感興趣,死活不彈了。我并不想讓她成為鋼琴家,但是看到別人都在讓孩子練琴,我怕她將來吃虧。”
爭議
在西方,當古典鋼琴擁躉們的頭發開始越來越白的時候,中國學童大軍的進入無疑令人激動萬分。為了讓孩子得到藝術熏陶,每到周末,一些家長帶著孩子去欣賞音樂會,在世界各地觀眾人數都在下降的古典音樂會在中國逆向而動。但是,爭議也隨之出現。不僅是肖荻這樣旅居國外的音樂家,中國國內的音樂家也開始對由考級熱帶來的鋼琴熱產生了質疑。他們覺得目前的鋼琴考級只是考幾首曲子,這樣就限制了孩子去廣泛地涉足各種曲目,影響對鋼琴更全面地學習。過分的功利心理還使得中國的家長只看重技術的訓練而不重視樂感的培養。
“在歐洲,除非有特殊的才能,老師一般不建議七歲以下的孩子學習樂器。相反,他們認為孩子要在游玩中開發創造力和想象力。鋼琴在西方并沒有在中國國內吹捧的種種奇效,跟學畫畫、踢足球一樣,學鋼琴只是興趣愛好的一種。”肖荻說,“我自己也是從4歲開始學的琴,最后能走上職業音樂家的道路并一直堅持走下去,是因為我在演奏、學習中不斷發現新的樂趣,所以一天不練琴都覺得難受。別人看我每天練五六個小時,覺得太辛苦,卻不知我其實樂在其中。所以我并不是說練琴不好,練習很重要,尤其對想搞專業的孩子們來說更是必要的。我不主張的是強迫性的、毫無趣味的長時間練習,尤其是孩子骨骼還在發育成長的過程中,超強度的練習很容易影響、甚至傷害他們的身體健康。”
早在2007年,德國著名的鋼琴教育家凱沫林對《深圳晚報》記者說:“在歐洲,一般是根據不同曲目來判斷能力。學校每隔幾個月會開一種觀摩會,檢驗學生到達一個什么水平,老師會告訴家長,學生存在什么毛病。根本沒有什么考級的制度。當學生達到一定程度,可以考專業音樂學院深造。對一個孩子來說,彈琴是需要持之以恒的,不是會彈幾首曲子,通過一個考級就行了。”
也有人認為肖荻的擔憂有些夸張。14歲就通過了鋼琴十級考試,現在在一家出版社擔任編輯的王甜甜認為,她自己就是考級熱帶動的鋼琴熱造就的一名普通音樂愛好者:“如果沒有考級熱和鋼琴熱,我可能會去推鉛球,立志參加奧運會了,因為我那時很胖。可是家長安排我學了鋼琴,雖然最好的學習方法可能應該從趣味出發,但是考級熱讓很多的孩子練上了鋼琴,練比不練還是強。雖然小時候我也因為練琴挨揍,可是現在我為我比一般人高很多的音樂修養感到自豪。”
現在有更多的鋼琴教育者在盡量減少考級帶來的負面影響。畢業于中央音樂學院的鋼琴碩士李玥,是中國交響樂團年輕有為的鋼琴家,業余時間她也教一些孩子鋼琴演奏。中國的鋼琴熱使得李玥這種級別的鋼琴老師,每課時45分鐘的收費大約能達到500元人民幣以上。“我讓我的學生從鋼琴六級開始考,不參加前五個級別的考試,這樣就避免過早地只練習考級的有限曲目,可以多接觸些其他的鋼琴曲目。”李玥說,“你不讓學生參加考級不可能,畢竟國際國內的各種鋼琴比賽有限,要求也高,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參加。考級或多或少能證明孩子的學習成果。”
支持
獨生子女的家長們對孩子前途的深切期許與政府對藝術的支持,使得鋼琴熱何時降溫變得遙遙無期。
400年前當西方音樂正式進入中國時,統治者并沒有像抵觸西方政治制度一樣去抵觸樂器。1601年,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向萬歷——明代統治時間最長的皇帝,獻上了一架羽管鍵琴,這種琴就是鋼琴的前身。美國人梅文詩和她的丈夫美籍華人指揮家蔡金冬合作撰寫的《紅色狂想曲:西方古典音樂在中國》一書中引述到:“皇帝的太監在琴上試彈了一會兒,然后就將其閑置一邊。它靜靜地躺在一個盒子中達數十年之久,直到崇禎皇帝這位明朝的末代皇帝,才發現了它而且找到一位德國傳教士向他解釋如何演奏的。在之后的皇帝中間,康熙和乾隆都對西方音樂顯示出濃厚的興趣;后者統治了中國幾乎18世紀中大部分時間,他組建了一個滿員的室內交響樂團,太監們穿上歐洲人的服裝,戴上假發進行演奏。”
如今,政府更加重視藝術對于孩子們素質的提高,教育部近日出臺了關于推進學校藝術教育發展的若干意見。根據意見,教育部將從2015年起對中小學校和中等職業學校學生進行藝術素質測評,并將測評結果記入學生成長檔案,作為綜合評價學生發展狀況的內容之一,以及學生中考和高考錄取的參考依據。意見明確,義務教育階段學校開設藝術課程,應確保藝術課程課時總量不低于國家課程方案規定總課時9%的下限,鼓勵有條件的學校按總課時的11%開設藝術課程,初中階段藝術課程課時不低于義務教育階段藝術課程總課時的20%。普通高中要保證藝術類必修課程的6個學分。中等職業學校要將藝術課程納入公共基礎必修課,保證72學時。普通高校要面向全體學生開設公共藝術課程,并納入學分管理。鼓勵各級各類學校開發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地方藝術課程。
“我認為鋼琴熱、提琴熱是好事。”東京藝術大學小提琴演奏博士王中男說,一個擁有人文藝術方面修養的人,對事物的反應會敏感許多。
王中男博士稱,歐洲國家在兒童的小提琴教育也開始傾向于中國式強迫教育。“孩子懂什么?日本這幾十年研究發現,你把所有練習曲都寫得異常優美也不管用,孩子就是不喜歡練琴。音樂是美妙的,但是練習是艱苦的,在掌握基本技術以前,快樂教育完全不管用,這是我自己的觀點。日本最棒的小提琴家美島莉兩歲就表現出音樂天賦,但也因為不喜歡練琴被母親毆打。”
其實,王中男自己就是被在大連一家樂隊擔任圓號演奏員的父親扇耳光強迫練出來的。國家交響樂團青年鋼琴家李玥的甜美外貌和氣質,無不透露出自己優越的音樂世家的出身,但是因為彈奏錯誤被母親打得哭聲不斷,對于兒時的李玥來說是最常見不過的事,“那時我是哇哇地哭”。如今中國鋼琴熱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附屬品,仍然是孩子們的哭聲。
(編輯·宋冰華)
ice705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