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諾、本雅明通信選[6]
譯/蔣洪生

本雅明致阿多諾
柏林,1928年7月2日
親愛的維森貢德先生:
你誠懇的信箋1激勵了我,使得我能夠滿懷喜悅,等待你《舒伯特》手稿2的到來。我想那正是你向我暗示的。與此同時,我希望你關于舒伯特的手稿能夠成功收尾。我可否事先得到你的允準,允準我將你的手稿也給恩斯特·布洛赫3看看?如果我能夠和他一起閱讀你的手稿,這對我來說有著極大的好處。
那次在柏林的時候,你對我的朋友阿爾弗雷德·科恩4表現得如此友好,并對他如此地不吝支持,以至于我覺得確實應當告知你事情的結局,或者說更不幸地和更準確地,告知你科恩所從業的生意的失敗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失業。當然所有這一切還沒有正式宣布,科恩生意的清償仍然是一個商業秘密。但是到10月份,他的處境肯定會變得極其困難,除非他的朋友能夠出手相助。在這一點上,我現在必須也肯定會盡我的全力來幫他的:但是如果事情要成功,那么我就需要就我的朋友科恩的處境與你再談一次。當然我理解,你們先前所建議的“柏林籌劃”現在是不可能的。難道你不覺得現在對他來說,法蘭克福可能有某些機會嗎?我知道,為著再次表達你的友誼和影響,我已經為你說得足夠多了,是否你認為在這件事上有成功的前景。
對了,一開始我想邀請卡普露斯小姐5順道來訪,這件事迄今未能實現;可是后來我突然想到,我可能給人造成我似乎忘記了這回事的印象。但是就我來說,這不是由于我忘記了這件事,而僅僅是因為在最近的幾周里,我覺得我的心神完全為互相交纏得厲害的各種任務和困局所系6,以至于我完全沒有機會去接觸她。
一旦這里的事情有所好轉,我希望在短期內,你會從她那里聽到我的消息。
致以最熱烈的問候,你的,
瓦爾特·本雅明
(翻譯底本:Theodor Adorno and Walter Benjamin,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1928-1940. ed. Henri Lonitz, trans. Nicholas Walker, Polity,1999)
本雅明致阿多諾
波韋羅莫7(馬里納·迪·馬薩),1932年9月3日
親愛的維森貢德先生:
我不得不如此長久地等待你的信件,你信件的到來給我帶來了極大的歡悅。特別是因為其中的某些段落,是如此地接近你的《戲劇的自然史》極好的結論部分8的設計。《戲劇的自然史》是一個極大的和令人信服的成就。我衷心感謝你把這一作品的結論部分題獻給我。我認為,整個的結論部分來自于你對舞臺及其世界的高度原創性和真正巴洛克式的看法。確實,也許可以說,其中包含了一些“巴洛克舞臺的一切未來史的緒論”之類的東西。通過題獻,你很好地揭示了這些隱秘的主題關系,對此我尤感高興。對我來說,自不必說,你的這一作品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實際上,《戲劇的自然史》的“劇場休息室”(Foyer)部分也有一些很好的東西,比如有關兩個鐘面的意象的論述,比如關于幕間休息時的節食的極具洞察力的思想。我希望我能很快在“霍克海默檔案”9中讀到你的文章。如果允許我進一步表達我的愿望的話,我希望在你的這一論文之外,我也能收到“霍克海默檔案”的第一期,我自然對此極感興趣。我們在這里有很多讀書的時間。在我五個月前出發到這里的時候,我帶來了一個小小的圖書館,我現在幾乎把里面的書全部瀏覽完了。你會有興趣聽到,我再一次地帶來了四卷本的普魯斯特著作集10,這是我讀了又讀的。但是現在我在這里得到了一本新書,這是一本我想提請你注意的書,這就是由羅沃爾特(Rowohlt)出版公司出版的阿圖爾·羅森貝格撰寫的一本關于布爾什維克歷史的書11。這本書我剛剛讀完,對我來說,這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忽視的一本書。就我自己而言,我必須說這本書大大擴展了我的視野,使我關注到包括那些政治意志影響個人命運的領域。種種情形,以及你最近提到的西薩爾茲(Cysarz)12,給了我思考后者的由頭。我一點也不反感和西薩爾茲建立某種聯系。但是我仍然不是很明白為什么他自己不首先聯系我,不論是直接聯系我,還是通過格拉布(Grab)13寫信給我的方式聯系我,如果他確實對此感興趣的話。我毫不懷疑,在類似的情況下,處在他的位置上,我會首先聯系他。如果我不去這樣做的話,那自然不是出于聲名的考量使我止步不前,而是因為我深深地感到,這樣的一段友誼從一開始犯下的錯誤,隨后被不斷地、成比例地擴大。我想憑著西薩爾茲的影響力,比如說,他完全可以為我從布拉格某個合適的團體或機構獲得一個演講的邀請。如果有機會的話,也許你可以把這個意思告訴格拉布。無論如何,對你在你的研討班14報告之后所附的對我的邀請15,我要表示我最為誠摯的謝意。自不待言,能有機會去你那里講演我是多么的高興;也不必說,能有機會看看那些能夠顯示迄今為止事情進展到何種地步的文件16,于我來說是極有價值的。當然,如果我們能夠一起來做這件事情,那將會是極為可取的。可是在當下--這也關乎我去法蘭克福的機會--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做不了自己的主。我既不知道何時回柏林,也不知道柏林那邊的情況會怎樣。我肯定會在這里再呆上幾個星期之久。在這之后我也許會返回柏林:一方面為著處理房子的問題,另一方面是因為羅沃爾特出版公司似乎堅持要出版我的論文集17。在德國無論呆多長時間,其誘惑本身對我來說當然不太大。到處都碰到困難,在廣播領域里產生的困難18可能會使我在法蘭克福現身的機會更加稀少。如果你恰好知道舍恩19的情況,請讓我知道。我一點兒也不知道他的情況。今天我就寫到這里。我唯一還想說的是,我正在寫作一系列與我的童年記憶有關的隨筆。我希望我很快能夠給你看看其中的一些篇章。
致以最誠摯的問候,
你的,
瓦爾特·本雅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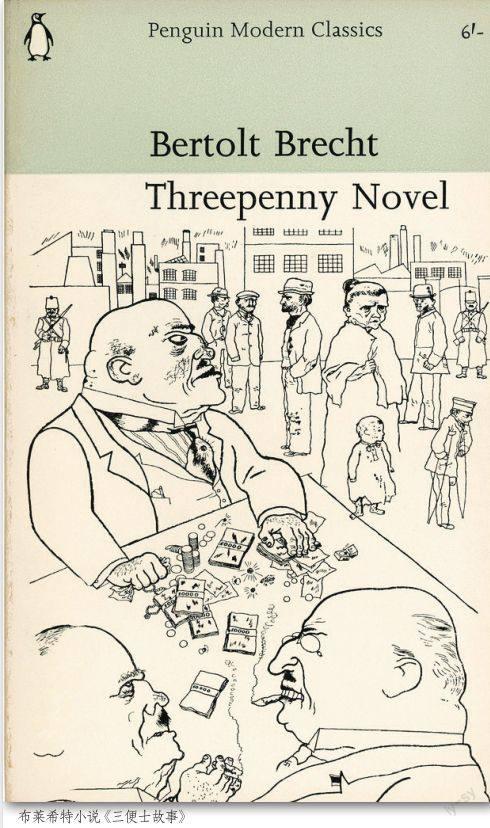
另:使我很高興的是,我發現了你關于“扭曲”的論文21。在我的評論中,我引述了沃爾夫斯凱爾(Wolfskehl)22的說法,他是這么說的:“難道我們不應該說招魂士是在不可知(Beyond)之中捕魚嗎?”23
(翻 譯底 本:Theodor Adorno and Walter Benjamin,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1928-1940. ed. Henri Lonitz, trans. Nicholas Walker, Polity,1999; Walter Benjam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Walter Benjamin 1910-1940, ed. Gershom Scholem and Theodor W. Adorno, trans. Manfred R. Jacobson and Evelyn M. Jacobs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阿多諾致本雅明
柏林北區第20郵政區,王子大街60號,在卡普露絲處1934年3月4日
親愛的本雅明先生:
關于湯姆·索亞24的問題,你的信自然是我收到的唯一有實質內容的東西,所以幾個星期以來,我一直隨身攜帶著你有關此問題的詳信。但是同時,我從菲麗西塔絲25那里聽說你自己處于極為嚴重的困境之中26,在這種情況下,我能設想,在當下的語境之下進行任何長篇的美學討論,看起來只不過具有侮辱性的性質。
所以我寧愿為你做些實在的事情。真正來說,這得通過赫茨貝格爾夫人27和我的姑媽28。你曾經在我的陪同下,在法蘭克福見過赫茨貝格爾夫人一次。當赫茨貝格爾夫人碰巧呆在法蘭克福的時候,我的姑媽曾向她提起過你的事情(赫茨貝格爾夫人實際上住在諾因基縣(Neunkirchen),那里有她的公司)。我姑媽給我寫信告知我說,她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功。關于幫助的金額,我目前完全說不上來。可以設想,金額將不會太多的。29但是它還是會解決你的燃眉之急的。我以最緊急的方式,努力地向她們解釋所有的一切,請求她們立即為你做些事情。我想這些幫助會及時發生的。無論如何,我都要很感謝你就你自己的整體處境所傳遞的快捷信息。由此我能夠代表你,在必要的時候,在這件事上施加進一步的影響。
進一步的計劃尚未成熟,因為那個原住巴黎的、與此事相關的人現在不住在那里30。于此我也會盡我所能地幫助你的。
關于“湯姆”,我要說的僅僅是:我相信主宰著“可怕的孩子們”(Les Enfants terribles)的星星對這一作品而言,并不特別有利。這里有待解決的是極為不同的東西,我希望,不僅僅是我個人的東西。語言的熱烈并不等同于真實的孩子們的熱情,甚至也不等于我們在為兒童寫作的文學中所碰到的熱情31。以洞穴場景為其當然焦點的行動過程,我也不覺得是那樣的無害。如果不是顯得太傲慢的話,我也許會表明,我在這一作品中偷偷放入了大量的東西;我也許會表明,在它即刻顯現的意義上講,沒有什么東西是特別有意為之的;我也許還會表明,我正在使用孩子氣的意象來表現一些極為嚴肅的事情:在這一方面,比起關心童年本身的喚起而言,我更為關心這種童年意象的展示。這一作品演進的過程也包含著那些有點危險的時刻,這是些你沒有在其中找到的東西。這當然不是要和讓·科克托32,也不是要和布萊希特的“史詩劇”相比較來衡量。如果說有什么東西可以比較的話,那最密切相關的是我有關克爾凱郭爾的書。我的《印第安·喬的財寶》的中心問題是背誓,整個事情就相當于一場被預計好的逃亡,是對恐懼的表達33。如果你重新看看我的這一作品的話,也許它會向你呈現出一幅與先前不同的、與你更為相投的面貌。因為我不能相信,你作為我這一作品的理想讀者,竟然會欣賞不了它。--順便來說,你不僅熟悉《印第安·喬的財寶》整個的規劃,也很熟悉其中的兩個場景(墓地和鬧鬼的屋子),這是我在舍恩的住處34所朗誦的部分。在同一個晚上,你為我們朗誦了“拱……”(我差點寫成了“拱廊”!35這是一個多么明顯的筆誤!),不,你為我們朗誦了“柏林童年”的最初的部分。我絕非強加給你完全意料之外的東西,要為這種指控辯護,這真是太簡單了。至于音樂創作方面36,我進展得很順利。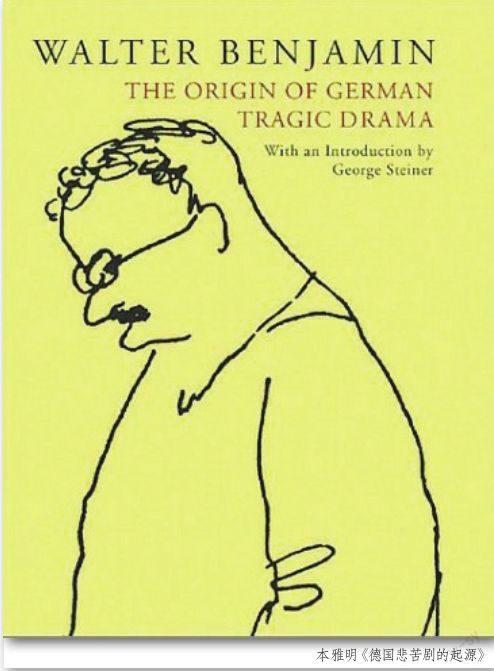
但是你的“拱廊計劃”的研究實際上進展得如何?我想到,我們可以以一種老套的方式來著手我們兩個行動方案中的一個(第二個方案仍在未決之中),可以通過我們的朋友來安排一個正式的題獻。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讓他來做這件事,但是我至少想事先知道你對這個想法怎樣看。自不必說,我的完全自我本位的、真正專注于你的“拱廊計劃”的興趣有多強烈!對如此明確的任務的支持,也許將會證明有利于這一工作。
目前我有很多工作要做,也有一些很奇特的事情。我正為《音樂》雜志寫作一篇有分量的論音樂批評的危機的文章37。它與我的那篇音樂-社會學論文是緊密相關的38。
你忠實和誠摯的,
泰迪·維森貢德
(翻譯底本:Theodor Adorno and Walter Benjamin,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1928-1940. ed. Henri Lonitz, trans. Nicholas Walker, Polity,1999)
本雅明致阿多諾圣雷莫
1935年1月7日
親愛的維森貢德先生:
我想你已經回去了,我打算著手回復你12月17日的長信。也不無些許憂慮,你的信是如此的重要和如此直接地切入問題的核心,以至于我無法以一次通信的方式對你的長信進行公正的評判。由此,在進行其他事情之前,越發重要的是,我要再次讓你知道,你對我的著述的強烈興趣,讓我感到了多么大的快樂!我不僅僅是在閱讀你的信件,而且是在研究它。你的信件要求我一句一句地去思索。因為你準確地捕獲了我在文章中39的意圖,所以你所指出的我文章中走偏的地方,對我來說具有最為重要的意義。你認為我對“遠古”(the archaic)概念的掌握不夠充分,這尤其正確;由此,你對我有關“永世”(eons)和遺忘問題的保留意見,也十分中肯。至于其他方面,我將干脆痛快地接受你對我使用的術語“實驗性企圖”(experimental attempt)的反對意見,我也將考慮你對于默片的極為重要的意見。你對卡夫卡《一只狗的研究》("Investigations of a Dog"["Aufzeichnungen eines Hundes"])的特別強調,于我是一個有用的暗示。恰恰是卡夫卡的這一篇文章--也許是卡夫卡唯一的一篇文章--我仍然感到陌生,即便是我在撰寫《弗朗茨·卡夫卡》這篇論文的時候。我也知道--就這一點,我曾經對菲麗西塔絲說過--我仍然需要領悟這篇文章到底意味著什么。你的評論與我的這一設想正好相符。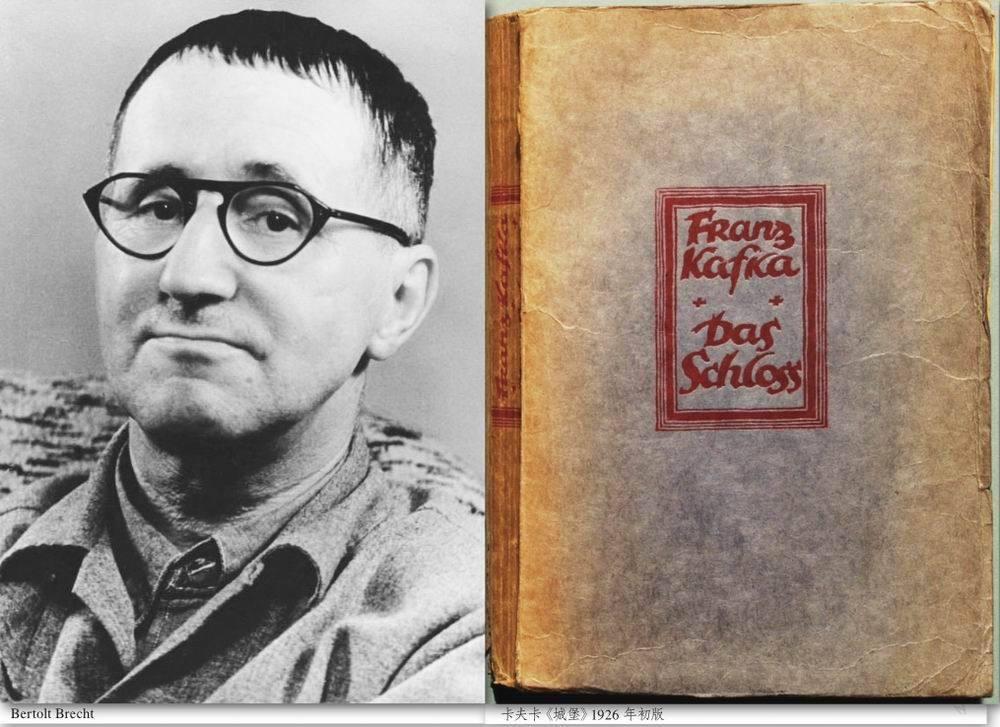
既然我的卡夫卡論文的兩個部分,也就是第一和第三部分已經發表,那么修訂40之路也就敞開了。全文最終能否發表,朔肯41是否會以圖書的形式出版我卡夫卡論文的擴展版,都還是一個問題。就我目前所能看到的而言,修訂工作將主要影響到第四部分42,盡管這一部分被我視為重點--也許因為太過重點了,所以即便像你和朔勒姆這樣的讀者,對于這一部分都不太可能表明某種立場。否則,到現在為止,布萊希特也會是公開對此表明意見的人之一43。因此總而言之,一種音樂意象縈繞著它,我仍然希望我能從中學到一些東西。我暫定打算撰寫一部反思集,但是我還沒有考慮如何將它們逐漸投射到原初的文本上去。這些反思將以“意象=象征”這一關系等式為中心;比起與之形成對比的“寓言(parable)=小說”這一等式,我相信“意象=象征”這一等式,能以一種更為公正地對待卡夫卡之思維模式的方式,捕捉到表明卡夫卡作品特征的悖論。對卡夫卡小說形式的一種更為精確的定義仍然尚未存在。我同意你的意見:對卡夫卡小說形式的定義很關鍵,但是這只能通過間接的方式來實現。
我希望--這很可能--這些問題中的一些問題將保持著開放,直到我們下次的見面。也就是說,假如我真的可以寄希望于菲麗西塔絲的提議,她說,你可能考慮在復活節的時候來圣雷莫一趟44。如果真的是這樣,那我會很高興的,確實,我會比你能設想的更為高興,你不能了解目前的我是多么的與世隔絕。可現在我有望從這種隔絕中暫時脫離出來;我在等待維辛45的來訪,這樣我可能成為維辛在柏林度過的最近幾個月的非直接見證人,而你則直接經歷了柏林的最后時日。這也使得我很想見到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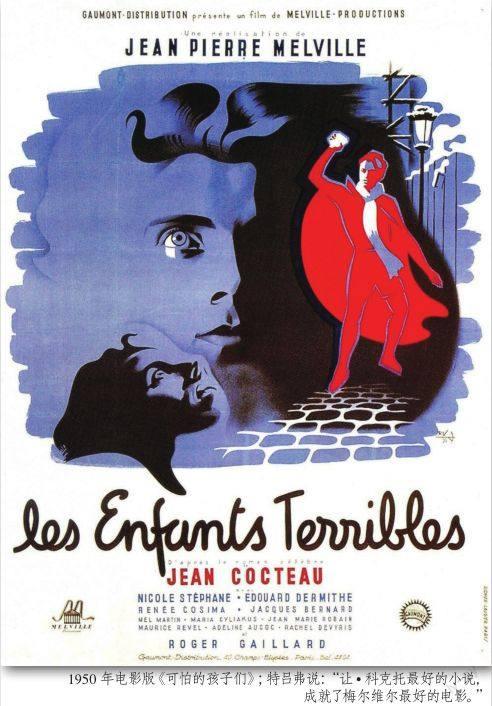
目前我沒有考慮復活節以外的事情。布萊希特再次請我立即到丹麥去,是的,立即。不管怎樣,在五月之前我或許不會離開圣雷莫。另一方面,雖然圣雷莫是一處很有價值的避難所,我不會讓我自己永遠呆在圣雷莫的,因為長期而言,我與朋友們的隔絕和我在這里的工作方式,將把圣雷莫變成為對我的忍耐力的危險試煉。當然另外一個考慮因素是,在這里我完全為最起碼的生活必需物所限,這使我常常覺得自己是個廢人。回復你在12月份所作出的、我為此而真心感謝你的友善提議,--在現有的條件下,研究所每月給我100瑞士法郎,這意味著我至少可以滿足最低生活需要,所以就我而言,我實際上現在不需要求助于外人。千真萬確的是,在這一特別的時刻,我以最微薄的生活條件,以最小的行動自由,產生了很大的主動性,但這是如何做到的呢?
另一方面,你從你自己的經驗就可以知道,當你以一種外語撰寫首批論文的時候,就需要激發起最多的主動性。我正在為《新法蘭西評論》 撰寫關于巴霍芬的論文46,所以我能夠感覺到這一點。對于我們自己最基本的一些關心,這一寫作計劃能夠很好地為我們提供大量談資。因為巴霍芬在法國幾乎毫無知名度,他沒有任何作品被翻譯為法文,所以這就迫使我必須在顯要處為法國人展示大量關于巴霍芬的一般信息。說到這一點,無論如何,我要對你在12月5日的來信中就克拉格斯和榮格所作的評論,表達我毫無保留的同意。正是根據你在信中所示意的精神,我認為有必要獲取有關榮格的更多知識。你手頭上是不是正好有榮格關于喬伊斯的研究?
你能告訴我你這段話出自什么地方嗎?這句話是:“幾乎什么也不是的東西再次令所有東西變好。”47你可以把你所暗示的關于倫敦公共汽車票的文章寄給我嗎?無論如何,我都期待能夠盡快讀到你論留聲機的文章,這直接觸及到了如此多的我所感興趣的重要領域。
首次給我寄的布洛赫的書48一定是寄丟了,出版商承諾給我再寄一本。我真正感到遺憾的是,布洛赫,就像我們大家一樣,肯定需要讓他自己聽聽作為專家的朋友們的意見,可是他卻不是去求諸朋友,而只是自顧自地闡述看法,滿足于讓朋友們自己去享用他的著述。
你讀過《三便士故事》49嗎?我感覺這是一個完美的成功。請你一定寫信告訴我你對這一作品的看法。也請詳細告知我關于所有事情的詳細信息,別忘記讓我知道你自己工作的進展情況。
致以誠摯的問候,
你的,
瓦爾特·本雅明
1935年1月7日
圣雷莫
綠色別墅(Villa Verde)50
(翻譯底本:Theodor Adorno and Walter Benjamin,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1928-1940. ed. Henri Lonitz, trans. Nicholas Walker, Polity,1999; Walter Benjam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Walter Benjamin 1910-1940, ed. Gershom Scholem and Theodor W. Adorno, trans. Manfred R. Jacobson and Evelyn M. Jacobs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