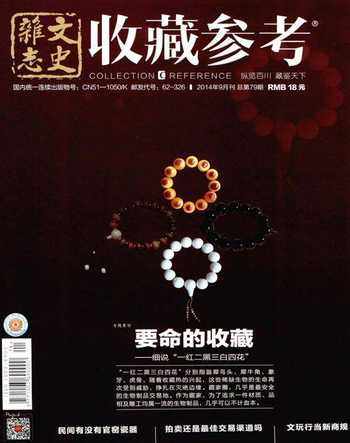蔡國強就該挨罵
林明杰
蔡國強在黃浦江上炸出了喝彩也炸出了責罵。喝彩有道理,責罵也有道理。在此,我這個曾在現場觀看焰火并喝彩者,倒想說說罵的道理。
首先,在上海這樣一個人口密集、節奏快速的脆弱都市(城市越大越脆弱),你搞這么驚天一炸,不能僅僅考慮場內觀眾的觀感,卻沒考慮到更多市民并不知情。那種節日里放的焰火,你隨便放,他們不會怕。但蔡國強的焰火不是公眾經驗范圍內的焰火。不了解的人從遠處的樓宇上,高架橋上,突然發現這個城里火光沖天、濃煙驟起,能不驚悚嗎?沒有因此發生慌亂事故,挨罵算是幸運的了。
由此可見,才誕生兩年的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還需要積累更多經驗。今后若搞可能嚇到別人的活動(那是一定要搞的,不搞就不是當代藝術博物館了),一定要事先廣為告知,要事先預料到公眾可能的誤會。既然是公共空間的藝術,就要多考慮些事兒。
再則,當代藝術作為實驗性藝術、探索性藝術,其本質就決定了要被罵。
實驗性藝術,就像是科學實驗,必然會有大量失敗的、不成熟的作品。只不過科學實驗的失敗一般都匿了起來,而實驗性藝術則必須拿出來亮相,因為只有在公眾的審視中,在罵和贊的交鋒中,它才能被檢驗,也才起作用。
當代藝術作品應該超出人們習慣性思維,超出常人的審美習慣,因為其價值就在于拓展人類的視野和思維。那么,如果當代藝術作品都像是唱堂會那樣喜聞樂見,就失去了意義。看近現代藝術史,從莫奈、凡·高、畢加索、波洛克、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到上海的任伯年、關良、吳大羽等,他們的作品都曾被罵,甚至今天還有人罵。罵罵更健康,不罵沒價值。真的是不罵沒價值,因為不罵就說明你完全沒有超出人們的審美習慣。想想,就拿我們從小到大見到過的所有新事物,從時髦的服裝到音樂,哪個沒挨過罵?說極端點,對當代藝術來說,挨罵的不一定是好東西,但不挨罵的基本不是個東西。
中國“當代藝術”急于精英化、學術化、國際化和商業化。這急吼吼的“四化”使得他們根未深、蔭未廣,就自娛自樂起來,并以他們高傲、自戀的眼光忽略被漠視和忽視的人們。這也是中國“當代藝術”活該被罵的原因。
在衣耕社會環境中的人,養成適應社會緩慢發展的心理素質。而當今的人類則需以更大的心理承受力、應變力和包容度來應對急速發展、日新月異的當今社會環境。當代藝術,正是當今人類可以借以提升想象力、創造力、應變力和包容度的練習場。它只是個練習場,打臭球沒關系,被旁觀者罵臭球也很正常。當代藝術的博物館實質也是練習場,從公眾到文化藝術主管者都不要把它當作盧浮宮、大都會這樣經典藝術的圣殿,記住它是個練習場。
當代藝術不需要膜拜,只需要空間和自由。
我不擔心當代藝術挨罵,我倒擔心不能罵它。
記得中國當代藝術最重要的展示平臺——上海雙年展初創階段,有很多人罵,一些領導、媒體人士都看不順眼。我當時的總編大人(我很敬重的新聞前輩,已去世)就罵它是“垃圾”。這下好了,作為報道藝術的記者,我稿子沒法寫了。說實話,我對大多數的所謂“當代”作品也不喜歡,更懶得和這個圈子里的牛人打交道。但我覺得喜不喜歡是我個人的事,然而我們不能因為自己不喜歡就認為它都是垃圾(從理論上講,當代藝術作品中包含大量垃圾才是正常的)。我心有不甘地找我的“現管”——部主任大人,“我是不是可以寫一篇讓罵雙年展的人也能理解雙年展存在意義的稿子啊?”部主任大人竟然非常有魄力地說:“你寫吧!”結果,第二天頭條刊出。據說總編大人審稿時沒有反對。我覺得,當代藝術就需要這么點包容和空間。
不料,雙年展后來搞著搞著,官方竟然支持起來,甚至給予了資助。這下好了,曾一度貌似不能罵了。這更可怕。不能罵了那還是當代藝術嗎?它豈不成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唯一真理?
被權力綁架了的藝術才不許罵,被資本綁架了的藝術才害怕被罵。不許罵當代藝術,就等于殺了當代藝術。
公眾有罵和贊的自由,藝術家也有堅持探索、展示、解釋的自由。這才是現代文明的體現。上海雙年展和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能夠在這里誕生并成長,正體現了這座城市的現代文明程度。
罵不起的人不要從事當代藝術。同樣,作為當代藝術的“黑后臺”——當代藝術博物館,也要有挨得起罵的膽魄。我這么說,并不意味著當代藝術就該死豬不怕開水燙。一位真正的藝術家,應該在罵聲中堅持,在罵聲中完善,在罵聲中壯大,最終用藝術的魅力影響人們的看法。對藝術來說,最重要的是自由,那么藝術家也要尊重別人罵他的自由。
其實對當代藝術來說,一件作品的成敗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是否能建立起一種環境,在這個環境中,我們能更好地交流彼此的看法,同時都尊重對方的不同看法和生存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