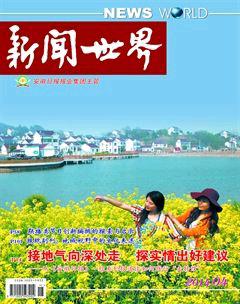新媒體時代西方軍事行動的輿論導(dǎo)向
祝良文
【摘 要】在信息即時傳播的新媒體時代,媒體和公眾是戰(zhàn)爭的第二戰(zhàn)場。為了同時打贏戰(zhàn)場和所謂“公理”兩條戰(zhàn)線,西方國家的軍官們巧妙運用軍事文化軟實力,通過軍事行動代號的命名千方百計地妖魔化對手,將戰(zhàn)爭的真正戰(zhàn)略意圖隱藏起來,擺出捍衛(wèi)弱者的姿態(tài)以及借口反恐和宣揚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觀等手段,為戰(zhàn)爭“正名”。
【關(guān)鍵詞】新媒體 軍事行動
進入21世紀(jì),隨著以計算機網(wǎng)絡(luò)為中心的信息即時傳播的新媒體時代的到來,無論是對參戰(zhàn)人員還是國內(nèi)外民眾,想要隱瞞戰(zhàn)爭的真相已經(jīng)變得十分困難。如何使一場戰(zhàn)爭在輿論和戰(zhàn)場兩條戰(zhàn)線上同時打贏,是西方國家發(fā)動戰(zhàn)爭前必須慎重考量的因素之一。他們深知贏得“公理”比打贏戰(zhàn)爭更難,在發(fā)動一場戰(zhàn)爭時,總會為軍事行動起一個形象而頗具意義的作戰(zhàn)代號,一方面為戰(zhàn)爭正名,另一方面也要起到動員戰(zhàn)爭輿論的作用,以此將一些非正義戰(zhàn)爭利用代號的方法轉(zhuǎn)變其“性質(zhì)”,誤導(dǎo)公眾,掩人耳目,使戰(zhàn)爭合法化、正義化,體現(xiàn)了對西方國家軍事文化軟實力的巧妙運用。從第一次海灣戰(zhàn)爭、科索沃戰(zhàn)爭到伊拉克戰(zhàn)爭、阿富汗戰(zhàn)爭、利比亞戰(zhàn)爭,概莫能外。
一、朝鮮戰(zhàn)爭和越戰(zhàn)軍事行動代號的教訓(xùn)
美軍軍事行動代號的命名有一套成熟的規(guī)范和合理的指導(dǎo)原則,但并不歷來如此。在朝鮮戰(zhàn)爭和越南戰(zhàn)爭中,美軍行動代號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士氣,但同時也觸犯了輿論和政治宣傳的大忌。
1951年2~4月間,為了鼓舞日漸低落的士氣,美國新任盟軍總司令李奇微將一系列反攻行動命名為“雷電”、“屠夫”、“撕裂者”等。這些代號在當(dāng)時確實起到了一定的煽動作用,但美國國內(nèi)的一些民眾和政客認(rèn)為“屠夫”、“撕裂者”這類行動代號過于血腥,以美軍為首的“聯(lián)合國軍”很容易被人誤解為“劊子手”。
越戰(zhàn)時期,在軍事行動的命名上,美軍又重蹈覆轍。如在1964年美軍第一空中騎兵師實施了一次被稱為“搗碎機”突擊行動,并被報紙頻頻曝光。美國總統(tǒng)約翰遜對此十分生氣,因為美國政府當(dāng)時正在南越推行所謂的“和平戰(zhàn)略”,軍方的這個血淋淋的代號使美國政府在道義上陷于被動。
這些教訓(xùn)使美軍認(rèn)識到,一個理想的代號不僅要鼓舞士氣,提高戰(zhàn)斗力,還要“政治正確”,對國內(nèi)外的民眾和輿論作全面考量。因此,在1975年美軍參謀長聯(lián)席會議對軍事行動代號、綽號和演習(xí)名稱的命名進行了規(guī)范,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指導(dǎo)原則:一是要與美國傳統(tǒng)價值觀和外交政策一致,不能表現(xiàn)出好戰(zhàn)色彩;二是要照顧到特定的社會群體和宗教信仰,不能對他們表現(xiàn)出絲毫的貶損意味;三是不能引起盟友或所謂的“自由國家”的不快;四是語法修辭和藝術(shù)性上的要求,如不用外來語、陳詞濫調(diào)、商標(biāo)以及低級趣味的詞語,并且要求音調(diào)長短相配,抑揚頓挫,簡明易記,又有沖擊力等等。直到今天,這些都是美軍給軍事行動命名時要考量的標(biāo)準(zhǔn)。
二、現(xiàn)代戰(zhàn)爭的新特點及西方軍隊對新聞輿論態(tài)度的改變
1、二十世紀(jì)末至二十一世紀(jì)的戰(zhàn)爭的兩個新特點
第一,西方國家發(fā)動的戰(zhàn)爭,其主要對手與自己的力量不在一個量級上,例如美國等西方國家和巴拿馬、南聯(lián)盟、伊拉克之間,有的甚至并不是嚴(yán)格意義上的國家武裝力量之間的正規(guī)對抗,例如美國和塔利班、本.拉登之間。也就是說,非正規(guī)戰(zhàn)成為主要戰(zhàn)爭形式。非正規(guī)敵人知道自己在正規(guī)對抗中毫無取勝的機會,因此,他們藏匿于民眾之中,從持同情態(tài)度的本地人中招募并培訓(xùn)新的武裝人員,竭力爭取持中立或敵對態(tài)度的群體。因此,西方軍隊在戰(zhàn)場上的絕對優(yōu)勢固然不必?fù)?dān)心,但是必須考慮敵人為爭取民眾而作的輿論宣傳。
第二,新媒體時代的出現(xiàn)及信息的“對等生產(chǎn)”,使民眾不僅成為信息的接受者,同時也可以是信息的發(fā)布者。所謂“新媒體”時代,本質(zhì)上是指一個信息環(huán)境,是相對于上述三個階段的傳統(tǒng)媒體而言的。在傳統(tǒng)媒體中,平面媒體、廣播電臺、電視乃至因特網(wǎng)仍然只是公眾接受信息的平臺,信息創(chuàng)造和發(fā)布者掌控了對公眾的話語權(quán),受眾要發(fā)送信息必須另覓他徑。到2000年左右,傳統(tǒng)網(wǎng)絡(luò)開始大洗牌:以網(wǎng)絡(luò)為基礎(chǔ)的新型公司與服務(wù)倡導(dǎo)“互動”與“用戶創(chuàng)造內(nèi)容”,信息的接受與發(fā)送融為一體,網(wǎng)絡(luò)進入第二代。企業(yè)家蒂姆·奧萊利創(chuàng)造了一個詞“web2.0”來描述它,在這個網(wǎng)絡(luò)里,個人和自發(fā)的團體創(chuàng)造的內(nèi)容與公司及政府發(fā)布的內(nèi)容形成競爭關(guān)系:Youtube是一個視頻共享網(wǎng)站;Myspace和Facebook則是兩個社交網(wǎng)站;無數(shù)論壇允許個人發(fā)表評論,分發(fā)文本、圖像或視頻文件等等。
2、新媒體環(huán)境的兩個特點
一是計算機與網(wǎng)絡(luò)成本的降低,顛覆了信息與文化生產(chǎn)的資本結(jié)構(gòu)。遍布全世界的電信主干網(wǎng)這一基礎(chǔ)設(shè)施大幅降低了因特網(wǎng)與電信服務(wù)的價格,而且隨著計算成本的下降,數(shù)字技術(shù)日趨完善,因特網(wǎng)和移動電話價格低廉,迅速普及。公眾對大眾傳媒的參與度和人數(shù)急劇增加。
二是“web2.0”提供了大眾參與的平臺,互動成為新媒體時代的顯著特征。隨著因特網(wǎng)四處滲透,以網(wǎng)絡(luò)為基礎(chǔ)的創(chuàng)新軟件不斷出現(xiàn),新的公眾互動場所由此產(chǎn)生:博客、圖片與視頻分享網(wǎng)站、專題論壇、社交網(wǎng)站、留言板以及普通網(wǎng)站。進入大眾傳媒領(lǐng)域的門檻顯著降低,其中非專業(yè)人員數(shù)量顯著增長。“新媒體”環(huán)境下,信息發(fā)送者幾乎喪失了對信息近乎壟斷的地位,促使了大眾與媒體互動的融合,煥然一新的因特網(wǎng)將人們直接連在一起,使他們能夠展開對話,新媒體發(fā)揮了名副其實的平臺作用。許多人擁有Myspace空間,觀看Youtube視頻,在網(wǎng)上聊天,訂閱博客節(jié)目,閱讀博客,使用維基百科、Skype網(wǎng)絡(luò)電話、微博,在線共享故事、圖片與視頻等等。
由于因特網(wǎng)開放式的網(wǎng)絡(luò)架構(gòu)和新媒體環(huán)境的上述兩個特點,無論是對參戰(zhàn)人員還是國內(nèi)外民眾,想要隱瞞戰(zhàn)爭的真相已經(jīng)變得十分困難;朝鮮戰(zhàn)爭中的行動代號單純地激勵己方的士氣,也不能適應(yīng)新型戰(zhàn)爭的需要。西方國家已經(jīng)充分認(rèn)識到,在以網(wǎng)絡(luò)為中心的信息即時傳播的“新媒體”時代,媒體和公眾是第二戰(zhàn)場。為了同時打贏戰(zhàn)場和所謂“公理”兩條戰(zhàn)線,西方國家的軍官們對輿論宣傳,采取了一系列有意識的引導(dǎo)。
三、新媒體時代西方軍事行動的輿論導(dǎo)向
20世紀(jì)末期至21世紀(jì)以來,鑒于新媒體時代的信息環(huán)境和美軍在朝鮮戰(zhàn)爭和越戰(zhàn)的經(jīng)驗和教訓(xùn),西方國家在確定一些重大軍事行動的代號時更加謹(jǐn)慎,希望全面考慮各方不同的期待,以努力改善公共關(guān)系,樹立政府和軍方所謂的正面形象。為了達到以上目的,西方國家的軍方采用了以下手段:
一是妖魔化對手。妖魔化對手就是為了讓國內(nèi)外民眾,甚至交戰(zhàn)國的民眾以為戰(zhàn)爭是為了保護他們而哄騙民眾支持戰(zhàn)爭。如1989年12月20日,美國以巴拿馬國防軍司令諾列加在選舉中舞弊、軍事獨裁、毒品走私和謀殺美國軍官等非正義活動為由,發(fā)動了所謂的“正義事業(yè)行動”出兵巴拿馬。真實原因是諾列加要求美國提前歸還運河,嚴(yán)重觸犯了美國利益。開戰(zhàn)在即,美軍指揮官、擁有新聞學(xué)本科學(xué)歷的凱利中將經(jīng)過深思熟慮,把這次行動代號由“藍匙行動”該為“正義事業(yè)行動”。除了更能激勵美軍士氣之外,更重要的考慮是要搶占輿論和道德高地,突出懲罰諾列加的正義性,而且巧妙地掩蓋了入侵主權(quán)國家和早年扶植諾列加的尷尬。這個名稱至少在美國公眾中受到了普遍的歡迎,這也使美軍高層開始充分意識到軍事行動代號對輿論引導(dǎo)的重要性。
同樣被妖魔化的還有薩達姆。在2003年3月20日,美英發(fā)動代號為“自由伊拉克”的伊拉克戰(zhàn)爭,美國政府及其操縱的主流媒體就一直不遺余力地抹黑薩達姆,將其描繪成一個正在發(fā)展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的獨裁者及殺人狂魔,指責(zé)他一直靠血腥暴力鎮(zhèn)壓和恐嚇反對派以維護統(tǒng)治地位,伊拉克人民根本沒有尊嚴(yán)、自由和人權(quán)。所謂“自由伊拉克”就是據(jù)此而特別擬定的。“自由”就是要使飽受摧殘的伊拉克人民得到解放,獲得安全、自由、尊嚴(yán)和人權(quán)。
二是將戰(zhàn)爭的真正戰(zhàn)略意圖隱藏起來。例如1990年8月,針對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美軍為首發(fā)動了名為“沙漠盾牌”行動的第一次海灣戰(zhàn)爭。美軍利用矛與盾的關(guān)系,暗示這是因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對沙特阿拉伯構(gòu)成嚴(yán)重威脅,美國才被迫出兵自衛(wèi)的。它向世界表明美國是為了保衛(wèi)科威特在內(nèi)的海灣地區(qū)人民的安全和發(fā)展而采取的正義的軍事行動。這個代號贏得了西方國家的普遍好感,為美國實施軍事打擊作了有利的政治動員。
但是這只不過是美國政府的一場輿論公關(guān),實則是為了維護美國自己在海灣地區(qū)的經(jīng)濟利益。因為中東地區(qū)是世界最重要的石油出口地,美國大量石油依靠從此地進口。中東地區(qū)一旦受到對美國不友好的伊拉克的威脅,美國的經(jīng)濟就會命懸一線,美國出兵從根本上還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經(jīng)濟利益。
三是擺出“捍衛(wèi)弱者”的姿態(tài)。美國輿論一般先將欲攻打的對象國分成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的民眾,借口支持和解救所謂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民眾而去攻打統(tǒng)治者。美軍深知支持弱者就能占領(lǐng)輿論高地,樹起道德大旗。據(jù)稱北約攻打敘利亞的理由就是“人道主義災(zāi)難”,是為了“懲罰”“膽敢動用”化學(xué)武器對付反對派民眾的巴沙爾,去解救那些因沖突而背井離鄉(xiāng)的敘利亞難民,因此將這場戰(zhàn)爭命名為“安全天堂行動”。
四是借口反恐和宣揚民主自由等所謂的普世價值觀。2001年,在“9·11”恐怖襲擊后,美國決定對本·拉登藏身的阿富汗發(fā)動所謂的“反恐”戰(zhàn)爭。鑒于“9·11”恐怖襲擊給美國民眾帶來的巨大心理恐慌,美軍決定起一個振奮人心的代號,不僅要以此來鼓舞美國精神,而且還要宣揚和推廣美式民主自由價值觀。這次行動的代號屢經(jīng)修改,最后幾乎確定為“無限正義”這個大氣而又詩意的代號。但是,“9·11”之后,美國參議院外交關(guān)系委員會特別重視對穆斯林世界的公眾外交,鑒于伊斯蘭教教義認(rèn)為只有真主安拉才有資格用“無限正義”這樣崇高的字眼,這樣的代號必定會觸怒整個穆斯林世界,因此此代號被否定了。最后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確定用“持久自由行動”作為行動代號,以表明美國對所謂“自由世界”的捍衛(wèi)。正如約瑟夫·奈所說的那樣:“在削弱極端主義分子的影響時,民主國家的領(lǐng)導(dǎo)人應(yīng)該利用軟實力來傳播關(guān)于全球化和美好未來的積極而正面的言論,以此來吸引溫和派人士,并同圣戰(zhàn)主義者在網(wǎng)絡(luò)上的錯誤思想進行抗衡。”
由此可以看出,進人21世紀(jì)后,西方國家的軍事行動代號,相對早期的重點在于鼓勵士氣而言,它更加注重國際國內(nèi)的輿論影響,為此不惜使用粉飾、誤導(dǎo)和抹黑等手段,這樣既照顧了國際國內(nèi)的情緒,又反映了軍事行動本身,還以軍事外交的方式“推銷”了民主自由等價值觀念,把軍事行動代號軟實力的功能發(fā)揮到了極致。但是無論如何掩飾,我們都應(yīng)該睜開眼睛,認(rèn)清西方國家軍事行動背后的殘酷與血腥,千萬不要被諸如炸毀北越一座大橋的“卡羅萊納的月亮”這樣藝術(shù)化的名稱所迷惑。□
參考文獻
①鄭誠 編譯,《從“藍匙”到“正義事業(yè)”——漫談軍事行動命名》[J].《國外社會科學(xué)文摘》,2002(5)
②羅威廉,《戰(zhàn)斗名稱應(yīng)有的放矢》[N].《參考消息》,2010-3-22
③李響,《從作戰(zhàn)代號看美軍輿論引導(dǎo)》[J].《軍事記者》,2006(8)
④《美國怎么給軍事行動取名的》[J].《黨政論壇》,2001(12)
⑤托馬斯·里德、馬克·埃克:《戰(zhàn)爭2.0——信息時代的非正規(guī)戰(zhàn)》[M].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2011
(作者單位:陸軍軍官學(xué)院中文教研室)
責(zé)編: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