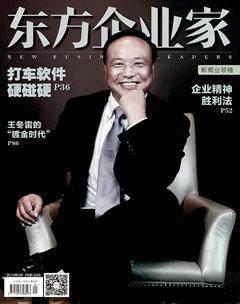企業(yè)精神的實質
中國企業(yè)群體泛濫的“精神”,總是用中式或者生活化的語言表達。讓我們嘗試與管理的概念進行對比,有助于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一部分可以歸入經理人,特別是管理者的情商。克勞塞維茨在《戰(zhàn)爭論》中寫道:“軍事天才是各種精神力量和諧的結合……要想不斷地戰(zhàn)勝意外事件,必須具有兩種特性:一是在這種茫茫的黑暗中仍能發(fā)出內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二是敢于跟隨這種微光前進的勇氣。前者在法語中被形象地稱為眼力,后者就是果斷。”
這種情商是從小,而不是從學校和就業(yè)才開始培養(yǎng)的。韋爾奇的父親只是一個鐵路檢票員,熱愛自己的工作,“每當老杰克早上5點穿著他那身熨得平整的藍黑色制服和母親漿得硬挺的白襯衣離開的時候,他的神情就好像站在上帝面前一樣。”韋爾奇的母親總是擔心自己會死得很早,她的家人都死于心臟病,因而總是鼓勵韋爾奇學會獨立。
韋爾奇的父親喜歡和人們打招呼,結識有趣的人,他特別提到“父親告訴我說,他列車上那些大人物的話題總離不開高爾夫球賽”。因此韋爾奇九歲時去附近的鄉(xiāng)村俱樂部當了一名球童。這項運動伴隨他一生,因為“結合了我所熱衷的東西:人和競爭。”
大部分可以歸入組織文化。組織是一個有機體,普魯士軍事家所形容軍隊的“集體人”,組織中的個體是集體人的器官。正如每個細胞的DNA都攜帶物種的全部信息,細胞間不斷地交換物質和信息,組織中的個體也分享一套價值觀,一套慣例的溝通和協(xié)作方式。
主席說過: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遠古的先民對此已有知識。《舊約·創(chuàng)世記》中巴別塔的故事,“神說:看吧,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語言,如今既作起這事來,以后他們所要做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于是變亂人們的語言,建通天塔的事就荒廢了。這可以視為一個組織文化的隱喻。
文化聽起來很玄,什么都不是,又什么都是。某位經理描述組織文化,和某位法官描述色情如出一轍:“我不能下定義,但看到的時候心里就明白。”
當年IBM PC項目將操作系統(tǒng)外包給微軟,成就其霸業(yè)。第一次拜訪微軟,IBM經理人一貫的西裝革履,看見比爾·蓋茨穿著T恤。于是第二次去,特意換上T恤,到了卻看見蓋茨一身西裝。穿西裝還是T恤就是兩種組織文化的一個表象。穿得和對方一樣,縮小文化差異,表達了談判的誠意。
組織文化也如同物種的進化,不是某個意志一次設計出來的,而是多元合力長期形成。越多元融合,組織文化就越強大。至少撐過一次大危機,組織文化才稱得上成熟。
組織總是生存于具體的文化背景,絕大部分組織的歷史都不能和文明相比。在形成組織文化的多種力量中,文化背景是最間接、最深遠的。美國文化高度的個人主義,對權威缺乏尊重,美國企業(yè)中的一些溝通,在其他文化看來是冒犯的。硅谷又比東北部更甚。日本文化追求共識,造成日本企業(yè)中繁冗的會議,“為了避免刺激出席人員,一面察言觀色,一面提出方案,確定沒有反對意見的氣氛后,再進行討論。”
但這并不意味著組織完全是文化背景的俘虜。特別是新創(chuàng)立的組織,可以有所揚棄。這也是在和組織共生過的所有個體中,創(chuàng)始人的影響無疑是最重要的。IBM和三星在家族企業(yè)二代手中成長壯大,他們不是法律上的但是精神上的創(chuàng)始人。惠普有兩個平起平坐的創(chuàng)始人,兄弟般情誼終其一生。兩人用擲硬幣的方式決出公司名稱為HP(兩人姓氏首字母)而不是PH,這個細節(jié)也能反映這家企業(yè)的文化。
組織文化與業(yè)務模式密切相關。1986年挑戰(zhàn)者號航天飛機失事,為此組成羅杰斯委員會調查。其成員之一波音747總設計師喬·薩特表示:“我工作在一個把安全當作頭等大事的環(huán)境。當?shù)弥贜ASA(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這里情況有所不同,不禁大為吃驚”。
但NASA的文化仍然沒有脫離業(yè)務。曾有幾名工程人員對航天飛機的設計持保留意見,包括導致挑戰(zhàn)者號失事的部件。其中之一告訴委員會:“我因為在飛行預備會議上使用‘我覺得、我認為這樣的表述受到懲處。他們認為這不是一份正確的報告,我覺得、我認為不是基于工程的論述,不過是判斷罷了。如果沒有一套完整、綜合并且可證實的數(shù)據(jù),沒有人會提出異議。”過去的成功促使NASA如同委員會調查報告中所寫:“始終懷有我們無所不能的信念,這是必要的,但樂觀的同時,必須認識到它并非無所不能。”
這正是郭士納所指出的:“成功的組織幾乎總是會建立這樣一種文化氛圍,即強化使組織更加強大的那些因素。當環(huán)境發(fā)生變化,組織文化很難發(fā)生變化,這時就會成為轉型的巨大障礙。”最近的一個案例是諾基亞等傳統(tǒng)手機巨頭,在iPhone推出后迅速地衰落,他們仍然擁有雄厚的資源和技術積累,但其組織文化難以將這些資源轉換到新的方向。
除了具體行業(yè)屬性,業(yè)務模式對組織文化的影響還體現(xiàn)在考核的難易。考核依賴信息的能見度,又分兩個層面:產出,組織的行動;結果,產出對世界的改變。當產出可見,可以精細地過程管理,結果可見,可以運用物質激勵和約束。而如果產出和結果都不可見,稱為解決方案型組織,只能通過營造組織文化,發(fā)揮員工的主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