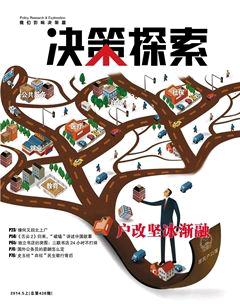緣何又回北上廣
劉偉鵬 胡飛
從一線城市到二三線城市,再回到一線城市,體現的是選擇和適應的過程,也是尋找答案的過程。
“北上廣是地獄,二三線城市是天堂。”這是許多人離開北上廣時的心情寫照。但不久他們發現,二三線城市的生活與想象中的相去甚遠,并非曾經以為的世外桃源。兩相權衡下,他們又回到曾經想要遠離的北上廣。與“逃離北上廣”這個話題一樣,“逃回”的趨勢和人數雖然沒有權威的統計,但同樣也是大家熱議的話題。
通過媒體的案例分析和網絡社區的話題討論,我們可以看到,選擇回到北上廣的人們幾乎都是因為無法忍受城市間的落差,他們是懷著對二三線城市的失望情緒而離開的。許多人“逃離北上廣”是為了尋找歸屬感,這個愿望在二三線城市能實現多少目前尚不好說,但曾經因遠離而忽略的二三線城市的缺點卻一一出現。“這些缺點難以忍受的程度甚至比北上廣的環境污染、交通擁堵和房價飆升等‘城市病還要強烈。”一家紙質媒體在討論到這個話題時引用學者的話說。
二三線城市最終沒能讓一部分人留下來。選擇“逃回”,能找出的理由很多,簡單地說可以這樣來概括:二三線城市也許只是“看上去很美”。
“人在迷途”
“逃離是想找回生活。”這是蘇小偉曾經的愿望,然而在老家江蘇泰州經歷了一年小城市安逸的生活后,他驚訝地發現自己產生了不安全感:工作沒有挑戰,看不到成長,甚至可以預見到幾十年后的自己過著怎樣的生活。他笑言自己選擇回到北京的理由:“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會被安逸的生活所累。”一逃一回,讓他看清了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想要繼續奮斗,他相信自己總會在北京找到立足點。
與蘇小偉有同樣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數,在某知名社區網站上,有許多人表達了這樣的想法。“當你習慣了每天處于競爭當中,抓緊一切機會提升自己,然后突然換回一個普遍悠閑混日子的工作圈,你更多的是一種孤獨和乏味,時間久了,你就懷念那個競爭激烈的北上廣。”在北上廣是“人在囧途”,回到小地方是“人在迷途”。習慣了大城市的豐富多彩,小地方的單調生活無法滿足精神生活的需求。另外,與大城市相比,教育水平和醫療服務水平相差的不是一個等級,公用設施和文化環境都跟不上節奏。
媒體和專家則更多地將焦點集中在城市本身。除了低收入高物價、沒有適合的崗位和上升的空間造成發展前景黯淡等因素之外,普遍繞不開的話題是權勢關系和房價。
“北上廣拼錢,小地方拼關系”,這似乎是個普遍的共識。《人民日報》的報道稱:“大城市往往更加開放、相對公平,而二三線城市往往更講等級關系、人情關系。一些人到了小縣城工作,卻發現自己并不適應當地的人際交往模式,因為在一個熟人社會,做事更要講關系、論人情,發展或許更難。”
在一家門戶網站進行的一項哪些事把人逼回北上廣的調查中,“權勢關系網”這一項得票最高。“職場上,靠的是關系,而不是能力;商場上,靠的不是方案,而是交際能力。自己創業,如果上邊沒有人,那么‘有關部門會三天兩頭來找你的麻煩。”況且,在北上廣奮斗多年的人,經營多年的生活圈子和社會關系都不在本地,拼關系幾乎沒有勝算。
網絡上的討論則更加直白,人們用“拼爹”來描述這一現象:“小地方的關系更加赤裸裸,關系小但密,回去只能‘拼爹。”媒體如此解讀這一說法:“回鄉創業的白領無法面對的是匱乏的‘拼爹資源。一些小地方基層的權力不彰,圍繞極其有限的資源,‘拼爹事實上成了最大的規則。”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指出一個殘酷的現實:回到家鄉,由于父母無權無勢,更是死路一條。一位網名為于浩淼的網民在與記者的交流中,表達了對這種“拼爹”方式的憤慨:“我在上海干活靠自身,靠自己的社會關系,我不用給領導送禮也能活。在家里沒有背景,給領導送禮的錢比工資都高。我為什么不回上海?”
房價也是大家抱怨的主要方面。高房價曾經是他們逃離北上廣的主要原因,但是如今在二三線城市,房價漲幅并不一定比北上廣低,靠一己工資同樣很難買到房。媒體這樣描述這種困境:“很多人因為一線城市壓力大,選擇了二三線城市,如今忽然發現,原來二三線城市房價比北上廣漲得還瘋狂,真不知道他們接下來將逃向何處?”
蘇小偉的父母在老家有一套房子,他想要獨立出來,自己買套房住,發現面臨的情形與在北京是相似的。談起買房,他同樣無奈:“既然都買不起房,還不如回北京多掙點錢。”
在觀念的代溝、思維方式的差異和精神生活匱乏的對比下,北上廣的優點明顯突出:城市資源多,所以機會很多,并且在這些個人關系被逐漸湮滅、契約精神在慢慢成長的大城市里,公平的競爭平臺,能讓個人憑借自己的才干和能力獲得成就。有人這樣形容自己的選擇:“逃離是為了自由,逃回是為了尊嚴。”
回不去的家鄉
“有對比,才有突出。就像購物一樣,貨比三家,才知道哪一個是最適合自己的。經歷了家鄉一眼望到頭的生活,我現在更需要的是北上廣的競爭環境。”蘇小偉如此形容自己作出選擇的過程。城市之間的差異性是逃回的人們作出選擇的“誘因”。從一線城市到二三線城市,再回到一線城市,體現的是選擇和適應的過程,也是尋找答案的過程。
從“逃離”到“逃回”,表面上看,是一個年輕人不安于現狀的“折騰”,實際展現的是社會大眾情緒的征候癥。人們對融入城市缺乏歸屬感,回歸地方卻又沒有成就感,不得不陷入左右為難的困境。逃離的決定本不容易做,逃回更加需要勇氣。蘇小偉在面對父母阻攔時這樣說:“因為知道自己即將面對什么,反而會比當初在北京時更加坦然。”這份坦然是他對邁向成功的準備,還是對事實無奈的妥協,我們不得而知。然而現實是,回到北京的蘇小偉面臨的是比離開前更加瘋狂的房價和更加激烈的競爭。
專欄作家沈彬將“逃回北上廣”的現象歸咎于體制問題。“為照顧老干部,就將公職崗位作為獎勵,‘恩蔭給官員子弟,嚴重敗壞了社會公平,形成了一些欠發達地區門閥制度的小政治氣候,進一步敗壞吏治,妨礙人才流入,又進一步影響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讓當地的年輕人‘逃回北上廣。”他認為,一線城市競爭激烈,生活、工作壓力大,但欠發達地區甚至連競爭的機會都沒有,樣樣靠人情關系網,所以很多年輕人寧愿選擇生活在相對公平的一線城市,也不回靠關系生活的家鄉。
這種體制性和結構性的缺陷其實到處都有,對于在北上廣艱難謀生的人而言,也有體制上的缺陷讓他們感到謀生之艱難。但正如許多人在解釋“為何難也要留下”時坦言的,內地、小城市和農村這些開放程度較差的地方,體制問題只會比大城市更多、更難解決。
一些媒體則認為,一逃一回,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區域發展不平衡,資源分布上巨大的差異。“很多的年輕人不能忍受的不一定是物質條件,更重要的是社會分配問題。比如公平競爭、自由度和市場規則等。這種不平衡不但是經濟發展程度上的,還包括競爭空間的公平自由度。”
《南方都市報》如此分析這些選擇的背后:“無論是逃離還是逃回,問題的根源都不應該細究一線城市或者二三線城市本身。具體到個人,逃離也好逃回也罷,當然有其復雜的個人因素考量,但從社會結構的層面切入,問題的核心還在于資源分配上的公平與否。”一線城市與二三線城市本身就存在不平等,政策資源的傾斜必然導致優質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的聚集,資源的不均衡則必然導致機會的不均衡。
甚至有專家認為,“逃離北上廣”未必不是好事。這樣的逃離,使大量聚集在大城市的人才等各種社會資源有個平衡,但是現在又“逃回來”,這種現象其實又加劇了這種不平衡。
2011年,門戶網站在分析“逃離北上廣”風潮時指出,那種真正適合年輕人發展并且大量吸納人才的中小城市,其實并不多。整個社會的資源與資本都在向大城市傾斜,交通、教育、醫療、文化等種種莫不如此。在資源分配不均衡的現階段,人力資源的逃離只會是社會資源的浪費,而不甘于守在小地方過著平庸生活的人們,最終只會回到北上廣。資源不“逃離”,人怎么會逃離?如今看來,現實似乎正在驗證著這一觀點。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