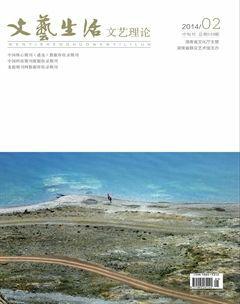淺析歷史與書(shū)法的辯證關(guān)系
王冉
(西南交通大學(xué)藝術(shù)與傳播學(xué)院,四川 成都 611756)
淺析歷史與書(shū)法的辯證關(guān)系
王冉
(西南交通大學(xué)藝術(shù)與傳播學(xué)院,四川 成都 611756)
一般說(shuō)來(lái),一個(gè)社會(huì)必然有一個(gè)社會(huì)的風(fēng)尚,這種社會(huì)風(fēng)尚也必然要影響社會(huì)文化的各個(gè)方面;而社會(huì)文化各方面對(duì)這一風(fēng)尚的歡迎或抵制,又必然會(huì)直接影響到這一社會(huì)風(fēng)尚的興盛與消亡。同樣,各個(gè)時(shí)代對(duì)書(shū)法藝術(shù)的審美風(fēng)尚也不一樣。如何引導(dǎo)這種審美風(fēng)尚,使之成為這一時(shí)代審美的主導(dǎo)風(fēng)尚,就成為各個(gè)時(shí)代書(shū)論家們所關(guān)注和探討的問(wèn)題。如漢魏時(shí)書(shū)論中的“尚象”、晉時(shí)書(shū)論中的“尚韻”、唐時(shí)書(shū)論中的“尚法”、宋時(shí)書(shū)論中的“尚意”等等,無(wú)一不是對(duì)各個(gè)時(shí)代書(shū)法藝術(shù)實(shí)踐中審美風(fēng)尚的總結(jié),而通過(guò)總結(jié)反過(guò)來(lái)又指導(dǎo)書(shū)法創(chuàng)作的實(shí)踐,促進(jìn)書(shū)法藝術(shù)的發(fā)展與繁榮。
漢字;歷史;發(fā)展聯(lián)系
漢字,亦稱中文字、中國(guó)字,是漢字文化圈廣泛使用的一種文字,屬于表意文字的詞素音節(jié)文字,為上古時(shí)代的漢族人所發(fā)明創(chuàng)制并作改進(jìn),確切歷史可追溯至約公元前1300年商朝的甲骨文。再由秦朝的小篆,發(fā)展至漢朝被取名為“漢字”,至唐代楷化為今日所用的手寫(xiě)字體標(biāo)準(zhǔn)——楷書(shū)。漢字是迄今為止連續(xù)使用時(shí)間最長(zhǎng)的主要文字,也是上古時(shí)期各大文字體系中唯一傳承至今的文字。中國(guó)歷代皆以漢字為主要官方文字。
中國(guó)的書(shū)法藝術(shù)開(kāi)始于漢字的產(chǎn)生階段,“聲不能傳于異地,留于異時(shí),于是乎文字生。文字者,所以為意與聲之跡。”因此,產(chǎn)生了文字。書(shū)法藝術(shù)的第一批作品不是文字,而是一些刻畫(huà)符號(hào)——象形文字或圖畫(huà)文字。原始文字的起源,是一種模仿的本能,用于形象某個(gè)具體事物。它盡管簡(jiǎn)單而又混沌,但它已經(jīng)具備了一定的審美情趣。這種簡(jiǎn)單的文字因此可以稱之為史前的書(shū)法。
中國(guó)文字產(chǎn)生伊始,書(shū)寫(xiě)者就有一種意識(shí)或是下意識(shí)的求美心里,并且人們還意識(shí)到它所蘊(yùn)含的外在的形式美,通過(guò)不斷的增進(jìn)、改善、發(fā)展逐漸過(guò)渡到把文字的書(shū)寫(xiě)升華為一門(mén)藝術(shù)。所以,書(shū)法藝術(shù)是中國(guó)的方塊象形文字為法身存在的基礎(chǔ),以中國(guó)特有的筆、墨、紙、硯為創(chuàng)作工具,在中國(guó)傳統(tǒng)的美學(xué)思想和審美方向指導(dǎo)下形成的在一幅幅絕妙的書(shū)法作品中無(wú)不表現(xiàn)獨(dú)特的風(fēng)采氣韻和精神意趣,我們?cè)谧屑?xì)看看書(shū)法家在書(shū)寫(xiě)漢字時(shí)中鋒、側(cè)峰、圓轉(zhuǎn)、方折,以及用筆的輕重表現(xiàn)的如此絕妙,那種書(shū)寫(xiě)中輕靈優(yōu)美難以言表的美,是西方各種畫(huà)派藝術(shù)無(wú)法企及的。
在研究書(shū)法史時(shí),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每個(gè)時(shí)代的書(shū)法的發(fā)展各具特色,差異頗大,雖然這種差異不是立刻顯現(xiàn)的,往往是長(zhǎng)時(shí)間累積的結(jié)果,但改朝換代對(duì)書(shū)法的影響卻是客觀存在的。秦代將文字統(tǒng)一為小篆之后不久,其統(tǒng)治地位到漢代就被隸書(shū)所取代,而到了魏晉,隸書(shū)又被楷行草書(shū)所掩蓋,除了文字發(fā)展自身的規(guī)律之外,難道就沒(méi)有其它原因了嗎?那為什么基本上同隸書(shū)平行產(chǎn)生的行草書(shū)不也在漢代成熟發(fā)展?為什么隸書(shū)在東漢剛剛成熟沒(méi)多久,其地位到魏晉就被楷行草取代了呢?為什么北魏會(huì)楷書(shū)碑版盛行?為什么唐代書(shū)學(xué)鼎盛,而到五代則幾成絕響?為什么宋代崇尚寫(xiě)意而元代則又主張復(fù)古呢?因?yàn)槊恳淮纬妫粌H是對(duì)現(xiàn)有成果的破壞,更是統(tǒng)治思想隨著形勢(shì)的發(fā)展服從于鞏固統(tǒng)治需要的不斷變化。
漢代的強(qiáng)盛必然要求與之相適應(yīng)的藝術(shù)形式,而隸書(shū)的質(zhì)樸內(nèi)質(zhì),飛動(dòng)的氣勢(shì),正是這種需要的產(chǎn)物;魏晉偏安江南,不思進(jìn)取,以閑雅陶情為尚,隸書(shū)古板怎比得上行草書(shū)更適合進(jìn)行揮灑,不拘形式!北朝異族統(tǒng)治,大興佛教,倡導(dǎo)來(lái)世,盛行厚葬,所以墓志相率而盛;五代十國(guó),戰(zhàn)亂不斷,人物喪失,人人自危,何暇從藝?元代同是異族入主,厚遇出仕的趙孟頫,力倡柔媚書(shū)風(fēng),掀起復(fù)古之風(fēng),是欲泯滅人們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不滿,使其安于現(xiàn)狀……正是這種因時(shí)而變的統(tǒng)治思想對(duì)書(shū)法史各朝代書(shū)體風(fēng)格的形成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
書(shū)法應(yīng)該如何書(shū)寫(xiě)?是書(shū)法語(yǔ)言自然延續(xù)的記錄,還是書(shū)法思想的客觀陳述呢?而作為歷史本身是否僅僅是一種真相的記錄呢?歷史的書(shū)寫(xiě)本身是否獨(dú)立于現(xiàn)實(shí)?
自然,以筆者疏淺的學(xué)力無(wú)法得出其答案,但是這一連串的、邏輯略顯混亂的發(fā)問(wèn)事實(shí)上則可以歸結(jié)為兩個(gè)層面,亦即書(shū)法史學(xué)的兩個(gè)研究維度:書(shū)法的歷史和歷史的書(shū)法。那么,書(shū)法史到底是什么呢?陳振濂將其分解為三個(gè)層面:書(shū)法史是歷史真實(shí)的再現(xiàn):書(shū)法史是史家觀念的展現(xiàn),與真實(shí)無(wú)關(guān);書(shū)法史中有真實(shí),但真實(shí)受觀念支配。其實(shí),后兩個(gè)層面可以合并為“受觀念支配的真實(shí)”這一層面。如果按照保羅·利科的邏輯,書(shū)法史所含蘊(yùn)的內(nèi)容就是書(shū)法歷史的客觀性和主觀性及其不同性和不同方向的思考、研究,在他看來(lái),書(shū)法史的書(shū)寫(xiě)本身就具有一種無(wú)限的多元性和可能性。
書(shū)法的歷史就是書(shū)法作為書(shū)法的本體演變史,而歷史的書(shū)法則是指從全歷史的視野加以觀照,所含蘊(yùn)著的書(shū)法的時(shí)代意義和歷史價(jià)值。前者的主體是書(shū)法,后者的主體是歷史。前者圍繞“書(shū)法”這一核心,就書(shū)法本體語(yǔ)言所延泛的文化、社會(huì)、思想等因素進(jìn)行陳述。后者的核心則是書(shū)法與時(shí)代的關(guān)系重構(gòu)的問(wèn)題,以此確定書(shū)法的時(shí)代文化身份。因此,前者對(duì)后者是一種體現(xiàn)和超越印證,而后者則是對(duì)前者的一種關(guān)照和限制。一部完整的書(shū)法史正是在二者的交互、回應(yīng)甚至沖突、悖離中得以延續(xù)和變遷。
[1]馬宗霍.書(shū)林藻鑒.
[2]班固.漢書(shū)藝文志.
[3]劉文正.書(shū)學(xué)之要.
J292
A
1005-5312(2014)05-014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