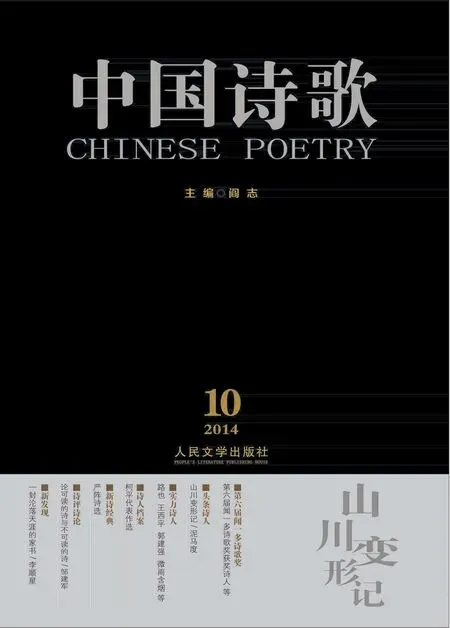蟄居的冒險(xiǎn)家:我理解的柯平的詩(shī)
□蔣 峰
蟄居的冒險(xiǎn)家:我理解的柯平的詩(shī)
□蔣 峰
柯平在他的詩(shī)里描繪的詩(shī)人或者說(shuō)詩(shī)意的處境深刻地吸引了我。這些詩(shī)歌大多寫(xiě)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交際處,仿佛一柄銅劍的鋒刃,既代表著陰陽(yáng)兩個(gè)世界,又展示著陰陽(yáng)兩面的沖突,更確切地說(shuō),可能是這兩種沖突在一雙柔軟的手中的和諧,這完全取決于一個(gè)讀詩(shī)者的態(tài)度。
我們時(shí)代無(wú)法回避的東西
和飛舞而來(lái)的東西是什么?
一排衰柳 兩塊殘碑 三只燕子。
電視臺(tái)隔壁的唐朝。
報(bào)紙里的冷雨。汽車(chē)后箱的四只花圈。
機(jī)器人手指處
杏花瞬間開(kāi)謝 使人無(wú)法救贖工業(yè)的罪行。
——《清明》
垂柳、燕子、唐朝、雨、杏花和殘碑、報(bào)紙、機(jī)器人、工業(yè)的罪行,交替出現(xiàn)在一個(gè)語(yǔ)言平面上,那些遠(yuǎn)在唐朝(假設(shè)就是唐朝)的詩(shī)意來(lái)到了這個(gè)世界上。你也許會(huì)說(shuō)這些詩(shī)意被機(jī)械的世俗包圍了。不,在柯平的詩(shī)意世界中,從來(lái)就沒(méi)有包圍,有交替,有平行,有穿梭,但是沒(méi)有包圍,也沒(méi)有封閉,你會(huì)看到在成堆的建筑物下面,在板著臉的行政指令下面,依舊有一絲青色的煙氣在縹緲,就像一只燕子,像一首唐朝的絕句,像一朵消失在手中的杏花,或者就像睡醒的柯平本人。
湖州市的官員們命令我在
沙礫下面歌唱黃金。
他們說(shuō):到生活中去!
于是我幽居水下
——《記憶中的湖州市》
柯平只是面對(duì)“我們時(shí)代無(wú)法回避的東西”。在我的理解中,這還不僅僅是一個(gè)“我們”的“時(shí)代”所無(wú)法回避的東西(柯平用了“我們”也許是出于他一貫的嚴(yán)謹(jǐn)),在所有的時(shí)代我們都有無(wú)法回避的東西,在兩晉,在唐朝,在二十世紀(jì),都有我們的必然性。但是在面對(duì)這種無(wú)法回避的東西時(shí),柯平的態(tài)度和他的詩(shī)意聯(lián)系在一起,沒(méi)有一絲浮躁的抱怨出現(xiàn)在他的詩(shī)中,只有對(duì)已經(jīng)逝去并且在不斷逝去的生活有足夠的理解力才能做到這一點(diǎn)。“可棲居的,這也許是結(jié)構(gòu)的最佳定義。”我們棲居在周?chē)纳町?dāng)中,可以不停地抱怨,但同時(shí)又不無(wú)痛苦地忍受著某些日常瑣事、習(xí)慣、樂(lè)趣、安逸、壓力等等。柯平詩(shī)意的花園早已從這些上面掠過(guò)。這是不是說(shuō)他的詩(shī)意已經(jīng)不具有現(xiàn)實(shí)性?不,他的詩(shī)歌具有了更高層次的現(xiàn)實(shí)性。那就是一種存在的現(xiàn)實(shí),或者說(shuō)一種空間的現(xiàn)實(shí)。他作為一個(gè)詩(shī)人同時(shí)作為一種詩(shī)意存在于這個(gè)世界上,唐朝、啼鳥(niǎo)、春日等詩(shī)意的象征從遙遠(yuǎn)的地方來(lái)到他的詩(shī)中,仿佛詩(shī)人是一個(gè)來(lái)自詩(shī)國(guó)的過(guò)客,而他的詩(shī)意和他的詩(shī)意的到來(lái)都不是單純的:
生活真難啊
既要保持皮膚的濕度 又要柴米油鹽。
走到市場(chǎng)門(mén)口 他在鱸魚(yú)眼睛里
看見(jiàn)魏晉風(fēng)度 他發(fā)出驚呼
他寫(xiě)下獻(xiàn)給張翰的詩(shī)句 但運(yùn)龍蝦的飛機(jī)
將他純情的吟唱打斷。
——《春日起床的詩(shī)》
但是他的詩(shī)意從來(lái)沒(méi)有在國(guó)家、機(jī)械、菜場(chǎng)或商店的混響中淹沒(méi)、沮喪。柯平不停地在詩(shī)歌中書(shū)寫(xiě)自己,從來(lái)不為了希求眾人的喝彩而降低詩(shī)歌的濃度,一種精神從他的詩(shī)歌中表露出來(lái):
道場(chǎng)山上的塔。
你想知道我對(duì)你
真實(shí)的愛(ài)情嗎?
我寧愿看到你
在仇恨的大火中塌陷,
也不想看到你
被塑料的面孔圍擁。
——《道場(chǎng)山上的塔》
這是柯平所有詩(shī)歌中最激動(dòng)、最直接的詩(shī)了吧?我們很多人都錯(cuò)誤地認(rèn)為存在另一種現(xiàn)實(shí),或是認(rèn)為現(xiàn)在我們所處的是一種不理想的現(xiàn)實(shí),認(rèn)為還存在一種更為理想的現(xiàn)實(shí),其實(shí)現(xiàn)實(shí)只有一種,就是你生活于其中的。當(dāng)我們期待另一種現(xiàn)實(shí)的時(shí)候,我們其實(shí)在期待一種意義,然而意義和現(xiàn)實(shí)并沒(méi)有關(guān)聯(lián),相對(duì)于我們?cè)跁r(shí)間撐起的那個(gè)空間來(lái)說(shuō),意義簡(jiǎn)直就不值一提。柯平在他的詩(shī)歌中并不提現(xiàn)實(shí)的意義但是他的詩(shī)歌和生活卻明顯地流露一種信仰對(duì)作為一個(gè)詩(shī)人的存在的信仰,對(duì)作為一種意義的空間的信仰。盡管這種存在和空間與周遭的一切發(fā)生關(guān)系、碰撞、受到擠壓,但是這個(gè)空間依然如煙似霧,輕吟低唱,在你的面前蕩漾,這就像一株混凝土建筑屋頂上的瓦楞草。
高速公路上的浪子 騎著一頭蹇驢
他將在斜挑的酒簾下暢飲青島啤酒。
看春江水暖 汽艇在上面橫沖直撞
螺旋槳卷住蘇軾的青布長(zhǎng)衫。
有人在電視塔上吹笛,看到的人都喊“危險(xiǎn)”!
但我覺(jué)得這樣很好
他已經(jīng)穿過(guò)雨季 進(jìn)入晴朗的部分。
——《清明》
柯平有一雙特別的眼睛,就像電影鏡頭一樣在看著自己,看著自己走過(guò)。咸陽(yáng)古道和青島啤酒、螺旋槳和蘇軾的青布長(zhǎng)衫一起糾纏在鏡頭中,不同的是,一種是變化無(wú)常的現(xiàn)實(shí)一種是“垂之久永”的歌聲,但當(dāng)兩者共同出現(xiàn)在鏡頭當(dāng)中,已無(wú)高低貴賤之分,他們共同組成了柯平的過(guò)去、他的空間、他的詩(shī)意的生存。我不想說(shuō)也許我們對(duì)柯平的詩(shī)歌關(guān)注、理解得都還不夠,因?yàn)槲蚁嘈乓欢〞?huì)有另一雙眼睛將柯平和他的世界也放進(jìn)自己的鏡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