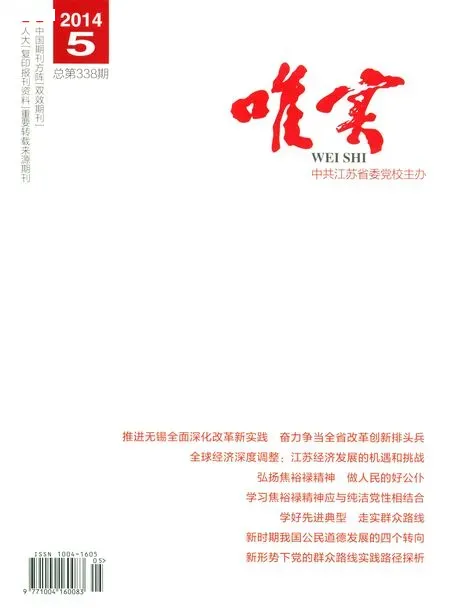權利視角下的我國收入分配格局調整
金雁
權利是收入分配最為重要的基礎性內生變量,追索收入分配背后的權利因素以及與之相聯系的權力分配,是對我國收入分配關系進行制度性調整的基本前提。我國收入分配結構失衡的根源是權利結構的失衡,因此,公平配置權利應成為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
一、收入分配中的權利因素
1.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首先是一項“權利”
要素報酬由市場決定是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基本分配原則,其基本規定性為,個人收入由其投入經濟活動中的生產要素的量和與之對應的價格決定。從權利的角度分析,我們可以認為,收入是由一系列的權利及其實現程度決定的。
經濟主體對生產要素所擁有的交換權利是影響收入的關鍵因素。在完整的交換權利下,權利人對生產要素的市場交易至少應擁有兩個方面的選擇自主權:一是可以自主決定生產要素是否轉讓;二是可以決定要素轉讓的方式、范圍、對象和最低索價等。但是,在現實中,擁有要素的法律歸屬權并不意味著擁有完整的要素交換權,制度規則、社會條件等因素往往會削弱或剝奪其部分的要素交換權,如我國農民對其土地和勞動力的交換權利就是殘缺不全的。要素交換權的殘缺或不平等,剝奪了要素所有者的獲利機會,進而影響其收入或收益。
社會權利的現實擁有狀況是影響收入的重要因素。知識、技能、經驗、偏好、健康等個人特性的差異使每個人發現機會、捕獲機會進而獲得較為有利的要素交易條件的能力大相徑庭。與對要素的所有權不同,由個人特性決定的權利行為能力具有很強的可塑性,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民社會權利的現實擁有狀況是最為重要的影響因素。可見,社會權利的現實擁有狀況通過要素支配能力的傳導成為收入分配的重要影響因素。
制度是一種對社會權利結構及其相互作用機制的規定,既規定了經濟主體的權利邊界,同時又是其權利的保障機制。政治參與權利在不同主體間的配置以及各個經濟主體政治參與能力的差異必然導致制度的偏向,導致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的差異,進而帶來收入分配的差異。
可見,市場經濟條件下,按要素分配實質上是按權利分配。對生產要素的所有權、交換權、社會權利及政治參與能力都是制約分配格局的重要因素。
2.權利平等是公平分配的基礎
權利平等決定公平分配。權利平等并不意味著收入均等,相反,權利平等條件下的按要素分配,要素所有者所擁有的要素所有權不同、個人能力和努力程度的不同,必然導致其收入的差異,這種差異是必然的,也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效率的源泉。但是,權利平等卻能保證一種可接受的公平分配制度。
首先,權利平等要求每個人自由選擇并自行承擔選擇的后果。公平分配的基礎是自由選擇。權利平等保證了個人自由選擇的各項權利是可靠、完整和平等的,相應地,個人必須承擔起相應的義務,并對自己自由選擇的后果負責。
其次,權利平等保證了收入分配的程序正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分配的程序正義首先表現為平等地分配機會,而機會平等的背后是權利的平等,即建立一種開放的社會體系,各種機會都向所有人敞開,人人都擁有平等的權利去把握這些機會。
第三,權利平等有利于收入流動性的提高,實質性地改善收入不平等的狀況。一方面,較快的收入流動性特別是快速地向上流動,可以從實質上改善收入不平等的狀況。加快收入流動性是促成并擴大一個國家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路徑;另一方面,收入流動也可以大大減少不同收入階層之間的社會心理壓力以及社會矛盾。收入流動性的大小從根本上依賴于權利平等、機會平等的市場環境。權利與機會越平等,每個人通過努力改變目前收入狀況的可能性越大;相反,各種特權阻滯了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有效配置,必然降低社會的收入流動性。
二、權利結構失衡:對我國收入
分配格局的現實分析
我國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表現為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勞資之間以及國家與民眾之間的收入差距。在這種收入分配結構失衡的背后,是權利關系、權利結構的失衡。
1.城鄉之間權利失衡
城鄉差距是導致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最大因素,而城鄉居民的權利差異,則是城鄉收入差距的最為重要的根源。首先,農民交換權利的殘缺,造成城鄉居民收入機會的巨大差距。從財產要素看,土地和住房是農民的主要財產,但是,政府對土地市場的壟斷、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對土地交換范圍和用途等的嚴格限制,使農民幾乎失去土地和住房的交換權利,難以從中獲得財產性收入。從勞動力要素看,戶籍制度及二元勞動力市場的壁壘,限制了農村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使之成為勞動力市場中最弱勢的受雇群體。其次,農民社會權利的不足,造成了城鄉居民獲取收入的行為能力的差距。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的差異造成城鄉居民人力資本積累的差異,影響農民獲取收入的能力與機會。
2.勞資之間權利失衡
與資本報酬相比,我國的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這與我國“資強勞弱”的權利格局密切相關。資本與勞動的權利關系的失衡,固然與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和勞動力過剩的市場供求關系相關聯,但是,勞動者集體權利的缺失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勞動者的權利包括個人勞權和集體勞權。個人勞權是指勞動者作為個體享有的勞動就業、工資、休息休假、職業訓練、社會保險、職業安全等權利。集體勞權則是為了抗衡資本的強勢地位,改變個別勞動關系實際存在的不平等而賦予勞動者集體享有的權利,包括團結權、集體談判權和爭議權等“勞動三權”,是勞動者運用組織力量維護自身利益的權利。從我國勞動關系的現狀來看,還只是剛剛建立起個別勞動關系的調整范式,以“勞動三權”為核心的集體勞動權利體系的確立和有效行使尚有許多障礙,從而導致勞資之間嚴重的權利失衡,資本獲得了超強的收益索取權。
3.民眾與政府之間權利失衡
民眾與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權利失衡是我國收入分配諸多問題的根源。政府的公共權力進入市場,并且與市場主體的權利發生粘連,形成了特權。其后果,一是嚴重抑制了民眾的權利。政府掌握著大量資產權利,獨占著諸多領域的投資權和經營權,控制著資金、土地、礦產等重要生產要素的配置權利,民眾參與經濟活動的各項權利被限制和侵害。二是形成了壟斷特權。這種壟斷特權最終體現在供電、電信、金融、煙草等壟斷行業的畸高收入上。三是權力尋租行為泛濫,形成大量灰色收入,對我國收入分配格局造成非常嚴重的不良影響。endprint
三、公平配置權利:收入分配格局調整的制度支點
收入分配的背后是權利配置,權利的公平配置是收入分配公平的基礎和前提。要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必須先賦予農民平等的公民權利待遇;要縮小行業收入差距必須先打破壟斷行業特權;要縮小不同階層收入差距必須先實現各階層權利平等。否則,收入分配改革無解。縮小貧富差距的根本出路是權利的“等貴賤”,即盡可能保障公民在市場、社會和政治各領域里的權利平等,而不是分配結果的“均貧富”。
1.調整政府權利與民眾權利的關系,賦予民眾權利應有的地位和選擇空間
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是國家與民眾之間的權利關系的調整,是國家高度集中的經濟權利向社會民眾的逐步回歸。政府還權于民,將生產要素的配置交給市場,一方面,可以消除公權對于民眾經濟權利的剝奪和抑制,賦予民眾權利在市場經濟中應有的地位和更大的選擇空間;同時,更能夠減少因政府公權介入生產要素配置而產生的種種特權以及由此產生的大量不公平分配。首先,要為國企定性、定界,將國有資產從一般競爭性領域向公共產品領域轉移,從而為民間資本騰出更多的發展空間;其次,要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對民間資本全面開放各投資領域,使之能夠自由投資、自由創業;再次,要完善各類要素市場,消除對資金、資源、人才、信息等各種生產要素的行政性壟斷和區域流動、城鄉流動的制度性障礙,使生產要素的供求雙方能夠通過市場自由流動、自由選擇、自由交易。
2.注重改革與發展的均衡性,消除改革與發展進程中非均衡的權利配置
統籌城鄉發展。要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體制機制,消除城鄉居民在經濟、社會、政治等各方面的權利差別。其中最為關鍵的,一是確立和保護農民土地和住房等財產權利的完整性與可靠性;二是城鄉公共服務均等配置以保障農民的社會權利;三是戶籍制度的一元化以保障農民的自由流動權利。
統籌區域發展。我國的地區收入差距不僅源自區域間的要素稟賦差異,同時也是梯度推進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戰略帶來的區域經濟權利差距的結果。因此,不僅要在制度和政策上給予欠發達地區同發達地區平等的經濟權利,而且,要加大對其資金、技術和人力資本等各方面的扶持力度,補償其長期累積的發展差距,防止其陷入權利的“貧困陷阱”。
加大改革力度。破除對舊體制下既得利益者的保護,調整“利益存量”,均衡“體制內”與“體制外”的權利配置。尤其是對壟斷行業和國有企業等與公權力相聯系的既得利益者的自我改革,更需要“壯士斷腕”的勇氣。
3.完善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的供給機制,保障公民社會權利的均等化
構建一個平等的收入能力基礎,最為關鍵的就是要構建一個平等的社會權利體系。社會權利是與公民資格相聯系的,權利平等是社會權利的基本特征。然而,在現實中,欠發達地區和農村的部分民眾,因公共服務缺乏可得性與可及性而無法充分實現其社會權利。因此,必須通過推進公共服務對不同區域、不同群體的均等化供給,縮小公民社會權利的實現差距,確保公民參與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起點公平。
4.建立健全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博弈機制,以社會建設推進權利平等
只有通過平等參與、公平博弈而形成的收入差距,才是具有社會合法性的差距,既能解決差距的合理性問題,又能保持差距的正向激勵功能。在這一點上,政府的最佳選擇是建立健全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博弈機制,即承認不同的社會群體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護其權利;在社會利益主體間建立起溝通和協商的渠道;構建制度化解決社會利益沖突的機制。其中,保障博弈公平性的關鍵是確立和保障工人、農民的集體權利,即建立組織和集體協商的權利。權利聯合起來的力量,比起政府的善良愿望更加有助于公平和獲得平等權利。沒有這種自我的力量聯合,即使公權力完全站在弱勢者這一邊,也很難改變偏向于強勢者的利益分配格局。
5.保障公民政治參與權利,創造獲取平等政策的平臺
相對于其他決策方式來說,民主決策更有利于平衡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更能合理地對社會利益和社會負擔進行分配。因此,要切實保障民眾的有序政治參與權利,提升政府決策的民主化水平。一方面,要限制強勢群體在政治領域中的影響力,特別是排除既得利益集團的干擾,減少財產不平等對政治平等的不良影響;另一方面,要使更多的弱勢群體進入公共決策領域,公平配置各類參政議政的機會,使他們的訴求能夠對公共決策產生應有的影響。
(作者單位:中共南京市委黨校)
責任編輯:浩 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