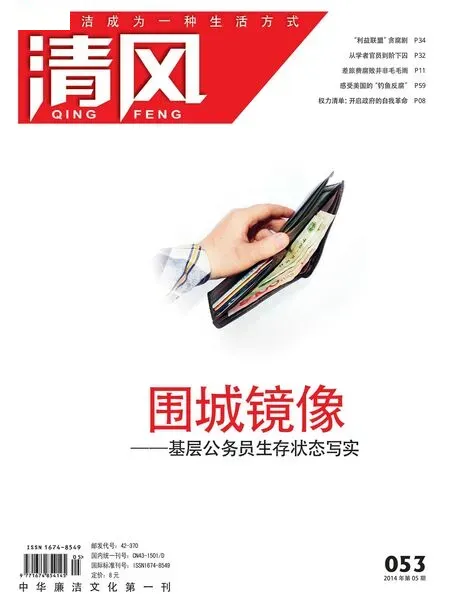岳陽縣公務員的“相對論”
文_本刊記者 王義正
岳陽縣公務員的“相對論”
文_本刊記者 王義正
談到公務員,會給人什么印象?在高檔的辦公樓中辦公,收入穩定、高福利,不交養老金,與老百姓打交道話難聽,事難辦,臉難看……事實真的如此嗎?
同樣是公務員,其實也存在很大的差異,這些差異主要緣于職務級別、部門職能、所在地域、地方政策等各方面原因。而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往往看到的是那些級別較高、職權部門較強勢、經濟發展較好地區的公務員,因為他們所掌握的公權力由于客觀原因所附加的東西,更容易被公眾關注。但是,公務員并非只有他們,還有一些級別相對較低、職權相對較小、所在地域相對欠發達的公務員,他們似乎很少被關注,但卻是公務員整體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基層公務員的“圍城”
如今,很多事情不能再純粹地從經濟收益出發了。但如果單從職業的選擇來說,當公務員真不如出去打工。
2011年,從湖南師范大學畢業的黃和平,通過參加國家公務員考試進入了湖南省岳陽市岳陽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經過三年的努力,如今已經是人社局辦公室副主任了。
在外界看來,二十多歲就能在縣里任個一官半職,多少也算是年輕有為了。但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黃和平卻似乎不這樣想。他告訴記者,他的工資收入主要包括職務工資和級別工資,每個月只有1000元左右。全年所有福利、補貼共18600元,平均每月1550元。平均每月下來的收入2500元左右。正當記者感到詫異時,黃的一位同事告訴記者,其實黃每個月都需要家里的接濟。
如今已年近三十的黃和平,無房、無車、無存款,有的只是這份讓很多“局外人”羨慕不已的工作。但這份工作的“性價比”到底如何,值得深思。
黃和平說:“當時報考公務員,一方面是受社會輿論影響,大家都覺得這個職業好,每年很多人報考,所以自己就隨大流了。另一方面是父母要求考公務員。但時至今日,自己有些懷疑當初的決定是否正確。”
自秦朝“以吏為師”開始,崇官心理便在中國人的頭腦中更加深入。隋唐的科舉制更是將這一思想進一步深化加強,即便今日,這種影響依舊余音不絕。然而,當記者問及公務員在社會生活中是否真的會受人尊敬和追捧時,黃和平及其同事卻說:“時代不一樣了。當下的人更多是以社會財富來評判一個人的社會價值;對于公務員,尤其是基層公務員而言,在社會生活中沒有任何特殊性。”
今年已經35歲的游毅是岳陽縣相思鎮的經管站長、紀委副書記。他在相思鎮上班之前,曾經在廣東打過8年工,他告訴記者,比起打工時的收入,現在差了一大截。如果不是因為妻子的收入相對可觀,自己的壓力將會非常大。“俗話說,父母在,不遠游。況且父母年事已高,很多事情不能再純粹地從經濟利益出發了,只能回到這里。但如果單從職業的選擇來說,真不如出去打工。”
在鄉鎮單位工作是不分節假日和上下班的,因為很多村民沒有這個概念,只要有事就會來找你;如果不解決,就可能引發誤解。加之鄉鎮一級的基層公務員往往身兼數職,因此加班加點是常事。游毅是相思鎮經管站長、紀委副書記,同時,還要負責綜合治理和計劃生育等方面的工作,工作壓力十分大。由于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民眾的民主法治意識越來越強,按道理說這是好事;但少數群眾對法律和政策往往一知半解,卻又喜歡鉆牛角尖,這樣一來,反而加大了基層公務員的工作難度。
為什么不“出城”
雖然收入不高,但時間很充裕,可以有比較多的時間照顧家庭,這是很多人堅守在“城內”的重要原因。
有人可能會認為,基層公務員叫苦是在“撒嬌”“矯情”;也有人會質問,當公務員收入低,為什么不辭職呢?
吳秀英是岳陽縣人社局公務員管理股股長(副科級級別),從1991年參加工作至今,她可謂“貨真價實”的基層公務員代表。然而對于這個職業,她似乎有很多異樣的感受。“公務員就像是一座圍城,外面的人想進來,里面的人想出去。但到了我現在這個年紀,出去還能干嗎呢?在這里幾十年了,沒有任何特殊生存技能,而且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方式,所以就只能在這里等退休。工資再低也沒辦法,只能這樣。如果再年輕點,我可能就出去了,有個一技之長,那肯定收入比這里高。”或許正如吳秀英所說的那樣,其他生存技能的缺失以及公務員的生活習慣,使她成為“圍城”中的寄居者。
唐榮平是岳陽縣縣委宣傳部新聞辦公室主任。對于她來說,從事公務員這一職業似乎挺好。黃榮平告訴記者,自己喜歡新聞學方面的東西,也很樂意做這方面事務性的工作。在縣委宣傳部工作,接觸最多的就是媒體人,有時一天要接待好幾批。
唐榮平說,自己一直很向往新聞職業,然而沒機會成為一名職業新聞人,但在這里能從事新聞方面的工作也十分不錯。偶爾還能自己寫一寫稿子,對外宣傳岳陽,能為家鄉做一些事情,覺得很有成就感,關鍵的是自己喜歡做這個。談到經濟收入和工作壓力等方面的問題時,唐坦然說,能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其他的也就無所謂了。
當記者問及為何不離開公務員隊伍二次創業時,岳陽縣人社局辦公室副主任黃和平苦笑著沒有回答。記者揣測原因,可能與公務員時間充足、工作穩定及能照顧父母不無關系。但另一個原因可能就是等待升遷。如今,他還不到30歲已經小有所成,有機會能獲得提拔。然而,對于大多數基層公務員而言,升遷真的那么容易嗎?
基層的“磁鐵吸力”
基層就像是一塊磁鐵,大多數公務員都被“吸住”在這里,可能是幾年,也可能是一輩子。
李滿秋在相思鎮工作已經27個年頭了,從事司法工作10余年,成功調解糾紛2000余起,2011年被評為“全省優秀人民調解能手”,2012年被評為“全國優秀人民調解能手”。但這么多年,李滿秋依舊供職于相思鎮司法所。
采訪中,記者特意去了李滿秋的住處:一棟有些年頭的磚木結構兩層小樓。門上的紅漆已經脫落,斑駁的墻上留下了風吹日曬的痕跡。李的妻子沒有什么文化,所以這些年一直在家里務農,以此來補貼家用。
當記者問及這些年最大的收獲是什么時,李笑著說:“老百姓都認可我,贏得的是老百姓的吆喝聲。”但當下又有多少人是為了賺取老百姓的“吆喝聲”而成為公務員的呢?
對于很多報考公務員的年輕人來說,考公務員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考上了公務員卻發現要想晉升簡直是“千軍萬馬走鋼絲”。眾所周知,基層公務員的升遷,是一個十分繁雜的過程。首先,是考上公務員先“入門”,入門后先是一年的試用期,一年后才能從“臨時工”成為正式公務員。兢兢業業工作三年,才有機會從科員升為副科級,再三年成為正科級。到這里,才算正式邁入領導階層的第一步。
然而,這只是理想狀態下要走的正常程序,大多數基層公務員其實到了這里就到此為止了。而要真正成為領導還需要組織部門的培養。從近期官方給出的數據顯示,其出線率僅為4%。從整體來看,基層公務員最少需要13年的基層鍛煉,日常工作則是一個不確定的函數,真正能算出正確答案,成為領導的人又能有幾個呢?基層,就像是一塊磁鐵,其實大多數基層公務員都被“束縛”在了這里,可能是幾年,也可能是一輩子。
記者前往岳陽縣采訪時看到這樣的情形:在縣委大樓的大廳里,一位年過六旬,手中提著一個白色編織袋,腳穿一雙貌似很久沒洗過的“解放鞋”的老大爺,正在大廳里徘徊。正當記者猜測老人前往縣委的意圖時,門衛給老人送來了一杯熱茶。記者在最后寫上一個貌似跟全文都沒有關聯的事情。然而,門衛的一個舉動、一杯茶,能給人很多思考。
近年來,由于反腐的力度不斷加大,媒體監督的力度不斷加大,越來越多的貪官墨吏被媒體曝光,越來越多的公權力部門不作為、亂作為的現象被質疑,公務員在社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甚至被“臉譜化”“污名化”,一定程度上被涂抹了負面色彩。但中國有著960萬平方公里的陸地面積,全國有34個省級行政單位,有著702萬公務員,不能一概而論。至少在岳陽,記者的所見所聞,讓人不至于失望。一杯茶很簡單也很普通,但這是對群眾的一種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