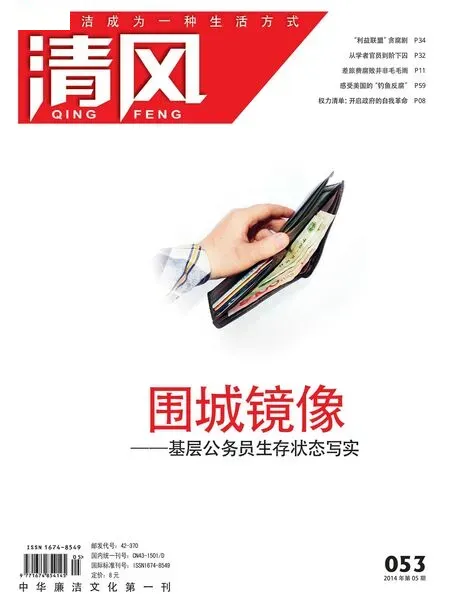沉重的錯位
文_康德滬
沉重的錯位
2013年8月14日下午,50多歲的陶福友身著囚服站立在江蘇省鎮江市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的被告席上,他的頭垂得很低,或許是沒有勇氣抬頭看看眼前身后的這些人吧。這個地方對他來說,實在是太熟悉不過了。過去的30多年間,他沒少來這里,但每次都是坐在那高高的深色法官椅上,身穿法袍,威嚴無比。而如今,他卻站立在這個與從前相對的地方,等待審判長莊嚴的宣判。
一審判決下達:他犯“受賄罪”和“濫用職權罪”,兩罪罪名成立,證據確鑿充分,判處有期徒刑13年,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10萬元。陶福友自知“罪有應得”,對于這一判決,他表示認罪服判,不上訴。
一名曾經優秀的法官,何以淪為階下之囚?陶福友的蛻變過程究竟如何形成的?這些問題值得人們深思。
“問題法官”浮出水面
最初發現陶福友的問題是在2009年下半年,南京市審計局在一次審計工作中發現,南京雨花臺區法院執行庭原庭長陶福友、執行員駱濤和南京一家服飾有限公司企業法人朱順達、周亞寧和黃國等人存在著諸多違法犯罪嫌疑。當時查出的主要問題是:陶福友等人將集體土地以國有土地的名義進行資產評估,并故意大幅度高估地價;雨花臺區法院違規發函辦理拆遷,導致相關公司得到超標準補償,金額共計757.70萬元,讓國有財產遭受重大損失。
這一查,問題相當嚴重!陶福友身為一名法官,本該用法律的利劍主持公平正義,可是他卻在辦案過程中,把“以事實為基礎,以法律為準繩”的司法原則拋到了一邊,而是打著“法律”的名義,給相關人員謀取利益,然后自己坐等好處降臨。
審計人員順藤摸瓜,陶福友的其他犯罪行為也相繼浮出了水面。2008年4月,南京市雨花臺區西善橋街道的一家磚瓦廠土地使用權及地上修建的房屋,由商人賈正炎以220萬元價格從法院拍賣取得。雖說名義上這筆錢是由賈正炎所在的南京一家服飾公司所出,但實際上,出資者還有股東金鑫發和洪坤財,他們各占股32%,賈正炎只占股36%。時間到了2010年5月,這塊土地要被征用拆遷。賈正炎覺得發財的機會來了,他與另外兩名股東一番商定后,將本來只有220萬元購買的土地,拆遷時要價提高到1500萬元。為了提高談判的籌碼,3人又將磚瓦廠拍賣裁定書進行篡改,將220萬改為420萬。
一天下午,金鑫發通過關系,找到了負責此次拆遷執行工作的法官陶福友,請他在拆遷事情上給予“關照”,并承諾幫忙后必有重謝。
陶福友心領神會,他安排相關人員對此地塊重新進行評估,將實際評估不到500萬元的磚瓦廠集體土地使用權及房屋,當作國有出讓土地使用權進行評估,將拆遷補償款定為980余萬元。這樣算下來,3人可多拿489萬元。
2010年10月,拆遷款到賬后,金鑫發拿著20萬現金送到了陶福友辦公室,陶福友欣然接受。
曾是“先進個人”“十佳法官”
陶福友畢業于名牌大學,最初走上法官之路時,他頗有一番自己的想法:一心要為百姓打好官司,彰顯公平正義。最開始時,他的確也是如此做的。曾與他共事過的人都還記得,陶福友曾經負責辦理過一件民事案,一方當事人要請陶吃飯,陶福友礙于相關朋友的面子,還是去了飯店。但坐下后,他一口酒不喝,一口菜也不動,只是從法律和道義上給當事人說道了兩個多小時,語重心長的話語,說得那位當事人緊緊地握住了他的手,激動地說:“陶法官,你這是在給我們上教育課啊,我們算是碰到大好人了!”案件庭審宣判結束后,雙方當事人均感到滿意,雙雙向法院送來錦旗。這之后,在新法官上崗宣誓時,老法官都會把這個故事當作經典范例講出來。
文_康德滬
從事審判工作30多年來,陶福友曾榮獲“全國法院執行工作先進個人”和“南京市十佳法官”等榮譽稱號。由于工作突出,他也從一名普通法官一步步地走上執行局長的位子。雨花臺區法院于2009年年初召開的年度工作表彰大會上,法院院長在總結報告中說,“去年以來,我院涌現出了以‘全國法院執行工作先進個人’陶福友為代表的優秀法官群體,這是我們作為法官的驕傲……”
然而實際上,陶福友的思想早已經悄然發生變化,他變得聽不得批評,而只熱衷于聽那些奉承的話。思想發生變化后,行動上自然得到體現。于是,那個過去常在辦公室燈下夜讀、廉潔自律的陶法官,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取而代之的是混跡于燈紅酒綠場所里,夜夜歌舞升平的他。夜夜歌舞升平是需要大量金錢來支撐的,誰來買單?當然是那些與其有著利益勾連的群體。執行局長手中的權力有多大,圍在他身邊的那些人自然知曉。
2010年7月,在一起執行工作中,陶福友嚴重違反程序,違規操作,違法作出執行裁定,給一家企業造成了數百萬元損失,陶福友也因此被法院予以行政記過處分。如果陶福友記住了那一次的教訓,那么他可能會在以后的工作中牢記準則,盡職盡責,也就不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了。然而,處分并沒有給他帶去什么改變,他依然行進在通往泥潭的路上。
執行官“原則性很強”
事后雖說陶福友吃了處分,但在執行工作中,他的地位與人氣依然很旺。業界人士對他的評價則是,在受到處分以后,他堅持的“原則”已不是公平公正,而是“不給錢拖著不辦”“給錢就辦好,歪的也能辦成正的”。
辦案人員在調查中發現,陶福友在利用職務便利的同時,還會充分利用自己的法律專業知識,想盡一切辦法把不可能變成可能。2010年年初,陶福友將權力范圍內裁定的一筆1500萬元的款項扣到法院,因為相關當事人的利益協調沒有達成一致,陶福友利用權力掌控,把此案從這一年的2月初拖延至5月中旬,然后才對銀行和當事人提出的執行異議進行立案受理。工作人員在審理過程中發現,因為陶福友所在法院對此案沒有管轄權,案件隨后被移送到另一個法院。在法院判決生效前,陶福友不顧執行工作原則中規定的“執行的標的物確是其他法院或仲裁機構正在審理的案件爭議標的物,應當裁定中止執行”的規定,指示相關人員違法將1100萬元執行款發給不該得到錢物的一方公司,導致二審法院的判決無法執行,銀行貸款本息共計1100萬元無法追回。目的一經達到,陶福友的好處自然是少不了,至于原則和規定,早已被他拋到了九霄云外。
在陶福友最后的法官生涯中,執法原則早已成了他自己的一套歪理原則,即“以金錢為基礎”,以“拖著不辦、敲你竹杠、和稀泥”為辦事三部曲。
還有一個案子也很能說明問題,在將南京一家材料總公司申請執行淮安市漣水縣建筑工程公司駐南京辦事處貸款一案的辦理中,陶福友明知有許多違規的地方,但他硬是將該案協調到了其所在法院來辦理,致使他所幫助的當事一方獲得的利益不小。半個月后,這家利益所得公司的一名辦事員專程來到陶福友辦公室,把裝在一個大信封里的5萬元送到了陶的手上。這名辦事員至今對當時的情景記憶猶新:陶福友收下5萬元后,很客氣地給他泡茶,與他聊天,送他出門,還站在法院高高的臺階上,向他揮手致意……這名辦事員說:“這樣的法官真的很好當,他拿了5萬元,就好像什么事也沒發生一樣。托他辦這事,才幾天工夫,他拿到的錢,相當于我一年的工資。”不過用陶福友的話來說卻是:“在伸手向別人要錢時,此時此刻,雖伸手,表面上看似無事,心里其實還是會有些發慌的。”
說是這么說,但至于是不是真的“心里會發慌”,恐怕也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了。2008年8月,陶福友為請托人吳治國獨資的南京一家機械配件廠拆遷事宜謀取了不正當利益。吳隨后便驅車拿著錢來到了位于南京市雨花南路上的雨花臺區法院大門口,吳在明晃晃的國徽下,明目張膽地將10萬元現金塞到了陶福友的包里。
拒腐不能只靠“精神定力”
“無論是誰,做什么也別犯罪。哪怕是跪在大街上乞討,也好過失去自由。”2013年8月,在神圣的法庭上,審判長向陶福友宣布他還有最后陳述權的時候,陶發出了這么一番感慨。他邊說邊流淚,現場氣氛很是凄涼。
陶福友說,一切的錯誤都是從“利益魔鬼”鉆進了心里開始的,為了追求個人私利,他不惜投機鉆營,玩弄法律,最終掉入錢眼。“只要有錢,什么違法的事都敢干,不怕。從開始收一點拿一點、撈一點占一點,不犯大錯;到后來吃一點喝一點、玩一點樂一點,是人之常情無傷大雅;再到最后剎不住車。這一系列變化過程中,我就像一個有病的人,不去治,任其發展,小病變大病,大病成重癥,重癥不治,直至死亡邊緣,真的很后悔!”
南京法院系統的一位資深法官在總結陶福友案時,感觸很深,他說:值得警示的是,拒腐的確是需要“精神定力”的,一個人走上領導崗位后,都有可能要面臨許多嚴峻考驗,比如以前夢寐以求的,現在唾手可得了,如何把握?各種各樣的誘惑實在是太多了,面對這一切,法官是什么,你始終牢記著嗎?一個人民的法官,到什么時候都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
司法是守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而一個本身就底線失守的法官,能夠守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嗎?如果拒腐只能靠法官的“精神定力”,那么,“陶福友們”的出現就不會是偶然。這個問題,值得有關部門認真審視。
(文中除陶福友外均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