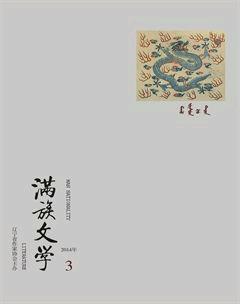邊臺漫記
楊子
這篇札記是由兩枚老銅錢引出的。
今時我手中,藏有兩枚碧影粼粼、銹跡斑斑的老銅錢,素以為珍之。這兩枚老銅錢,一枚為“昭武通寶”,一枚為“洪化通寶”。“昭武通寶”,鑄于清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此際吳三桂于云南昆明舉旗反清,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加冕周王,國號為周,年號昭武;“洪化通寶”,鑄于康熙十七年,即1678年,此際吳三桂已死,其孫吳世璠于湖南衡陽嗣位,年號洪化。周吳王朝,歷時八年,至康熙二十年,即1681年,以吳世璠自殺身亡,宣布告終。吳三桂本在云南稱帝,吳世璠本在湖南登極,然而,這兩代王的鑄幣,即“昭武通寶”、“洪化通寶”,卻在關東柳條邊出土,且發(fā)現(xiàn)地點接近臺邊小城九臺。其地理相距千里萬里之遙。那么,怎會有這種情形呢?這就關系到這道柳條邊與吳三桂遺丁落籍的事了。
吳三桂原籍遼東人。其舅父祖大壽,為明末鎮(zhèn)守山海關總兵,后歸順大清。現(xiàn)在遼寧興城,仍有祖大壽號稱“登壇駿烈”坊,以彰顯其功績。然而這事,卻被乾隆帝所看不中,曾寫詩譏諷道:“燧謹寒更烽候朝,鳩工何暇尚逍遙。若非華表留名姓,誰識元戎事兩朝。”吳氏覆滅后,其部下便被遣送到柳條邊沿邊效力當差,其稱謂為臺丁。無疑,這兩種銅錢,是其由云南、湖南一帶,經(jīng)迢迢漫漫旅途,帶到關東大地,遺落柳條邊沿邊地帶的。清初順治年間,曾在遼東鳳凰城至山海關,修筑一條長達一千九百余華里的柳條邊,史稱“盛京邊墻”,又叫“老邊”;清康熙初年,又在遼北開原威遠堡至吉林舒蘭卡岔河,修筑一條長達六百九十余華里的柳條邊,史稱“新邊”。這里所說的,即柳條邊新邊。柳條新邊,在經(jīng)由舒蘭、九臺地段,沿途設有九個臺,即:頭臺,置舒蘭法特鎮(zhèn)頭臺河西,今稱頭臺村;二臺,置舒蘭法特鎮(zhèn)王大村北;三臺,置九臺上河灣鎮(zhèn)三臺村;四臺,置九臺上河灣鎮(zhèn)四臺村,其有大四臺、小四臺之分;五臺,置九臺上河灣鎮(zhèn)五臺村;六臺,置九臺城子街鎮(zhèn)六臺村;七臺,置九臺城子街七臺村;八臺,置九臺葦子溝鎮(zhèn)腰八臺屯,即樣子邊屯附近;九臺,置九臺市區(qū),因其地有上臺屯、下臺屯兩屯,1911年吉林至長春鐵路經(jīng)由九臺,在下臺屯立站,遂將其二臺綜合之,形成一名,故有下九臺地名生出。
由于吳三桂的遺丁駐守邊臺,柳條邊新邊穿越九臺,致使九臺風土人情,城南城北迥然不同。民國初年,吉長鐵道從九臺中心穿越,將九臺城分成道南、道北兩個地界,出現(xiàn)“一城分二縣,兩地結雙區(qū)”的獨特地理情勢。道南歸永吉四區(qū)所轄,道北由德惠七區(qū)所管,其實不僅如此,在柳條邊新邊形成不久,九臺便日漸形成兩個不同的格局。道南,多為吳三桂遺丁所住,為西南或江南籍人氏;道北,多為東北土著。道南客居,尤其女性,多纖細苗條,面色白皙;道北土著,特別女性,多粗壯魁梧,膚色深重。民國年間,曾發(fā)生過這樣一個故事,一年正月十五燈節(jié),道南道北秧歌上街,爭奇斗艷。其間,道北有一看秧歌男子耍流氓,乘人不介意,悄悄將其私物拽出,靜靜放入道南一女倒背的手中。那女也沒有回頭,更沒有聲張,而是猛勁一抓,說時遲那時快,待那男嚎叫倒地時,五指甲印已深插肉里。那時已有巡警。巡警看過,也只是有視無睹,不了了之。這個鐵南弱女勇戰(zhàn)鐵北悍男的故事,一直流傳很久,成為九臺街市上的趣話。還有一次。那是在偽滿時期,有一年學校開運動會,鐵南鐵北兩校師生發(fā)生毆斗。在原日新書店,即宏光照相館南街口,鐵北敷文小學學生,被鐵南一完小學生,打得落花流水,望風而逃。更有甚者,鐵南一女生,竟用錦旗桿鐵尖,將鐵北一男生腿肚子穿個透亮過,致使百名警察趕來,此事才算平息。但事過后,鐵南師生受到應有處分,校長楊永維記大過,教員李九河、崔諸真,以及學生劉興漢被開除。究其原因,別看道南女生,纖弱白嫩,卻是善武;休睹道北女生,傻大黑粗,卻不經(jīng)風。道南女兒,盡皆來自江南,大有武功根基。當然,這種情況,也與水源有關。道南水好,在早有個叫“張寶老爺”的院子,院內(nèi)有口大井,人以“甜水井”稱之,每當大年午夜煮餃子,人都爭著到那里挑水;而鐵北井水多是銹水。因此那時,九臺街多有驢車拉著道南水去道北賣。大街賣涼水的事,那時九臺就有了。
九臺,為柳條邊上的邊臺,這個稱謂是應該肯定下來的。但也不失有“烽火臺”或“墩臺”之說。據(jù)九臺一中退休老師曹牧子先生回憶,在他青少年時期,由老家沐石河來九臺讀書間,曾數(shù)度到九臺小南山和小南河游歷。那時的小南山北麓,臨近小南河處,非常陡峭,水深波泓。那陡峭的山麓,即懸崖處,見有夯土層,并有類似土坯砌筑物的痕跡,山勢也高。他斷定,那里曾是古烽火臺。但不是清柳條邊修筑時的建筑,上溯可推測到遼金元明,那個烽火臺,當是作為古時戰(zhàn)爭傳遞信號、發(fā)施軍令之用的。我曾沿柳條邊考察過,沿邊稱之為“臺”的地方不少,但尚有許多地方不稱為“臺”,而稱之為“邊”的。如,長春新立城附近柳條邊經(jīng)由的地方,沿邊就有“靠邊王”、“靠邊孫”、“靠邊吳”、“邊沿子”、“南邊里”、“北邊外”、“東邊頭”、“西邊屯”等屯落。這些帶有“邊”字屯名的形成,都與柳條邊有關。但盡管其是邊臺之地,卻又不能稱之為“臺”,這說明,九臺或下九臺,所以稱之為臺,其前,即明元金遼時期,曾筑有烽火臺的可能。曹牧子還說,當年九臺小南山西側,有大片杏林,每當春季,杏花藹藹,落雨繽紛;小南山東側,則以柞林稱著,每年秋季,霜風一打,柞林若火。關于九臺為吳三桂遺丁所居事,還有一證。九臺胡家回族鄉(xiāng)蜂蜜營村段氏家族,其先人段應龍,原為吳三桂降將,家中藏有清康熙十八年即1697年兩道官府正式文書《書札》,其中一道云:“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奉上諭:段應龍原為游擊,相應授以游擊,札付戶部,取緞二疋,賞給可也;發(fā)往起程之時,預先奉聞,賚交兵器。欽此。”另一道為四日后發(fā),稱:“綠頭牌奉:段應龍著急速前去。欽此。”其即奉此書札,遷居到九臺境的。
邊臺小城九臺,如今美得像個柳影婆娑的少女,也像個古老的雕花漆盒,而那個城南的小南山與小南河,竟像女兒胸前垂掛下的一線玉墜,一圓佛珠,一滴翠碧。吳三桂“昭武通寶”、吳世璠“洪化通寶”,這兩枚銅錢,當年所鑄即很少,流傳到關東者更少,且經(jīng)歷時間甚短,因此相當珍貴。這兩枚古銅錢,證實著柳條邊為吳三桂遺丁所筑,九臺道南為其遺丁所居的歷史。那是一段充滿悠悠遐想、布滿漫漫蒼涼的歷史。
〔責任編輯 廉 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