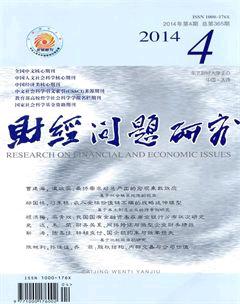企業間關系資本與高管薪酬
富曉軒++許凌達
摘 要:本文基于2003—2010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數據,將高管的企業間關系資本操作化為網絡位置(集中度和結構洞)后,研究發現:高管的企業間關系資本與高管薪酬顯著正相關,即高管在企業間關系網絡中的集中度越高,其薪酬水平越高,高管在企業間關系網絡中的結構洞數目越多,其薪酬水平越高;另外,筆者發現在對高管薪酬的影響程度上,集中度要強于結構洞。上述發現不僅在理論上表明企業間關系資本能夠影響高管的薪酬水平,同時也在實踐中為制定高管薪酬決策提供有益參考。
關鍵詞:企業間關系資本;高管薪酬;網絡位置
中圖分類號:F2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4)04009707
一、引 言
Jensen和Meckling[1]指出在所有權與控制權相分離的股份制公司中,高管薪酬在激勵高管完善經營管理和提升公司價值中處于關鍵地位。那么,哪些因素會影響高管的薪酬水平呢?學術界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來解答此問題:一是市場層面。Rajagopalan和Prescott[2]指出,在一個行業出現(一個或多個)公司時,就可能會出現“薪酬慣性”的同構性壓力,致使公司內部高管的薪酬水平隨著行業而發生整體調整,而且行業薪酬模式的改變能夠有效提高高管薪酬。二是企業層面。Conyon和Lerong [3]指出,公司價值的增加是高管能力的一種體現,為獎勵高管的這種能力,公司愿意授予高管更高的薪酬。三是高管層面。Bebchuk和Fried[4-5]認為,高管是自利的社會人,他們能夠通過自己在公司內部積累的權力影響高管薪酬的制定過程,獲得較高的薪酬水平;James和Marua[6]認為,由于高管本身具有專有的知識、經驗等資本,能夠創造更好的經濟績效并且保持長期的經濟增長,因此,公司就會傾向于支付較高的薪酬。
前兩個層面僅僅以企業為研究對象,忽略了企業薪酬的授予對象——高管的作用,弱化了高管的自身價值。在高管層面,盡管關注到高管的作用,但是這些研究僅僅注意高管自然資本的特征(如高管的權力、知識和經驗等),鮮有文獻關注高管的企業間關系資本對高管自身薪酬的影響。企業間關系資本是指公司高管在兩家或兩家以上的公司董事會擔任職位所形成的關系資本。因此,本文主要考察高管的企業間關系資本對高管薪酬影響作用。同時,由于我國轉型經濟環境具有的特殊性,作為非正式制度的社會關系網絡被視為正式制度的一種替代機制,已成為企業生存與發展的主要方式,而且研究學者將我國這種特殊的情況稱之為“網絡資本主義”[7]。但是因為在轉型過程中我國政府的特殊角色,國內學者主要考察企業成員的政治關系資本對高管薪酬的影響作用。如劉慧龍等基于1999—2008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樣本,認為在國有控股公司中,高管的政治關系與高管的薪酬績效敏感性負相關,在非國有控股公司中,高管的政治關系與高管的薪酬績效敏感性正相關[8];章永奎等以2005—2010 年的民營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高管的政治關系資本增大了公司內部的薪酬差距以及薪酬差距的粘性[9]。實際上,除了政治關系資本之外,高管還具有企業間關系資本。相對來說,作為企業資源的基礎部分,高管的企業間關系對企業具有更高的價值。一些學者指出高管的企業間關系資本增加公司績效、提升投資效率[10]和擴大公司的融資能力,但是這些研究主要關注于企業間關系資本對企業的作用,卻忽視了對具有該資本主體的作用,特別是對主體薪酬方面的影響。
基于此,本文依據社會資本理論,以我國特有的薪酬制度為背景考察高管的企業間關系資本對高管薪酬的影響。具體而言,通過選取2003—2010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數據為樣本,將企業間關系資本操作化為網絡位置集中度和網絡位置結構洞,來考察網絡位置的集中度和結構洞與高管薪酬的關系。與以往研究相比,本文頗有新意的地方主要在于:現有研究主要關注于市場層面和企業層面對高管薪酬的影響,而本文從企業間關系視角基于社會資本理論研究其對高管薪酬的影響,并實證檢驗了企業間關系資本對高管的薪酬價值性,是對現有研究的有益補充。此外,關于高管薪酬的高管層面研究著重考察了高管的自然屬性的作用,忽略了關系屬性的作用。雖然存在個別文獻論及到高管的關系屬性的可能影響,但是他們主要是關注于高管的政治關聯資本,而本文主要考察高管的企業間關系資本對高管薪酬的影響,會對高管的關系資本的薪酬影響研究做出增量貢獻。最后,從實踐的角度,本文的結論有助于企業更好地關注于高管企業間關系資本的影響機制,為制定有效的薪酬契約提供有益啟示。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組織存在于一個包含其他企業的經濟環境中,作為一個開放的系統,實質上它不僅能夠從外界獲得有形的(未加工材料、收入)和無形的(合法性、支持性)資源,而且通過與其他公司的合作也能夠獲取內部的競爭優勢。因此,外部環境和組織相組合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在競爭性結果中還充當著重要的角色。Granovetter[11]研究指出個人關系網絡影響組織的經濟活動,其中企業間關系(也即職位聯結)形成的網絡所具有的影響程度最大。一般情況下,企業間關系被概念化為內部組織的交流機制,而且也充當著主要包括對環境變化洞察力、戰略與結構選擇以及決策過程等各種關鍵性信息的傳播渠道。另外,企業間關系還能夠給目標公司提供有關其他公司最新的政策和實踐信息,例如,律師事務所的選擇、企業捐贈等。事實上,獲得這些信息也是管理者接受外部公司董事會邀請的一個主要原因。當管理者在其他公司的董事會工作時,他們能夠直接觀察到其所管制的公司中決策的制定過程,獲得和接近新戰略選擇的政策,而不用原公司付出直接的經驗成本。
根據這種關系,信息不僅可以傳遞給目標公司,還可以傳遞給外部或者獨立的個體。例如,第三群體經常缺少公司及其管理的一手資料,他們為獲得可靠的信息必須求助于現有的資源,此時,企業間關系就充當著資源與公司之間的傳遞渠道。內部組織間的關系表示著認同,它們反應的事實是其他組織能夠接受該公司并作為可以信賴的聯盟。在存在企業間關系的情況下,對高管進行邀請的公司能夠作為公司認為該高管具有提供價值建議和指導的專業能力的一個信號,這同時也表示對該高管自身公司良好印象的認同。事實是,在某種程度上,管理者關系網絡將他們的公司與相類似或優越的公司相聯結,能夠使目標公司獲得較高的地位收益,以及他們對公司競爭具有顯著的影響。聯盟以及關系聯結地位能夠幫助公司吸引更廣泛的潛在的交易伙伴、促進公司的快速增長以及降低交易成本。基于以上原因,Podolny和Castellucci[12]將高管的企業間關系定義為“有益于公司成功的‘生產資本”,也即社會資本。但是在高管的企業間關系網絡中,網絡位置表示接觸和獲取外部資源的機會,而因不同的高管所處網絡位置的差異,使得接觸和獲取外部資源機會具有差異,從而決定了高管的社會資本的程度不同,再者由于薪酬水平能夠反應社會資本的價值,所以網絡位置對高管薪酬水平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在社會網絡分析中,網絡位置指標的衡量變量有很多,但是學術界廣泛認同且最能夠反應網絡位置影響薪酬水平的變量主要是集中度和結構洞,故本文主要是通過集中度和結構洞來表示高管的企業間關系網絡中的網絡位置。因此,提出假設如下:
假設1:高管在企業間關系網絡中的集中度越高,高管薪酬水平越高。
假設2:高管在企業間關系網絡中的結構洞數目越多,高管薪酬水平越高。
三、研究設計
1.研究樣本及數據來源
模型1—模型4是在基準變量的基礎上,逐漸引入待考察變量——網絡位置,也即假設1和假設2的測試結果。模型1—模型3是將網絡位置,集中度引入基準模型,是關于假設1的實證檢驗結果。在模型1中,網絡位置中間集中度(CEN_B)的回歸系數為正值(0.010),但是不顯著(P>0.10),這說明中間集中度并不影響高管的薪酬水平,這可能是因為中間集中度主要關注的是高管之間相互交流的控制影響力,該指標能夠反映出某一高管向外部傳遞信息同時又能夠從外部獲取信息的程度,他能夠通過控制或曲解控制信息的傳遞來影響整個網絡,但是該指標在實證中并不顯著,這說明公司還沒有注意到高管相互交流的控制影響力的作用。在模型2中,網絡位置接近集中度(CEN_C)的回歸系數為正值(3.31),
而且顯著(P<0.01),這說明位于高管關系網絡位置接近集中度越高的公司的高管越可能具有較高的薪酬水平,這主要是因為接近集中度主要反映的是網絡中高管與其他高管之間的親密性程度[20],不僅能夠更容易接觸有效且準確的信息,而且還能夠對信息實施有效的監控,減弱由信息經由中介傳遞時造成的質量下降的影響,再者Freeman[25]指出該指標能夠反映出高管不受其他高管控制的程度,這樣就會給公司帶來更有價值的信息資源,幫助公司獲得較高的效益,故公司會為此償付給高管較高的薪酬。在模型3中,網絡位置程度集中度(CEN_D)的系數顯著為正(系數為0.30,P<0.01),這說明處于高管關系網絡位置程度集中度越高的公司越會給予高管更高的薪酬,這可能是因為程度集中度能夠反映出高管與網絡中其他高管之間的交往能力即高管的活躍程度,在公司網絡中,描述了諸如資源、信息等網絡資本從其他組織進入本組織與將這些資本發送到其他組織相抗衡的程度,該集中度越高,則說明公司獲取資本的能力越強,發送的程度會越弱,因此,公司會更大程度地激勵使公司處于公司集中度較大的高管,并為其提供較高的薪酬。這些結果支持了假設1。
模型4是將網絡位置結構洞引入基準模型,是關于假設2的檢驗結果:結構洞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系數為0.02,P<0.01),這說明位于高管關系網絡位置結構洞有效規模越高的公司,越有可能給予高管較高的薪酬。這主要是因為結構洞代表了網絡中一種非冗余的關系[26],而且在同一群體內的信息資源要比不同群體之間的信息資源更具有同質性,因此跨群體的高管更可能會熟悉另類的信息資源,就會有更多的機會選擇所需的信息資源[27],進而該類型的高管能夠接觸到差異化且豐富的信息資源,并且從這些信息資源中篩選整合出對公司更具有價值的信息資源,最終將其輸入本公司,為公司節省大量的搜尋和整合成本。由于結構洞能夠幫助高管獲取“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提供機會,所以會比網絡中其他位置的高管更具有較高的競爭資本,故而公司會更大限度地為該類型的高管提高激勵,即增大其薪酬水平,讓其更好地為公司服務。從而假設2得到證實。
另外,我們將網絡位置集中度和網絡位置結構洞指標的回歸系數進行比較發現CEN_C的系數3.31和CEN_D的系數0.30均高于結構洞的系數0.02,這說明在網絡位置中集中度的影響程度要高于結構洞的影響程度。
CEN_C和CEN_D系數標準化之后為0.33和0.30而NETWORK2標準化后系數為0.02,結論和上述一致。
4.穩健性檢驗
為了考察前文結果的穩健性,我們進行如下測試:(1)將高管薪酬用“前三名董事的平均薪酬總額”的自然對數進行替換,結果并未發生改變。(2)在測量網絡位置指標時,我們使用因子分析法,得出網絡位置的一個綜合指標,與高管薪酬進行回歸檢驗結果并未發生實質的改變。以上結果說明本文研究結論的穩健性。
五、結論與啟示
高管的關系資本主要包括政治關系資本和企業間關系資本,且這兩種資本均對公司績效產生重要影響。已有證據顯示具有較高政治關系資本的高管具有較高的薪酬水平,那么具有企業間關系資本的高管是否也會有著更高的薪酬水平呢?更進一步,在什么情境下,高管的關系資本對高管薪酬的影響會更大?本文基于2003—2010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高管企業間關系及高管薪酬數據,研究發現:高管的企業間關系資本與高管薪酬顯著正相關,即高管在企業間關系網絡中的集中度越高,其薪酬水平越高;高管在企業間關系網絡中的結構洞數目越多,其薪酬水平越高;集中度對高管薪酬的影響要強于結構洞的影響。
上述發現有兩點理論啟示:其一,體現在高管的企業間關系上,現有研究高管薪酬主要體現在市場層面和企業層面,忽略了企業間關系對高管薪酬的可能影響。其二,高管的社會關系資本上,除了高管的政治關系資本對高管薪酬影響外,企業間關系資本也對高管薪酬具有影響,因此,要完整地考察高管的社會資本對高管薪酬的影響,不僅要關注高管的政治關聯資本,還要考慮到他的企業間關系資本。上述發現也為高管的薪酬契約設計提供了實踐啟示,企業在設計高管薪酬時,需要關注高管在其他企業的任職經歷,這對有效設計高管薪酬契約具有重要影響作用。
參考文獻:
[1] Jensen, M.C.,Meckling,W.H.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4): 305-360.
[2] Rajagopalan,N.,Prescott,J.E.Determinants of Top Management Compensation: Explaining the Impact of Economic,Behavioral,and Strategic Construct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Industry[J].Journal of Management,1990,16(3):515-538.
[3] Conyon, M.J.,Lerong,H.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CEO Equity Incentives in Chinas Listed Firms[R].ESSEC Business School,2008.
[4] Bebchuk,L.A.,Fried,J.M.Executive Compensation as an Agency Problem[J].Journal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3,17(3): 71-92.
[5] Bebchuk, L.A.,Fried,J.M.Pay without Performance: The Unfulfilled Promise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6] James,G.C.,Marua,S.S.Managerialist and Human Capital Explanation for Key Executive Pay Premium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3,46(1):63-73.
[7] Boisot, M.,Child,J.From Fiefs to Clans and Network Capitalism: Explaining Chinas Emerging Economic Order[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6,41(4):600-628.
[8] 劉慧龍,張敏,王亞平,吳聯生.政治關聯、薪酬激勵與員工配置效率[J].經濟研究,2010,(9):109-136.
[9] 章永奎,馮文滔,杜興強.政治聯系、薪酬差距與薪酬粘性: 基于民營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D].中國會計學會2012年學術年會,2012.
[10] 盧昌崇,陳仕華.連鎖董事理論:來自中國企業的實證檢驗[J].中國工業經濟,2006,(1):113-119.
[10] 陳運森,謝德仁.網絡位置、獨立董事治理與投資效率[J].管理世界,2011,(11):113-127.
[12] 段海艷.連鎖董事關系網絡對企業績效影響研究[J].商業經濟與管理,2009,(4):38-44.
[11] Granovetter,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 (3): 481-510.
[14] 陳仕華,李維安.公司治理的社會嵌入性:理論框架及嵌入機制[J].中國工業經濟,2011,(6):99-108.
[15] Podolny,J.M.Networks as the Pipes and Prisms of the Market[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1,107 (1): 33-60.
[16] DiMaggio,P.J.,Powell,W.W.The Iron Cage Rvisited: Institutional R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3,(17): 143-166.
[12] Podolny,J.M.,Castellucci,F.Choosing Ties from the Inside of a Prism: Egocentric Uncertainty and Status in Venture Capital Markets[M].Boston: Kluwer Academic,1999.
[18] Podolny,J.M.,Phillips,D.J.The Dynamics of Organizational Status[J].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1996,5 (2): 453-472.
[19] 林南.社會資本——社會結構與行動的理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0] Geletkanycz,M.A.,Boyd,B.K.,Finkelstein,S.The Strategic Value of CEO External Directorate Networks: Implications for CEO Compensation[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1,22(9): 889-898.
[13] 辛清泉,譚偉強.市場化改革、企業業績與國有企業經理薪酬[J].經濟研究,2009,(11):68-81.
[14] Horton,J.,Millo,Y.,Serafeim,G.Resources or Power?Implications of Social Networks on Compens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J].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2012,39 (3-4): 399-426.
[15] Engelberg,J.,Gao,P.,Parsons,C.The Value of a Rolodex: CEO Pay and Personal Networks[R].Available at SSRN 1364595,2009.
[16] 陳炎炎,郟麗莎.機構投資者持股與我國上市公司管理層薪酬的實證研究[J].金融經濟,2006,(12):134-135.
[17] 李維安,劉緒光,陳靖涵.經理才能、公司治理與契約參照點——中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決定因素的理論與實證分析[J].南開管理評論,2010,(2):4-15.
[18] 張必武,石金濤.董事會特征、高管薪酬與薪績敏感性——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分析[J].管理科學,2005,(8):32-39.
[19] 蘇方國.人力資本、組織因素與高管薪酬:跨層次模型[J].南開管理評論,2011,(3):122-131.
[20] 方軍雄.我國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存在粘性嗎?[J].經濟研究,2009,(3):110-124.
[21] 王志強,張瑋婷,顧勁爾.資本結構、管理層防御與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J].會計研究,2011,(2):72-78.
[22] 劉鳳委,孫錚,李增泉.政府干預、行業競爭與薪酬契約[J].管理世界,2007,(9):76-84.
[23] 謝德仁,林樂,陳運森.薪酬委員會獨立性與更高的經理人報酬業績敏感度[J].管理世界,2012,(1):121-140.
[24] 陳冬華,陳信元,萬華林.國有企業中的薪酬管制與在職消費[J].經濟研究,2005,(2):92-101.
[25] Freeman,L.C.Q-Analysis and the Structure of Friendship Network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Machine Studies,1980,12(4): 367-378.
[26] Burt,R.S.Cooptive Corporate Actor Networks: A Reconsideration of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 Involv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80,25 (4): 557-582.
[27] Burt,R.S.Social Contagion and Innovation: Cohesion versus Structural Equivalence[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7,92 (6): 1287-1335.
(責任編輯:劉 艷)
[16] 陳炎炎,郟麗莎.機構投資者持股與我國上市公司管理層薪酬的實證研究[J].金融經濟,2006,(12):134-135.
[17] 李維安,劉緒光,陳靖涵.經理才能、公司治理與契約參照點——中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決定因素的理論與實證分析[J].南開管理評論,2010,(2):4-15.
[18] 張必武,石金濤.董事會特征、高管薪酬與薪績敏感性——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分析[J].管理科學,2005,(8):32-39.
[19] 蘇方國.人力資本、組織因素與高管薪酬:跨層次模型[J].南開管理評論,2011,(3):122-131.
[20] 方軍雄.我國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存在粘性嗎?[J].經濟研究,2009,(3):110-124.
[21] 王志強,張瑋婷,顧勁爾.資本結構、管理層防御與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J].會計研究,2011,(2):72-78.
[22] 劉鳳委,孫錚,李增泉.政府干預、行業競爭與薪酬契約[J].管理世界,2007,(9):76-84.
[23] 謝德仁,林樂,陳運森.薪酬委員會獨立性與更高的經理人報酬業績敏感度[J].管理世界,2012,(1):121-140.
[24] 陳冬華,陳信元,萬華林.國有企業中的薪酬管制與在職消費[J].經濟研究,2005,(2):92-101.
[25] Freeman,L.C.Q-Analysis and the Structure of Friendship Network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Machine Studies,1980,12(4): 367-378.
[26] Burt,R.S.Cooptive Corporate Actor Networks: A Reconsideration of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 Involv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80,25 (4): 557-582.
[27] Burt,R.S.Social Contagion and Innovation: Cohesion versus Structural Equivalence[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7,92 (6): 1287-1335.
(責任編輯:劉 艷)
[16] 陳炎炎,郟麗莎.機構投資者持股與我國上市公司管理層薪酬的實證研究[J].金融經濟,2006,(12):134-135.
[17] 李維安,劉緒光,陳靖涵.經理才能、公司治理與契約參照點——中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決定因素的理論與實證分析[J].南開管理評論,2010,(2):4-15.
[18] 張必武,石金濤.董事會特征、高管薪酬與薪績敏感性——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分析[J].管理科學,2005,(8):32-39.
[19] 蘇方國.人力資本、組織因素與高管薪酬:跨層次模型[J].南開管理評論,2011,(3):122-131.
[20] 方軍雄.我國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存在粘性嗎?[J].經濟研究,2009,(3):110-124.
[21] 王志強,張瑋婷,顧勁爾.資本結構、管理層防御與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J].會計研究,2011,(2):72-78.
[22] 劉鳳委,孫錚,李增泉.政府干預、行業競爭與薪酬契約[J].管理世界,2007,(9):76-84.
[23] 謝德仁,林樂,陳運森.薪酬委員會獨立性與更高的經理人報酬業績敏感度[J].管理世界,2012,(1):121-140.
[24] 陳冬華,陳信元,萬華林.國有企業中的薪酬管制與在職消費[J].經濟研究,2005,(2):92-101.
[25] Freeman,L.C.Q-Analysis and the Structure of Friendship Network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Machine Studies,1980,12(4): 367-378.
[26] Burt,R.S.Cooptive Corporate Actor Networks: A Reconsideration of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 Involv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80,25 (4): 557-582.
[27] Burt,R.S.Social Contagion and Innovation: Cohesion versus Structural Equivalence[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7,92 (6): 1287-1335.
(責任編輯:劉 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