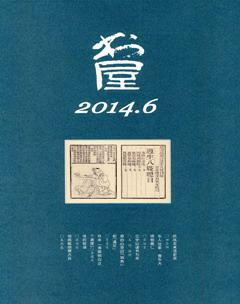并非“誰都明白這個道理”
李建華
當人們終于認識到學生上學時接受的教育主要是在課堂里完成的時候,探討課堂教學的文章日漸增多起來,這是一種很值得欣慰的現(xiàn)象,至少說明教育工作者開始關注當代教育的“中心工作”了。最近讀到《探尋課堂“黑箱”的關鍵屬性》(刊《中華讀書報》2014年1月22日,以下簡稱《探尋》)一文,及其推薦的《教學的穩(wěn)與變》(以下簡稱《穩(wěn)與變》)一書,都認為課堂教學是教育的“重中之重”,可謂觸到了當代教育的根本問題。《探尋》、《穩(wěn)與變》雖然都抓住了課堂教學這個“重中之重”,然而作者理解的課堂教學就是教師傳授知識,未免失之片面。除傳授知識之外,課堂教學還有更豐富多彩的內(nèi)容與不可舍棄的目標,卻忽略了。且作者理解并解釋的課堂教學質(zhì)量,也是有悖教育的基本常識與教學經(jīng)驗的,不能反映課堂教學的真實情況;作者不吝筆墨地大談特談“黑箱現(xiàn)象”、“黑箱之謎”,并未觸到當代課堂教學普遍存在的急需解決的問題。
《探尋》認為:“要想提高課堂教學質(zhì)量,……必須不斷改進教學;要想改進教學,必須發(fā)現(xiàn)教學問題;要想發(fā)現(xiàn)教學問題,必須在教學實踐中研究教學活動。”并進一步認為:“實際上,誰都明白這個道理。”且不說“提高課堂教學質(zhì)量”的道理在當代教育界是否“誰都明白”?那個看上去順理成章的“不斷改進教學”——探討教學方法的做法本身就讓人懷疑:教育界探討教學方法已經(jīng)很多年了,結果不僅沒有取得什么進步,社會各界對教育的不滿卻與日俱增。況且目前課堂教學中普遍存在的“照本宣科”,絕不是個教學方法問題。“教書育人”這是人類堅守“教育是傳統(tǒng)的”根本意義所在。傳統(tǒng)積累的常識告訴人們,課堂教學質(zhì)量是由教師的素質(zhì)能力決定的,不是在教學方法上變出什么新花樣就能提高教學質(zhì)量的。
一、課堂教學質(zhì)量的定義
人類在數(shù)百年近代教育積累的基本常識,幾乎被熱忱于探討教學方法的人們忘記了:課堂教學質(zhì)量是指課堂教學在實踐中所達到的優(yōu)劣程度,它集中地體現(xiàn)了教師的價值理念、思想情感、學問修養(yǎng)、語言表達、課堂駕馭、教材把握,乃至氣質(zhì)形象與人格魅力等諸方面,在課堂上所表現(xiàn)出來的狀態(tài)與水平。教師的綜合素質(zhì)水平唯一重要地決定了課堂教學質(zhì)量的優(yōu)劣。由教師的綜合素質(zhì)水平創(chuàng)造的課堂教學質(zhì)量,對學生的學習質(zhì)量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教學質(zhì)量并不必然地決定全部學習質(zhì)量。因為在實踐中,面對一個差生,再優(yōu)秀的教師往往也無能為力——誰也不會因此評價這位優(yōu)秀教師的教學質(zhì)量如何低劣,所以這種特例絲毫不應動搖探討課堂教學質(zhì)量就是探討教師的綜合素質(zhì)水平這個根本原則。《探尋》、《穩(wěn)與變》都認為,教學質(zhì)量是在“教師、學生、教材三者相互作用中產(chǎn)生的結果”。這個說法在實踐中是不能成立的。凡“相互作用”的產(chǎn)生,無不源于相互者都有主動意識,都能發(fā)揮主動作用。且不說一部沒有生命的教材哪來的這種主動意識與主動力,其“相互作用”純屬子虛烏有。就是學生與教師之間的所謂“相互作用”基本上是一種單向力,大多情況下仍然是教師的主動作用引起學生必然的“被動”活動。某些課堂教學“以學生為主體”,也只能是在教師的引導下,學生提出問題,大家討論、教師作結罷了。教師的主體地位與主導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也是不可動搖的。否則必定出現(xiàn)適得其反的后果,學生如果成了教育的主體,在教學中居主導地位,很可能是一場災難,人類在這方面是有慘重教訓的。所以《探尋》、《穩(wěn)與變》斷言的那種“相互作用”實際上并不存在,也不應該存在,這種觀念在時下教育界很是流行,許多教師在探討課堂教學的方式方法上不遺余力,卻不能在提高自身素質(zhì)水平上花功夫,這樣的“探討”自然收效甚微。將提高課堂教學質(zhì)量的希望寄托在教學方法的變化上,只能是舍本逐末。“師道尊嚴”、“為人師表”、“率先垂范”、“學高為師,德高為范”等都是人類在長期的教育實踐中總結出的寶貴經(jīng)驗,集中地體現(xiàn)了教師在教學中的主體價值與主導作用。教師的素質(zhì)水平“唯一重要地決定了課堂教學質(zhì)量”,離開了教師的綜合素質(zhì)水平這個根本點,探討教學質(zhì)量,是多年來教育界經(jīng)常推行的“不斷改進教學”成為徒勞無功的“鬼打墻”的根本原因。
《探尋》、《穩(wěn)與變》關于“不斷改進教學”這種在方式方法上花功夫的說法,不僅模糊了“課堂教學質(zhì)量”的本質(zhì)意義,湮沒了教師在提高“課堂教學質(zhì)量”中的不可替代的主導作用,而且很容易將提高“課堂教學質(zhì)量”引向歧途。就像中津津樂道的“黑箱狀態(tài)”、“變異理論”、“內(nèi)在機制”、“行動性試驗”、“審辨是學習的基礎”……諸如此類說法,不過是當前見多了的一些雖新鮮卻很空洞的流行概念。這些概念試圖概括的并非是課堂教學的實際情況,對如何提高“課堂教學質(zhì)量”不會有實踐價值;雖然強調(diào)“必須發(fā)現(xiàn)教學問題”,然而讀遍這些文章可以看出,這些教育工作者所看重的“教學問題”,不過是連他們自己都搞不明白的“黑箱狀態(tài)”、“黑箱之謎”。毋寧說,“照本宣科”才是當前教學中普遍存在的、又急需解決的問題。關于“照本宣科”其實大家都看得明明白白,連學生也十分清楚——這是一個教師的綜合素質(zhì)水平有待提高的問題。如何改變“照本宣科”這種由來已久的教學狀況,實質(zhì)上就是如何提高教師的綜合素質(zhì)水平,這才是當前教育工作中面臨的突出任務。
二、學生最反感的是“照本宣科”
所謂“照本宣科”,就是教師將課本上那些用抽象語言概括的、用文學語言敘述的——諸如價值理性、思想情感、精神境界、審美觀念、定義、定理、定律、原理、規(guī)律、方式、方法……不經(jīng)過自己消化后的“再創(chuàng)造”——這個教學中不可缺少的備課過程,直接將課本內(nèi)容照搬到課堂上,向學生生硬地灌輸。毋寧說,這種灌輸都是毫無個性的宣講。所以“照本宣科”將豐富的東西單調(diào)了,將深刻的東西淺薄了,將動人的東西枯燥了,將感人的東西冷漠了,將靈巧的東西機械了,將精妙的東西粗俗了。一些本來生動活潑的內(nèi)容,在“照本宣科”中成了冰冷僵化的文字符號,學生只能在了無興趣中對這些文字符號死記硬背。在“照本宣科”中,教師形同會說話的機器,教師原本應有的風度形象的魅力、語言表達的魅力、情感渲染的魅力——這些對課堂教學有著神奇妙用的力量,都被這架會說話的“機器”“胎死腹中”了。“照本宣科”由于缺了教師的“再創(chuàng)造”,使得授課內(nèi)容既無理趣,更無情趣,學生在一種枯燥、乏味、單調(diào)、無趣、沉悶的課堂氛圍中形同遭罪。形同遭罪的課堂學習,又怎能不助長學生厭學的心理呢?endprint
當然,普遍存在的“照本宣科”并非都是教師不備課造成的。調(diào)研中發(fā)現(xiàn),多數(shù)“照本宣科”是教師由于受知識結構與學養(yǎng)水平的限制,無法實現(xiàn)對課本上的內(nèi)容消化后的“再創(chuàng)造”,所謂“再創(chuàng)造”,簡單說就是教師把要講的“道理”吃透后加以通俗化。例如對于一個新概念,教師講一百遍學生不一定聽明白;但教師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學生馬上就會茅塞頓開、明明白白了。然而舉例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子必須恰當、生動,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識,這需要教師有很寬的知識面,有很高的學養(yǎng),一句話:教師要看很多的書。
在一定意義上說,課堂教學就是教師向學生講真理的意義,然而學生在幾十分鐘里對這些真理從認識到理解,從理解到掌握,是件很不容易的事。為了引起學生對真理的興趣,更為了便于學生理解,教師必須將課本上表述的真理還原成問題,即在課堂上展示前人發(fā)現(xiàn)真理的原始過程,這個過程最能體現(xiàn)教師的水平與能力——圍繞問題旁征博引、畫云戳月,利用顯例舉一反三、深入淺出,末了或有畫龍點睛之妙,或出海闊天空之新。再復雜的真理,也會在這個過程結束時的水到渠成中豁然開朗起來。而這個過程中貫穿的“以事實為根據(jù)、以邏輯為準繩”的思想,既培訓了學生的邏輯思維,又培養(yǎng)了學生的科學理性——毋寧說,這一切都是在教師展示問題過程的駕輕就熟中不知不覺實現(xiàn)的。然而“照本宣科”或簡化了這個過程,或干脆沒有了這個過程。于是這樣,再簡單的道理灌輸給陌生的學生也是困難的。何況在大、中、小學的課本中都有許多學習的難點,通常情況下,這些難點是教師最費心力的地方,花去的備課時間最多。即便這樣,在短短的四十五分鐘里要想講明白,要想讓學生很好地掌握,也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教師將這些難點也“照本宣科”,豈不是害苦了學生?能怪學生怨聲載道嗎?
實際上,課堂教學不僅僅是“教師把知識傳授給學生”,觀測教學質(zhì)量的要素也不單純是作者所認定的學生是否“有效地掌握、理解并能應用所學的知識”。課堂教學中必須完成的道德教育與“精神成人”,《探尋》、《穩(wěn)與變》都沒有提到,這是作者的學術欠缺,在探討課堂教學中,這是一個不應漏掉的十分重要的問題!
三、課堂教學中的道德教育與“精神成人”
如果說學校的中心任務是教學,教學的重點在課堂;那么,培養(yǎng)“健全的、完整的人”這個教育的根本宗旨,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zhì)水平這個教學的唯一目標,毫無疑問也是在課堂上完成的。“學生的綜合素質(zhì)”與“健全的、完整的人”實質(zhì)上是學校實現(xiàn)教育、教學目標的兩個不同說法,其意義都是相互滲透的。所以課堂教學中,教師既要把知識傳授給學生,又要負責培養(yǎng)學生的道德品質(zhì)、精神素養(yǎng)、意志能力,幫助學生營造自己的精神家園,也就是現(xiàn)代“教育學”中所倡導的“精神成人”,從而使學生成為一個具有綜合素質(zhì)水平的、健全的、完整的人。然而,不僅《探尋》、《穩(wěn)與變》將課堂教學看作單純的教師傳授知識,當代教育界幾乎都是這樣理解并實踐的。自從專業(yè)化被奉為教育的圭臬后,這是一種持續(xù)了半個多世紀的現(xiàn)象。
學校的道德教育之所以收效甚微,就像賀麟當年所批評的,把道德律條寫在書上、掛在墻上,向學生宣講一番就萬事大吉了,以為學生就會有道德了,實際情況絕非這樣。成功的道德教育是將道德變?yōu)閷W生的自覺行為。然而單純的道德說教無法實現(xiàn)這一點。有關知識告訴我們,道德的自覺行為,與頭腦的理性密切相關,與心理的情感千絲萬縷,與良知系統(tǒng)一脈相承。所以,看上去一目了然的道德行為,在道德主體那里有著復雜難辨的精神脈絡。然而這僅是就道德賴以生存的主體而言;實際上道德變?yōu)閷嶋H行動時,卻又必須借助外來的力量:
實踐中的道德往往表現(xiàn)為一種知恥行為,所謂知恥——“知道不應該干什么”的根本意義,是面對“不應該干的事情”時,表現(xiàn)出的一種自制力,這種自制力雖然與理性、情感、良知都有關系,但主要來源于敬畏意識。敬畏是人由于崇拜、崇敬某個神圣崇高的客體而衍生的畏懼心理,實質(zhì)上是人的良知系統(tǒng)受客體影響后的一種優(yōu)化現(xiàn)象。這種“優(yōu)化現(xiàn)象”與功利無涉,是一種純粹的精神品質(zhì),蘊含著不受功利左右的巨大潛能。所以只有知恥的人,才可能不為名氣所動,才可能戰(zhàn)勝功利的誘惑,才可能經(jīng)受生死的考驗。中國文化中贊揚的氣節(jié),實質(zhì)上就是知恥產(chǎn)生的不可侮的凜然風度。人類道德教育的成功經(jīng)驗是,首先要教育學生樹立積極、健康、遠大的理想,要有神圣、崇高的信仰——由此產(chǎn)生為人處世不可或缺的敬畏心理。人類的過去與現(xiàn)在都可證實,凡有信仰的民族,都有敬畏心理,所以他們的道德行為大都是自覺的。相反,沒有信仰的人一般地缺乏敬畏心理,這樣的人往往“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怕”的人什么事情干不出來?這樣的人,所謂知恥,所謂道德,也就無從談起了。可以看出,自覺的道德行為有著豐富的精神來源,絕不是道德家拿道德律條教化的結果。所以,道德教育實質(zhì)上是一項精神培養(yǎng)的系統(tǒng)工程,它涉及到人生觀、價值觀、審美觀,以及信仰與情感等方方面面。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道德教育只能分解在全部的教育內(nèi)容中,特別是課堂上——“寓教于樂”地滲透在各個科目共同構成的豐富多彩的課堂教學里。其涵有的人文精神在教師的主導下對學生的耳濡目染與潛移默化,才是道德教育的理想途徑,也是其真正的希望所在。所以課堂教學不僅僅是知識的傳授,還應有理性的張揚、情感的渲染、審美的提升,以及對謙卑、敬畏、知恥、向善的永不懈怠的堅守——這一切都是在教師講課時貫穿的人文精神里,不知不覺地滲透到學生的骨子里了。這便是本文強調(diào)的課堂教學的“原旨要義”——知識傳授、道德教育、“精神成人”的既有區(qū)別又有聯(lián)系的全部意義。下面舉例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
《史記》中的《項羽本紀》之所以被歷代節(jié)選在學生課本里,主要原因在于,《項羽本紀》是中國古典散文中最優(yōu)秀的篇章之一。就像有人所推崇的“即便《史記》全書散失了,只要《項羽本紀》流傳下來,司馬遷在中國文史上的大家地位也是巋然不動的”。然而語文教師如果僅從《項羽本紀》中——語言的生動凝練與醇厚雋永,人物的血肉豐滿與逼真感人,情節(jié)的起伏跌宕與波瀾壯闊等文學的角度授課,可能是一堂成功的語文課,但畢竟缺了——司馬遷若地下有知,一定會抱怨,后人讀《項羽本紀》怎么忽視了其中最重要的方面?項羽身上寧死不辱的知恥精神,才是《項羽本紀》最有意義也最光彩照人的地方!endprint
《項羽本紀》之所以成為千古名篇,絕不僅僅是個寫作水平問題。文章中處處散發(fā)的作者對項羽的理解、同情、贊揚,以及那扼腕中的一唱三嘆,都是作者的人生觀、價值觀,以及審美情操的一種無可奈何的寄托:司馬遷切身地痛感到,自從劉邦當上皇帝后,流氓文化大行其道,中國文化中最具恒久價值的理念之一——知恥,在項羽的身上成了絕響。唯其這種“絕響”才成就了《項羽本紀》涵蓋千古的絕唱。烏江的悲劇不僅是項羽個人的,更是這個民族的,乃至中國文化的。所以,才有了項羽殉難烏江一千三百年后,李清照的“生當做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之久傳不衰。項羽為什么“不肯過江東”——“籍與江東父兄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有何面目見之?”李清照為什么要謳歌一位失敗的英雄?當南宋大小官員在山河破碎中“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時,這樣偏安一隅的朝廷只知花天酒地,不管生靈涂炭,已經(jīng)是“無恥之恥,無恥矣”。所以,對《項羽本紀》授課中的這種層層深入,既是審美意義上的需要,更是教書育人中不可替代的感化——項羽不僅以其“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英雄形象立世,更以其感天地、泣鬼神的知恥精神光照千秋。古人的知恥精神必定在這樣的課堂教學中引發(fā)震撼靈魂的道德自省。
萬有引力定律是中學物理中一節(jié)十分重要的課。雖然這是一堂講授科學知識的課,但是其中涵有的“精神成人”的意義,卻是物理教師在課堂上必須認真對待并予以完成的:教師的授課不能僅僅停留在——“兩物體之間由于其質(zhì)量而產(chǎn)生相互吸引力,該引力的大小與它們的質(zhì)量乘積成正比,與它們距離的平方成反比”F=Gm1·m2/r2的講解上,因為圍繞牛頓發(fā)現(xiàn)萬有引力定律前后的一些史實,不僅生動感人,這些史實中的那些饒有興致的理趣,對學生更有著不可多得的“精神養(yǎng)成”幫助。例如那個著名的蘋果落地故事。雖然有人懷疑這個故事的真實性,但這個故事在邏輯上是成立的,何況這個故事是牛頓的好朋友威廉·斯圖克萊在其撰寫的牛頓傳記中講到的。故事的真實性在這里已沒有討論的意義,即便這個“邏輯”是假設的,它卻生動地表達了一個科學家不可或缺的品質(zhì):問題意識與批判精神——而這,恰恰是中國文化、中國人所缺乏的。所以,將蘋果落地故事移植到課堂上,教師若對其含有的科學家的思維方式與批判精神有意地引申闡釋,對學生來說不啻為一堂妙趣橫生的培養(yǎng)問題意識與邏輯思維的課。這堂課若進一步拓寬——萬有引力定律發(fā)現(xiàn)后,牛頓向人類宣告的那個“上帝是第一推動力”,可謂石破天驚地道出了“人類是十分渺小”的深刻哲理。當人們明白了這個哲理后,肯定會在神奇遙深的宇宙面前多一份刻骨銘心的敬畏與謙卑。敬畏與謙卑是人之所以為人最重要的品質(zhì)。像人類面臨的:動物的瀕臨滅絕,冰川的融化,地球的變暖,以及地震、海嘯、洪澇、干旱自然災害的頻發(fā),大氣污染、水土污染、生態(tài)失去平衡……日漸增多的生存危機都是人類丟棄了敬畏與謙卑,在欲望的驅使下為所欲為造成的。所以說,如果人類的來路上曾經(jīng)有過什么失誤,首先是教育的失誤。教育的失誤,使人類在失去敬畏與謙卑的任意妄為中走向災難。
僅僅課堂教學質(zhì)量的提高,就不是個短期內(nèi)能夠實現(xiàn)的問題,因為它涉及到教師的綜合素質(zhì)水平的提高,這種提高不是人們常見的短期培訓可以奏效的,它需要教師耐得住寂寞讀書,讀書,再讀書。從思想上真正認識到所謂教學是教與學的辯證統(tǒng)一:“教一輩子,學一輩子;學一輩子,教一輩子。”在提高課堂教學質(zhì)量的常識中起步,并非是件輕而易舉的事。例如某直轄市早在多年前,就以紅頭文件的形式,硬性要求教師必須一年閱讀多少冊書——這個讀書指標與個人的獎金、職稱、提干、工資待遇等掛鉤。然而幾年下來,教師的讀書情況并不讓人樂觀,或者說,“教書匠不讀書”的狀況并未得到根本扭轉。教師讀書到了這種行政干預也難以奏效時,不僅是教育界的難堪,也是當代教育的悲哀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