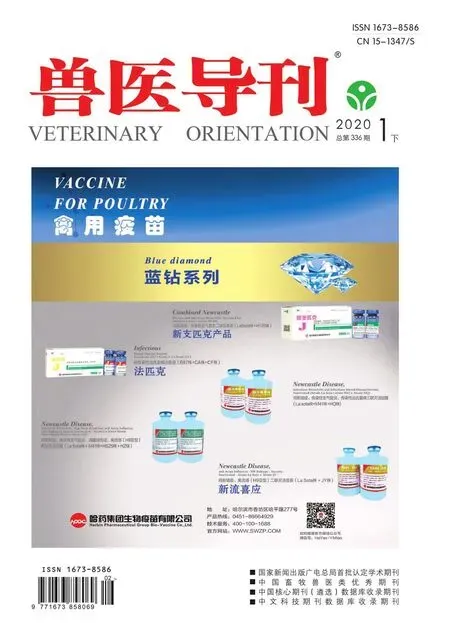生豬標準化養殖技術
陳遠紅 何安奎
(鎮坪縣畜牧獸醫中心,陜西鎮坪 725600)
1 圈舍建設要求
1.1 圈舍選址
要具備三通(通路、通電、通水),地勢干燥,背風向陽,利于排污。
1.2 圈舍結構
標準的鎮坪模式圈舍。即圈舍外墻為雙磚夾泡沫的保溫墻,地面下設U形火道,山墻設兩個風機孔,兩個通風窗,舍內設一個操作間(緩沖間)位于進火口端,每欄安裝兩個自動飲水器,走道設在圈舍正中,糞溝設在兩邊,圈舍橫向坡降為1%,走道應高于圈面1-2cm,糞溝縱向坡降3%,屋頂由下至上為屋架、檀條、彩條布、6cm泡沫板,紅瓦蓋頂。
1.3 排污及無害化處理設施
配套干清糞發酵棚、三級沉淀池和病死豬無害化處理池。
2 良種繁育技術
2.1 品種選擇
適宜我縣推廣的種豬為長白、大約克、杜洛克等優良豬種。
2.2 雜交模式

2.3 后備母豬的選留
選留的后備二元雜交母豬體型要符合繁殖生產技術要求,體格發育良好,陰戶較大,有效乳頭7對以上,排列整齊,性情溫順。
2.4 適齡配種
由于二元雜交母豬的性成熟較晚,母豬出現初情期時先不要急于配種,在3個發情期后,也就是第四個發情期才能配種。一般認為,優良品種的母豬初配年齡為8~10個月,體重達100~140kg宜。
2.5 母豬的發情鑒定方法
采用“一看、二算、三聽、四按背、五綜合”的發情鑒定方法。即觀看母豬外陰是否紅腫,顏色是否發紅,是否有分泌物;推算是否為母豬的發情期;聽母豬是否鳴叫、鬧圈;進行壓背試驗,按壓母豬腰背部母豬是否靜立不動、兩耳直立、尾根豎起。
2.6 配種時間
母豬發情后一般在第2~3d配種,按照“老配早,小配晚,不老不小配中間”原則,對青年母豬發情后推遲配種,老母豬發情后早配種,中年母豬在發情中間配種;一般母豬陰戶流出的粘液呈拉線狀,陰戶腫脹開始消退,陰門開始裂縫,顏色由潮紅變為紫紅,壓背試驗出現靜立反射便是適宜的配種時間。第一次配種后經12~20h再配種一次。
2.7 妊娠鑒定
母豬配種之后不再接受公豬的爬跨,并表現出貪食、貪睡、容易上膘,皮毛光亮,性情溫順,外陰部較干燥,配種結束后18~24d未表現發情癥狀,即可鑒定為已妊娠
3 飼養管理技術
3.1 妊娠母豬的飼養管理技術
妊娠母豬在妊娠前期實行分群飼養,每群4~5頭,到妊娠后期實行單豬單圈(欄)飼養;妊娠前期(配種后1個月以內),一般飼喂2.5~2.8kg/d,加強營養,減少哺乳時的失重,一般消化能為2950~3000MJ/kg,粗蛋白水平14%~15%;妊娠中后期(妊娠第31天-臨產前)飼喂量為2.3~2.5kg/d,消化能為2950~3000MJ/kg,粗蛋白水平13%~14%;嚴禁飼喂霉爛和農藥污染飼料,發霉變質會產生大量毒素,如玉米發霉、黃曲霉素等會影響受精卵著床和胚胎的發育,造成胚胎死亡和流產。
3.2 哺乳母豬的飼養管理技術
3.2.1 哺乳母豬的飼養管理。哺乳母豬要飼喂營養全面優質的全價飼料,粗蛋白17%,消化能3200MJ/kg;母豬產前3天減少喂量,產前第2d少喂,產前當天不喂;產后第1d不喂料,第2天少喂,第4d以后增加飼喂量和次數,喂5次/d,一般哺乳期母豬日采食時5~9kg;提供足夠的飲水,母豬哺乳期每天飲水量在10~15kg左右。
3.2.2 接產技術。仔豬出生后,接產人員應立即用毛巾將仔豬口鼻中粘液擦凈,再將全身擦凈,將初生仔豬置入30~32℃的保溫箱中。先將臍帶內血液向仔豬腹部方向擠壓,然后距腹壁3~4cm處用縫合線結扎后剪斷臍帶,斷端涂5%碘酒消毒,以防破傷風。
3.3 仔豬的飼養管理技術
重乳食,過好初生關。讓仔豬充分吸食初乳,使其獲得必要的營養物質和免疫物質,以增強體質。早開食,過好補料關。抓旺食,過好斷乳關。仔豬達4周齡后,進入旺食期,采食量增加,生長迅速。為了提高仔豬的斷乳窩重,必須抓好旺食期的飼養管理。
3.4 育肥豬的飼養管理
3.4.1 圈舍清洗。新圈舍在進豬前5d,老圈舍在進豬前一周,對舍內所有設備進行一次徹底清洗。
3.4.2 消毒。新舍進豬前一天對豬舍用20%的石灰水或“8.4”消毒液進行全面消毒。
3.4.3 加溫。新圈舍進豬前2~3d火道加溫,老圈舍進豬前一天加溫,豬舍溫度控制在26~30℃,濕度小于70%。
3.4.2 飼料。進豬前準備好仔豬采食的飼料,如顆粒料或配合飼料,最好選用原仔豬場采用的同一品種飼料。
3.4.3 飲水。仔豬入舍時應及時將自動飲水器關閉,在食槽內加入溫水和口服補液鹽+電解多維+土霉素片(阿莫西林粉或痢菌凈粉),保證仔豬入舍后半小時內有充足的飲水。
3.4.4 消毒。前2周每三天消毒1次,第3周后每周消毒1消毒液更換使用,消毒液濃度適當加大。
3.4.5 驅蟲。每兩周用敵百蟲(2%)+來蘇爾(2%)體表噴灑,驅體外寄生蟲或防濕疹。
4 生豬程序免疫
4.1 種母豬免疫程序
每隔4-6個月免疫口蹄疫滅活苗、豬瘟弱毒苗、高致病性藍耳病滅活苗;配種前免疫豬細小病毒滅活苗和豬偽狂犬基因缺失弱毒苗;產前4~6周免疫豬大腸桿菌雙價基因工程苗和豬傳染性胃腸炎、流行性腹瀉二聯苗。
4.2 商品豬免疫程序:
25-35日齡免疫豬瘟弱毒苗,60-70日齡加強免疫一次;30~40日齡免疫高致病性藍耳病滅活苗,間隔一個月加強免疫一次;35~45日齡免疫口蹄疫滅活苗,間隔一個月加強免疫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