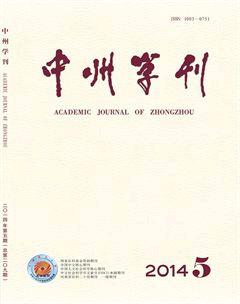中國傳統孝文化的歷史演變
黃振萍
摘要:孝作為傳統人倫秩序,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演變的過程。禮崩樂壞后的西漢王朝,將孝文化作為國家體制建構的基礎。隨著佛教的傳入,孝道思想逐漸深入民間,成為魏晉隋唐時期底層社會的核心理念。宋元時期,佛教、道教和民間信仰的融合,使孝道思想成為一般民眾精神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明代國家政治體制與儒家理念互為依據與支撐,形成一個整體,孝文化成為國家政治體制的合法性來源,而清朝的國家體制與儒家倫理并不呈現完全合一的狀態,儒家孝道倫理也并不是整個國家全民的行為規范,呈現一種多元復合型局面。“五四”時期,在傳統中國向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思想界對作為傳統國體基礎的孝道進行了重新思考。
關鍵詞:孝文化;孝道;儒家倫理
中圖分類號:K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14)05-0005-06
一、兩漢時期的“孝”:
孝文化與國家體制建構理念的結合人類是依賴性的理性動物,只有群居共處才能生存和發展,由此也就產生了人倫情感和秩序,世界各大文明都以此為發端。①傳統中國也是如此。在人倫秩序之中,血緣最近之父子、母子關系無疑最為自然,父母對孩子有生養之恩,后代對祖上有感念之道,個體與他人的共同體關系就如同細胞互聯一般建立起來,作為人倫秩序規范的孝道由此產生,并成為社會共同體規范——禮的核心。據說起源于司徒之官的儒家對這一秩序最為看重,在儒家經典五經中處處可見崇孝的言論,《孝經》的出現與尊崇更是明證。孔子說:“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②孝道自然成為儒家認可的行為規范。不過,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儒家學說只是眾多學說的一種,還有道家、墨家、法家等學說,他們有著不同的孝道觀。
到秦漢之際,宗法社會崩潰,邦國林立的局面改變,秦朝實現大一統,漢繼秦建立以官僚制為基礎的國家。這一國家體制在世界文明史上有著獨特的價值,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甚至認為“中國是創造現代國家的第一個世界文明”③,“西漢的中國政府幾乎符合現代官僚機構的全部特征”④。在這一國家體制里,不再像封建制度時期那樣以血緣為紐帶,世卿世祿不再施行,而是實行官僚治理,那么,失去血緣紐帶之后的國家要靠什么來完成建構呢?國家政體的基礎是什么?社會需要靠什么來凝聚?就成為統治者需要面對的關鍵問題。
漢王朝曾在初期短暫地施行過黃老之術,無為而治、休養生息。到武帝時,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闡發天人感應學說,宣稱君權神授,國家獲得來自上天的神權支持,儒學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在經歷了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之后,真正實現了“政”與“教”的合一。而實現政教合一的目的就是為了國家建構,從此,漢朝國家體制擬構了以儒家孝道為基礎的家族。家族的秩序和原則,放大了就是國家的秩序和原則,漢代中國的倫理觀念和社會秩序,就是從家庭、家族、宗族關系中引申出來,認同的合理性基礎建立在人們對于身邊的家庭、家族和宗族的感情上,這種感情承認的秩序漸漸放大,就成為普遍的社會倫理和國家制度。“國”成為“家”的放大,而構成家族基礎的孝道就被移植到國家建構過程中,這樣一來,本來只是家族范圍內的孝,就成為國家建構的基礎,形成傳統中國的家族國家體制。所以,漢代的皇權宣稱以孝治國,立《孝經》博士,察舉孝廉,設孝悌力田,甚至刑罰也會根據行孝的情況酌情增減。班固《漢書·惠帝紀》顏師古注:“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謚,自惠帝以下皆稱孝也。”⑤體現了國家推行孝道的決心,景帝也被群臣頌為“永思孝道”,是以孝德治天下的表率。朝廷如此身體力行,社會自然上行下效,凝聚力加強,風俗淳樸,成為后世王朝的榜樣。由此可見,是漢代完成了以孝文化作為國家體制基礎的建構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為國盡忠與在家盡孝本來是兩個范疇里面的不同規范,兩者在先秦時期雖然有交互關系,比如曾子認為能行孝道是由于有忠的精神,“忠者,其孝之本與”⑥。但仍各行其道。然而,自漢朝把孝道納入國家建構之后,作為個體的人,當家與國這兩級共同體之間出現矛盾,面對如何處理忠孝沖突的問題時,對國家的“忠”無疑具有優先性。⑦對于“家”這個小共同體的“孝”原則,不僅僅是服從于國這個大共同體的“忠”原則,而且,用明人袁可立的話說:“為親而出,為親而處。出不負君,移孝作忠。處不負親,忠籍孝崇。”⑧移孝作忠,完成的是儒家倫理的政治化過程,在“家”和“國”兩級共同體之間建立起溝通橋梁,而且,“忠籍孝崇”,表明個體在家的孝行程度也成為衡量對國的忠誠程度,這樣就時刻把個體與“國”這個龐大共同體的關聯具象化,無疑大大加強了個體對國的認同,把個體、家和國凝結成一個有機整體,也成為不同個體之間對“國”產生共同認同的凝結紐帶,這就成為后世維持大一統中國的認同基礎。
二、唐宋時期的“孝”:
一般民眾精神世界的最重要組成雖然接續兩漢的是動蕩的魏晉南北朝,佛學傳入,國內大暢竹林玄風,但孝文化仍舊構成社會文化的主體,《梁書》《陳書》《北史》都有《孝行》傳,其他如《南史》等也有《孝義傳》,記載事跡繁多,不勝枚舉。而且,佛教進入中國之后,也漸漸華化,本來講究出世的佛教也出現了孝道思想,諸如《父母恩難報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地藏菩薩本愿經》以及《盂蘭盆經》,宣揚父母恩重,行孝道報恩的思想,這無疑是佛教思想的一大變化,是適應中國文化的結果。同時,由于夷狄的沖擊,世家大族南遷,帶動中原文化的南移,移民對自身家族譜系的關注,帶來譜牒之學的興盛,對原來蠻荒的南方起到了文明化的作用,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在動蕩中實現了孝文化在南方的普及與推廣。
唐朝立國格局宏大,儒釋道三教并尊,文化呈現多元融合的局面。唐玄宗既御注《孝經》,又對《金剛經》《道德經》青眼有加。在士人層面,儒家也并未獨尊,韓愈興起古文運動,文起八代之衰,為的是文以載道,重續儒家道統。雖然唐朝在國家和精英層面對孝道的提倡不如漢代,但仍舊非常重視,唐玄宗《孝經序》強調孝道“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于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⑨。同時,社會層面重視人倫、以孝為本的這一特點基本并沒有大的改變,孝道在中國底層社會里仍舊是核心理念,從敦煌出土文書如《太公家教》等可以清晰看到這一點。
經歷過五代的混亂局面,宋朝尤其注重恢復秩序,消弭社會危機,對外患有足夠的防御力和戰斗力,因此希望在國家體制方面能比之前的王朝有所加強,希望有穩固的社會結構,改變五代那種殺伐不已的局面,在這方面,宋王朝看到了禮制的作用,編定《政和五禮新儀》,同時,宋王朝比唐朝更為重視孝文化凝聚國家與社會的作用。北宋士大夫為此付出了巨大的智力努力,濂洛關閩之學都非常重視以家庭倫理為基礎的社會構成,思考如何完成以儒家倫理塑造社會和國家的問題。他們比漢朝之后的歷代精英更加重視孝道的闡釋與弘揚,最明顯的,如把《大學》從《禮記》中抽出,強調齊家才能治國平天下,從而使家族擴大為國家的步驟更為清晰。同時,他們非常重視基層社會的建設,他們對家族的祠堂祭祀、鄉約、族規、家法和家譜的編纂都投入了非凡的熱情,目的就是期望有強大的基層社會,支撐起因內憂外患而搖搖欲墜的整個王朝,以此來實現儒家經世濟民的內圣外王理想。這一切的努力,到南宋由朱熹總其大成。
朱熹是新儒學的集大成者,著述浩繁,對儒學的各個門類幾乎都有精深的研究。然而,他留給后世影響最大的,卻是幾本薄薄的小書,主要是《四書章句集注》和《小學》。雖然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并稱“四書”在北宋已經開始,但只有到了朱熹終其一生為其注釋,才伴隨著弟子授受而傳播四方,并由后世皇權的支持列為科舉標準,儒家倫理孝道精神也就大為彰顯。其次就是《小學》產生莫大影響。朱熹給《小學》作序,稱:“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⑩朱熹認為修身齊家必須要從小培養起,于是編輯此書,授之童蒙,第一篇為立教,第二篇為明倫第,即是講明“父子之親”的孝道。因為《小學》在后世被采納為童蒙讀物,對于大多數只是經歷了童蒙教育階段,并沒有機會接受更為深入教育的人而言,《小學》和《孝經》對他們的影響就更值得認真對待,這標志著一個社會基本的思想底色。
雖然,程朱理學在南宋僅在短暫時期被官方采納,之后的元代由于是蒙古人統治,官方更無暇顧及,然而孝文化在這段時間的發展卻有目共睹。其表現之一就是《二十四孝》的出現及其各種形式的普及。元人郭居敬撰輯《全相二十四孝詩選》(通稱《二十四孝》),作者有爭議,有認為是他弟弟郭守正,也有認為是郭居業編纂,據范泓《黃籍便覽》和《大田縣志》記載,郭居敬字義祖,性至孝,親沒,哀毀過禮,嘗集虞舜以下二十四人孝行之概。可見郭居敬本人是孝子,由他纂輯很合理。《二十四孝》收錄24個行孝故事,這些故事有些取材于漢代劉向《孝子傳》,有些來源于類書《藝文類聚》等收錄的孝子故事,是民間孝行故事的集合。此后,《二十四孝》以各種形式廣泛出現于多種場合,最常見的是配圖印刷,比如,明朝人蔡培元和李錫彤輯錄《二十四孝圖詩合刊》,《女二十四孝圖》,以二十四孝為題材的木雕、版畫、建筑彩畫幾乎能在各地看到,又如黟縣西遞村的履福堂的天井兩側各有12扇門,每扇門中段各雕了一則孝義故事,合起來恰是一幅《二十四孝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道觀、佛寺甚至也出現二十四孝的磚畫,如云南大理巍寶山長春洞、少林寺地藏殿、普陀山法雨寺、四川省廣元市皇澤寺和四川青城山三清殿內均發現有二十四孝圖。民眾佛教、道教和民間信仰場所出現宣揚儒家孝道思想的圖畫,表明孝道思想在底層得到最廣泛傳播,孝道思想成為一般民眾的精神世界的最重要組成。
表現之二,是元朝服膺理學的士子繼續大力弘揚儒家倫理,孝文化得到更多闡釋與宣揚,從而構筑起更為堅固的社會精神。盡管元朝統治時期科舉時興時廢,實際施行的時間總共只有42年,但元朝的科舉制度比宋朝有一重大變化,是確立以《四書》取士。延祐元年(1314),元仁宗宣布“開科取士”,并且將程朱理學尤其是朱熹的《四書集注》作為“考試大綱”。仁宗強調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這無疑繼承了王安石變法改革科舉的精神,改詩賦取士為經義取士,只是以《四書》代替《三經新義》。這大大提高了《四書》以及朱熹《四書集注》的地位,使得儒家倫理精神從國家層面得到了確定。與此同時,民間的儒生促進了儒學的普及化,比如,朱升把方逢辰《名物蒙求》、陳櫟《歷代蒙求》、黃繼善《史學提要》和程若庸《性理字訓》提升到與“四書”并列的地位,稱為“小四書”,核心是“秩序五典,維持三綱。君臣以立,父子以匡”的儒家教化思想,孝道無疑在其中是核心地位,也由此得到更廣泛的發揚。
以上從漢到元,是傳統中國孝文化作用于國體,并逐步社會化的第一階段。漢朝以孝立國,完成了儒家理念的制度化,國家體制是儒家化的政體,家族的組織結構被放大為國的體制,精神內核是儒家的,或者說以孝道為核心的倫理規范,從而完成了國家秩序的建構。魏晉南北朝、隋唐延續了這一建構,雖然國家層面的孝道提倡有所削弱,但社會和民間層面的孝文化綿延不絕,形成強有力的凝聚力,從而即便遭受游牧民族的沖擊,仍舊能重新聚集起國家體制,使得大一統局面得以維持和延續。宋朝是新儒學產生與發揚的時期,孝道重新獲得國家層面的重視,士大夫精英致力于社會治理,對孝道進行更為廣泛地弘揚,所以盡管元代是蒙古人的統治,但仍舊維持了社會的同一性,并使得科舉采用“四書”為標準,給明代重新儒家化提供了制度基礎。
三、明清時期的“孝”:
底層社會意識形態的核心理念明代是繼漢朝之后最為儒家化(理學化)的朝代,重新實現“政”與“教”的合一。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之后,政策制定方面以“去胡元弊政,復中國先王之舊”為宗旨,標榜恢復“漢唐舊俗”,以上古三代為法。為此,朱元璋特編定并頒布《大誥》,他在序言中說:“華風淪沒,彝道傾頹,自即位以來,制禮樂,定法制,改衣冠,別章服,正綱常,明上下,盡復先王之舊,使民曉然知有禮義,莫敢犯分而撓法。萬機之暇,著為《大誥》,以昭示天下。且曰忠君孝親,治人修己,盡在此矣。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頒之臣民,永以為訓。”《大誥》在朱元璋時代要求全民講讀,民間社學定期誦讀,“天下有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余人,并賜鈔遣還”,如此興師動眾,朱元璋的目標是“忠君孝親,治人修己”,完成社會和國家秩序的重整。
朱元璋以《大誥》文辭繁多,誦讀不易,進而頒布更為簡明的“圣諭六條”:“孝順父母,尊重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守生理,勿作非為。”這個圣諭第一條就是孝順父母,以家庭倫理作為社會和國家秩序的出發點。明朝比此前朝代的一個突出之處,就是在民間社會設立了實際的組織來進行教化。比如,明代老人制的設立。自洪武十年(1377)始,朱元璋命令天下郡縣選民間年高有德行的老人充當“耆宿”,耆宿的職責是接受地方官對政務與民間事務的咨詢,并受官方委托處理民間婚姻、田地等方面的訴訟事項。老人制往往與里甲制配合,以“里”為單位設立“耆宿”,所以也被稱為“里老人制”,這無疑是加強地方控制的有效手段。又比如,明代在地方實行鄉飲酒禮,《大誥》載:“鄉飲酒禮敘長幼、論賢良、別奸頑、異罪人,其坐席間高年有德者居于上,高年淳篤者并之,以次序齒而列。”并規定了鄉飲酒禮的圖式,如果違反則要笞五十。鄉飲酒禮以恢復古禮的形式來強化秩序精神,對高年有德者的尊崇自然在社會里形成好的榜樣,弘揚敬老孝親的風氣。
然而,歷史的進程卻出現不那么合拍的情況,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奪了侄子朱允炆的帝位,改元永樂。為塑造其奪位的合法性,朱棣篡改《洪武實錄》,謬稱自己為高皇后親生,并編纂刊行《孝順事實》,為其張目。永樂十八年(1420),朱棣將《孝順事實》一書頒發給文武群臣、兩京國子監和天下學校。該書是朱棣命儒臣輯錄古今史傳諸書所載孝順事跡而成,共十卷,收錄孝行卓然可述者207人,每事為之論斷并系以詩,朱棣親自制序冠首,他在序里說:“朕惟天地經義莫尊乎親,降衷秉彝莫先于孝。故孝者,百行之本,萬善之原,大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微足以化強暴格鳥獸孚草木,是皆出于天理民彝之自然,而非有所矯揉而為之者也。”“《孝順事實》俾觀者屬目之頃,可以盡得其為孝之道,油然興其愛親之心,歡然盡其為子之職,則人倫明,風俗美,豈不有裨于世教者乎?”客觀來說,朱棣對孝道的弘揚固然有其私意,但也進一步使孝道成為明朝政治倫理規范的基石,名副其實地以孝治天下。
可以說,明王朝政治進程中的很多大事與孝道有關聯,比如,嘉靖朝的大禮議、萬歷朝的張居正奪情。嘉靖的大禮議是由于正德荒嬉而死,因無后而使皇位空虛,依照兄終弟及的祖訓,正德的從弟、興獻王之子朱厚熜榮登大寶。那么,朱厚熜是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就要面對所謂繼統還是繼嗣的問題,如何確定世宗生父的尊號、如何處理與弘治帝關系,都成為問題。嘉靖登基后下令集議其父興獻王的封號,正德舊臣大多認為朱厚熜應過繼給武宗之父弘治帝,稱弘治為皇考,而以生父為皇叔父。嘉靖認為這違反孝道,要求尊己父為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為楊廷和等拒絕,由此展開延續差不多20年的大禮議。大禮議核心就是禮制與人情(孝道)出現沖突的情況下,如何進行協調的問題。最后以嘉靖帝獲勝而結束,但這使得朝政議題集中在政治倫理次序方面,而對南倭北虜的邊患問題則有所疏忽,導致危機。隆慶后期和萬歷初期,張居正柄政,大刀闊斧進行政治變革,實施考成法,重新核定田畝,為衰敗中的明王朝重新鼓舞起生氣。然而,萬歷五年(1577),張居正的父親去世,按照祖制,朝廷官員的父母過世,必須回到祖籍守制三年(實際為27個月),期滿再起復為官。可是此時正是改革的關鍵時期,張居正回家葬父三月后,萬歷特命官員促其回京,許其不用繼續守制至期滿,此謂之“奪情”。此舉遭到大臣的激烈反對,成為張居正驕奢縱恣罪名的由來,后世張居正仍舊被論定為:“擅權嗜進,遂罹清議,奪情一事,尤屬不經。”可見孝道成為國家政治的核心理念,無論是誰違背,都將遭到清議。
由此可見,明朝政教合一的體制,國家政治體制與儒家理念互為依據與支撐,形成一個整體,孝文化既是國家政治體制合法性的來源,又得到國家體制權力的支持,形成倫理國家,與后世的法理型國家大為不同。當然,這種倫理國家也有導致道德沙文主義的弊端,排斥了其他傳統,形成儒家道德獨尊的情形,導致國家被既有規范給束縛住,面對變幻的世界不那么切實務,而固執地以儒家理念為本,心心念念的是如何維持道德共同體的穩定,從而對東北邊疆事態、世界航海與貿易都不那么究心,錯過了發展的機會。
清朝的情形則略有不同。一方面清承明制,國家繼續采用儒家倫理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合法性的來源與依據。明清鼎革之后不久,順治十三年(1656),順治召集文臣蔣赫德等用唐石臺《孝經》定本為《孝經》作注,并親自撰序,“朕惟孝者首百行而為五倫之本,天地所以成化,圣人所以立教,通之乎萬世而無斁,放諸四海而皆準,至矣哉,誠無以加矣”。對孝道的推崇無以復加。《清圣祖實錄》記載康熙的上諭說:“朕自沖齡,篤好讀書,諸書無不覽誦,每見歷代文士著述,即一字一句,于義理稍有未安者,輒為后人指摘。惟宋儒朱子,注釋群經,闡發道理,凡所著作,及編纂之書,皆明白精確,歸于大中至正,經今五百年,學者毫無訾議。朕以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為弘巨,應作何崇禮表彰,爾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詳議具奏。尋大學士會同禮部等衙門議覆,宋儒朱子,配享孔廟,本在東廡先賢之列,今應遵旨,升于大成殿十哲之次,以昭表彰之意。”康熙把朱子升為配祀孔子的十哲之次,給予了比在明朝更為尊崇的地位。這表明,清廷努力對晚明曾經活躍的思想界進行整肅,以朱子學說為標準,表面上繼續遵守儒家倫理治國。
另一方面,清廷統治者的特殊性,使得國家的統治方式發生變化,國家體制與儒家孝道倫理之間的關系相比明朝呈現出更為復雜的面貌。清廷的統治階層是滿人(包括一部分蒙古貴族),而統治對象是人口占據絕對多數的漢人。從政治學角度看,這是一種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而且清廷對邊疆的擴張,使得國家納入了相當多沒有儒家化的土地,如何對這么多人和這么廣闊的疆域完成有效統治是清廷必須考慮的首要任務。雖然清廷把朱子學列為官方意識形態,但是主要針對區域是清楚的,就是原來漢人所處的地域,而對滿、蒙、回、藏、新疆的廣大地區,則采取因地制宜的策略,并沒有積極推行儒家化的政策,清廷以實用主義的策略來對待明朝的儒家倫理政治。因此,清朝的國家體制與儒家倫理并不呈現完全合一的狀態,儒家孝道倫理也并不是整個國家全民的行為規范,呈現的是一種多元復合型局面。
即便是在施行儒家倫理政治的區域,由于實際統治的需要,清廷壟斷對儒家思想的解釋權,清前期的《大義覺迷錄》案件就是典型事例,為的是維持穩定,防止動亂的發生,于是思想的活力不可避免地被壓制。社會對孝道的遵行當然在延續,但對儒家倫理的解釋空間被遏制,文字獄的高壓,使得士大夫被迫轉而走向樸學之路,因此,清人對《孝經》的研究可謂蔚為大觀。清代著名學者大多有注解《孝經》的著作,比如,魏裔介《孝經注義》、李光地《孝經注》、汪紱《孝經章句》、周寅亮《孝經集注》、魏源《孝經集傳》等,翻檢《清史稿·藝文志》即可略知大概。另外,在中國自五代以后失傳的《古文孝經》從日本回傳中國,鮑廷博把它收入《知不足齋叢書》,引起學術界的興趣,齊召南等學者對此均有討論和研究。
四、五四新文化時期的“孝”:
傳統孝文化與新文明的沖突16世紀大航海時代之后,西方世界獲得開發新世界所帶來的資源契機,帶動資本主義產生,相繼發生啟蒙運動、工業革命,從而走向了現代化,與東方世界出現二水分流的局面。乾隆末年,馬戛爾尼訪華,東西方發生碰撞,經過鴉片戰爭等一系列戰爭和不平等條約,中國被迫向西方開放,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中國艱難而蹣跚地走向近代。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社會性質發生變化,按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描述是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作為傳統中國國體基礎的儒家倫理也勢必會出現動搖,遭受爭議。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在傳統中國原本不成為問題的“孝道”,這時候成為大家關注和爭議的焦點。1919年11月,魯迅在《新青年》月刊第6卷第6號發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稱:“研究怎樣改革家庭;又因為中國親權重,父權更重,所以尤想對于從來認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問題,發表一點意見。總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罷了。”繼而,魯迅撰寫《二十四孝圖》等大批文章批駁三綱五常的禮教,號召把線裝書丟到茅廁里,實行文化革命。持自由主義立場的胡適也掛出“無后主義”的招牌,以此姿態與傳統決裂,然而,1919年3月16日長子胡祖望出生,他于是在7月30日寫詩說:“樹本無心結子,我也無恩于你。但是你既來了,我不能不養你教你,那是我對人道的義務,并不是我待你的恩誼。將來你長大時,這是我所期望于你: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做我的孝順兒子。”這是與傳統對待兒子完全不同的方式。胡適在答汪長祿的信中進而闡發:“我的意思以為古人把一切做人的道理包在孝字里,故戰陣無勇,蒞官不敬,等等都是不孝。這種學說,先生也承認他流弊百出。所以我要我的兒子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他做我的孝順兒子。我的意想以為‘一個堂堂的人決不致于做打爹罵娘的事,決不致于對他的父母毫無感情。”
這樣的論述在新文化運動期間比比皆是,主旨是把個人從傳統的家族和國家等共同體里獨立出來,每個人具有平等的尊嚴和地位,比如,吳虞在《說孝》中說:“以為父子母子不必有尊卑的觀念,卻當有互相扶助的責任。同為人類,同做人事,沒有什么恩,也沒有什么德。要承認子女自有人格,大家都向‘人的路上走。從前講孝的說法,應該改正。”這是當時思想界的主潮,不僅是中國人這么看,西方學者也是如此認為。1920年,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演講,并撰述了大量中國問題的文章,他認為中國傳統道德好的地方就是什么樂天知命那一套,但是最壞的就是孝道。因為孝道是私德,但是中國社會的問題是缺少公德。由此可見,在五四時期,中外學者和思想家對孝道有大體共同的看法,這代表了在傳統中國向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思想界對作為傳統國體基礎的孝道的重新思考,他們的結論也往往是要拋棄傳統孝道,走向新的文明。
然而,在現代化焦慮之下,有學者對孝道也有著不同的看法,1930年,在中山大學執教的鄔慶時撰《孝經通論》,他在自序中說:“迨仇孝之說自蘇俄輸入,大義日晦,舉國若狂,家庭之間遂從此多事矣。”“即主張法治之國將來亦必有改用孝治之一日。然則《孝經》一書今雖無人過問,而有待于研究者固甚亟也。”鄔慶時此論無疑具有前瞻性。中國在經歷了20世紀的文化革命和全面西化之后,道德滑坡,信任缺失,給國家和社會帶來的弊端也日益顯現,現代性在西方也成為一個思考和批判的主題,原子化的個人主義也越來越使人失去自由,查爾斯·泰勒、麥金太爾等學者對此都進行了反思。現在的21世紀,中國該往何處走,成為一個擺在所有中國人面前的一個迫切命題。對孝道在傳統中國的歷史沿革的梳理,也就成為應有之義。
總而言之,孝文化是與傳統中國的社會發展水平和政治文明程度相配合的,是在匱乏經濟條件下凝聚社會與國家的必需力量,在外敵環伺,時刻面對游牧民族侵擾的情況下,采取國家和社會優先的策略,個人置于整體性之中,是一種理性選擇,但是,由此也使得國家這個大共同體具有過多權力,公私領域合一,容易出現個體選擇空間小,個人權利被束縛,個人尊嚴被踐踏的情況,引發了不少社會問題,所以戴震有“酷吏以法殺人,后儒以理殺人”的判斷。在現代科學革命之后的社會,處于豐裕經濟的情況下,政治文明得以啟蒙,當今中國如何調整個人與國家的關系,是一個重要問題。我的總體看法,應把孝道從傳統國體基礎的位置解放出來,恢復其弘揚人性之美、倫理道德的本質,同時注重保護個人自決的權利,把國家建立在法治基礎上,在個人、家庭、社會和國家之間保持適當的彈性和距離,形成開放的空間和制衡機制,避免出現整個民族、全體個人被綁架的極端情況,這既是個人之幸,也是國家之幸。
注釋
①對此的最新論證,請參考美國哲學家麥金太爾(MacIntyre)的新著《依賴性的理性動物》,劉瑋譯,譯林出版社,2013年。②《藝文類聚》卷二六《人部十》引《孝經鉤命決》,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464頁。③④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45、131頁。⑤班固:《漢書》卷二《惠帝紀》,中華書局,1962年,第86頁。⑥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卷四《曾子本孝》,中華書局,2013年,第92頁。⑦比如楊家將故事,漢代以后的史書撰述、大眾讀物和民間傳說都是表彰和宣揚這種優先性的,例子甚多,不贅述。⑧《考城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456號,成文出版社,第1444頁。⑨《孝經注疏》卷首,阮元:《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第2540頁。⑩朱熹:《小學原序》,《朱子全書》修訂本第13冊,安徽教育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93頁。朱升:《朱楓林集》卷四《小四書序》,黃山書社,1992年,第51頁。《明太祖實錄》卷一七六,洪武十八年十月己丑,臺灣“中央研究院”校訂本,1962年,第2665—2666頁。《明史》卷九三《刑法志一》,中華書局,1974年,第2284頁。《孝順事實》,《北京圖書館藏古籍珍本叢刊》史部第14冊,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489頁。陳鵬年:《道榮堂文集》卷三《吳復庵先生祠碑記》,岳麓書社,2013年,第867頁。《御制孝經序》,載駱承烈編《歷代<孝經>序跋題識》,光明日報出版社,2013年,第196頁。《清圣祖實錄》卷二四九,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丁巳,《清實錄》第六冊,中華書局,1985年,第466頁。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第140頁。《胡適文存》卷4《我的兒子》,《民國叢書》第一編,上海書店,1989年,第101頁。原載《星期日》社會問題號,1920年1月1日,載《吳虞集》,中華書局,2013年,第17頁。具體論述參考羅素《中國問題》,秦悅譯,學林出版社,1999年。鄔慶時:《孝經通論》,商務印書館,1930年,第1頁。戴震:《與某書》,《戴震全集》第一冊,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212頁。
責任編輯:王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