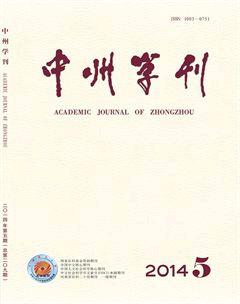孝道時間性與人類學
張祥龍
摘要:研究孝道與人性的關系,離不開當代人類學對于人類獨特性的新發現。這些發現否定了一些以往的論斷,又新發現了一些以前不知者,兩者中都有與孝道相關者。在梳理了這方面的情況之后,通過哲學人類學的視野來探討男女為何會成為夫婦,孝道為何是一種人類特性,尤其是孝是如何在人類時間意識的變化中出現于人類生存過程中的。廣義人類的兩足直立行走方式導致了人類新生兒的極度不成熟。相比于工具的改進、打獵獲得肉食等其他影響人類進化的因素,新生兒不成熟的特征更持久深刻地改變了人類的基本育子方式和生存方式,導致了人的內時間意識的深長化,為孝道的出現準備下了長期記憶的意識前提。孝道意識的呈現不可歸因于年長者的有用,而是深長時間意識被育子經驗反轉激活的結果。
關鍵詞:人類特性;夫婦及家庭的形成;人類嬰兒的極度不成熟;內時間意識的深長化;親子互繞聯體
中圖分類號:B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14)05-0011-10
一、引言
要探究孝道的哲理根基,必先曉得它與人性的關系,因為孝道的哲學問題首先就是:它是人性的表達還是僅僅因后天的文化和所受教育形成的?我們對人性的認識,相比于以往兩千多年,在20世紀有了重大變化。除了生物學(比如基因學說)、心理學特別是弗洛伊德潛意識心理學、文化社會學和歐洲大陸哲學(如現象學、結構主義)等之外,造成這種變化的一個重要動因是人類學及相關學科的新發展。比如,由于人類學的新發現,我們現在不能再將能使用工具、有反思意識、會使用語言符號(而不是具有發聲語言)等特點看作是人類的獨有特性了。我們也不能再受摩爾根的影響,斷定人類本性與家庭沒有必然關系了。
但我們也知道,與人類本性相關的話題,在某些方面是相當敏感的。比如,主張人類本性受到種族基因的影響,或者說人性與性別——不管是異性性別還是同性性別——有某種內在關系,都可能受到激烈的、超出純學術的批評,甚至譴責。人類學與我們的切近還可由威爾遜1975年出版《社會生物學》引起的軒然大波窺見。①它引發的抗議和近乎政治運動的爭論,除了因此書的最后一章以講其他社會生物物種的方式——基因、性別關系、社團結構等——講到了人類的特性②,還由于這位科學家表露出了對于我們這種人的“過時”性的不滿,認為“它是為了部分地適應那消逝了的冰河期而草率形成的”,所以今天的人類或許應該“朝向更高的智力和創造性而堅決推進”③自身的改造。這種要從根基處改造人類或人性使人“進化”到“后人類”的危險主張,甚至成了某種意義上的科學規劃或科學實踐的主導目標。④
可見,人類學以及會重新塑造人性的科技都不止于知識和技術了,它們與我們對于人性和孝道的理解、估價越來越直接地相關。關注人類本性和人類命運的哲學家們,已經越來越重視它們了。如果現在我們處于兩三百萬年前,同時有四種或更多的人族(huminin)和人屬(genus Homo)存在⑤,或十萬到四萬年前,同時起碼有三種人——智人、尼安德塔人和亞洲的某一種,比如弗洛勒斯人,那么當我們談論“人性”時,就不會那么容易地“先天而天弗違”,或那么想當然地下定義了。如此一來,簽訂“人權公約”就要難得多,哲學與人類學就更難分開了。同理,高科技和相應的文化、政治經濟學正在構造新的人屬,那時我們將降到進化表的第二級。這豈不是個更根本的形而上學的問題嗎?
“草色遙看近卻無。”人類學、靈長類學、社會生物學甚至生物學這些學科與哲學的內在關聯,有時要到“遙感”的距離才會對我們出現,就像一些荒原和森林里的古跡要在高空中才能“遙感”到。距離過近,看到的就只是不同乃至沖突。
本文是對人類學進展如何影響到我們對于親子關系、特別是孝道的理解的一個初步的、不全面的和粗糙的闡述。限于作者的微薄學識和形成此文的時限,難免掛一漏萬,只是希望引起有心人的一點關注,得到方家們的批評。
二、人與其他動物的區別何在?
從珍尼·古多爾1960年的發現以來,加上后來更多的觀察表明,黑猩猩和一批靈長類都是會使用工具的。⑥而且,黑猩猩等也有合作捕獵的能力,并與同類分享獵到的肉食。⑦一些靈長類(如獼猴、猩猩類)也有學習的或形成代際傳遞的“文化”能力。⑧此外,黑猩猩已被證實“可以學會使用(如果不能說的話)語言”。⑨兩只黑猩猩,華舒(Washoe)和露西(Lucy),從小被收養人教授美國手語(American Sign Language),學會了100多個代表英語單詞的符號,并能將它們組成簡單的句子,與人交流,如“你,我,出去,快”、“[旁邊猴舍中]骯臟的猴子”、“臟貓”等。⑩當然,靈長類或猩猩類(黑猩猩、波諾波猿、大猩猩等)的這些能力,與人類相比,實在是原始得很、“萌芽”得很,但它們畢竟說明,在這些方面,人與其他高等動物(其實還有海豚等)之間的區別,只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本質的或性質上的。那么,人與其他動物的比較真實的區別何在呢?科塔克在《人類學:對于人類多樣性的探討》中寫道:
看來人類是最能合作的靈長類,表現在尋找食物和其它社會行為中。除了黑猩猩中有獵肉分享之外,猿類傾向于個體的尋食。猴類也是獨行覓食的。在人類的尋食者們那里,男人一般去打獵,女人則采集,然后都將得到的食物帶回營地來分享。那些不再覓食的老年人從年輕些的成年人那里得到食物。每個人都分得大獵物的肉。由于受到年輕者的供養和保護,年長者過了生育年齡后還活著,并由于他們的知識和經驗而得到尊重。在一個人類群組(band)中儲存的信息,遠大于任何其它的靈長類社會所具有的。
相比于黑猩猩和波諾波猿(bonobos,倭黑猩猩),人類的性伴侶的聯系傾向于更排外和更持久。由于我們這種更穩定的性關系,所有人類社會都有某種形式的婚姻。
人類從自己出生社群(group)之外的社群中選擇性伴侶,因此夫妻倆人中至少有一個是外來的。然而,人類終生都與兒子們和女兒們保持聯系。維持這些親屬和婚姻聯系的體制造就了人類與其他靈長類的主要區別。
讓我們來分析一下這三段引文。首先,人類盡管是最能合作的靈長類,但其他靈長類中也有某種合作,所以人類在“合作”這個性質上與其他靈長類的區別只是程度上的。但是,下面列舉的一些特點卻有某種結構上的變化了。人類有男女之間的覓食分工,這是其他靈長類所沒有的。人類有養老、敬老的特點,而其他靈長類或所有其他動物都不具備它。人類有排他的、長久的性伴侶關系,這在動物中很少見。人類的性結合有婚姻制保障,這當然是獨特的。人類是外婚制,這在猿中間也有表現。但更被強調的,而且是被很合適地強調的是“人類終生都與兒子們和女兒們保持聯系”,即人類的親子關系是獨特的。總之,是人際關系的結構和樣式,即發自夫婦陰陽對生婚姻和分工的生存時間樣式,比如終生親屬認同和代際間的雙向關愛,而不僅是某一種孤立的能力,將人類與其他靈長類更真實地、對于我們也更有意義地區別開來。這是很有見地的,其實也是人類學多年調查和反復研究達成的共識。
當然,人類與其他靈長類,尤其是猿類之間,有明顯的解剖的和基因上的區別。比如人類是直立和兩足行走,由此造成了一系列身體結構上的重大后果(我們下面會再討論它們)。但是,只有將這些生理上的特點與人際關系結構及其造成的基本行為結合起來看,才會出現對于我們的生存理解來說有意義的區別,而不僅是博物館和宗教里的區別。
人,或我們這種人,不是一般的社會性動物。它是男女有別、養老敬老、結婚成家和終生維持親子關系的動物。沒有這種人類學視野,非抽象的人性就由某種理論來虛構了,或者被淹沒在籠統的“社會性”、“文化相對性”之中了。但我們確實是有“人性”的,它并不抽象、固定,而是我們這種人類具有的“道德”“政治”所從中生出的親子時間根源。人的美德乃至道德,就是從這種人的代際倫理時間而來!
我們從來就是有倫理的,而且是具體鮮活的倫理。它們不是詳盡的道德規范,而是由不同人群的文化塑造出來的,但它們又絕不像“亞當的犯罪智慧”或“理性”“語言”“社會性”那么抽象。所以儒家講的“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是不知西方人類學的情況下所達到的充滿了人類學見地的灼見。
三、男女為什么要成為夫婦?
近現代的人類學從西方開始,所以,以往的人類學家大多以西方男女觀和婚姻觀為基底來觀察其他文化人群的男女及婚姻關系。一開始,他們相信某種近乎西方家庭和親屬觀的模式是普遍有效的,接下來,他們發現世界上的“原始民族”中存在許多不同于這個模式的兩性關系和家庭組合方式,于是就倉促地做出一些判斷。19世紀的某些人類學家,如摩爾根,宣稱人類早期有過一段無婚姻、無家庭的雜交時期,或所謂“共夫共妻”的時期。但是,后來更嚴謹、求實的大量人類學研究表明,摩爾根在這個問題上錯了,人類從頭就有婚姻,有家庭。而且在同一時期的不同人群里,可以同時存在多種不同的家庭形式。一夫一妻婚姻和家庭也不必完全基于私有財產的繼承,當然,也不一定只基于情感。以往的哲理想象力太簡單,太想當然,被非此即彼(主觀/客觀、物質/精神、功利/情感等)的實在觀和單線進步觀框定,進不到幾百萬年人類進化的委曲之中。在這里,有文字記載的數千年“文明史”說明不了什么問題。時間的悠長使“考古”或“本原學”(arche-ology,考古學)的幸運發現和想象力在根本處不可避免。那么,有什么理由來解釋人類男女關系為什么會是這樣(這種夫妻化)而不是那樣(亂交、嚴格的一雄多雌、一雌多雄、社會昆蟲式的兩性關系、嚴格的一夫一妻等)呢?
對于人類形成夫婦關系最常見的也最基本的一個解釋可稱為“育子須父”說——漫長而艱難的人類嬰兒養育期使“父親”或“丈夫”的育子貢獻具有相當大的生存意義。比如戴蒙德寫道:
人類嬰兒即便在斷奶之后,所有的食物仍由父母親供應;而猩猩斷奶后,就自行覓食。大多數人類父親密切涉入子女的撫育,母親就更不用說了;而黑猩猩只有母親這么做……因為我們取得食物的方法既復雜又依賴工具,剛斷奶的嬰兒根本無法喂飽自己。我們的嬰兒,出生后得長期喂養、訓練與保護——比黑猩猩母親需要付出的,多得太多了。因此人類父親只要期望子女存活、長大,通常就會協助配偶養育子女,而不只是貢獻一粒精子。
如果情況是這樣,那么兩性關系就需要是長期的和基本對偶的。在采集—打獵時期——這是人類進化中最漫長而構造人性的時期,一夫養不了多妻及其子女,多夫養一妻則難以區分子女歸屬,投資不劃算。這個假說很有些道理,以一個極其重要的人類學現象,即此引文中涉及的人類嬰兒非“長養”而不能成活的生存時間特點為依據。之所以會這樣,有一系列原因,其源頭或許是人的直立兩足行走,由它而導致了多米諾骨牌效應,盡管這種效應是極其緩慢地形成的。直立兩足行走允許猿人比黑猩猩更多地用前肢或手來運用工具,這就可能慢慢刺激人腦體積以及頭顱體積的增長。但另一方面,直立行走又限制了人的骨盆開口處的寬度,不然就支持不了直立的上身。這樣,人類的婦女生孩子就艱險了:胎兒頭大,骨盆開口又限制了產道,使她無法像其他哺乳類包括黑猩猩那樣地順利生產,于是,就只能在嬰兒還極其不成熟時就產下它。結果就是人類撫育子女的漫長和艱難,特別是在采集—打獵時期的游動生活方式中,更是這樣。于是,若無父親的協助,一位人類母親要養活子女、特別是連著養活幾個子女的可能就不大了。
可是,這父親是如何幫助母親或丈夫如何幫助妻子的呢?一種19世紀末以來就流行的、甚至現在還有影響的學說是“獵人丈夫說”。假設人類男子自遠古(比如自能人、直立人乃至古智人時期以來)就是獵人,而且這獵人的獵物——肉食——對于妻兒們的生存至關重要。但是,這幾十年的研究起碼在頗大程度上削弱了它。根據對于現存的采集—打獵社會的研究,獵手們打到的獵肉并不只在他(們)的家庭中享用,而是分給此社群中的每個家庭。這也就是說,獵肉是一種“公共福利”,它的分配是以社群而非家庭為單位的。這樣一來,獵肉就不能直接有助于塑成夫婦關系了。
要代替這個假說的,是“男獵人競爭女人說”。一些學者提出,男性的獵人或戰士是為了爭得女子而冒險涉難,因為他的成功為群體帶來高等食物和安全,提高了他在群體成員心目中的價值,女人就更愿意委身于他,他娶到更能干的女人的機會就大,他的后代即便在他不參與直接喂養的情況下,其存活率也就更大。這個學說似乎沒有充分解釋為什么男人會基本上維持穩定的夫婦關系,而不是到處拈花惹草。或許此假說假定了,男人們打獵成功的機遇總的說來是比較平均的。不管怎么說,這兩種假說都將男女結合成夫婦歸為多于性關系的動因。
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也有學者論證道:在采集—打獵的人類社會中,是女人的采集而不是男人的打獵提供了食物的主要來源,盡管部落中的人好像更看重獵肉。這個論證有利于上面兩學說的后一個。
另一個解釋人類夫婦關系的是“保護說”或“保鏢說”,即夫婦關系的形成主要由于男人為自己的配偶和子女提供了保護。學者們注意到,在靈長類中有殺嬰現象,即有的雄性(比如新成為社群首領的雄性)要殺死不是自己后代的同類幼仔。有的學者特別重視它對于塑造靈長類的雌雄關系乃至人類男女關系的作用。按照它,雌雄乃至男女的終年結盟或結伴關系主要出自保護自己后代的進化適應。在加拿大的一項調查證實,結了婚的女子受到性侵犯殺害和性騷擾的概率確實較低。
還有“金屋藏嬌”的假說。其認為人類女子隱性排卵的特點(不同于其他靈長類),使男子無法確定女人的受孕時間。為了保證她生下的后代是自己的,男人就必須與女人長相守,由此導致了夫婦關系。而且,女人沒有確定的發情指標,也避免了其他男人在特別時期的沖動干擾。
總之,現在幾乎所有人類學家都承認人類的夫婦關系模式——在眾多男人共處的社群中夫婦終年廝守,甚至終生相伴(包括一定程度的一夫多妻等現象和婚外情)——的自然事實。而且認為,相比于其他動物,特別是靈長類,這種關系是獨特的。也就是說,夫婦關系是不尋常的人性特征。看來儒家主張的“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是相當“人化”的或“人性化”的。不少人類學家在談到人類的配偶關系時,傾向歸因于人類性活動的終年化,乃至體毛減少等生理特點。其實,那只能說明人類成人在生殖期中可以經常有性活動,邏輯上也包括亂交的男女關系,卻無法說明人類夫婦關系的形成。夫婦形成的理由既有生理性的,也有超生理性而又非體制性的。
它表明,人類是特別能權衡妥協或者說是特別有內時間意識的中道存在者,而不是像其他的高等動物那樣,雄性之間在爭奪雌性時或是完全排外的,或是雜亂無序的。這種內時間意識也使得黑猩猩的“自身—他者意識”和“欺騙意識”成為可能,但它在人這里的深化使得人的“夫婦意識”成為可能。當然也可以反轉一下,從女性的角度來看,女性在應對男性的體力優勢時,進化出獨特的平衡機制或“欺騙”機制,比如隱性排卵,既迫使男子比較專一,又減少了群體內男子間的競爭烈度。因此,人類從根本上就有家庭,包括基本上是一夫一妻的家庭,因為這是人性的表達,是內時間意識的智慧表現,是人類進化適應的優勢所在,與私有制無關。
但迄今的所有探討都忽視了一個在我看來絕非不重要的問題,即人類子女與父母保持終生的密切關聯對于形成夫婦關系的意義。迄今有關的人類學研究幾乎都關注于同一代的雌雄男女的關系,頂多涉及從親代到子代的垂直關系(比如提及人類有終身親屬關系),而對于更有時間跨度的代際關系,特別是從子代到親代的反向關系,置若罔聞,好像那是可以完全忽視的。可是,如前所說,人類的特點就是內在時間意識的深長化,這樣的存在者的基本結構怎么能不與代際間性相關呢?比如可以設想,子女與父母的終生聯系參與塑造了人類的社會關系網,改變了它的結構,促使父母或前輩夫婦關系的形成和穩定。這方面的可驗證模型也是不難做出的。
四、孝:被忽視了的人類特性
孝這個人類現象迄今還沒有成為一個重大的人類學問題,也沒有成為一個重大的哲學問題。這種狀況應該改變,因為它是人類的內時間意識的集中展現,從中可以窺見人性的最獨特之處。不理解孝,人類學就還在頗大程度上徒有虛名,哲學家們討論的人性和人的生存結構就是無根之木。但是,人類學和當代現象學及生存哲學的研究畢竟為我們反思這個問題提供了一些可貴的觀察視角和佐證。
1.孝是一種非特殊的人類獨特現象
孝,如這個漢字所顯示的,意味著子代對于老去的親代的照顧、尊重、懷念和繼承。它在其他動物中存在嗎?好像是不存在的,盡管中國的孝書中有“慈烏反哺”一類的說法,但從來沒有確鑿的根據。甚至在黑猩猩、波諾波猿中,也沒有它存在的證據。上面述及,原來不少被認為是人類的獨特之處的,如使用工具、自身意識、運用語言符號、政治權術等,現在都在動物、特別是我們的表兄弟猩猩類中被發現了,起碼是它們的初級形態。但是,孝這個現象,就像兩足直立行走,卻只是特立于人類之中的。那么,難道孝如一些人所說的,只是人類的特定文化現象而不是一個非特殊的人類現象嗎?看來也不是的。人類學家們已有共識,孝行——當然人類學家們多半不會直接用這個詞——是人類的基本現象。比如,《人類學:對于人類多樣性的探討》在表述人類的特點時有這樣一段第一節已經引用過的話:
那些不再覓食的老年人從年輕些的成年人那里得到食物……由于受到年輕者的供養和保護,年長者過了生育年齡后還活著,并由于他們的知識和經驗而得到尊重。
可見孝不只是個特殊的文化現象。在談到人與猿的區別時,靈長類學家和人類學家們就會注意到這個現象;或者,在分析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s)時,也會注意相關的現象。比如,尼人的骨骼上往往有創傷,可能是獵大獸時導致的(也可能是尼人群體間相互爭斗造成的),但其中的大多數都痊愈了,“證明在這種人族存在者(hominins)中有社會協助”。這就讓人可以去推測,尼人中或有家庭和孝養行為的存在。但是,這種家庭和孝行肯定遠不如我們這種現代智人發達,因為相比于現代智人,尼人里邊老年人和嬰兒的百分比較低,而青春期的和成年的人所占的百分比較高。
2.動物——包括黑猩猩——無孝可言
古多爾等人多年觀察的黑猩猩的典范母親弗洛(又譯為“芙洛”),曾身為猩群中雌黑猩猩的老大,養育了數個子女,當她變老后,那些后來很成功的子女——法賓、費岡、菲菲——并沒有來照顧她。最后她死于一條河邊,無“猩”理睬。請看珍尼·古多爾的描述:
這時,老弗洛看上去已經很蒼老了,她估計快50歲了,牙齒都磨壞了,曾經黑亮的頭發都變得又黃又稀疏,滿臉的皺紋,虛弱得像個老太太,已經經不住弗林特[弗洛的最后一個兒子,此時8歲]騎到她背上了……他們兩個老是單獨在一起,因為老弗洛虛弱得都跟不上大伙兒了,她的衰老使她和弗林特都很孤單。
老弗洛死于1972年,這是我特別難過的一天。我認識她這么長時間了,她教了我很多東西。她是在過水流湍急的卡岡比河時死的。她看上去很安詳,好像她的心臟是剛剛突然停止跳動似的。
黑猩猩沒有絕經期,這是與人類的又一個區別,所以弗洛至死還在盡母親之責。弗洛死后三周,弗林特也死了。弗洛的子女們就生活在同一個群中,他們也曾很依戀她,幫她對付其他的黑猩猩,女兒菲菲也曾對于弟弟很有興趣(可能是在不自覺地積累養子經驗),弗洛死后菲菲也曾試圖幫助弟弟弗林特,可見黑猩猩中是有某種親屬認同的,但他們都沒有來實質性地幫助年老的母親。為什么會是這樣?在弗洛最需要成年子女照顧的時候,它不在那里。這并不說明她的子女們不好,而是他們還根本不知道這是好的、應該的。黑猩猩的意識還達不到“子女應該照顧年老母親”的程度,因為他們的時間感受能力沒有那么深長。按一般的進化論解釋,這時弗洛子女對于她的照顧,是無生存競爭效應的,因為她衰老了,無大用了(比如弗洛最后生的兒子弗林特就被寵壞了,缺少生存競爭力),應該將寶貴的精力用到照顧他們自己的后代身上。“弗洛死后20年,她的子孫形成了迄今為止岡比[Gombe,又譯‘貢貝]最強大的家族。”
五、為什么會出現孝?——更深長的內時間意識
但在人那里——直立人?或要到古智人?——卻出現了明確的孝行,而且進化論學者們也可以為這孝行找到增強進化適應力的根據,比如老年人的知識和經驗對于群體的生存有幫助,特別是在出現異常狀況時,像旱災時記得哪里有水,饑荒時知道哪種植物可食,瘟疫時知道哪種草藥可療。但是,這個轉變是如何發生的?老年如何從無用變為有用?特別是人猿之共祖如何知道這種有用?卻是這種解釋無法說明的。情況倒似乎是:造成孝行與造成“它有用”實際上是一個過程。沒有深長的時間意識,老年人就不會比中年人更有知識和經驗的優勢[在今天這個技術橫行的時代里,老年人又似乎變得無用了]。
關鍵在于,在人這里,不管是能人(平均腦容量600—700cm3)、直立人(腦容量900cm3)、古智人(腦容量1135cm3)、尼安德塔人(腦容量1430cm3),還是現代人(腦容量1350cm3),在某一時代、某一階段那里出現了足夠深長的時間意識,致使他或她能夠記得或想到:母親和父親對于自己曾有大恩,應該在他們年老時回報。如果不這樣做,就會在某個時刻感到不安和愧疚。能夠有這種孝意識的人,一定是能進行跨物理空間和物理時間而想象和思考的人,能積累知識和經驗,能夠在各個層次上合作,也就是到老也能夠被后代認為是有用的人。
1.什么使深長時間意識出現?——人類新生嬰兒的極度不成熟以及親子聯體
相比其他哺乳類、靈長類,人類新生嬰兒的不成熟不只是量的變化,它深刻改變了人類嬰兒與母親、父親或任何抱養人的關系乃至父親與母親的關系,也改變了人類本身的親屬及社會關系結構。人們總習慣于將男女或夫婦比作最明顯的人類陰陽關系,相對、互補而又出新;但就人類的形成史和實際生存樣式而言,由兩足行走導致的新型親子關系,才可能是那產生一切新形態的陰陽發生的源結構。人類嬰兒的不成熟達到了什么程度呢?看一位人類學家M. F. Small所寫:
人類嬰兒出生時,它從神經學上講是未完成的,因而無法協調肌肉的運動……在某個意義上,人類嬰孩的非孤立性達到了這種程度,以致它從生理和情感上講來只是‘嬰兒—撫養者這個互繞聯體的一部分。
這講得不錯。人類嬰兒與撫養者(在迄今為止的人類史上,這撫養者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嬰兒的父母)不是兩個個體之間的親密關系,而首先構成了一個互繞聯體。人類嬰兒必須提前出生,它與母親之間的肉體臍帶雖然斷了,但梅洛—龐蒂身體現象學意義上的身體臍帶還活生生地聯系著母子乃至父子。所以親子關系,更可以被稱為陰陽關系。正是由于它,導致了人類家庭。人類的夫婦關系,如前所說,也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這個關系。從現實的生成順序看,有夫婦才有親子;但從人類學、哲學人類學或人類形成史的發生結構看,有親子才有夫婦。
嬰兒出生的不成熟如何導致了內時間意識的深長化呢?嬰兒出生的極度不成熟,意味著它的生命的極度微弱,隨時可能而且比較容易死亡。因此,養活這樣的生命需要母親乃至父親完全投入,甚至深刻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從帶孩子開始,親代就失去了“自己的”生活,而進到一個互繞聯體的生活之中。嬰兒的不獨立就等于親代的不獨立。這從母子夜間睡覺的方式可以略加窺見。另外,由于嬰兒出生時腦部是遠未完成的,所以出生之后的一段時間內,頭顱和腦要像個氣球一樣快速擴張,最后頭骨才能合攏。可以想見,在這段意識身體(主要表現為頭)的塑成期或“正在進行時”中,嬰兒與母親或撫養人的互動具有深層構造的、終身的后果。在某種意義上,嬰兒與養育父母的內在關聯“長進了”它的生命之中,而不只是一般的記憶關聯。此現象或可名之曰“后天的先天關聯”,因為嬰兒出生后的“后天”,在其他靈長類那里還是在母腹中的“先天”。
心理學家們將記憶分為短期記憶和長期記憶。人類嬰兒與父母的關系,其核心肯定屬于長期記憶,而且應該是一種不會被遺忘的本能記憶或現象學意義上的身體記憶。我們學了外語,即便建立了長期記憶,但由于長期不使用,或由于年老,也會淡化或在相當程度上遺忘。但我們一旦學會了第一語言,或學會了游泳、騎車,即便長期不用它,其核心部分也不會被遺忘。人與養育己身父母的關系,甚至早于第一語言的學習,所以起碼屬于后一種長期記憶,即質的長期記憶。人隨著歲數的增長,甚至到年老時,這種記憶可能變得更強烈,即便父母在他或她年輕時就故去了。
除了親子之間的深度關聯,這種關聯持續的時間之長在動物中也是罕見的。現在的人類后代,平均14—15歲性成熟,能夠生活自立更晚。而我們可以推想,人類形成史上的嬰兒成熟期從生理上還要遲,因為對黑猩猩和大猩猩的研究都表明,野生自然生活的要比圈養的成熟期遲得多。野外的雌黑猩猩生第一胎的平均年齡是14.5歲,圈養的是11.1歲;野生的大猩猩生第一胎的年齡是8.9歲,圈養的是6.8歲。而現代人,特別是經過工業革命后的人類生活方式,相當于被圈養。靈長類養育后代要比其他動物包括其他哺乳類艱難。黑猩猩養后代也比大猩猩更困難,比如黑猩猩母親攜抱她的嬰兒達5年之久,而大猩猩嬰兒發展自身的運動能力比黑猩猩嬰兒快得多,6個月的大猩猩幼仔就能騎到媽媽背上而不會掉下來,兩歲就基本上不用母親抱了。我們知道,黑猩猩要比大猩猩從生理到智力都更接近我們。情況似乎是:養孩子越是艱難、越是時間長久的,就越是被這種“長期投資”逼得要發展出內時間意識。
這兩個情況加在一起,使得人類必須有長遠的時間視野,能做出各種事先的預測、計劃和事后的反省、回憶,不然就難以養活子女,傳承種族。
2.養兒艱難的時間意識效應
相比于威爾遜津津樂道的所謂人類的好戰性、一夫多妻制、鮮肉的極端重要性,人類嬰兒出生的極度不成熟才是一個真正持久和影響深遠的事實,它在狩獵—采集的人類社會中發揮了更大的作用。因為它,在那樣一個不斷遷移的社團中,父母親必須有更長遠的時間意識,知道如何養活、保護自己和嬰兒。比如,那時的婦女必須“維持四年的生育間隔,因為母親必須照顧幼兒,直到他們長大,跟得上大人”。由于拉扯幼小子女的母親的勞動能力和移動能力都很受限制,可以想見,她必須獲得人際的合作才能維持自己和子女的聯體生存。首先,她擇偶一定會極其看重男人的護家素質,除了他的保護能力之外,還有為人的可靠——忠實、熱誠、慷慨等,而這些都含有內時間因素。而且,這男子不可太軟弱,又不可一味地好斗,那樣最終會葬送家庭,因為在這種“拉家帶口”的情勢下,幾乎沒有誰是戰無不勝的。所以男子必須有權衡、合作、妥協和把握時機的能力。哪里最可能找到食物,哪里最可能有朋友而不是敵人,哪里是危難時可以藏身或避難的地方,哪種生存策略最能經受不測未來的顛簸,這是所有父母永遠要操心牽掛的。再者,一位母親與家庭、家族乃至鄰里中的女性的合作也相當重要。婆婆、嫂子、小姑、女友等,都是能夠為她臨時帶兒女的分身存在者,她都要盡量與之協調。二三十年的育兒期,哪種意識能應對,它才會在幾十代、幾百代、幾千代的考驗后,留存在人性之中。因為這個或這些“小冤家”,人類才不得不是一種時間化的存在者。
一些有見地的人類學家指出,生態位的開辟及新工具的使用與人族更長的成熟期有內在相關性。但是,他們這里是否將因果弄顛倒了,或起碼是將原來是一個相互因果的雙向過程簡化為單因果的了?是復雜工具和習得的越來越重要導致了人類成熟期的延長,還是應該反過來看,是人類成熟期的延長導致了習得及工具使用的更加必要?就人類進化史的總體而言,這應該是一個互為因果的雙向正反饋或“自催化”過程。但是就人族和人屬的早期進化而言,也就是人類的發源動機而言,嬰兒出生時的極度不成熟以及相應的人類成熟期的長久似乎是更根本的或更身體本能的。原因是,黑猩猩的平均腦容量是390cm3,而屬于人族的南猿(被認為是人類的最早起源,是我們所知最早直立兩足行走的人科動物)的平均腦容量從430cm3(A.afarensis)、490cm3(A.africanus)到540cm3(A.robustus)。其頭顱骨肯定比黑猩猩的大,而且就其高值而言,這個差距(100至150cm3)在這種腦容量水準上也不算很小。而且,南猿的產道比后來的人族要狹窄。所以,盡管南猿嬰兒的頭顱骨要比人屬的小,但嬰兒出生的不成熟和青少年期的延長現象應該已經出現,盡管從量上無法與后來的現代人相比。科塔克寫道:
年輕的南猿們(young australopithecines)一定要依靠他們的父母和親戚來得到食物和保護。這種多年的兒童期依賴狀態會為他們提供用來觀察、受教和學習的時間。這也就為他們具有某種初步的文化生活提供了間接依據。
所以,情況可能是:南猿青少年期的拉長所形成的養育壓力或選擇壓力,促使了他們的父母對于新食物和新工具的尋求和珍視,因為直立兩足行走必會導致不成熟的嬰兒出生和延長的成熟時間,但卻不必然導致新食物和新工具的尋求。無論如何,養育時間延長不會晚于、也不應歸于新工具的尋求和使用。南猿與黑猩猩的最大區別不是工具的制造使用,而是直立兩足行走造成的養育延長現象的有無。
南猿乃至“阿爾迪”一類的“始祖種”,兩足直立行走始于接近400萬年前,乃至440萬年前,而迄今發現的最早的人類加工過的石器工具是250萬年前的,據說是南猿的“garhi”種使用的。當然,還沒發現不證明石器工具不會更早出現,但情況似乎是:兩足直立在人類形成史上最早出現,養育延長和石器工具的制造跟在后邊出現。如果嬰兒早出生導致的養育延長與當時的工具和食物譜達成了平衡,氣候和生態環境又變化不大的話,人類的進化可以有漫長的停滯期,比如直立人在100多萬年間,其工具沒有大的變化。如果進化的動力只來自打獵和相關工具的話,那么就無法解釋這么長久的停滯,因為這動力應該一直在發揮作用。可是,如果認為原初的進化動力主要來自養育延長的話,那么,這種延長了的養育期是可以與某種環境、某種因素達成平衡的。工具總會在使用中不斷改進,而人的身體卻可能在適當的條件中維持原狀,試想四萬年前人類進化的“大躍進”和一萬年前的農業出現以來,人類的身體并無重大進化,而工具卻發生了何其巨大的改進,就可知道這個差異了。
3.孝出現的契機
如上所示,孝指子女對年老父母乃至前輩親人的照顧、尊重、懷念和繼承,孝道則指對這種孝行的自覺化、深刻化和信仰化。它的出現而非保持,并不能只由不少人類學家給出的“老人保存和傳遞有用知識”這樣的理由來解釋,因為孝的出現與能夠保存有用知識是一個而非兩個過程,使得孝出現的時間意識也會使保存知識成為可能。所以,能夠對孝做實用主義的考慮已經預設了孝。對于人之外的其他動物,包括我們的表兄黑猩猩,孝是無用的,徒然浪費可用來維持己身和撫養后代的精力與能量,于該種群的生存不利。
這拐點很可能出現于人類子女去養育自己的子女之時。這個與他/她被養育同構的去養育經驗,這個被重復又被更新的情境,在延長了的人類內時間意識中忽然喚起、興發出了一種本能回憶,過去父母的養育與當下為人父母的去養育交織了起來,感通了起來。當下對子女的本能深愛,與以前父母對自己的本能深愛,在本能記憶中溝通了,反轉出現了,蒼老無助的父母讓他/她不安了,難過了,甚至恐懼了。于是,孝心出現了。他/她不顧當時生存的理性考慮,不加因果解釋說明地干起了贍養無用老者的事情,他/她的子女與他/她的父母的生存地位開始溝通,盡管說不上等同。起頭處,他/她不會知道年老父母的“用處”,或知道了一點也影響不了日常的行為模式。因為在有孝之前,人活不過多老,也積累不了多少能超出中年人的智慧。但憑著內時間意識中過去與當下的交織,越來越多的“過去”被保持在潛時間域中,只要有恰巧應時的激發,那跨代際的記憶反轉就可能涌現。此為人的意識本能的時間實現,與功利后果的考慮無關。“養兒[時]方知父母恩”,說的就是構成孝意識的時間觸機。
孝心的出現,表明人的時間意識已經達到相當的深度與長度,能夠做宏大尺度的內翻轉。而且,由于孝迫使當前子女身荷未來(自己子女)和過去(自己父母)的雙養重負,導致更大的生存壓力,人類變得更柔弱、更不易成熟和死亡,于是其內時間意識就被逼得還要更加延長和深化,新的工具和生態位就更是生存的渴望和創造了。基于這種推想,四萬年前在現代智人身上發生的進化“大躍進”,或許是人類實現孝的最晚時刻。從此以后,許許多多新的發明創造——精巧的新工具如骨器、復合工具、魚鉤、網、弓箭,及高明的藝術如洞穴壁畫、雕塑、儀式,乃至我們所說的這種語言,等等——以及它們體現的身心特征就奠定了現代人類的生存基底。
六、總結:仁者人也
以上哲學人類學的研究,所運用的是“朝向事情——即現有人類本性的形成——本身”的方法,也就是“道不遠人”“仁者人也”的方法。社會生物學化的人類學研究過于強調基因的普遍決定,而自由主義、極端女性主義等則過于強調人的文化性,似乎人性只是一張白紙,任由特殊的文化來打扮。人有自己的身體,一個并非個體化和完全肉體化的時間生存的身體,在物質與精神、基因與文化的二元化之先,人身就已經在生存的長河中形成、演變、再形成,如此循環往復。
儒家講的“男女有別”,現在看來,確是一個極悠久的人類現象和原則,有豐富的多重含義,比如生理的、勞動分工的、外婚制的。它不但沒有歧視某個性別之意,反倒隱含男女在差異之中的互補式平等之意,當然殊不同于西方意識形態傳來的外在形式上的“男女平等”。
但一切源于人——含人科動物、人族、人屬和智人——的生存之道,主要就是撫育嬰兒成熟,以致再去養育嬰兒之道。直立兩足的最重要后果就是人類嬰兒的極度不成熟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后果。由它或它們形成了人朝向自身形成的發動結構。由于這種極度不成熟和隨之而來的青少年成熟期拖后,養育人的后代必須有眾男性群體中的父親,而不能像其他靈長類那樣,或者是“單親[母親]撫養”,或者是一雄多雌,或者是孤立的一雄一雌。
亞里士多德說人是個“政治聯盟的存在者”,很有見地,但他斷定“人就其本性而言是一種要生活在城邦中的動物”,就有問題了,因為人就其本性而言,首先是一種要生活在夫婦家庭和血親/姻親家族中的動物,而不必然是城邦中的動物。《禮記·禮運》寫道:
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人之義。
這“人義”[即做人的含義]的順序,也可看作是人的政治發生順序,即親子[“父”是“父母”的縮寫]為源頭,導致夫婦、家族乃至國家。國乃家的延伸,故被現代人正式名曰“國家”。但《孟子·離婁上》已云:“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講“家之本在身”,表明家的最真實含義要通過學六藝之“修身”來獲得,但這“身”卻首先不是個體之身,而是親子一體、家庭聯體之身,所以《孝經·開宗明義》要講“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所有這些,會導致人的內時間意識的深長化,即所謂窮—變—通—久。“窮”指人類嬰兒之完全被動,養育之艱難困厄;必“變”而活之,母之父之,親之戚之,謀劃之、器具之,與時偕行之;此變創出新生態位,“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禮記·大學》引殷湯之《盤銘》);于是有“通”,總有新意涌出,達于未來之幾;如此則“久”,即內時間意識之深長化、回旋化,使人可歷經無數患難變遷,從數萬年、數十萬年、幾百萬年前一路行來,而曾與之同行的多少物種,乃至多少人科、人族的兄弟種,都滅絕了。中華民族及文化,因得此人道正脈而在世界諸古民族古文化中最能持久。
當人的內時間意識達到能夠在代際間切身反轉時,即能夠在養育自己子女時意識到過去自己父母的同樣養育之恩情時,孝意識就開始出現了。這可能是人之為現代人的標志。從此以后,人成為完整意義上的、為我們熟悉的人,不管它是在打獵—采集、茹毛飲血、制網作弓、洞穴作畫,還是在播種耕田、范陶冶銅、筑城造字,或制禮作樂、立法建國,乃至科技至上、大戰世界。
孝即孟子所講的“不忍人之心”的發端,不忍見年老之父母有凄涼晚景,如老年黑猩猩之遭遇。《孟子·公孫丑上》將“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作為人的標志,這惻隱或不忍人之心以孝為源頭。動物特別是鳥類和哺乳類,也有親代對子代的不忍之心,但缺少子代對于親代的不忍之心。人從能孝開始,才算是與其他動物有不同生活世界的人。《論語》里有“孝弟也者,其為仁[人根]之本與”,《孝經·開宗明義》里有“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人并非是因為會使用工具、會欺騙、會搞政治,或有自我意識和他者意識而成為人,而是因為能孝順父母長輩親人,因而特別能受教而成人。
這一切,都指向一個關鍵維度,即人的內時間意識的深長化。所以孟子講孔子為“圣之時者也”,我們認儒家為“時中”之學,絕非虛言。
注釋
①[美]愛德華·威爾遜的自傳《大自然的獵人——生物學家威爾遜自傳》,楊玉齡譯,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年,第17章:“社會生物學大論戰”。②[美]愛德華·O·威爾遜:《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7章(人類:從社會生物學到社會學),第519頁。③Edward O. Wilson. On Human Nature. Cambridge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208.④何傳啟:《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機遇與對策》,《科學與現代化》2011年第2期。⑤Robert Blyd & Joan B. Silk. How Humans Evolved (fifth edition). Los Angeles: W. W. Norton, 2009, p.253. 此書主張,在400萬至200萬年前的非洲,起碼有四大類人族物種生活,它們是:Australopithecus, Paranthropus, Kenyanthropus和Homo.⑥“使用工具”可以被簡單地理解為:運用外物甲去改變外物乙的形狀、位置和狀態。外物甲就被看作是工具,而“運用”可理解為使用者在使用工具之際或之前,抓住、攜帶這工具,因而對工具的有效移動方向負責。這基本上就是B. Beck于1980年提出的工具定義。見Primates in Perspective, ed. C. J. Campbell, A. Fuentes, etc.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 Press, 2007, chapter 41, “Tool Use and Cognition in Primates”, by Melissa Panger, p.665.有關哪些靈長類會使用工具的信息,參見此書第671頁,表41.1。黑猩猩也有制造工具的簡單行為,比如修理草棍,使之適合于釣白蟻之用。⑦⑧⑨⑩Anthropology. The Exploration of Human Diversity (twelfth edition). by Conrad P. Kottak, McGraw-Hill Companies ,人民大學出版社與McGraw-Hill出版(亞洲)公司合作出版, 2008, p.81, p.81,p.222,pp.222—223,p.83,p.83,p.84,p.105,pp.104—105,p.83,p.110,p.108, pp.109—111.有的學者舉出早期博物學家的傳聞乃至日本古代小說所言的一些原始民族不養老、遺棄老人的例子,以否認養老的人類屬性。這種論斷有方法上的弊端,因為人類在局部或短期內不養老,并不說明他們在主流生存形態和長期生活中不養老。還有就是解釋角度的問題,不同文化對某個現象可以有非常不同的理解。比如西藏的天葬習俗,在漢人看來就是對親人遺體的大不敬,但在藏文化中可以有很不同的解釋。20世紀人類學基于廣泛的田野調查和考古發掘而得出的古人類“供養和保護老人”的結論,應該是更可靠得多和有全局意義的。參見[美]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古代社會》上冊,楊東莼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47頁及以下。如[法]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在為《家庭史》的序中寫道:“他們[觀察家和理論家]一律摒棄那種陳舊的理論:認為在人類歷史上家庭出現以前,有一個所謂‘原始雜處的階段”,“如今,總的傾向是承認‘家庭生活(在我們賦予這個詞組的意義上)在人類社會的長河中都是存在的”。引自《家庭史》,安德烈·比爾基埃等主編,袁樹仁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8頁。《家庭史》的作者們也認為:“家庭也像語言一樣,是人類存在的一個標志”(《家庭史》,第15頁)。又見威爾遜:《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幾乎所有的人類社會的建筑單元都是核心家庭”,第519頁。[美]杰拉德·戴蒙德:《第三種猩猩》,王道還譯,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52、73、197、39頁。關于人類直立行走的原因,流行的有“適應開闊草原生態說”。由于數百萬年前的氣候變化,非洲東部有些熱帶雨林變為熱帶稀樹草原,原始人族動物為適應這個“從樹林下到草地”的新環境,發展出了直立姿態的兩足行走,因為這種行走有幾個好處:便于高草中的遠視,便于長距離地攜負獵物,便于兩前肢的手化,還有利于減少太陽的輻射,以維持體溫(參見The Exploration of Human Diversity, p.104)。當然還有別的解釋的可能。這幾十年的發現表明,在直立兩足行走、腦擴大和獵取大型獸類這三種人類現象之間,有上百萬年的間距。但以下介紹的“獵人說”,還是很有些影響。參見Kristen Hawkes. “Mating, Parent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Pair Bonds”.Kinship and Behavior in Primates, ed. B. Chapais & C. M. Berman,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444.參見Kristen Hawkes.“Mating, Parent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Pair Bonds”. Kinship and Behavior in Primates,p.443, p.445, pp.460—461,p.444, p.452,p.464.愛德華·O·威爾遜寫道:“由于男性生育間隔時間比女性短,因此,一對一的性紐帶關系因某種程度上的一夫多妻現象而有所削弱。”參見愛德華·O·威爾遜:《論人性》,方展畫、周丹譯,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6頁。“我們有節制地實行一夫多妻制,兩性關系中的變化大多數由男性引起。占全部人類社會四分之三的社會允許男性擁有數名妻子,其中多數還得到法律和風俗的認可。反之,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社會贊成一妻多夫。其他實行一夫一妻制的社會也只是在法律意義上如此,姘居和其他婚外關系的存在,造成了事實上的一夫多妻現象。”(《論人性》,第113頁)情況是不是就像威爾遜敘述的那樣,還有待更多角度的人類學文獻,特別是從女性主義角度的所做的認真研究的結果。威爾遜對于我們這種人的特性或本性抱有某種藐視,他寫道:“人類物種[因為科技的不斷發達]能改變自己的自然屬性。它會選擇什么?是依舊在部分地為適應早已不復存在的冰河期而倉促形成的基礎上踉蹌行進?還是強迫自己形成因某種較高級的——或較低級的——情感反應能力而出現的更高級的智力與創造性?社會性的一些新模式能逐步地建立起來。在遺傳學意義上模仿白臂猿近乎完美的核心家庭生活或者蜜蜂和諧友愛的手足情意,是完全可能的。”(《論人性》,第190頁)他在這里好像表面上只是提出問題,但從他書中間或透露的看法,可知他傾向于贊成利用人工手段干預人類進化。這么“天真”(讀了他的自傳,我不認為他像他的對手們攻擊的那樣是種族主義者)的學者,盡管學識淵博,富于探討精神,但在關鍵處,還是不敢當下就信其論斷。Primates in Perspective, ed. C. J. Campbell, A. Fuentes, etc.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 Press, 2007,p.671.Handbook of Paleoanthropology, Vol.II, Primate Evolution and Human Origins, ed. Winfried Henke & Ian Tattersall, Berlin, Heidelberg,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2007,p.1729, p.1728.[英]珍尼·古道爾(即珍尼·古多爾):《和黑猩猩在一起》,秦薇、盧偉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9—130頁。[英]珍尼·古多爾:《黑猩猩在召喚》,劉后一等譯,科學出版社,1980年,第144、137頁。Meredith F. Small. “Our Babies, Ourselves”. Annual Edition. Anthropology 2002/2003 (Twenty-fifth edition), ed. Elvio Angelon, Guilford, Connecticut: McGraw-Hill Dushkin, 2002, p.108,p.107.Charles J. Lumsden & Edward O. Wilson. Promethean Fire: Reflection on the Origin of Mind, Cambridge, et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79.Eldon D. Enger & Frederick C. Ross: 《生物學原理》影印版,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387—389頁。杰拉德·戴蒙德:“人類發育、成長,很不容易,得花上20年,在動物界絕無僅有”(《第三種猩猩》,第135頁)。按照比較新的人類學研究,現代遺留的狩獵—采集社會中,男子要17歲、女子則要40歲靠后才能完全養活自己[Robert Blyd & Joan B. Silk. How Humans Evolved (fifth edition), p.289, Figure 11.7]。可以大致想見,在現代人類的形成期中,后期情況(那時已經發明較高明的打獵和采集工具)可能與這差不多,但更漫長得多的前期和中期里,情況多半不同。當然,這也依生態環境和人類吃的食物品種而變,生態好時這種年齡會提前,不好時會錯后;打獵已經很重要的時期年齡會后移(因為要學會獵捕大野獸的技術和體力要求高),而很早期的人族,起碼有的種類以吃植物為主,這年齡會提前。Caroline E. G. Tutin.“Reproductive Success Story——Variability Among Chimpanzees and Comparisons with Gorillas”, Chimpanzee Culture, p.184, Table1.參見[美]愛德華·O·威爾遜:《論人性》,方展畫、周丹譯,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5—125頁。Robert Blyd & Joan B. Silk: How Humans Evolved (fifth edition), Los Angeles: W. W. Norton, 2009, p.263,p.312.Anthropology. The Exploration of Human Diversity, p.114. How Humans Evolved (fifth edition), p.284. 西班牙《國家報》還有報道:“古猿340萬年前開始使用石器——人類進化史向前推90萬年”,《參考消息》2010年8月13日。以上談到過另一個因素,即人可能會像黑猩猩那樣,在“圈養”或“文明狀態”中,其性成熟期及生育時間提前;它有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由人類嬰兒不成熟出生造成的成熟期推遲[這種推遲按人類學的現有資料,會隨著人族的進化而加劇。參見How Humans Evolved (fifth edition), p.264, pp.291—292],形成某種平衡,于是導致長久的進化停滯,除非有重大的環境改變打破它。《禮記·郊特牲》:“夫昏[婚]禮,萬世之始也。取于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男女有別,然后父子親;父子親,然后義生。義生然后禮作。禮作然后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禮記集解》卷26,[清]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中華書局,1989年,第707—708頁。Aristotle. 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 ed. and trans. Ernest Barke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1979, p.5. 亞氏在那里講道:“從這些考慮可以明白地看出,城邦(polis)屬于那種憑借自身本性而存在的東西之列,而人就其本性而言是一種要生活在城邦中的動物”,“相比于蜜蜂或其他群居動物所能達到的聯盟狀態而言,人注定是一種政治聯盟的存在者。”苗力田主編的《古希臘哲學》將這些話譯為:“由此顯然可見,城邦是自然的產物,人天生是一種政治動物”,“人比蜜蜂以及其他群居動物更是政治的動物”(第577頁)。苗譯似有過簡之嫌,比如將“人就其本性而言是一種要生活在城邦中的動物”表達為“人天生是一種政治動物”,有含糊掉“城邦”與“政治”的差異的危險。
責任編輯:思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