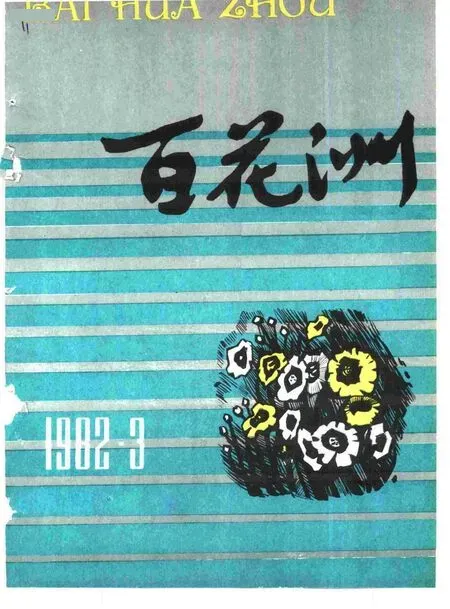元月所讀
丁伯剛
元月所讀
丁伯剛
頭一次接觸到“新儒家”這個詞,大約是九十年代初期了,后來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了一套“現代新儒學輯要叢書”,其中就包括牟宗三的《道德理想主義的重建》。我立即把那幾本都買了下來,有的一直保存到現在。但對現代那些儒學大家的喜愛,應該是在此前很久就開始了。記得同樣是一九七八年夏在修水縣城參加高考時,我購到上下兩冊的《章太炎政論選集》,這種書即便放到現在也未必能很好地讀懂,但當時我偏偏以一種難以思議的入迷勁沉入其中。這兩大本佶屈聱牙的文字,伴我度過了高考結束后等入學通知的三個月苦悶時間,其中不少篇目的標題如“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與汪康年書”、“孔子偽經考”之類,三四十年后的今天仍然隨口就能背出,就同念什么咒語一樣,真是怪事。以后讀書及畢業后教書,又相繼讀到王國維、梁漱溟等人的一些作品。有一本書叫《王國維美學論文選》,是從師專圖書館借的,作者在這里所談的絕不只是什么美學問題,不只談《紅樓夢》,談藝術,更談叔本華,談對宗教的諸多感受。因過于喜歡,我又用上那個老辦法,就是買了個專門的本子做摘要抄錄,不算薄的一本書基本給抄得差不多了。也是從這時起,還養成讀傳記、讀年譜的習慣。特別是年譜,不只反映出譜主的種種思想,而且更能展現出這種思想的具體來源與發展、演變的軌跡,演示他一生中的種種曲折與求索經過,給人的啟示最大,也最直接。許多年譜給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就在今天做這篇讀書筆記的時候,我到書堆中隨意亂翻,恰巧找到李淵庭、閻秉華的《梁漱溟先生年譜》,廣西師大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正是當年我讀過的一種,里面布滿密密的畫痕和簡要批語。在梁先生三十八歲于河南搞村治運動的一處,我用圓珠筆批了一行很大的字:“由佛入儒,中國的現實問題粉碎了所有的形而上要求。”這里表達的可能是我閱讀時的一個非常強烈的感受,就是對梁漱溟放棄精神探索走向具體現實問題的遺憾和失望。梁是個早慧的人,十七歲時開始對人生問題感到煩悶,從利害之分析追問,而轉入所謂苦樂之求索,歸結到人生唯是苦之認識,于是遽變傾向印度出世思想。梁漱溟讀佛家的書大致有兩個時期:一是十四五歲,辛亥革命之前;一是民國以后辭去記者職業,進北京大學之前在家閑居時。他說他開始并不懂得什么大乘小乘,什么密宗禪宗等,但由于自己對人生苦樂的探求與佛學合拍,便從較通俗的《佛學叢報》著手,邊學邊鉆,久而久之,漸漸入門。研讀佛學的結果,一是拒絕母親議婚,一是從十九歲開始吃素,一度還想出家為僧。由佛入儒,進而到達具體的社會操作層面,其變化是迅速的,軌跡也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現實問題、民族問題的強力裹挾。梁漱溟說:“感受中國問題的刺激和我對中國問題的熱心,又遠過于人生問題。同時在人生上,既以事功為尚,變加重這傾向。”事功的追求,不只來自社會,同時也來自家庭的影響,梁漱溟說到,他的思想無疑受到父輩的影響。“先父雖讀儒書,服膺孔孟,實際上其思想和為人乃有極像墨家之處。他相信中國積弱全為念書人專務虛文,與事實隔得太遠之所誤,而標出務實二字,為討論任何問題之一貫主張……其大大影響到我,是不待言的。”梁漱溟說,人類日趨下流與衰敗,是何等可驚可懼的事。拔本塞源,只有廢除財產私有制度,以生產手段歸公,生活問題由社會共同解決,而免去人與人之間之生存競爭,這就是社會主義。面對人類所遭遇的共同問題,那個時候的人,包括梁漱溟他們只以為在社會層面上就能徹底解決。世間的不平、人世的混亂不都是來自人的私利嗎?那么好吧,把所有屬于私人的東西全部沒收,把一切罪惡與痛苦之源都切斷,這想法有多么單純。相對來說,我對梁漱溟的興趣好像都集中在他在河南、山東等地搞鄉治運動之前的那段探索,此后覺得他基本上成了一個社會人,他的所思所想與我關系不大了。
牟宗三在文章中多次談到所謂道統、學統、政統問題,中國的道統就是他所說的以儒家為代表、接續民族文化生命之本源大流的德性之學、心性之學;學統就是知識之學,包括科學與民主之類;政統則是指政治制度方面的東西。道統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價值,護住孔孟所開辟的人生宇宙之本源;學統之開出,此即轉出“知性主體”以融納希臘傳統,開出學術之獨立性。牟宗三首先承認科學與民主是中國歷史文化中所缺少的,而又為我們民族走向近代化和現代化之所必需。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是否需要吸收西方的科學與民主,而在于如何吸收西方的科學與民主。科學與民主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這點為新儒家所共識,問題是如何讓它在這里生根成長。使科學與民主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成長,是新一代儒家學者謀求解決的中心課題。牟宗三認為,學統,也即他所說的科學與民主,在西方雖說是古希臘精神的傳統,雖說是源遠流長,然從文化生命之發展說,究非西方所可獨占。一切學術文化包括科學與民主,從文化生命發展方面說,都是心靈之表現、心靈之創造,它是無國界、無顏色的,這是每一民族文化生命在發展中所應視為固有的本分事。如是,科學雖先出現在西方,其心靈之智用雖先表現為知性形態,然吾人居今日,將不再說科學是西方文化,或西方文化所特有,而當說這是每一民族文化生命在發展中所共有,這亦如佛教所謂“共法”。不錯,我們的文化中并沒有自動孵生出知識之學、沒有孵生出科學與民主來,但在經過曲折醞釀、步步緊逼之后,時至今日,不得不被迫著要孵生出來。此被迫,表面觀之好像是外在的,但如果從深一層看,從內在于自己文化生命而觀之,則是內在的。這是文化生命開展之必然要求,是心靈開展之必然要求,是自己文化生命發展中固有之本分事。就并非是西化,而是自己文化生命之發展與充實,是我們生命內在的一種自我實現。如此一來,那為什么一說科學與民主,就以為是西方文化或者西化呢?了解一民族的文化,不能從其過去沒有后來所需要的,便作全盤否定。后來之需要無窮,沒有一個民族的文化能在一時全具備了,所以了解一民族的文化,只應從其文化生命發展之方向與形態上來了解,來疏導,以引出未來繼續的發展或更豐富多樣的發展。本此認識,以逼出民主政體建國之大業,乃是華族自盡其性的本分,根本不是什么西化。看到這里,我不由又一次失聲笑起來,覺得牟宗三的這些觀點既顯示出不一般的豁達與洞見,而從另一方面看,又表現一副孩子式或老頑童式的自尊自愛,同時還有幾分說不出的無賴氣。你口袋里裝的那東西確是個好東西,那也是我應該有的。我應該有,那就表明這是一種我們共有的東西,不僅為你一人所獨有,只是你暫時先有而已。即便不向你要,我們自己遲早也會有。這樣一來,我既向你要了那東西,自己的面子又很好地保住了。
如果說在對待民主與科學的看法上,牟宗三表現得可敬、可愛而又可笑,那么當他談到有關宗教,特別是儒教的一些問題時,作為一代大儒其所表現出的幼稚與不通,令我真有些驚訝乃至難以置信了。在中國雖有儒釋道三教并稱,但唯獨儒教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宗教,應該是個不言自明的共識。一九二四年泰戈爾訪華時,就此問題與梁漱溟曾有過一次專門的討論。那天徐志摩約梁漱溟去拜訪泰戈爾,兩人到時,正值泰戈爾與楊丙辰在談宗教問題。楊以儒家為宗教,而泰戈爾則說不是,梁漱溟不由加入了談話。泰戈爾認為宗教是在人類生命的深處有其根據的,所以能夠影響人。尤其是偉大的宗教,其植根于人類生命者愈深不可拔,其影響愈大,空間上傳播得愈廣,時間上也傳播得愈久遠,不會被推倒。然而儒家似乎不是這樣。孔子在人倫方面和人生各項事情上,講究得很妥當周到,如父應慈、子應孝、朋友應有信義,以及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好像一個法典,規定得很周全。這些規定自然都很妥當,都四平八穩,可離生命不免就遠了。由此泰戈爾判定儒家不算宗教,但又很奇怪儒家為什么能在人類社會與其他各大宗教都有同樣長久偉大的勢力。梁漱溟說,孔子不是宗教是對的,但孔子的道理卻不盡在人倫綱常中。梁漱溟就此說了好久,泰戈爾連連點頭,說梁先生讓他懂得了許多儒家的道理。但梁漱溟說來說去,有一個前提是不變的,那就是承認儒教并非真正的宗教。牟宗三其實也承認此點,但他以為在中國的文化生活中,假如有人說儒家所承繼所發展的只是俗世的倫常道德,而無其超越的一面,無一超越的道德精神實體之肯定,神性之實、價值之源之肯定,如此一來所謂文化生命就不成其為文化生命,中華民族也就不成其為一有文化生命的民族了。若平心睜眼觀之,有誰敢如此說,并且忍心如此說?這里涉及到牟宗三的一個基本觀點,他認為宗教,也只有宗教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立國之本,而中華民族的立國根本自古以來就是儒家和儒教,那么儒教便一定是宗教。我們一個堂堂大族,如果說沒有宗教,沒有立國之本,能講得過去嗎?即便講得過去,誰又忍心這么說?基于這樣一種心理,牟宗三認為儒家不只是宗教,而且應該比其他的宗教都要高級才對。他是如此推導的:“儒家所透徹而肯定這超越而普遍之道德精神實體,決不能轉成基督教所祈禱崇拜之人格之神,因此儒教之為教變決不能成為基督教之方式。此基本密義若能透徹,立見佛教之有不能令人滿足處,基督教之有不能令人滿足處。”儒教不能轉成基督教,據此怎么馬上就能看到佛教、基督教的不滿足之處來?
《現代漢語詞典》對“宗教”一詞釋義時帶有一種莫名其妙、完全不知從哪里來的道德優越感,采用嘲諷、批判口吻。相比倒是百度的解釋更客觀:“宗教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出現的一種文化現象,屬于社會意識形態。主要特點為,相信現實世界之外存在著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實體,該神秘統攝萬物而擁有絕對權威、主宰自然進化、決定人世命運,從而使人對該一神秘產生敬畏及崇拜,并從而引申出信仰認知及儀式活動。”其他的解釋還有各種各樣,其實都有不夠清楚處。我個人理解,宗教應該包括兩個層面的意思:第一,苦難、罪惡、罪孽以及人的生老病死、人的有限與無救等等意識;第二便是基于苦難意識之上的拯救或說超越問題。面對人世的苦難、人生的殘酷,如何拯救、如何超越呢?靠我們人自身當然是不行的,于是便有了對一種外在于人又高于人的絕對者、永恒者、至高無上者,一種無限存在者、超越時空者的向往與吁求。這種東西是萬物的起源和歸宿,是一切存在的根基及依據。這種向往與吁求便是一種信仰,是一種信仰要求、宗教要求。苦難意識是所有宗教產生的共同前提與基礎,所以我一直以為,所有的宗教在最內在、最實質意義上都是相通的,至于它們之間的不同處,便是具體的拯救方法問題了。拯救方法不同,便決定了宗教與宗教之間的相互區別,決定了同一種宗教之間派與派的區別、宗與宗的區別。從這方面來看,儒教是缺乏宗教的基本前提的,儒家學說中看不出任何苦難意識及對人本身局限性的認識。儒家學說的出發點與實質內容只是基于一種社會的治亂意識,說穿了這只是一種治國、治世的方略,一種社會經營術與維穩術。在孔子及其學說面前,所有的人世苦難與在此苦難中輾轉掙扎的每一弱小個體都一齊給拋棄了,他的心目中只有一個大而無當的所謂家國天下。一種治國術不只在當時風行一時,而且竟被當作立國根本千古流傳,孔子本人也給當作萬世師表的教主,這其實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俄羅斯在他的幼年時期遇到了東正教,其民族性中那屬于神性、超越性的一面得到更大的發揮,而我們民族在自己的幼年時期遇到的則是儒學。其實夏商周三代,是中國傳統宗教發展的鼎盛時期,和世界上許多古老的民族一樣,當時的中國也是全民族信教的。自孔子及其弟子出,刪“三禮”,儒學大盛,自此以后我們便踏上了一條沒有任何超越情懷,而只有權術橫行的赤裸裸的世俗社會之路。而牟宗三不知是出于認識的原因還是其他原因,對“宗教”一詞所給出的定義是與所有的人都不同的:“凡道德宗教足以為一民族立國之本,必有其兩面:一足以為日常生活軌道(所謂道揆法守),二足以提撕精神,啟發靈感,此即足以為創造文化之文化生命。”能給日常生活提供一種行為規范、道德規范,另外能振奮人的精神,激勵人的生命力,這是許許多多的世俗學說所共有的特點,莫非這些學說都是宗教了?正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牟宗三認定儒家之倫常固然有其日常生活之軌道一面,而其所透徹而肯定之超越而普遍之道德精神實體,則正代表提撕精神,啟發靈感之文化生命一面。中國文化所凝聚成之倫常禮文與其超越而普遍之道德精神實體尤具圓滿之諧和性與親和性,不似西方之隔離,儒家教義即依據此兩面之圓滿諧和形態而得成為人文教。牟宗三進而認為,儒教,也即所謂的人文教中的三祭:祭天、祭祖、祭圣賢,皆因超越而普遍之道德精神實體而得實,而得其客觀存在性,在圓滿諧和形態下祭祀崇敬,主客、內外、本末混融而為一,形成一超對立之客觀與絕對。“基督教中之上帝,因耶穌一項而成為一崇拜對象,故與人文世界為隔;而人文教中之實體,則因天、祖、圣賢三項所成之整個系統而成為一有宗教意義之崇敬對象,故與人文世界不隔:此其所以為人文教也,如何不可成一高級圓滿之宗教?唯此所謂宗教不是西方傳統中所意謂之宗教而已,豈必一言宗教即為西方傳統中之形態耶?”
牟宗三在文章中曾就蔡元培以美術代宗教的看法提出批評,認為這是反宗教,“彼固不明‘宗、教’或‘宗教’的意義與職責”。實際上牟宗三自己更是如此。取消宗教的基本內涵,然后依自己所好隨意設定一個東西,說這就是宗教,然后再依此設定,推導出自己的宗教有多么圓滿多么高級,比世上所有的宗教都要好得多,只是我們的宗教與你們的不一樣罷了。這些話固然說得好聽,聽的人與說的人都感到很舒服,但畢竟離真正的宗教遠了。如果說我們這里所有的祭天祭祖祭圣賢也算一種宗教的話,那只是宗教的最低級而原始形式,是一種宗教化石,與原始人類的祭祀是一個層次。在讀《生命的學問》等書時,我一直理解不了,作為一代大儒,牟宗三是真的弄不清這一點,還是有意不愿弄清?據牟宗三所說,他的老師熊十力先生所持看法同樣如此,熊十力手造《新唯識論》,其理論規模大半有所資于佛家,而宗旨則為儒家。儒家義理規模與境界俱見于《易經》與《孟子》,而熊先生即融攝《孟子》、陸、王,與《易經》而為一,直探造化之本,露無我無人之法體。法體即本心,本心亦寂靜亦剛健,故為造化之源,引發生生不息,此即其宗旨為儒家而非佛家處。以此為本,《新唯識論》并評判整個佛教之空有兩宗,就根本言之,謂其“真如”只寂靜而無生生;自文化言之,不能開出人文,不能肯定人性、人道、人倫,是即無異直握佛教之宗趣而謂其為出世之偏曲之教也。此種真如,自然不能生生,不能繁興大用,開出人文。我沒有讀過熊十力《新唯識論》,不知牟宗三這里的轉述是否確實。如果熊先生原意真如此,那么他對宗教,特別是這里對佛教宗旨的理解同樣是狹隘的、錯誤的,同時也是可笑的。他完全是以一種實用的、功用性的儒家立場,一種非宗教非超越性的立場來對宗教進行評判。新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唐君毅更進一步,對宗教的理解整個就是一通胡扯。唐君毅說在一般的宗教意識中只信一個唯一的神,如耶穌、釋迦牟尼、穆罕默德等。這種宗教意識以為我們中國人不應該把圣賢、豪杰、祖先當作神來崇拜,但我們自己則認為,真正最高無上的宗教意識,就應當把圣賢、豪杰、祖先當作神來崇拜。因為我們既說最高的宗教意識中所信仰的神如基督、如菩薩,一定是以擔負人類的苦罪為己任的,那么世間那些能為民眾去除苦罪的圣賢豪杰,極可能就是由神化身為人的。我們如果真信神的偉大,那么我們就應該相信圣賢豪杰祖先等道德人格就是神的化身,我們就應該以崇拜神、皈依神的態度來崇拜他,皈依他。所以我們說宗教意識發展到極致,一定會包含一種把圣賢豪杰等道德人格當作神的宗教意識,同時也會把祖先當作神的宗教意識。因為祖先在其本性上沒有不愛他的子孫,愿意分擔子孫苦罪的,那么在子孫心目中,他們的父母祖先便同耶穌、菩薩無異了。所以唐君毅以為,最高無上的宗教意識,一方面應該有對超越之神的崇拜皈依,另一方面也應該有對圣賢豪杰祖先的崇拜皈依。而中國先秦儒者一方面崇拜圣賢豪杰祖先為神,另一方面同時也信仰天神,至少沒有自覺地反對天神,由此可看出,這才是真正最高的宗教意識。反正吧,無論你們外面的人如何牛逼,到最后,最好的東西一定在我們這里。
在做這篇讀書筆記的時候,昨天夜里十二點多,我坐在衛生間邊洗腳,邊翻讀辜鴻銘的一本書,恰好讀到有關宗教的一段文字:“佛教和基督教的宗旨之一,是教導人們怎樣成為一個好人,而孔子的學說則進一步,教導人們怎樣成為一個好的社會公民。佛教和基督教告訴人們,如果人們想成為一名好人,一名上帝之子,人們只需思索靈魂的狀態及對上帝的義務,而不必思考現實世界。……換言之,本來意義上的宗教如佛教和基督教是一種為人們謀劃怎樣隱跡于山林荒野,以及為那些在北戴河避暑的小屋里,不干別事,只對其靈魂之狀態和對上帝之義務進行思索的人設立的宗教。”真正的宗教原本就是植根于人
世的深重苦難,怎會不思考現實世界只謀劃怎樣隱跡于山林荒野與北戴河的避暑小屋呢?新儒家懷著強烈的民族危機意識和使命感,致力于傳統文化之精神價值的弘揚、發掘,和民族自我的重建,企圖尋索到一條民族振興之路,這中間的所有努力與偏執我們都是能理解的。牟宗三一再強調:“我的目的不在成一家之言,而在貫通吾人的民族生命及文化生命,惟在這種貫通中,始能見出人類的積極精神來……人類內心深處的那種超越的親和力,亦就是正面的積極精神,最易于從歷史貫通的發展之體貼中蕩漾出來。民族生命,文化生命,統在這種貫通發展之體貼中復活。”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多年來我一直對他們抱著極好奇的心理,總想做一些認真的閱讀與清理。但讀得越多,不滿之處也就越多,出口閉口大而無當的家國天下、內圣外王,沒有最基本的屬于人的自我意識,與普通人生一點關系也沒有。尤其是有關宗教問題上的信口胡謅,更時時讓人啞然失笑。宗教根本不是這些儒家人士所以為的是什么立國之根本,而是立人之根本、立魂之根本、立魄之根本。宗教只應進入每個弱小個體的內心最深處。在疾病、在死亡、在世情冷漠之下,無數弱小個體孤苦無告、輾轉反側我們真的只是一些可憐的生物、可憐的個體,我們很卑弱。我們不需要內圣。我們只想在手心里抓撈到一點點什么,哪怕是一根稻草那樣的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