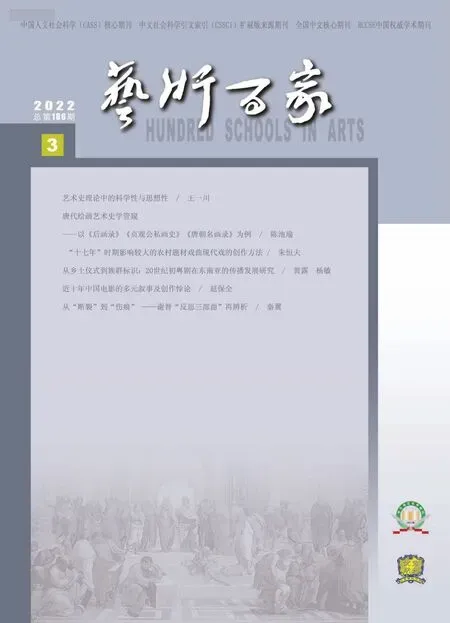論宋代裝飾紋樣的范式*
谷莉,周武忠
(1.東南大學 藝術學院,江蘇南京210018;2.江蘇師范大學 傳媒與影視學院,江蘇徐州221009;3.上海交通大學 媒體與設計學院,上海200240)
范式即模式,有時也叫程式,是藝術設計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現象,是工匠們在實踐經驗基礎上總結出的,以“約定俗成”或法規的形式被同行業廣為模仿的造型、裝飾、工藝、生產組織等方面的規范,或在一定時間和地域內有較大影響力的自成體系的藝術設計面貌。宋代是我國裝飾紋樣發展的集大成時期,裝飾紋樣繁榮發展。在宋代裝飾紋樣中出現了很多范式,如紋樣結構形式的定型,宋代瓷器、織物裝飾中有許多紋樣結構形式模式化,在前人的基礎上開始定型,對后世裝飾藝術有著積極的影響。
一、喜相逢結構形式的定型
在宋代很多瓷器、銅鏡裝飾上,無論是畫花還是刻花,出現了很多成對成雙的紋樣格式。常見的有兩條魚、兩個嬰孩、兩枝牡丹,最巧妙的是兩束荷花,有花和葉、蓮篷,用一根帶子結成一束,也互相對置在一個回形中,還有兩只鳳凰、兩只鸚鵡、兩只蝴蝶、兩只白鶴等,通常是一左一右,一上一下在一個圓形中,左右顧盼、上下相連,回旋往返、生生不息,似乎互相照顧又你追我趕,產生一種極其協調優美又互相對立的運動感。魚兒在水中追逐游動,鳥兒在空中嬉戲飛翔,花兒在風中搖曳飄舞,各種載歌載舞的歡樂形象使人看了之后會產生許多美好的聯想,從美學的角度來講,正符合“變化與統一”的美學法則,這種構成形式的美,剛好符合人們追求歡歡喜喜、熱熱鬧鬧、圓圓滿滿的心靈要求,這就是被稱為“喜相逢”的紋樣結構。
“喜相逢”的紋樣結構源于我國古老的太極形,最早出現在屈家嶺文化的紡輪上。它一黑一白,大小扣合,對立而和諧。是用一根相反相成的S形線,把整個畫面分成兩個陰陽交互的兩極,這兩極圍繞一個中心回旋不息,形成一虛一實,有無相生,左右相傾,前后上下相隨的一種核心運動①。這些太極形紋,以湖北天門石家河出土的新石器時代彩陶紡輪為最多,也最具代表性。這種圖形雖然是平面的,卻能體現出空間美感,不僅反映出事物的本質美,也充分顯示出完整的形式美,充滿生生不息、轉動不已的活力。原始社會樸素的陰陽相合的宇宙觀,體現在審美上即是彩陶紋樣的平衡、動感與生命力,反映了四五千年以前的原始人類對生命的把握及對生活真諦的領悟和追求。
唐末至五代時期,類似于太極圖的織錦紋樣程式已經出現在裝飾紋樣中,紋樣從團花邊緣相對發出,中心有“S”走勢的主線將團花分成兩部分。宋代,道教被定為國教,太極圖流行。太極圖據說是由五代至宋初的道士陳摶傳出,原來叫《無極圖》。陳摶是一位道士,相傳對內丹術和易學都有很深造詣。據史書記載,陳摶曾將《先天圖》、《太極圖》以及《河圖》、《洛書》傳給其學生種放,種放又分別傳給穆修、李溉等人,后來穆修將《太極圖》傳給了周敦頤,周敦頤寫了《太極圖說》來加以解釋。現在我們看到的太極圖,就是周敦頤所傳的。道教剛產生時并沒有以陰陽太極圖作為標識,而太極、陰陽、八卦等思想也原是屬于儒家思想。正緣于對陰陽太極圖思想上和心理上的認同感,道教接受了它并將其作為本教的重要標志②。受宋代太極圖式的流行,裝飾紋樣中所謂“喜相逢”的構成形式開始定型,其特點是以S形線,把圓形劃分為陰陽交互的兩極,形成一正一反、有無相生的變化統一的形象,極類似于太極圖式的結構,取其吉祥寓意名曰“喜相逢”。這種紋樣構成外形顯示為圓形,體現了完整的觀念,但是因取對立來實現完整,一整二分,十分生動有力。正如北宋王安石在其《洪范傳》中用以表述對立的概念,提出了“耦”即“對”,他認為,宇宙萬物是由水、火、木、金、土五種物質元素構成的。不同元素的同一屬性是兩兩相對的。由于這種對立處于各元素的對立之中,故王安石說五行中“皆各有耦”,“耦之中又有耦”,“萬物之變遂至于無窮”,這種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也是對“喜相逢”結構的最好詮釋。
“喜相逢”結構廣泛應用于宋代瓷器、銅鏡、絲綢、金銀器等裝飾之中,并盛行于中國封建社會后期,成為象征喜慶團圓的紋樣程式。典型的如“重蓮紋”是青海阿拉爾出土的重蓮團花錦,單位團花紋是由一反一正的兩個寫實蓮花構成。還有福建福州出土宋代織物上的重蓮紋也較為典型。
二、特定構圖形式的應用:開光
開光的方法,是瓷器裝飾的一種構圖方式,又稱“開窗”、“開堂子”,也俗稱“斗方”。為了使器物上的裝飾變化多樣,或突出某一形象,在器物的顯著部位以線條勾勒出圓形、方形、菱形、扇面形、云頭形等各式幾何或花瓣型的欄框作為分割部分,框內繪各種圖案,構成獨立的裝飾面,具有對比強烈、以靜襯動的特點,起到突出主題紋飾的作用,也能適應繪畫題材。其外用幾何紋填飾,得到豐富的藝術效果。此法借鑒古建筑上的開窗見光形式,故因此而得名。開光在宋代被大量應用,南宋吉州窯、金代耀州窯和磁州窯等瓷器上,普遍使用開光裝飾。到了元、明、清時期景德鎮瓷器上更是大量運用開光技法進行裝飾,并有所創新。開光紋作為構圖的一種重要手段主要應用于瓶、瓷枕、罐、盆、碗之上,在器物上開光的個數也有所不同,有一個的、兩個的,也有三個的,甚至在一件器物上達數十個之多的開光紋。在開光紋內往往繪制動物紋、人物故事紋、山水小景、詩詞歌賦或折枝花卉,而連續紋樣繪制較少。主紋一般繪于開光紋飾中部,周邊為邊飾紋樣或輔助紋樣。
三、程式化和寫實風格完美結合的纏枝紋
纏枝紋又稱“串枝紋”、“穿枝紋”、“卷草紋”、“蔓藤紋”,是一種典型的傳統花卉裝飾紋樣樣式。日本習慣上稱之為“唐草”。這類紋飾以各種花草的枝、葉、藤、蔓、花朵或果實等為表現題材,枝莖纏繞,呈連續的波狀形或渦旋形、S形等,由曲線或正或反地相切,使之反轉連綴,并在轉折的重點處配以花頭,在枝莖上填以花葉,組合成富麗纏綿的裝飾紋樣,即纏枝花。完整的纏枝紋由花草紋樣和幾何骨骼結合而成,二者缺一不可。喜相逢結構中就有許多纏枝格式。纏枝紋被廣泛用于石刻、彩繪、陶瓷、漆器、織繡等的裝飾中。纏枝紋的名稱可隨主題的變化而有所不同,以牡丹為主題的稱為纏枝牡丹紋,以葡萄為主題的稱為纏枝葡萄紋,加入鳥獸等動物形象的稱為纏枝鳥獸紋,加入人物形象的稱為纏枝人物紋。有呈連續的波形形成二方連續的組織形式,也有向四周做任意延伸或適合延伸形成的一種四方連續的紋樣構成形式。
纏枝紋有著明顯的傳承演變的關系,通過分析比較就能清晰地辨別出宋代纏枝紋與其他時代不同的特點。魏晉以前我國的植物類紋樣并不發達,佛教傳入我國以后,裝飾紋樣開始較多地接觸外來纏枝植物紋樣。受佛教的影響出現了很多忍冬紋,有一種觀點認為纏枝忍冬紋是漢代的卷云紋糅合了外來紋樣的特點而形成的。它繼承了南北朝卷草紋連續不斷的特點,呈現出流暢飄逸的美。到了唐代纏枝紋形狀顯得豐滿肥碩,富麗纏綿、卷曲流暢,形成了程式化的紋樣。如唐纏枝紋由一個中心圖案向四方對稱延續、豐富飽滿的構圖。五代開始,纏枝紋突出花頭形狀,葉子變小,寫實性增強。纏枝紋發展至宋代變得更加纖巧靈動,流暢飄逸的韻律線與寫實單位花紋形成線與點、動與靜的對比,既富有強烈的動感,又富有生生不息、萬代綿長美好寓意。各種花卉形狀不同,表現手法不同,但花和葉都非常寫實,是程式化和寫實風格完美結合的典范,影響了后世的纏枝紋風格。宋代瓷器上纏枝紋常見的形式有“纏枝牡丹”、“纏枝蓮”、“纏枝菊”、“纏枝葡萄”、“纏枝石榴”、“纏枝百合”、“纏枝寶相花”以及“人物鳥獸纏枝紋”等。江蘇常州北環新村宋墓出土的纏枝蓮花牡丹紋銀片,其上的牡丹、蓮花及枝葉也作了類似的變形處理。纏枝紋在宋代絲織品中稱穿枝紋,穿枝花一般以豐碩的牡丹、芙蓉為主體,有的配以梅花、海棠等較小的花蕾,形成花中有花、葉內添花的奇特效果;具體實例如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北宋年間的制帖綾,綾上紋樣為穿枝牡丹紋。穿枝花鳥題材很多,常見的有真紅穿花鳳、百花攢龍、真紅大百花孔雀、青綠瑞草云鶴等。花和枝葉穿插自然規整,禽鳥生動活潑,紋樣造型趨于寫實,表現得纖巧典雅。其二方連續樣式常應用于婦女服飾中的袖、襟、領等局部裝飾中,一般以波紋曲線為骨架,在空間配以逆向花紋。在建筑彩畫上穿枝紋被也大量應用。宋李誡所撰《營造法式》一書談到當時建筑裝飾紋樣時,提到“牡丹花、芍藥花、黃葵花、芙蓉花、荷蓮……,或于花內間以龍鳳化生飛禽走獸等物”。我們可以看到建筑彩畫上四季百花皆以枝干相連,花葉滿地鋪陳,龍風珍禽異獸飛舞奔馳其間的生趣。從雕刻紋樣上可以看出宋代纏枝花卉靈巧流暢,金、遼等融入了少數民族的文化特點纏枝紋顯得壯碩凝重;明清風格與宋代的風格一脈相承。一直到今天,我們在生活中還經常會看到或使用這一類紋樣。其多變的形式和寬廣的審美域,對裝飾藝術有著深遠影響,因而表現出頑強的生命力,在紋樣發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生色花裝飾紋樣造型的定型
“生色花”即寫實折枝花卉紋的總稱。所謂折枝花即通過寫生截取帶有花頭、枝葉的單枝花卉作為素材,經平面整理后保持生動寫實的外形和生長動態,作為單位紋樣。在組織排列上將數枝折枝花散點分布,注重花紋之間的相互呼應,造成生動自然又和諧統一的整體效果③。唐代李賀《秦宮詩》:“桐陰永巷調新馬,內屋屏風生色畫”。生色畫,即指色象生動的寫生畫,即寫實如生。《營造法式》中有“寫生”一詞,即指生色花。宋以前,花草的表現多有變形,較為程式化,花種本身的特色較為模糊,無論是蓮花、芍藥、茶花、菊花、芙蓉都有著理想化了的牡丹的影子。宋代院畫的興起對工藝美術影響至深。工筆花鳥講究精微刻畫、栩栩如生,故寫生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手段。裝飾紋樣在此基礎上出現寫實作風,宋代花草紋的描寫,多用寫實手法,因其寫實生動、恬淡自然而與自然物象近似,準確地反映了宋代審美意識,成為典型的宋代紋樣程式,因此又被稱為“生色花”。生色花在宋代陶瓷、染織等眾多的裝飾藝術中出現,如陶瓷中通常在器物的顯著部位繪畫一枝折下的花卉,有折枝牡丹、折枝梅、折枝桃等紋樣。染織中也多見,尤其在宋代織錦、紗羅、綾等織物裝飾中廣泛應用。沈從文先生在其《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中對宋代織錦的提花技術介紹時寫道:“生色折枝花的好尚,開始突破了唐代對稱圖案的呆板。”1957年在福州黃昇墓出土的絲綢中,其裝飾紋樣均是寫實花卉,花葉表現手法非常簡潔生動,花葉之間很注意植物的生長規律,其折枝布滿全幅,既不像團花那樣繁復,也不像散點式紋樣排列的對稱規整,而是用花、枝和葉的生長趨勢自由穿插來經營布局,其紋樣風格跟裝飾性較強的圖案型紋樣相比是迥然不同的。“生色花”的造型雖然寫實,但并非對植物原生態的生搬硬造。如果說植物的造型由原生態到花鳥畫,已經進行了由自然型向藝術型的轉化,那么“生色花”相對于花鳥畫則是在前者藝術形態的基礎上,進行了符合紋樣制作工藝和紋樣裝飾區域的進一步處理,使其造型及裝飾效果更加趨于理想的形式美的追求。同為形式語言,同樣以“寫生”為目的,而“生色花”于線條筆墨到枝、葉、花、實的再現中有了更多的凝練、提取、轉換。也因此,“生色花”作為一種寫實紋樣造型,在寫實中又透露著裝飾紋樣特有的韻味和魅力。④而且生色花瓣雖有簡化寫意,但仍有保持不同花種的特點。這種寫實折枝花卉紋既可以單獨成紋,也可以與動物、人物組合,構成各種形式豐富、寓意吉樣的紋樣。隨著宋代花鳥畫的發展,寫生花卉成為花卉紋樣的主要部分并在宋代定型,無論在染織、陶瓷上,都表現出明顯的形式特征,形成了中國裝飾藝術的新格局。
總的來說,在我國宋代主要裝飾紋樣形式定型,各種植物、動物、人物紋樣齊備,形成了一定的范式。不僅直接影響了元、明、清的裝飾紋樣,也影響了近現代中國民間的裝飾紋樣,在中國裝飾紋樣發展過程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① 雷圭元《中國圖案作法初探》,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5年版,第41頁。
② 朱玉周《道教陰陽太極圖的演變》,《黑龍江史志》,2008年第5期,第15頁。
③ 回顧《中國絲綢紋樣史》,黑龍江美術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頁。
④ 張曉霞《天賜榮華:中國古代植物裝飾紋樣發展史》,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