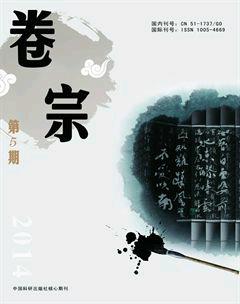基于現象學方法的彩陶紋飾分析
鄧椿山,鄧昱全
摘 要:本文意在試探性地以現象學方法對彩陶紋飾進行分析,通過對“生活世界”和“歷史”的懸置,對意向對象的明確把握,獲得純粹的意向活動。通過本質還原、自由聯想的變動程序以及對意向活動和內容的深入探索,形成現象學的彩陶紋飾分析法。
關鍵詞:現象學;彩陶紋飾;分析
基金項目:國家級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201310635076)
1 彩陶紋飾研究的懸置維度
1.1生活世界——想象力誘惑
康拉德早在《審美對象》中提到:審美對象的無前提性,這里的無前提性就是胡塞爾意義上的對“存在和歷史的懸置”。對“存在”的懸置就是要擺脫對生活世界的種種想象與猜測,對審美主體自身觀察范圍進行限制,排除一切非純粹的現象,直觀意識中的事物本身。這樣一來就能達到專注的“我思”,使我們的目光朝向知覺場里特定的對象,而不是按照經驗心理學的方式思考。彩陶紋飾的時代及其生活世界是我們不能把握的,就不能輕易地按照我們的想象進行描述,雖然通過其他科學的支撐可以進行大致描述,但是仍然得不到最直觀的結果。
1.2歷史——理解力誘惑
胡塞爾以建立科學的哲學態度創立現象學,并以其擺脫成見的著名方式實現這一點,是現象學之所以能夠煥發新的對于意向對象的觀察方法及理解方式的核心要素。而理解力引人將眼前的對象納入概念的確定性以便掌握它。歷史作為已成型的理解,總不是客觀的,是人理解的歷史,這種理解形式已然涵蓋了主客體的關系在內,與現象學態度是沖突的。
1.3意向對象的準確
意向對象不同于現實存在的對象(心或物),而是指一個觀念的所指、意義。想象的東西,幻覺和錯覺,虛擬的表象,只要是有意義的觀念,都有其“意向物”,它們一定是客觀存在物,但卻是可以內在直觀到的。如為表達某個理念而產生的彩陶紋飾,真正使其成為該理念藝術的不是彩陶本身,不是油彩和泥巴,而是意向對象。如圖一所示的尖底瓶旋紋展開圖,如果就“紋飾”概念作為意向對象那么是毫無意義的,真正進入我們意識流的是旋轉和具有律動感的線條以及這樣的意識經驗所包含的想象關聯物,我們所要關注的事物也正是這紋飾所帶給我們的實際體驗。
(圖一) 尖底瓶旋紋展開圖 (圖二)彩陶上的人面紋
2 意向對象和審美對象的雙重身份
當我們處于一種生動的“我思”中時,我們對一個對象是所指的,這個對象即是意向對象。然而作為審美知覺的發生條件,或者說作為更高級的體驗內容,彩陶紋飾具有極其明顯的感性質素,例如圖一的彩陶上的人面紋,一個人物臉部的形象和動態甚至快樂感、沖動感都包含在內的感性因素體驗就是從本身不具有任何意向性的感性材料中產生出來的。胡塞爾寫道:“無論怎樣論述,我們都無法徹底弄清在感性的質素和直觀的形態之間形成的二元性和統一性的矛盾。這種矛盾在被構成的時間性層級內的現象學領域里被永遠地保持著,或者說在整個現象學領域內這種兩性同在的特征,還一直起著支配作用。”[1] (P118)通過不斷地統一在一個意向性結構中,彩陶紋飾對觀察者完全敞開。同樣是這個人面紋的例子,我們首先能夠知覺到一個紋飾的內容——形似人面,并不確定,可能有帽,五官清晰,然后能夠知覺到感性質素:快樂、詭異、從容、沖動等等。并逐漸形成意識流,以此人面紋為中心的想象域和知覺域。
3 本質還原與自由聯想的變動程序在此問題上的兩個考慮
3.1彩陶紋飾的類比邏輯研究
我們的考察,將使我們對意識的復合體產生新的認識,它似乎是從意向作用中被抽取出來的。在經驗和經驗思維的范圍里,我們的思考將轉向意識連續體和意識體驗的非體驗關聯體。同時,這其中的一些體驗又通過意義關聯體,使同一個對象的各種意識彼此聯結起來。[1](P121)正是在對明晰度把握的要求中,知覺場容納了本質把握的相關對象。那么我們能不能通過演繹思維或它的抽象形式--數學思維而獲得事物的本質共性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形式邏輯的演繹推理只是適合建立事物之間的橫向的協同關系,例如蘇秉琦《關于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一文中對鳥紋演化的演繹邏輯實例,“時間關系從出土單位得到證明”[2],
(圖三)鳥紋從具象向抽象的演化過程
(圖四)一般演繹邏輯
(圖五)真實演繹邏輯
(圖六)類比邏輯
而且鳥紋的形象之間關系非常連續,概念本身很具體,那么它們之間的關系就主要是協同式的,是適合演繹邏輯的。然而,也并非確定的事實,如圖四圖五所表明的一般演繹邏輯和真實演繹邏輯,多種因子可能會導致相同結果,鳥紋似乎是按照這個時間進行了演變,然而并不一定是具象到抽象的演化,有無數的其他可能作用于這個歷程,然而并不為我們所知和確定,并且,我們不能從這一組“演化”中得到關于鳥紋對象的普遍性本質。
如果概念之間的關系很間斷,概念本身較抽象,那么它們之間的關系才主要是共同性的,這個時候一般適用于類比邏輯,如圖六所示。圖二人面紋與真實的人臉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我們可以通過與人臉的類比得到關于“人面”紋絡的信息,這些信息是紋飾在我們意識當中顯現的,它的如何呈現恰恰是關鍵所在。從本質直觀的過程中,我們能夠完全洞見人面紋的被給予性,也就是顯現在觀察者面前的材料——“人面紋”呈現的現象。
3.2我們的審美經驗和自由聯想的變動程序
仍然以人面紋為例,我們的知覺總是起于一點,或者一瞬間,在知覺場里我們目光投向的一瞬間,然后逐漸清晰地意識到人面紋。此前我們引用到胡塞爾的論述,意向性活動就此展開,并且一些感性質素也同時進入了意向活動當中。通過進一步對“人面紋”觀察的“意向活動”(Noesis)和“意向相關項”(Noema)的考察,我們可以發現我們所調用的審美經驗是現代的、與紋飾的生活世界有差異的、有諸多應用趨勢的,甚至可能是虛構的、建立在一種當下理解和想象上的。(可能是波普藝術中曾看到過有相似重復的圖案;可能是聯想到羌族典型的“羊頭”;可能是想象到臉上涂滿各種油彩和掛著羽毛的原始人像)。筆者認為這樣的審美經驗與本質還原自由聯想的變動程序是不構成沖突的。本質直觀摒除是偏見的理念、肯定性的結論,然而我們的審美經驗已然處于意向性結構中,是審美知覺的一部分,所以此衍生出的審美的意義已然能夠超越經驗。這是因為現象學意義上的意識的意向性結構是意義的最終源泉,而意向性的觀念性(ideality)并不依賴于相關經驗的現實性(reality)。[3]
參考文獻
[1] 胡塞爾.《現象學》[M] . 重慶:重慶出版社.
[2] 蘇秉琦.《關于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J]. 考古學報. 1965(1):51-81
[3] 翟振明.《意義是如何超越經驗的》[J]. 中國現象學與哲學會議. 2001 (10): 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