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尚的立場
⊙宋 備[東南大學藝術學院, 南京 210096]
作 者:宋備,東南大學博士,東南大學藝術學院教師,研究方向:美術學、藝術學。
塞尚——現代繪畫之父,他對于繪畫藝術的突出貢獻主要在后半生,即與印象派分道揚鑣而獨自探索的三十年。早期的塞尚受挫于強調激情與動勢的浪漫主義繪畫。受挫之后便向畢沙羅請教,并與其一起進行戶外寫生。在印象派時期,塞尚的畫面筆觸出現越來越有序的特點,這種分組排列的筆觸,使得所繪物體具有一種堅實的塑造感,而這種繪畫形象的堅實感,作為塞尚作品的個人特色被其發展下去。
但作為利用光譜式色彩作畫的印象派,為了獲得準確的、肉眼所能感覺到的自然光色之閃爍感、振顫感,往往模糊了所繪物的形體和造型,這很容易陷入畫面缺乏構架、僅限于照著對象的色彩做自然主義描摹的危險。色彩與造型、感性與理性一直矛盾著,似乎很難統一。印象主義的危機就是形色分離,色彩大于形式與內容。在這種危機意識中就連對于細微色彩最為敏感的雷諾阿也覺得不得不研究文藝復興時的素描,以便獲得一種造型輪廓用來對其充滿微妙色彩的畫面重新組織。當時的德加、修拉、高更、梵高也都以自己的方式來利用印象派從自然中提煉出的響亮色彩去尋求一種新表現形式。作為印象主義的這波回頭浪,塞尚的課題是“要使印象主義變成像博物館里的藝術那樣堅實恒久的東西”①。
所謂“博物館里的藝術”指的是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繪畫中的古典主義藝術。“堅實恒久的東西”指的是古典主義繪畫中,畫面各形象經過編排和組織而形成的一種富有邏輯的、概括而莊嚴的秩序感,也是古典主義的魅力之所在。
塞尚無意去模仿古典藝術大師,他同時也認識到古典藝術大師們所考慮的并非只是對自然的簡單臨摹。如塞尚所喜愛的古典畫家普桑。然而印象主義的塞尚認為:靜穆的古典世界沒能表現自然持續變化的外觀,所謂自然持續變化的外觀是塞尚在印象主義時期,對于自然光色的捕捉而觀察到光色不斷變化而顯得豐富、自由、活躍的自然外觀。“古典主義藝術是在作一幅畫,而我們則是要得到一小塊自然。”②這里塞尚所欲追求的藝術,便是站在印象主義豐富而活躍的自然基礎之上,并使其作品具有一種古典世界中那種堅實而恒久的魅力。這種印象與古典合體的藝術,將是一種全新樣式的藝術。
這是一個大難題,印象主義是極端強調直觀與感性的,而古典則代表一種理性與嚴整的秩序,二者看似格格不入。關于對印象派的改造,德加、雷諾阿等人在保留印象派的明亮的色彩基礎上整合進古典繪畫的元素。由于古典藝術中的具有堅實感的形式構架與印象主義中活躍、散漫的光色存在著矛盾,如果說在德加、雷諾阿那里體現為一種折中的態度,作品表現為用簡練、質樸的輪廓線界定住了躍動著的光色,那么在塞尚那里則是一場創造。因為塞尚不但沒有削弱印象主義顫動著的光色,相反使之更加強化,最終能擊碎古典三維空間所緊密維系的造型法,依靠來自自然的均衡法則與光色原理重新構筑,使光色實現了永恒。
塞尚的意義在于對古典形式語言的解構與重筑,所謂的“設想普桑依據自然而再造”③。要體現印象主義那種豐富而活躍的自然外觀并具有古典式的永恒美感只能在造型形式上入手,對于日益散漫的色彩做約束,那么首當其沖的第一問題便是線條的處理,而純粹的古典用線有著嚴謹的法則約束,這只會犧牲掉印象主義活躍著的自然外觀,因此塞尚對于線條的改進直接牽涉到古典語匯的基礎──三維透視。
三維透視法是西方繪畫為實現二維平面上呈現三維視錯覺經過漫長的探索而得來的,包括線透視、色彩透視、隱沒透視。其中達·芬奇創立的隱沒透視,是由通過控制物象輪廓的清晰程度來產生空間感,并使得近處的主體形象突出成為畫面的中心地位。這種透視對于塞尚來說不適應表現印象主義式的豐富自然而取消,塞尚在邊緣線的清晰度上把風景拉到一個平面上來突出了線條在畫面中的作用,更有意義的是同時在此基礎上打破了傳統的線透視諸多法則,來進行形體的變形、反透視處理。在畫面中我們看到作為人物背景的板壁邊條不在一條水平線上,圓形杯口變成了不標準的橢圓,桌布在平坦的桌面上斜傾而起,且房舍、靜物故意處理成一片傾斜。塞尚的天才也正在于此,他借助于畫面的總體安排,使得我們在欣賞時并沒覺得有什么不妥;這種違反透視規律的變形,其目的是為了畫面均衡勢態的需要。由于消除了隱沒透視,在畫面中對于光影的均衡考慮讓位于在畫面中起構架作用的線條之均衡考慮。在中世紀、文藝復興時代的畫面中我們也看到一種線條的均衡,但是線條必須服從于形象、面貌,且符合透視規律,且整個中世紀、文藝復興的繪畫之線條之構成,皆為垂直與水平線的運用。而自然界的事物是復雜且各具形態的,塞尚所提煉出的線條能夠還原自然的豐富形態,同時通過變形與概括化處理形成畫面中力相互作用,使呈夸張傾斜勢態的均衡成為可能。

圖1 蘋果與桔子
在塞尚約創作于1895年中的《蘋果與桔子》(圖1)中便可見到這種帶有夸張化的傾斜勢態的構圖。水果托盤、水杯同桌面不在一個水平線上,由于托盤、水杯處于低視點上,視覺上有較強的穩定感,反襯得高視點下的桌布傾勢得有力。請注意托盤口的反透視處理:使距我們遠的那半邊弧形高起,這樣便與桌布的傾勢產生力的均衡。若按正常透視,則托盤口呈窄橢圓形,在整幅畫中給我們的視覺反為不適。
塞尚的線條特性在于:出于均衡審美需求,可將事物輪廓及結構進行變形。從美術發展來看,線條在這里并非只是事物的輪廓,已開始萌發了它的幾何意圖。
線條的幾何審美伴隨而來的是形體、結構的簡化,中晚期的塞尚往往只用幾條大線來切割更簡潔的畫面。關于形體的簡化他提出了著名的“三種圓”的理論,便是自然的物體都可以用球體、圓錐體、圓柱體相概括,也就是可以用簡化、結構的眼光看事物。
關于自然給塞尚一種深邃、博大的感受。這種感受在塞尚決定對印象派進行改造時就已經存在,而伴隨著對于畫面構造形式的確立,深化了這種感受,我們看到繪畫形式的作用決定了藝術家對自然不同層次的感受力。
塞尚通過具有自主性的線條運用,使印象主義的豐富自然進入了結構領域,而真正的難點還是無法回避的光色問題。也就是使印象主義變幻著的光色進入結構化的永恒世界。
光線與色彩是印象主義的靈魂,作為印象主義的塞尚在對古典造型秩序解構與重筑的同時,光色問題一直參與在其中,并在最終形式語言的形成中起著目標作用。“按照自然來畫畫,并不意味著摹寫下客體,而是實現色彩的印象。”④最終塞尚要創造的是光色印象中的大千世界。在塞尚印象主義及印象主義之后的探索中,由一種畢沙羅式的散點筆觸逐漸提煉成一種分組排列、有秩序的小色塊,這種方形小色塊活躍在畫面內各堅實的物體上給人一種視覺上的顫動感,仿佛光線與空氣在顫動。同時我們也看到印象主義是通過高度活躍的筆觸來創造純粹的光色世界,塞尚若要使其堅實的造型進入這種光色世界就必須加強筆觸的活躍度,然而這種顫動著的色塊又與堅實的造型有著矛盾:就是要么放棄造型之堅實,要么(同雷諾阿的末期一樣)限制住筆觸的活躍度;仿佛兩者無法共處一體。
為了適應畫面構架之需要,塞尚使自身色彩筆觸的形狀明確為一種色相勻涂的塊面,這種色塊已不是印象主義那種散漫的點狀,而是具有了造型輪廓的色塊。這個塊體由于在畫面中具有了造型意義,且與堅實構架的畫面相協調。這種面由于并不依附在具體形象上,因而完全可以服務于畫面中的結構美。這種色塊的相互參差及色相對比,便可形成強烈的光色活躍而顫動的效果,給畫面帶來強烈的光感與空氣感,仿佛形象本身在這種光線與空氣中一齊顫動,最后被色塊本身所消解、置換。
塞尚在此時的色塊處理已并非只是出于對自然界光色的表現,而是包含著對所繪物體的全部內容及畫面本身結構的表現。
“我看見各種色彩,它們整理著自己,按照它們的意愿,一切都在編織著自己,樹木、田野、房屋,通過色塊。”⑤“素描與色彩并無區分;畫色彩的同時也在畫素描;色彩越協調,素描也就越準確。色彩豐富,形式飽滿”⑥。這兩段話語有兩個含義:一是色彩本身能包含所需要表現的自然的內容;二是所謂素描即指造型,但是現在色彩在擺放的同時,造型已經被解決了,因為色塊本身就解決了造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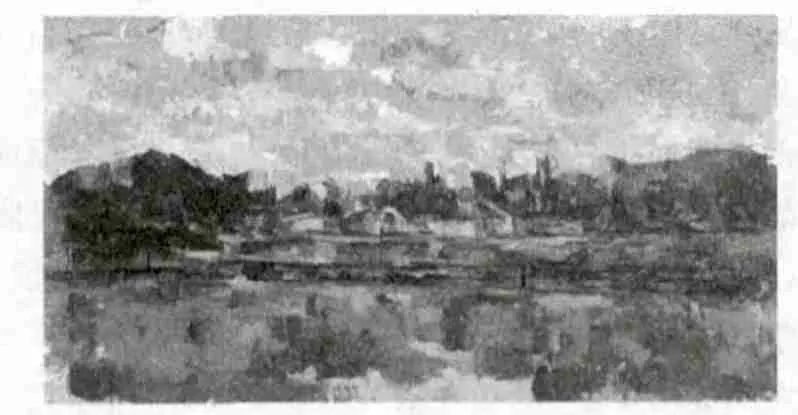
圖2 風景
在塞尚未完成的《風景》(圖2)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塞尚的作畫程序,除了標明區域的兩三根連接而成的長線外,其余皆為一塊塊勻涂的具有造型構架意義的大色塊。塞尚常常持筆沉思達一個小時才畫下一筆,這一筆應該包含著空氣、光線、繪畫對象、畫面以及繪畫的特色與風格。這種把物象的豐富納入到平涂的色塊中去的畫法,本身就標志著對物像的抽離,意味著美術形式語言的點、線、面等元素本身便反映著美術所需要的內容。對于塞尚作畫對象而言,無論是一只蘋果還是一張臉孔,都只是畫家的一種憑借,為的是一場線與色的演出。
塞尚便是運用這樣的色塊創造了如此世界:既有古典般的堅實、整體、深邃感,同時由于用線、用色的自由,加上色塊強烈的振顫,又是一曲光色爛漫的印象樂章。關于塞尚對繪畫的成就在于:使得印象主義獲得構架支撐,突破了古典的三維體系的數百年統治。這一般都歸功于其三圓理論,該幾何構成理論直接啟發了畢加索、布拉克等人的立體派畫風之創造。其實塞尚的關于色塊輪廓造型之思路也同樣重要。由于畫面上勻涂色塊的振顫能產生印象派特有的光色效果,同時為了肅穆感以及與構成畫的線條和畫面結構相和諧,色塊呈方形組合,那么這個方形色塊不再只是筆觸而有了造型意義,甚至一個色塊本身就能包含著許多繪畫所需求的內容,馬蒂斯把塞尚奉做老師的原因也在于此。勻涂色塊的邊緣線就是造型,這鼓舞了馬蒂斯用純色表現世界的想法,直至在馬蒂斯的野獸派、剪紙畫的試驗中,色彩最終實現了解放。
塞尚的難題最終是被其解決了。研究到這里,我們發現塞尚并沒有折中地去解決這一兩難命題,而是古典的堅實美感和印象派的顫動美感都被其在作品中強化。塞尚的立場問題也至此升華,因為他的探索本就是個人意志與思想的頑強表達,而非攪稀泥式的“借鑒”。關于塞尚還有很多東西要談,也許當初塞尚本意是想如普桑那樣嚴謹、實在地去畫一幅有韻律感的繪畫,但是塞尚的手并不巧,這從他早期浪漫風格作品中的生硬、枯澀感能看出來。但就是這樣的一種笨拙,加上他日益流露出的幾何化傾向被升華,成就了他的一切。
① [美]H.H.阿納森著,鄒德儂等譯:《西方現代藝術史》,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頁。
② [法]梅洛-龐蒂著,劉韻涵譯:《眼與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頁。
③④⑤ 《宗白華美學文學譯文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217頁,第215頁,第218頁。
⑥ [英]保羅·史密斯著,張廣龍譯:《印象主義》,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