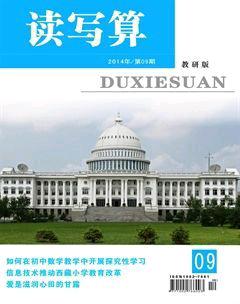回歸小學(xué)語文教學(xué)
馬敬安
摘 要:學(xué)生是一個(gè)包容很寬的概念,它可能是兒童,也可能是成人。就小學(xué)語文教學(xué)而言,其對(duì)象就是兒童。所以,小學(xué)語文課堂應(yīng)是小學(xué)兒童語文課堂。
關(guān)鍵詞:兒童;語文;教育
中圖分類號(hào):G622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B 文章編號(hào):1002-7661(2014)09-200-01
小學(xué)語文教學(xué)堅(jiān)守“童本”取向,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教師往往以“知識(shí)壟斷者”的身份出現(xiàn),在比較注重知識(shí)灌輸?shù)纳鐣?huì)里就無形地?fù)碛辛酥髟捉虒W(xué)、主宰課堂的特權(quán)。小學(xué)語文教學(xué)如何回歸“童本”課堂,我們自然可以作多向度、多層面的探索和闡述,但筆者在這里簡單的闡述一下。
一、兒童是天生的學(xué)習(xí)者
人類的每一個(gè)生命個(gè)體,都具有與生俱來的學(xué)習(xí)、成長和發(fā)展的能力。這是自然界的恩賜,也是生命降世所必須擁有的謀求生存、發(fā)展的基本生命活力。就如種子一定要頑強(qiáng)地發(fā)芽,草木一定要拼命地扎根一樣。所以。學(xué)習(xí)應(yīng)該是生命自身的一種行動(dòng)歷程,我們所有的
教學(xué)目標(biāo)和希望,都可以依托學(xué)生的自我生命來實(shí)現(xiàn),而且真正有效的教學(xué)。也只能憑借學(xué)生內(nèi)在的學(xué)習(xí)智慧來達(dá)到。必須認(rèn)識(shí)兒童是人類億萬年發(fā)展的成果,他們承傳了人類生命的全部精彩。教學(xué)必須堅(jiān)信兒童是天生的學(xué)習(xí)者,才能最大限度地開發(fā)他們的生命潛能,最大可能地運(yùn)用他們吸收內(nèi)化的積極性,從而使課堂成為兒童快樂起飛的平臺(tái)。尤其是語文學(xué)習(xí),語言學(xué)家都十分肯定人的語言本能的存在。從而認(rèn)為語文原則上不是靠別人的教,而要依靠自己的學(xué)。語文可以“無師自通”幾乎已成共識(shí)。父母并沒有把他們送到專門的學(xué)校去,也沒有學(xué)習(xí)口語的教材,更不上任何口語課,布置許多作業(yè),當(dāng)然也談不上去補(bǔ)習(xí)班或請家教。可為什么幾乎每個(gè)孩子都能在不知不覺中學(xué)會(huì)了口頭語言?這就從一個(gè)側(cè)面顯示了兒童作為天生學(xué)習(xí)者的潛力。兒童有三大特點(diǎn)體現(xiàn)了好學(xué)的天賦:一是“好問”。孩子總是有問不完的問題,這甚至令一些成年人不勝其煩。為什么“好問”?“好問”的實(shí)質(zhì)是求知,兒童希望了解許多不太清楚的事。二是“好玩”。游戲幾乎是孩子的全部生活,兒童的文化精神便是自由的游戲精神。孩子正是通過“玩”去認(rèn)識(shí)自然、認(rèn)識(shí)世界的。所以,“玩”就成了孩子最好的學(xué)習(xí)。三是“好奇”。兒童很容易發(fā)現(xiàn)新奇,也很喜歡新奇。“好奇”正是兒童天性的“求知欲”的強(qiáng)烈表現(xiàn)。
也許有人會(huì)質(zhì)疑:既然兒童是天生的學(xué)習(xí)者,為什么又會(huì)有不少的孩子學(xué)不好?這并不奇怪,除極少數(shù)兒童有生理因素(智能發(fā)育不良)外,基本上是由不正確的教育造成的。學(xué)習(xí)本來是一件快樂的事,可過高的要求,過多的作業(yè).過分嚴(yán)厲的訓(xùn)斥,過于費(fèi)解的交流……都有可能傷害了兒童的學(xué)習(xí)積極性,厭學(xué)情緒油然而生,好學(xué)的天性遭到壓抑。這就正如大教育家盧梭所認(rèn)為:“受錯(cuò)誤教育的兒童。比不受教育的兒童,距離智慧更遠(yuǎn)!”
二、“不需要教”,應(yīng)當(dāng)怎樣教
一個(gè)人在學(xué)校接受語文教學(xué)最多不過是十幾年.然而學(xué)生在離開老師之后能獨(dú)立運(yùn)用語文于工作、學(xué)習(xí)、生活。最有效的語文課堂的“教”自然應(yīng)當(dāng)著眼于學(xué)生離開學(xué)校之后的“不需要教”這一落腳點(diǎn)上,但似乎很少有人考慮它的逆命題。即“為了不需要教”,今天我們又應(yīng)當(dāng)怎樣教?否則,我們的語文課堂為什么總是擺脫不了“逐段講解”那“授予”式的基本套路,為什么總是超越不了“牽著學(xué)生走”的基本態(tài)勢.為什么總是突破不了教師淋漓盡致地展示才情而只是讓學(xué)生一旁“配合”的基本格局。如果我們能嚴(yán)峻地反思“為了不需要教。應(yīng)當(dāng)怎樣教”。答案恐怕只能是一個(gè),即這樣的教不應(yīng)當(dāng)是教師的全盤授予.更不是教師一廂情愿的講臺(tái)作秀,而應(yīng)當(dāng)是“導(dǎo)學(xué)”.引“導(dǎo)”學(xué)生自己去“學(xué)”.自己去“學(xué)會(huì)”學(xué)習(xí)。我們過去過度地在研究怎樣教,其實(shí)我們應(yīng)當(dāng)更多地研究如何“少教”、“不教”,實(shí)行“無痕之教”。
“教學(xué)論”發(fā)展至今,“教學(xué)”已不是視學(xué)生為容器,由教師單向灌輸?shù)男袨椤I踔烈膊皇恰敖處熃蹋瑢W(xué)生學(xué)”的雙邊授、受關(guān)系,而是“教師,教學(xué)生學(xué)”,一種應(yīng)當(dāng)以學(xué)生自主學(xué)習(xí)為核心的理念。其實(shí),教乃學(xué)之導(dǎo)的樸素意識(shí),在古賢的教學(xué)思想中時(shí)有閃現(xiàn),如子思在《中庸》的開篇中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就是說:大自然孕育了人的本性,自然的人性就是“道”.對(duì)道的修煉就是“教”。所以,“教”也就是修道者的學(xué),即學(xué)習(xí)者。而學(xué)習(xí)活動(dòng)也就是率性的、自由作為的,就像嬰幼兒的牙牙學(xué)語,都不需要刻意地去教。宋朝朱熹對(duì)此說得更為透徹:“事事都用你自去理會(huì)。自去體察,自去涵養(yǎng)。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探索。某只是做得個(gè)引路的人。做得個(gè)證明的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
教學(xué)發(fā)展到今天。最有效的“教”.更應(yīng)當(dāng)是教師對(duì)學(xué)生自主學(xué)習(xí)的一種指導(dǎo)、引導(dǎo)和誘導(dǎo)。一位教師教學(xué)《爬天都峰》一課(人教版第5冊),深讀課文伊始,就有一位小朋友說:“課文的題目是‘爬天都峰,這‘爬字有點(diǎn)兒土。我們說‘登山隊(duì)員,就沒有說‘爬山隊(duì)員的。用‘登天都峰作題目不是更好嗎?”老師正想解答這個(gè)并不復(fù)雜的問題.但又想何不把“教”轉(zhuǎn)化為讓學(xué)生自己“學(xué)”的過程。于是,教師現(xiàn)場改變了教學(xué)預(yù)設(shè),便說:“你的話有道理。用‘登天都峰作題目也可以,可作者為什么要用‘爬,在這里到底用‘登好還是‘爬好,讓我們來深讀課文研究一下好嗎?”于是有的學(xué)生找到了寫天都峰特別高的第二小節(jié)作依據(jù),說明“爬”比“登”好,因?yàn)椤芭酪帜_并用,正表現(xiàn)出這山的高,只能爬”。教師便乘機(jī)抓第二小節(jié)研讀感受。有的學(xué)生說因?yàn)榈巧降摹拔摇笔莻€(gè)孩子。還有一個(gè)是老爺爺,這一老一小要登山多不容易,就只好“爬”了。教師便因勢點(diǎn)撥學(xué)生深讀課文的第三至第七小節(jié)。有的學(xué)生還從課文的第八至第十小節(jié),說明這一老一小是依靠了互相鼓勵(lì),“從別人身上汲取力量”才上了天都峰,不是輕易上去的,用“爬”更能說明這一點(diǎn)……就這樣,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需求得到了滿足,生命潛能得到了充分調(diào)動(dòng),用自己的學(xué)習(xí)解決了自己的問題,而老師的“教”只是滲透在“導(dǎo)學(xué)”的過程之中。實(shí)踐證明。教師很多“教”的行為都是可以轉(zhuǎn)化為“學(xué)”的活動(dòng)的。應(yīng)當(dāng)說,“以學(xué)代講”是實(shí)現(xiàn)“為了不需要教”的一條可行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