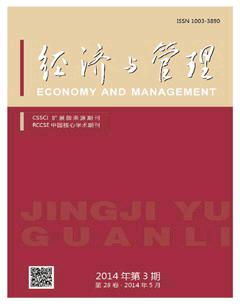中國省級人力資本水平度量與分析
王詢+孟望生
摘要: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動力源之一,也是地區發展差異的主要原因,伴隨著中國地區差異的不斷增大,人力資本勢必也存在一定的規律和特點。文章采用多元綜合法對我國各省2001~2011年間人力資本的平均水平進行了測度和分析。研究結論為:省級地區的人力資本分為學研、應用、素質和健康四種類型,且它們對人力資本綜合水平的貢獻依次遞減;人力資本和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呈較強的省際同步變化關系;與此同時,各省按人力資本及其政策變量歸為落后、發展中、欠發達以及發達四類地區,且各類地區在經濟發展水平、人力資本政策和投資主體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
關鍵詞:探索性因子分析;聚類分析;人力資本;省級地區
中圖分類號:F2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49(2014)04-0003-11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4.001
收稿日期:2014-01-11;修訂日期:2014-05-26
作者簡介:王詢,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孟望生,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甘肅政法學院經管學院講師。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the Provincial Regions Human Capital in China:
Based on a Multivariate Complexapproach
WANG Xun1, MENG Wangsheng1,2
(1. School of Economic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5,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Gansu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Lanzhou 730070,China)
Abstract:Human capital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economic growth, also it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development difference among regions. With the increasing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difference in China, human capital will have some regularity and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uses a multivariate complexapproach to measure and analyze the averag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in these 31 provincial regions during 2001~2011.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uman capital in every province has been composed by researching, application, quality and health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comprehensiv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are descending; There is a strong synchronous chang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mong regions; The provinces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categories area which are called backward, developing, less developed and developed area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human capital in different types and related policy variables.
Keywords: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clustering analysis; human capital; provincial region
一、引言與測度方法回顧
盧卡斯(Lucus)提出新增長理論后,學界普遍認同“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主要動因之一”[1]的觀點。自此,在經濟增長、地區差異等相關問題的研究中,人力資本作為解釋變量備受關注。隨著中國地區間發展差異的進一步增大,國內學者也越來越多地試圖從人力資本角度對其進行解釋。然而,有關這些解釋的研究之間存在較大爭議,無法完全令人信服。究其原因,爭議焦點主要集中在人力資本的衡量或其代理指標選取的合理性上。因此,選取合理的測度方法和指標體系對人力資本進行測度將使相關問題的解釋更具說服力。
當前,主流的人力資本測度方法及其對應指標體系有三種,分別為成本法、收入法和教育存量法。其中,成本法將一國特定年齡(男性26歲、女性20歲)以上的人口視為其人力(或稱國力)資本,從成本回顧的角度將每個成年人在“長成”過程中的累計投入成本視為其單個人力資本替代指標,并通過將所有成年人投入成本加總的方法來獲得該國的人力資本總體水平。侯風云[2]、焦斌龍等人[3]、錢雪亞等人[4~5]均采用此法測度了我國相應時期的人力資本總體水平。成本法最早被提出是旨在估量戰爭、瘟疫等災難導致人口大量減損時造成的國力損失[6]。因此,該法在衡量與人口數量相關的國力水平變化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隨著人力資本測度動機逐漸轉向對增長貢獻和地區差異原因的解釋,以收入展望為視角的收入法逐漸被人們所接受。
收入法將一國(或個人)的人力資本視為其財富創造(掙取收入)的能力,并采用預期收入作為人力資本的替代指標[7~8]。我國學者朱平芳等人[9]、李海崢等人[10]均采用此法測度了相應時期的人力資本水平。收入法測度的人力資本水平在解釋增長動因和地區差異方面比成本法更具理論合理性。然而,其通過現期收入來對主體未來總收入的推算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和數據換算誤差,且運用到地區間差異比較時,人們無法直接觀察到“單位人力資本”的數據,需要進行物質資本和產出數據的換算。這些不僅降低了收入法測度的準確性,還使其測算過程過于復雜。為此,學界更多用教育存量來
指代人力資本。
教育是人力資本形成的最重要元素。教育存量(比如教育年限)的多少不僅能反映受教育主體的人力資本投入成本,而且還決定其未來收入。加之該法具有指標數據易得和計算過程簡單等特性,受到大部分國內學者的青睞。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測度教育存量的指標選取上存在一定分歧。有人偏向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教育存量的衡量指標來反映我國人力資本水平[11],有人則偏向采用總受教育年數[12]。另外,賴明勇等人[13]、楊建芳等人[14]還用成人識字率、入學率、教育健康綜合相對數等其他形式的教育存量替代指標來衡量我國相應時期的人力資本水平。
以上方法均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是它們卻存在一個共同問題:視人力資本為一維變量,即用主體某一方面的能力來衡量其人力資本。如成本法只考慮成本,收入法只考慮預期收入獲得能力,教育法則僅考慮主體的受教育水平。人力資本的概念表明,其形成具有多維性[15],從而其蘊含主體能力的大小需要從多方面來反映。因此,僅用反映主體單方面能力的替代指標表征人力資本的方法可能遺漏重要信息。基于此,本文將多元綜合法引入對于國內省級地區的人力資本測度,是對之前國內相關研究的一大拓展。已有研究表明,多元綜合法將人力資本視為多維潛變量,將主體多方面能力反映指標納入其測度體系進行分析[16~18],測度結果相對比較全面和準確。本文另一創新點是,將人力資本測度口徑下潛到省級地區,并通過數據分析得出人力資本的四種類型劃分,同時將我國各省按其人力資本水平和相關政策變量分為四類(四個等級)。省級地區人力資本水平的測度與分析旨在探尋各地區人力資本的構成要素、相對水平和地域變化規律,可為政策制定者從總體和局部兩個維度制定人力資源開發政策等提供指導意義。
二、測度原理、指標及結果
1. 模型構建
用多元綜合法分析多維潛變量(如人力資本)時一般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通過探尋多維變量多個反映指標的共性,將這些共性通過公共因子的形式分離出來,以達到既能較準確地衡量多維變量,又能簡化分析過程的目的。根據萬斯貝克(Wansbeek)、 拉丁(Lattin)等人分別在2000和2003年提出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模型[19~20],本文的探索性因子模型形式如下:
2. 指標選取與數據說明
本文結合人力資本的定義和多維性特點,參考以往人力資本測量方法及其對應指標,選取14個指標,共分五類。第一類共5個指標,分別為小學在校生人數/萬人、初中在校生人數/萬人、高中在校生人數/萬人、大學在校生人數/萬人,用來反映地區人力資本潛在水平和儲備情況。第二類共2個指標,分別為成人識字率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用來反映地區居民的整體受教育程度,進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現存人力資本整體水平。很多研究都將成人識字率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人力資本的替代指標,但是這兩類指標將未進入和已退出勞動力市場的非適齡人口都包括在內進行統計,無法衡量現存人力資本的利用程度,略顯粗糙。為解決這一問題,本文引入第三類共4個指標,分別為初等(小學及以下)、中等(初中+高中)、高等(大專+本科)、高等以上(研究生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勞動者人數,用來反映各地區人力資本的利用情況。與此同時,創新能力是人力資本最活躍的因素,能極大程度上反映其擁有者的財富創造力。因此,引入第四類共3個指標,分別為技術市場成交額、研究與實驗發展人員全時當量、適齡人口千人專利授權數。另外,健康是個人多方面能力發揮作用的最基本條件,人力資本本身的形成過程和其對財富的創造過程都面臨巨大的健康風險,因此,我們引入第五類指標:存活率,用來反映地區勞動者的健康水平。存活率是指某一年活著的居民在下一年仍然存活的概率,計算公式為:存活率=1-死亡率。
上述各指標的最終統計分析數據均取自我國31個省(除港澳臺地區)2001~2011年對應指標數據的均值。由于數據缺失的原因,R&D人員全時當量取自2008~2011年對應指標的均值。數據來源為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和中經網統計數據庫。
3. 統計分析結果
經計算,巴特利特球度檢驗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各變量(指標)相關系數矩陣為單位陣的假設,且KMO統計量為0.703,這說明上述各變量適合作探索性因子分析。
于是,筆者做碎石圖,并用凱澤法則判定,存在四個公共因子,且它們對所有變量的累計方差貢獻率為84.994%。用方差極大法求得人力資本各變量的因子載荷矩陣及其方差解釋程度,詳見表1。
表1數據顯示,公共因子對除“高中生在校人數/萬人”和“技術市場成交額”外所有變量的方差解釋程度均超過了80%。且由因子載荷矩陣可見,因子1在變量“小學在校生人數/萬人”、“初中在校生人數/萬人”、“高中在校生人數/萬人”、“大學在校生人數/萬人”、“高等教育以上勞動者人數”、“技術市場成交額”以及“適齡人口千人專利授權數”上均具有較高的載荷度。這些變量是對地區的教育、科技發展水平和創新能力的反映,是地區經濟發展最活躍的因素。因此,我們將因子1命名為學研型人力資本。因子2在變量“初等教育程度勞動者人數”、“中等教育程度勞動者人數”、“高等教育程度勞動者人數”以及“R&D人員全時當量”上具有較高載荷度。這些變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現存人力資本
的利用程度
(受過教育的人的勞動參與程度)。因此,我們將因子2命名為應用型人力資本。同理,因子3在“成人識字率”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具有較高載荷
度,因子4在“存活率”上具有較高載荷度,前者是地區全民教育情況(素質)的一種反映,后者則是地區居民普遍健康水平的反映。因此,我們分別將其命名為素質型人力資本和健康型人力資本。
另外,考察因子協方差矩陣發現,其非對角線上的數字均非常小(小于0.3)。說明所提取的四個因子基本解釋了各地區不同類型的人力資本,且不同類型人力資本之間相互補充。
三、各省人力資本水平及特點
1. 人力資本特點
對各省不同類型的人力資本度量結果排序,結果見表2。分析排序結果可見,我國省級地區的人力資本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學研型和應用型人力資本水平普遍較低,且兩者在各地區的分布狀況存在較大差異。在31個考察省份中,僅有10個省份的學研型人力資本和應用型人力資本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得分為正),而絕大多數省份(21個省份)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這說明,現階段我國大部分地區的教育、科技發展水平和創新能力較低,且對現存人力資本的利用不夠充分,這可能也是導致綜合人力資本水平普遍偏低的主要原因。與此同時,學研型人力資本和應用型人力資本的地區分布狀況差異較大。如在學研型人力資本上具有絕對優勢的北京、上海、天津三個省份,在應用型人力資本上卻存在劣勢,排在全國所有省的后半段,天津甚至排在最后一位;在學研型人力資本上處于絕對劣勢地位的河南,在應用型人力資本上卻表現出較大的優勢,位居全國第四。同樣的,在應用型人力資本上具有優勢,位列全國第一和第三的廣東、山東兩省,在學研型人力資本上也表現出一定的劣勢。
第二,素質型人力資本水平普遍較高的同時,健康型人力資本普遍較低且與經濟發展水平間存在一定程度的“U”型空間變化規律。絕大多數省份(19個省份)的素質型人力資本處于全國平均水平以上。在學研型人力資本和應用型人力資本水平上均表現平平的省份,如陜西、山西、湖北、河北等,在素質型人力資本上表現出了一定的相對優勢;在學研型人力資本和應用型人力資本水平處于劣勢地位的西部地區,如青海、貴州、云南以及西藏等省份,在素質型人力資本上同樣處于劣勢。與此同時,近2/3地區(18個省份)的健康型人力資本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說明我國的健康型人力資本水平普遍較低,即勞動者的健康狀況普遍較差;且健康型人力資本水平較高的地區往往是經濟最不發達(如寧夏、新疆、海南和西藏等)和最發達的地區(如廣東和北京等)。而在全國范圍內,大部分經濟發展水平處于中等水平的地區,如湖南、四川及河北等,其健康型人力資本水平較低。說明健康型人力資本與經濟發展水平間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U”型空間變化規律。
第三,人力資本綜合水平普遍較低,且與經濟水平具有空間同步性,與地區人口數量不成比例。近2/3地區(31個考察省份中有18個)的人力資本綜合得分為負,說明大部分地區的人力資本綜合水平普遍偏低。同時,經濟發展水平落后的地區通常人力資本綜合水平也較低。如寧夏、貴州、青海、甘肅和西藏等西部省份,其人力資本綜合得分均低于-0.5,處于全國省級地區的最低水平;而經濟發達的北京、上海、廣東及江蘇等東部沿海地區,其人力資本綜合得分均大于1,處于全國最高水平。這說明,人力資本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具有空間同步性。另外,人口大省,如四川、河南、山東等,在綜合人力資本水平上表現平平,說明作為人力資本載體的人口數量與人力資本水平之間沒有必然關系。
第四,我國各類型人力資本的省際結構差異較大。反映人力資本省際差異的數據(全距)顯示,四類型人力資本在省際差異程度上由高到低依次為:素質型、學研型、健康型、應用型,且各類型人力資本的差異程度均超過其最大得分值。這說明,我國人力資本的積累在地區間存在較為嚴重的失衡現象。
2. 原因分析
首先,教育、科技發展水平和創新能力、現有(完成一定人力資本積累的)勞動力的利用程度以及勞動力的健康水平較低,
即學研、應用以及健康型人力資本均普遍較低,是造成我國人力資本水平整體偏低的主要原因。其中學研型人力資本和應用型人力資本最為關鍵,因為教育、科技發展水平和創新能力是地區發展最為活躍的因素,也是貢獻人力資本總量積累最為關鍵的力量。同時,應用型人力資本則保證了人力資本存量的利用程度,一地區所蘊含的教育、科技以及創新能力再強,如果沒有將其充分利用起來,這種能力的作用也會逐漸喪失。另外,將各省按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進行排序,并就各地區內的學研型人力資本、人力資本綜合水平及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作圖(見圖1)顯示:學研型人力資本和人力資本綜合水平具有很強的空間同步性,而其他類型的人力資本(應用型、素質型和健康型)與人力資本綜合水平沒有明顯的類似關系(因而未給出相關圖形)。這說明,四種類型的人力資本中,學研型人力資本(即教育、科技發展水平和創新能力)是地區綜合人力資本的核心組成部分。人力資本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交互影響,且應用型人力資本整體偏低,說明以學研為核心的人力資本在大部分地區未充分發揮其增長作用,反過來是經濟增長對人力資本的影響更多,促進了教育科技發展、創新能力以及勞動者素質等方面的提升。這也是當前我國經濟主要依靠投資(即物質資本)增長,且增長水平與人力資本綜合水平具有空間同步趨勢的主要原因。正如圖1所示,相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力資本綜合水平整體較低,且兩者在空間上具有同步趨勢。
其次,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力資本間的交互影響可能是當前我國人力資本存在地域結構差異甚至失衡的主要原因。在新增長理論提出后,“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主要源泉”這一觀點被世人普遍接受。然而,與短期增長相比,人力資本的形成需要更長的時間和周期,即人力資本積累對經濟具有長期作用,而經濟增長對人力資本積累存在短期效應。我國當前省域間的人力資本結構差異主要體現在東部省區人力資本水平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這種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人力資本地域結構差異,正是源自改革開放初期東部沿海地區首先獲得經濟發展政策優勢后,其不斷增長的經濟與人力資本積累互動影響的結果。
最后,發展程度和模式的差異可能是健康型人力資本與經濟發展水平間存在空間“U”型規律、人力資本綜合水平與人口數量不成比例的原因。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和開發程度較低,因而環境污染和勞動者的工作壓力均較小,比較有益于勞動者的身體健康;發達地區的發展模式往往已經完成了或者部分完成了由資源和人力粗放消耗型向環境和健康友好型的轉變,加之這類地區的保健和醫療水平均較高,從而有利于勞動者的健康維護;而處于中等發展程度地區的政府,在發展過程中往往對勞動者健康、環境保護等方面的考量不夠,加之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提高其醫療保健水平,從而導致這類地區勞動者的健康水平較低。另外,增長模式的轉變可能是使得人力資本綜合水平與人口數量并不存在比例關系的主要原因。當前經濟增長方式已基本轉向依靠科技、人才等推動的集約型發展模式,這種發展模式更加倚重技能和知識等勞動者的質量因素,而對人口數量的依賴越來越少,這使得人力資本存量與作為其載體的人口數量間并不具備比例關系。
四、聚類分析
1. 數據處理與類別確定
為進一步分析人力資本的地域空間特征,本文使用上面得出的四個類型的人力資本指標,并引入相關政策變量來對各省級地區進行分層聚類分析。反映地區人力資本相關政策變化的指標為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以及在校師生比。它們分別反映了地方政府對教育的重視程度和人力資本投入力度。其中,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用財政教育支出/GDP代替,且其計算均值的數據區間為2007~2011年。散點圖和箱式圖反映樣本存在以下異常值:北京的學研型人力資本和人力資本綜合水平、在校師生比;上海和天津的學研型人力資本;廣東的應用型人力資本和健康型人力資本;寧夏的健康型人力資本;西藏的素質型人力資本和財政教育支出/GDP。文章給這些異常值重新賦值,具體賦予同其最接近的非異常值。同時,各變量相關系數均低于0.8的臨界值,說明它們之間沒有多重共線性。本文分別采用歐式距離平方和離差平方和對樣本進行親疏度和分層聚類分析。凝聚系數(見表3)和凝聚樹狀圖均顯示,31個考察省份按人力資本水平高低和政策情況應歸為四類,且各類地區在各類型人力資本及相關政策上存在顯著的差異(指標的統計特征見表4)。
2. 聚類結果與分析
為直觀起見,對聚類結果做數據地理圖,詳見圖2。圖2顯示:第一類地區主要為西北、西南邊疆省份。這類地區的各項人力資本得分均值(健康人力資本除外)均處于最低水平,且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四類地區中最小,因此,我們稱其為“落后地區”。落后地區的財政教育支出/GDP為四類地區中的最高水平。第二類地區集中在中西部省份。這類地區的各類型人力資本水平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均高于第一類地區,且低于后兩類地區。同時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我們稱其為“發展中地區”。發展中地區的學研、健康以及綜合人力資本得分均值都為負,說明這兩項人力資本均處于全國平均水平以下;應用型和素質型人力資本得分均值為正,說明這兩項人力資本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第三類地區以東北地區為主,這類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較第一、第二類地區有很大提高,且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我們稱其為“欠發達地區”。欠發達地區的綜合人力資本水平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一樣,也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第四類地區集中了東部和東南沿海省市,這類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高于其他三類地區,我們稱其為“發達地區”。其不論在人力資本綜合水平還是在各類型人力資本方面(素質型人力資本除外)均處于全國最高水平。此外,港澳臺地區由于缺乏數據未予歸類,在地圖中未填充顏色;釣魚島和南海諸島等中國領土由于比例尺原因在地圖中顯示得不夠清楚,敬請讀者諒解。
總體來看,在地域(即四類地區)空間范圍內,人力資本綜合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也存在同步變化關系,說明兩者可能存在交互作用,即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動力,反過來經濟增長也會以增加教育、科技投入等方式提高人力資本存量水平。追根溯源,改革開放政策帶來的發展契機在第四類至第一類地區間的先后時機差異,通過各自區域內經濟增長和人力資本的交互影響才是當前人力資本區域存在較大差異的主要原因。另外,財政教育支出/GDP從第一類至第四類地區依次遞減,而綜合人力資本卻依次遞增,且第二、第三類地區的在校師生比明顯高于第一、第二類地區的現象可能源于兩方面原因:第一,落后地區的地方政府了解其在人力資本存量水平上與發達地區的差距,并正在人力資本的投入和政策扶持上付出更多努力,以彌補這種差距,但這種投入和政策未見明顯效果;第二,落后地區較低的國內生產總值本身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其財政教育支出/GDP水平較高。另外,發達地區的地方政府在人力資本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上都小于落后地區,但其人力資本水平高于這些地區的事實說明,發達地區的人力資本積累可能更多地倚重于轄區居民(或勞動者)自我投資完成,屬于主體(居民、家庭或企業)主導型;而落后地區的人力資本積累則可能更多地倚重于政府投資,屬于政府主導型。但由于政府投資在人力資本形成機制上的低效率、掌握主體信息不充分以及投資盲目性等方面的原因,使得政府主導型的人力資本投資模式往往是無效的,相比之下,主體主導型更加有效。
五、結論與啟示
方法的合理性是人力資本測量準確,進而作為解釋變量來進一步研究相關問題的關鍵。以往學者對我國人力資本水平的衡量暗含著人力資本是一維變量的假說。此類做法會遺漏重要信息,加之相關替代指標的測量誤差,使人力資本的度量和對相關問題的解釋爭議較大。本文在借鑒以往測度方法和指標體系的基礎上,采用綜合法對我國省級地區的人力資本水平進行了多維度的度量,最終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我國省級地區的人力資本由學研型、應用型、素質型及健康型人力資本四部分構成,學研型、應用型、素質型以及健康型人力資本對地區人力資本綜合水平的貢獻依次遞減,且學研型、應用型、健康型人力資本水平均偏低的狀態是造成當前省際人力資本綜合水平整體偏低的原因。學研型人力資本,即教育、科技發展水平和創新能力是地區人力資本形成的核心要素,進而也是地區經濟發展的關鍵;人力資本積累的目的在于“用”,而應用型人力資本水平整體偏低說明,各地區對其現存人力資本的利用程度偏低,大部分省份存在人力資本的閑置和浪費;素質型人力資本水平雖整體較高,但因其對綜合人力資本的貢獻有限,從而與經濟增長水平無明顯的省際空間依賴關系。
第二,地區健康水平和人口數量與人力資本綜合水平不成比例。人口大省(如四川、河南、山東等)在人力資本綜合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方面表現平平;人口因素對地區人力資本綜合水平進而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力有限;同時,健康型人力資本水平呈現出在經濟最落后和最發達地區均較高的空間“U”型特征。
第三,我國省級地區可按人力資本水平和政策情況分為落后、發展中、欠發達和發達四類地區。四類地區在人力資本水平和政策方面存在顯著的空間差異。從第四類到第一類地區,其獲得改革開放政策優惠的先后時機差異在各自地區內通過經濟增長和人力資本間的交互作用,形成了當前我國地區間在人力資本和經濟發展水平方面的差異,即所謂的“發達”和“落后”之分。同時,各類型人力資本省際
失衡局面可能也源于此。另外,當前我國發達地區的人力資本投資偏向人力資本主體(個人、家庭或企業)主導,落后地區人力資本投資則偏向政府主導。相比之下,主體主導型的人力資本投資方式比政府主導型方式更有效。
上述結論啟示:我國經濟增長在長期依靠物質資本(投資)推動后,未來可能要更多地依靠人力資本的作用[21]。基于此,各地區要從學研、應用、素質以及健康四個方面來提高其人力資本綜合水平,以期在未來的發展中占據主動。落后地區自身首先要在其教育、科研發展以及創新能力的培育、人才的引進、轄區經濟主體(個人、家庭或企業)自身人力資本投資引導等方面多下工夫;其次要借鑒發達地區的經驗和教訓,在努力提高本地區勞動者質量,加速人力資本積累的同時,積極探究新的發展模式以避免經濟發展對環境和勞動者健康的損耗。與此同時,中央政府要在人力資本發展的政策和資金支持上向第一、第二類地區(即落后和發展中地區)傾斜,以縮小地區間發展差異。
參考文獻:
[1] Lucas Jr R.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1).
[2] 侯風云. 中國人力資本投資與城鄉就業相關性研究[M]. 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 2007: 31-36.
[3] 焦斌龍, 焦志明. 中國人力資本存量估算: 1978-2007[J]. 經濟學家, 2010, (9).
[4] 錢雪亞, 劉杰. 中國人力資本水平實證研究[J]. 統計研究, 2004, (3).
[5] 錢雪亞, 王秋實, 劉輝. 中國人力資本水平再估算: 1995-2005[J]. 統計研究, 2008, (12).
[6] Dublin, L. I., A. J. Lotka.The Money Value of a Man[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Nursing, 1930, 30(9).
[7] Mulligan, C. B., X.SalaiMartin. A Labor Incomebased Measure of the Value of Human Capital: An Application to the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J].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1997, 9(2).
[8]
[JP2]Jorgenson, D. W., B. M.Fraumeni. The Output of the Education Sector[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303-341.[JP]
[9] 朱平芳, 徐大豐. 中國城市人力資本的估算[J]. 經濟研究, 2007, (9).
[10] 李海崢, 梁赟玲, 劉智強, 王小軍. 中國人力資本測度與指數構建[J]. 經濟研究, 2010, (8).
[11] 嚴善平. 城市勞動力市場中的人員流動及其決定機制[J]. 管理世界, 2006, (8).
[12] 胡鞍鋼. 從人口大國到人力資本大國: 1980~ 2000 年[J]. 中國人口科學, 2002, (5).
[13] 賴明勇, 張新, 彭水軍, 包群. 經濟增長的源泉: 人力資本、研究開發與技術外溢[J]. 中國社會科學, 2005, (2).
[14] 楊建芳, 龔六堂, 張慶華. 人力資本形成及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一個包含教育和健康投入的內生增長模型及其檢驗[J]. 管理世界, 2006, (5).
[15] Dagum. C., D. J.Slottje. A New Method to Estimate the Level and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Human Capital with Application[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00, 11(1).
[16] Fldvári, P., B.Leeuwen. An Estimation of the Human Capital Stock in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J].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 2005, 43(6).
[17] Dagum, C., G.Vittadini, P.G. Lovaglio.Formative Indicators and Effects of a Causal Model for Household Human Capital with Application[J]. Econometric Reviews, 2007, 26(5).
[18] Klomp, J. The Measurement of Human Capital: A Multivariate Macroapproach[J]. Quality & Quantity, 2013, 47(1).
[19] Wansbeek, T.J.,E.Meijer.Measurement Error and Latent Variables in Econometrics[M].Amsterdam:Elsevier,2000.
[20] Lattin, J.M., Carroll,J.D., Green P.E. Analyzing Multivariate Data[M].Pacific Grove,CA,USA:Thomson Brooks/Cole,2003.
[21] 王詢, 孟望生. 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回報率關系研究[J]. 當代財經, 2013, (7).
第二,地區健康水平和人口數量與人力資本綜合水平不成比例。人口大省(如四川、河南、山東等)在人力資本綜合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方面表現平平;人口因素對地區人力資本綜合水平進而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力有限;同時,健康型人力資本水平呈現出在經濟最落后和最發達地區均較高的空間“U”型特征。
第三,我國省級地區可按人力資本水平和政策情況分為落后、發展中、欠發達和發達四類地區。四類地區在人力資本水平和政策方面存在顯著的空間差異。從第四類到第一類地區,其獲得改革開放政策優惠的先后時機差異在各自地區內通過經濟增長和人力資本間的交互作用,形成了當前我國地區間在人力資本和經濟發展水平方面的差異,即所謂的“發達”和“落后”之分。同時,各類型人力資本省際
失衡局面可能也源于此。另外,當前我國發達地區的人力資本投資偏向人力資本主體(個人、家庭或企業)主導,落后地區人力資本投資則偏向政府主導。相比之下,主體主導型的人力資本投資方式比政府主導型方式更有效。
上述結論啟示:我國經濟增長在長期依靠物質資本(投資)推動后,未來可能要更多地依靠人力資本的作用[21]。基于此,各地區要從學研、應用、素質以及健康四個方面來提高其人力資本綜合水平,以期在未來的發展中占據主動。落后地區自身首先要在其教育、科研發展以及創新能力的培育、人才的引進、轄區經濟主體(個人、家庭或企業)自身人力資本投資引導等方面多下工夫;其次要借鑒發達地區的經驗和教訓,在努力提高本地區勞動者質量,加速人力資本積累的同時,積極探究新的發展模式以避免經濟發展對環境和勞動者健康的損耗。與此同時,中央政府要在人力資本發展的政策和資金支持上向第一、第二類地區(即落后和發展中地區)傾斜,以縮小地區間發展差異。
參考文獻:
[1] Lucas Jr R.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1).
[2] 侯風云. 中國人力資本投資與城鄉就業相關性研究[M]. 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 2007: 31-36.
[3] 焦斌龍, 焦志明. 中國人力資本存量估算: 1978-2007[J]. 經濟學家, 2010, (9).
[4] 錢雪亞, 劉杰. 中國人力資本水平實證研究[J]. 統計研究, 2004, (3).
[5] 錢雪亞, 王秋實, 劉輝. 中國人力資本水平再估算: 1995-2005[J]. 統計研究, 2008, (12).
[6] Dublin, L. I., A. J. Lotka.The Money Value of a Man[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Nursing, 1930, 30(9).
[7] Mulligan, C. B., X.SalaiMartin. A Labor Incomebased Measure of the Value of Human Capital: An Application to the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J].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1997, 9(2).
[8]
[JP2]Jorgenson, D. W., B. M.Fraumeni. The Output of the Education Sector[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303-341.[JP]
[9] 朱平芳, 徐大豐. 中國城市人力資本的估算[J]. 經濟研究, 2007, (9).
[10] 李海崢, 梁赟玲, 劉智強, 王小軍. 中國人力資本測度與指數構建[J]. 經濟研究, 2010, (8).
[11] 嚴善平. 城市勞動力市場中的人員流動及其決定機制[J]. 管理世界, 2006, (8).
[12] 胡鞍鋼. 從人口大國到人力資本大國: 1980~ 2000 年[J]. 中國人口科學, 2002, (5).
[13] 賴明勇, 張新, 彭水軍, 包群. 經濟增長的源泉: 人力資本、研究開發與技術外溢[J]. 中國社會科學, 2005, (2).
[14] 楊建芳, 龔六堂, 張慶華. 人力資本形成及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一個包含教育和健康投入的內生增長模型及其檢驗[J]. 管理世界, 2006, (5).
[15] Dagum. C., D. J.Slottje. A New Method to Estimate the Level and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Human Capital with Application[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00, 11(1).
[16] Fldvári, P., B.Leeuwen. An Estimation of the Human Capital Stock in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J].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 2005, 43(6).
[17] Dagum, C., G.Vittadini, P.G. Lovaglio.Formative Indicators and Effects of a Causal Model for Household Human Capital with Application[J]. Econometric Reviews, 2007, 26(5).
[18] Klomp, J. The Measurement of Human Capital: A Multivariate Macroapproach[J]. Quality & Quantity, 2013, 47(1).
[19] Wansbeek, T.J.,E.Meijer.Measurement Error and Latent Variables in Econometrics[M].Amsterdam:Elsevier,2000.
[20] Lattin, J.M., Carroll,J.D., Green P.E. Analyzing Multivariate Data[M].Pacific Grove,CA,USA:Thomson Brooks/Cole,2003.
[21] 王詢, 孟望生. 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回報率關系研究[J]. 當代財經, 2013, (7).
第二,地區健康水平和人口數量與人力資本綜合水平不成比例。人口大省(如四川、河南、山東等)在人力資本綜合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方面表現平平;人口因素對地區人力資本綜合水平進而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力有限;同時,健康型人力資本水平呈現出在經濟最落后和最發達地區均較高的空間“U”型特征。
第三,我國省級地區可按人力資本水平和政策情況分為落后、發展中、欠發達和發達四類地區。四類地區在人力資本水平和政策方面存在顯著的空間差異。從第四類到第一類地區,其獲得改革開放政策優惠的先后時機差異在各自地區內通過經濟增長和人力資本間的交互作用,形成了當前我國地區間在人力資本和經濟發展水平方面的差異,即所謂的“發達”和“落后”之分。同時,各類型人力資本省際
失衡局面可能也源于此。另外,當前我國發達地區的人力資本投資偏向人力資本主體(個人、家庭或企業)主導,落后地區人力資本投資則偏向政府主導。相比之下,主體主導型的人力資本投資方式比政府主導型方式更有效。
上述結論啟示:我國經濟增長在長期依靠物質資本(投資)推動后,未來可能要更多地依靠人力資本的作用[21]。基于此,各地區要從學研、應用、素質以及健康四個方面來提高其人力資本綜合水平,以期在未來的發展中占據主動。落后地區自身首先要在其教育、科研發展以及創新能力的培育、人才的引進、轄區經濟主體(個人、家庭或企業)自身人力資本投資引導等方面多下工夫;其次要借鑒發達地區的經驗和教訓,在努力提高本地區勞動者質量,加速人力資本積累的同時,積極探究新的發展模式以避免經濟發展對環境和勞動者健康的損耗。與此同時,中央政府要在人力資本發展的政策和資金支持上向第一、第二類地區(即落后和發展中地區)傾斜,以縮小地區間發展差異。
參考文獻:
[1] Lucas Jr R.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1).
[2] 侯風云. 中國人力資本投資與城鄉就業相關性研究[M]. 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 2007: 31-36.
[3] 焦斌龍, 焦志明. 中國人力資本存量估算: 1978-2007[J]. 經濟學家, 2010, (9).
[4] 錢雪亞, 劉杰. 中國人力資本水平實證研究[J]. 統計研究, 2004, (3).
[5] 錢雪亞, 王秋實, 劉輝. 中國人力資本水平再估算: 1995-2005[J]. 統計研究, 2008, (12).
[6] Dublin, L. I., A. J. Lotka.The Money Value of a Man[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Nursing, 1930, 30(9).
[7] Mulligan, C. B., X.SalaiMartin. A Labor Incomebased Measure of the Value of Human Capital: An Application to the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J].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1997, 9(2).
[8]
[JP2]Jorgenson, D. W., B. M.Fraumeni. The Output of the Education Sector[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303-341.[JP]
[9] 朱平芳, 徐大豐. 中國城市人力資本的估算[J]. 經濟研究, 2007, (9).
[10] 李海崢, 梁赟玲, 劉智強, 王小軍. 中國人力資本測度與指數構建[J]. 經濟研究, 2010, (8).
[11] 嚴善平. 城市勞動力市場中的人員流動及其決定機制[J]. 管理世界, 2006, (8).
[12] 胡鞍鋼. 從人口大國到人力資本大國: 1980~ 2000 年[J]. 中國人口科學, 2002, (5).
[13] 賴明勇, 張新, 彭水軍, 包群. 經濟增長的源泉: 人力資本、研究開發與技術外溢[J]. 中國社會科學, 2005, (2).
[14] 楊建芳, 龔六堂, 張慶華. 人力資本形成及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一個包含教育和健康投入的內生增長模型及其檢驗[J]. 管理世界, 2006, (5).
[15] Dagum. C., D. J.Slottje. A New Method to Estimate the Level and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Human Capital with Application[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00, 11(1).
[16] Fldvári, P., B.Leeuwen. An Estimation of the Human Capital Stock in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J].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 2005, 43(6).
[17] Dagum, C., G.Vittadini, P.G. Lovaglio.Formative Indicators and Effects of a Causal Model for Household Human Capital with Application[J]. Econometric Reviews, 2007, 26(5).
[18] Klomp, J. The Measurement of Human Capital: A Multivariate Macroapproach[J]. Quality & Quantity, 2013, 47(1).
[19] Wansbeek, T.J.,E.Meijer.Measurement Error and Latent Variables in Econometrics[M].Amsterdam:Elsevier,2000.
[20] Lattin, J.M., Carroll,J.D., Green P.E. Analyzing Multivariate Data[M].Pacific Grove,CA,USA:Thomson Brooks/Cole,2003.
[21] 王詢, 孟望生. 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回報率關系研究[J]. 當代財經, 2013,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