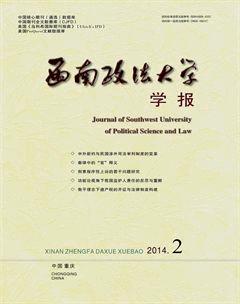商事仲裁庭組成程序的異化與修正
譚立
摘 要:當事人合意選擇仲裁員組成仲裁庭,是商事仲裁的特色之一。在仲裁實踐中,由于仲裁規則的設置有利于申請人,組庭程序從選擇雙方共同信任的仲裁員異化為排除己方不信任的仲裁員。筆者試圖運用博弈論的方法,從孤立博弈和序貫博弈角度分析組庭程序中當事人的行為,在分析名單法、邊裁選定首席仲裁員方法的基礎上提出組庭程序的意見和建議。
關鍵詞:商事仲裁;組庭程序;博弈論;名單法;邊裁選定首席仲裁員方法
中圖分類號:DF75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4.02.11
《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以下簡稱《仲裁法》)第30條規定:“仲裁庭可以由三名仲裁員或者一名仲裁員組成。由三名仲裁員組成的,設首席仲裁員。”這意味著我國的仲裁庭可以有兩種方式:三人庭和獨任庭,這種規定排除了當事人要求組成偶數仲裁庭以及超過三人奇數仲裁庭的選擇[1]。仲裁庭的組成方式有三種:當事人選定、仲裁機構指定和仲裁員選定。我國國內仲裁規則一般指向前兩種方式,第三種方式主要是三人庭中首席仲裁員的選擇方法。這種方式在國際上比較普遍,德國、瑞典、新加坡、我國臺灣地區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席仲裁員都可以通過這種方式產生[2]。
但在仲裁實踐中,組庭程序逐步偏離了原有的價值取向,異化為雙方當事人博弈的結果。本文通過歸納這些異化表現,運用博弈論分析當事人的行為,在分析名單法、邊裁選擇首席仲裁員規則的基礎上,擬提出合理的組庭規則。
一、仲裁庭組成程序的異化仲裁源于對仲裁員的信任與選擇。無論是古希臘雅典城邦的公共仲裁人、私人仲裁員,還是古代中國民間調解息訟的“中人”,都是德高望重、當事人信服的代表。長期以來,仲裁員的選擇建立在“由雙方信服的人解決爭議”這一基本前提之上,然而,在仲裁實踐中,爭議當事人已經不再以選擇信任的仲裁員為首要目的,組庭程序已經異化為排除不信任仲裁員為首要目的。下面區分不同情況說明這種異化的表現:
(一)獨任庭組成程序的異化
獨任庭組成程序的異化是最明顯、最徹底的異化,僅有的一個仲裁員名額是導致異化的根本原因。仲裁理論認為,雙方當事人合意選擇是最好的選擇,在當事人雙方無法達成一致時,可以由仲裁機構為其指定一名仲裁員。然而,在仲裁實踐中,由于爭議的實際存在,當事人達成選擇同一名仲裁員的合意常常是一種奢望。既然無法直接實現自己的選擇,排除對自己不利的選擇顯然是當事人的最優策略。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可以分析雙方當事人在不同情形的博弈行為:
假設前提:仲裁員名冊中只有5名仲裁員,分別為A、B、C、D、E。申請人信任的仲裁員為A,被申請人信任的仲裁員為B。
假設情形1:雙方按照己方的信任向仲裁機構提交了仲裁員選定結果。仲裁機構發現雙方無法在仲裁庭組成問題上達成一致,為了保證相對公平,仲裁機構排除了雙方的選擇。在C、D、E之間任意指定,結果為雙方當事人指定了仲裁員E。
假設情形2:申請人不希望選擇C作為仲裁員,故向仲裁機構表示選擇仲裁員C。同時,被申請人選擇其信任的仲裁員B。仲裁機構發現雙方無法在組庭問題上達成一致,為了保證相對公平,仲裁機構排除雙方選擇,在A、D、E之間任意指定。仲裁機構指定A作為仲裁員的概率為33.3%,指定B作為仲裁員的概率為0。
假設情形3:申請人不希望選擇C作為仲裁員,故向仲裁機構表示選擇仲裁員C。被申請人不希望選擇D為仲裁員,故向仲裁機構表示選擇仲裁員D。仲裁機構發現雙方無法在組庭問題上達成一致,為了保證相對公平,仲裁機構排除雙方選擇,在A、B、E之間任意指定。仲裁機構指定A或者B擔任仲裁員的概率均為33.3%。
假設情形4:申請人與被申請人均不希望選擇C為仲裁員,故都向仲裁機構表示選擇C為仲裁員。仲裁機構收到雙方選定結果后,認為雙方已經達成一致意見,認可C作為案件的仲裁員。申請人與被申請人均得到了最壞的結果。
西南政法大學學報譚 立:商事仲裁庭組成程序的異化與修正——基于博弈論的分析以上4種假設情形反映了獨任仲裁庭組成程序的異化過程。基于假設情形1,雙方當事人均按仲裁理論倡導的組庭價值行事,結果并未獲得利益最大化。基于假設情形2,申請人違背組庭價值的行為為其獲得了優勢。基于假設情形3,雙方當事人均違背組庭價值,獲得了同等優勢。假設情形4是雙方當事人均違背組庭價值行為可能產生的風險,但雙方當事人面臨的風險是相同的。任何理智的人均會在假設情形2、3、4中選擇。事實上,仲裁機構的仲裁員名冊動輒上百,甚至幾百,與假設情形的5名仲裁員不同,這意味著假設情形4在理論上存在,但實際發生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以選擇信任為借口排除不利于自己的仲裁員,成為當事人的首選。獨任仲裁庭受限于一名仲裁員,是異化最為徹底的情況。
(二)三人仲裁庭組成程序的異化
從當事人的選擇策略來看,三人庭的組成與獨任庭基本相同。當事人選擇兩名仲裁員,一名普通仲裁員,一名首席仲裁員。根據仲裁理論,仲裁機構一般會尊重當事人對于普通仲裁員的選擇,只要該選擇不違反正當程序的基本原則[3]。如果當事人對首席仲裁員的選擇無法達成一致,由仲裁機構為其指定一名仲裁員擔任首席仲裁員。這種方式對當事人選擇普通仲裁員考慮了意思自治,選擇首席仲裁員強調了雙方當事人合意的重要性。但在實踐中,當事人對首席仲裁員的選擇,將重復獨任庭的選擇策略,排除不利于自己的仲裁員擔任首席仲裁員是主要的異化表現。
此外,由于仲裁機構對當事人關于首席仲裁員與普通仲裁員的選擇區別對待,仲裁機構不得不干預當事人作出某種共同選擇。《仲裁法》第31條規定:“當事人約定由三名仲裁員組成仲裁庭的,應當各自選定或者各自委托仲裁委員會主任指定一名仲裁員,第三名仲裁員由當事人共同選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員會主任指定。第三名仲裁員是首席仲裁員。”各仲裁機構根據《仲裁法》的規定,都對首席仲裁員與普通仲裁員的選擇作了區分。從經濟分析角度來看,首席仲裁員與普通仲裁員的區分是有實際意義的,有利于裁決結果的最終作出,避免仲裁庭意見出現相互制衡的局面。但這種區分可能使申請人與被申請人選擇共同信任的仲裁員,由于雙方對該仲裁員的作用定位不同和仲裁員選擇程序上的“缺位”,導致雙方當事人必須重新作出選擇。
以上兩種異化情形可以表現為:
假設情形5:雙方分別選擇A、B作為普通仲裁員。申請人不愿意選擇C為首席仲裁員,被申請人不愿意選擇D為首席仲裁員。根據上述分析,雙方分別向仲裁機構表示選擇C和D作為首席仲裁員候選人。仲裁機構考慮到雙方意愿不一致,指定E作為爭議案件的首席仲裁員。
假設情形6:申請人選擇A作為普通仲裁員,B作為首席仲裁員。被申請人選擇B為普通仲裁員,D為首席仲裁員。此時,仲裁機構面臨3種選擇:第一,B為雙方共同選定的仲裁員,理應成為仲裁庭組成人員,并應作為首席仲裁員。第二,B盡管是雙方選定,但雙方對B的功能定位并不一致,B應當作為被申請人選擇的普通仲裁員。第三,B盡管為雙方選定,但雙方對B的功能定位并不一致,為了避免當事人的異議,要求當事人重新選擇其他仲裁員。
假設情形5是仲裁實踐的常態,其基本原理與獨任庭的組成基本一致,這里不再分析。
假設情形6是三人仲裁庭組成程序的特殊情形。仲裁機構的上述3種選擇都存在難以解決的問題:(1)針對第一種選擇,申請人的選擇全部得到了實現,利益得到了最大保證。被申請人選擇B為普通仲裁員,即希望B能在仲裁過程中表現一定的傾向性;但B作為首席仲裁員,任何傾向性都是不允許的。(2)針對第二種選擇,申請人必然存在異議,并可能在隨后的仲裁程序中利用該問題拖延仲裁程序。一旦申請人無法接受B表現出對被申請人意見的傾向性,就有可能以組庭存在瑕疵為由要求重新組庭,或者申請撤銷仲裁裁決。(3)第三種選擇或許是最無奈的選擇,當事人已經作出了意思表示,仲裁機構對意思表示進行了干預。組庭規則在此情形下的“缺位”顯露無疑。
筆者認為,首席仲裁員與普通仲裁員的區分是為了裁決意見的作出和仲裁庭內部的協調,當事人在選擇仲裁員時不應當區分兩者增加并認為某一仲裁員比另一仲裁員更具裁判和協調相互關系的能力。這也是某些仲裁員不愿意擔任普通仲裁員,只愿意擔任獨任仲裁員和首席仲裁員的原因之一。
(三)多個當事人組庭程序的異化
本文并不討論仲裁第三人的合理性問題,但不得不承認的是,缺少仲裁第三人制度確實給仲裁庭的組成造成了實際影響。在仲裁實踐中,一方面存在多方合同當事人,另一方面仲裁案件僅僅存在兩方當事人:申請人與被申請人。這種不匹配的現象是造成此類案件組庭程序異化的根本原因。
多個申請人的現象較為少見,通常是發生在申請人之間具有親屬關系或者婚姻關系的情形。一旦多個當事人分別具有不同的仲裁請求,將各自向被申請人提起仲裁,而非與其他當事人聯合提起仲裁。相反,一個仲裁申請人、多個被申請人的情形較為常見。一個當事人對多個當事人存在不同的仲裁請求,只要各個仲裁請求之間具有相關性,出于經濟因素的考慮,當事人將在一個仲裁案件中提出請求。
一個申請人、多個被申請人組庭程序的異化表現在:被申請人基本沒有可能實現自己的選擇,只能由仲裁機構指定普通仲裁員和首席仲裁員。這種異化可以用如下假設情形表現:
假設前提:仲裁員名冊中只有10名仲裁員,分別為A、B、C、D、E、F、G、H、I、J。爭議案件采用普通程序,組成三人庭審理案件。
假設情形7:申請人信任的仲裁員為A,不信任的仲裁員為C。第一被申請人信任的仲裁員為B,不信任的仲裁員為E。第二被申請人信任的仲裁員為D,不信任的仲裁員為F。三名當事人按照自己的偏好向仲裁機構遞交了普通仲裁員選定書,均選擇不信任的仲裁員擔任首席仲裁員。
仲裁機構審查之后,根據仲裁規則,A作為申請人信任的仲裁員,當然成為仲裁庭組成人員之一。被申請人一方盡管有兩人,但該兩名被申請人未就仲裁員人選達成一致意見。為了公平起見,排除B、D作為仲裁庭組成人員。在首席仲裁員的選擇上,由于被申請人內部無法達成一致意見,視為未選定首席仲裁員,按照仲裁規則應當由仲裁機構為案件指定首席仲裁員。同樣,為了公平起見,排除C、E、F作為首席仲裁員的人選,仲裁機構必須在G、H、I、J之間選擇。最終,仲裁機構選擇G作為普通仲裁員,I作為首席仲裁員,與A一起組成三人庭審理該案件。被申請人只實現了其排除不信任仲裁員的目的,而申請人不僅實現了這個目的,還成功地將己方信任的仲裁員送入仲裁庭。
假設情形8:申請人信任的仲裁員為A,不信任的仲裁員為C。第一被申請人信任的仲裁員為A,不信任的仲裁員為E。第二被申請人信任的仲裁員為D,不信任的仲裁員為F。三名當事人按照自己的偏好向仲裁機構遞交了普通仲裁員選定書,均選擇不信任的仲裁員擔任首席仲裁員。
仲裁機構審查之后,首先審查被申請人一方的仲裁員選擇情況,兩位被申請人均未就普通仲裁員、首席仲裁員的選擇達成一致意見,故仲裁庭的人選排除A、D。由于申請人選擇A為普通仲裁員,考慮到對后續程序的影響,仲裁機構將告知申請人重新選擇仲裁員,排除A作為普通仲裁員人選。申請人最終重新選擇B作為其信任的仲裁員。在首席仲裁員的選擇上,被申請人內部無法達成一致意見,視為未作選擇,根據仲裁規則,由仲裁機構為當事人指定首席仲裁員。出于公平考慮,仲裁機構排除了C、E、F。最終,仲裁庭指定B、G、I作為仲裁庭組成人員,其中I為首席仲裁員。在這種情形下,申請人與第一被申請人具有共同信任的仲裁員人選,但是由于仲裁規則的因素,仲裁機構進行了干預,申請人與被申請人均未能實現其選擇。然而,申請人仍然在此種情形下具有優勢,仲裁員B盡管不是其第一選擇,卻是其真正的意思表示。
假設情形9:申請人信任的仲裁員為A,不信任的仲裁員為C。第一被申請人信任的仲裁員為B。第二被申請人信任的仲裁員為D。兩名被申請人均信任仲裁員E,并一致選擇E為首席仲裁員。三名當事人向仲裁機構遞交了仲裁員選定書。
仲裁機構審查之后,首先審查被申請人一方的仲裁員選擇情況。兩名被申請人并未就普通仲裁員的選擇達成一致意見,故由仲裁機構為其指定。出于公平原則,排除B、D作為普通仲裁員人選。兩名被申請人就首席仲裁員的選擇達成一致意見,故仲裁機構認可E為被申請人首席仲裁員的選擇。A作為申請人的選擇,當然成為仲裁庭組成人員之一。但是,E并非申請人與被申請人的共同選擇,故由仲裁機構為其指定首席仲裁員。同樣出于公平原則,排除E、C作為首席仲裁員的人選。最終,仲裁機構指定A、F、I組成仲裁庭審理本案,其中I為首席仲裁員。在此情形中,盡管被申請人一方具有相同的選擇,組庭時也無法實現。申請人仍然具有優勢,A作為其第一選擇進入仲裁庭,排除了己方不信任的仲裁員C,并且排除了兩名被申請人共同選擇的E。
假設情形10:申請人信任的仲裁員為A,不信任的仲裁員為C。兩名被申請人信任的仲裁員為B。第一被申請人不信任的仲裁員為D,第二被申請人不信任的仲裁員為E。三名當事人按照自己的偏好向仲裁機構遞交了普通仲裁員選定書,均選擇不信任的仲裁員擔任首席仲裁員。
仲裁機構審查之后,首先審查被申請人一方的仲裁員選擇情況。被申請人共同選擇B作為普通仲裁員,仲裁機構予以尊重。被申請人未就首席仲裁員的選定達成一致意見,故由仲裁機構指定首席仲裁員。A作為申請人的選擇,當然成為仲裁庭組成人員之一。仲裁機構最終指定仲裁員I作為首席仲裁員,與A、B一起組成仲裁庭審理本案。或許只有在此種情形之下,被申請人才占據部分優勢,B作為兩者的第一選擇進入仲裁庭,并排除了兩名不受信任的仲裁員。申請人的第一選擇A進入仲裁庭,僅排除了一名不受信任的仲裁員。
總結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有兩名被申請人的情況下,仲裁庭組成程序的內核是傾向于申請人的。即使在假設情形10,被申請人可能獲得些微優勢,但從總體組庭情形占比、仲裁實踐中爭議復雜化以及利益個人化的趨勢來看,假設情形10發生的概率是極低的。
在仲裁實踐中,這種組庭程序的異化常常被人為利用,用于增強申請人的優勢地位。特別是在居間合同爭議中,申請人愿意以居間費用換取居間人作為被申請人參與仲裁活動,從側面“幫助”申請人證明被申請人的違約行為。居間人作為被申請人之一,在組庭程序中擁有選擇的權利,可以打亂被申請人的組庭安排。與作為證人參與仲裁活動相比,居間人作為被申請人擁有更多發言的權利,可以不限于仲裁庭以及爭議當事人的提問,從而全面充分地表述自己的意見,如此一來,申請人的優勢地位更為增強。
二、組庭程序的嵌套博弈分析通過上文對申請人與被申請人之間博弈行為和博弈結果的分析可以看出,既然申請人在組庭程序中占據了較大優勢地位,無論被申請人采用何種策略,一定處于弱勢地位。因此,被申請人選擇不配合,將是其最節省爭議解決成本的策略。然而,在實踐中,無論當事人雙方是否屬于真正意義上的“理性人”,在仲裁程序的初期,基本上都會采取合作策略。這與理性人的利己意愿是相悖的,采用合作的方法甚至會在一定程度上傷害己方利益。造成這種悖論的原因,需要運用“嵌套博弈”理論,將這種看似不理性的博弈行為放置在整個仲裁博弈的環節,即可以找出當事人行為的原因。
所謂嵌套博弈(nested game),是指人們的互動行為與決策不是某個孤立博弈的結果,而是受到他們所處的更大范圍的關系與結構的影響,即該博弈可能嵌套于某個大博弈之中,從而產生了不同于單個博弈的均衡結果[4]。嵌套博弈可以用于說明經濟活動與其他社會活動的相關性,也可以用于解釋一系列序貫博弈活動中博弈人某一行為異常的原因。嵌套博弈是新制度經濟學思想的體現,格蘭諾維特教授(Granovetter)研究過經濟活動的社會嵌入性(social embeddedness),認為經濟行為和經濟制度不是孤立運行的,都要受到社會關系的約束。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主要研究獨立的、非社會化的人類行為,只是繼承了功利主義的傳統。這些理論通過假設而忽略了社會結構及社會關系對生產、分配和消費的影響,因而不能合理地解釋一些社會問題,必須研究人類行為對抗性的大環境以及小環境的交互性[5]。
從整個仲裁程序來看,申請人與被申請人處于整個程序的母博弈之中,仲裁庭組成程序只是其子博弈的一部分,嵌套在整個程序的博弈之中。雖然申請人在仲裁中處于主動地位,被申請人一直處于被動防守地位,且仲裁規則本身對申請人是有利的,但申請人要想在組庭階段即獲得最大利益,將面臨被申請人的報復:退出仲裁活動,或者不配合仲裁程序之推進。無論是上述哪一種情況,對申請人在整個仲裁活動中追求的利益都是一種拖累。嵌套博弈中的“蜈蚣博弈悖論”[6](centipede game)可以直觀地表現以上活動。“蜈蚣博弈悖論”是羅森塞爾(Rosenthal)在1981年提出的一個動態博弈問題,運用逆推法論證了人們在博弈活動中對預期利益的期望將導致行為偏離經濟性。由于其博弈擴展形式經過展開之后形似蜈蚣,故又被稱為“蜈蚣博弈”。
整個仲裁程序的推進符合“蜈蚣博弈”的前提。申請人與被申請人在整個仲裁程序中輪流進行策略選擇,而可供選擇的策略只有合作與不合作兩種。由于申請人是仲裁程序的發起者,被申請人的決策選擇將直接關系到程序推進的效率。我們可以用下圖來表現雙方當事人在子博弈中的利益:
圖1:組庭程序中的博弈形式
如上圖,博弈從左至右進行,橫向連桿代表合作策略,向下的連桿代表不合作策略。每方下面對應的括號代表相應的人采取不合作策略,博弈結束后各自的收益,括號內左邊的數字代表被申請人的收益,右邊代表申請人的收益。由于申請人在組庭環節占有優勢地位,被申請人如果選擇不合作,雙方收益為(1,1)。如果被申請人合作,雙方收益為(0,5),顯然,被申請人選擇不合作的可能性增大。為了使被申請人選擇合作,申請人就會獲得更大的收益,申請人需要放棄部分收益,增強被申請人對仲裁庭公正處理爭議的信心,才能使博弈繼續。我們假設,申請人主動調整收益為(0,3),如下圖所示:
圖2:申請人調整收益后的博弈形式
如此一來,申請人的收益就會降低到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結合當事人尋求爭議解決的意愿,被申請人愿意通過“賭博”來配合申請人進行仲裁活動,繼續推進仲裁程序。組庭程序就被嵌套入整個仲裁程序,申請人利用被申請人在仲裁程序開始階段信息掌握不均衡、信息量少的劣勢,通過降低自身收益行為,吸引被申請人選擇合作策略,最終形成“蜈蚣博弈”的完整形態。
圖3:仲裁當事人的完整蜈蚣博弈展開形式
上圖嵌套了所有仲裁程序的博弈形式:隨著被申請人逐步選擇配合申請人的活動,雙方當事人的活動收益均在增大,但申請人占有仲裁規則優勢本節博弈分析收益均為符合基本收益傾向的假設值,只用于說明一般情形下申請人收益要相對大于被申請人收益的情形。,可以獲得比被申請人更多的收益。申請人讓步利益越大,被申請人越能夠與申請人合作,仲裁程序推進的階段越向裁決靠近,申請人的收益越大。在“蜈蚣博弈”中,由于申請人與被申請人利益的相關性,最終無法達到(10,10)的利益均衡,被申請人會在某一階段,如收益為(8,8)時,選擇不合作策略,保護當時的既得利益。程序的推進最終將依靠仲裁庭的強制裁決。
由此可見,被申請人從程序開始階段即選擇不配合,是降低申請人活動收益的最優決策。申請人在組庭階段主動放棄部分利益,尋求被申請人的合作,是擴大己方收益的有效手段。被申請人應當及時衡量己方收益,及時選擇不合作策略以對抗申請人。
三、仲裁庭組成程序的建議除了上面從孤立博弈行為和序貫博弈行為分析當事人行為的經濟性以外,我們還需要考量仲裁機構在仲裁程序推進中的作用。作為仲裁規則的制定者,仲裁機構并不直接參與當事人之間的博弈行為,然而,由于仲裁并不實施地域管轄,仲裁機構之間存在廣泛競爭,這種競爭是規則設置上的競爭。仲裁規則過分偏向一方當事人導致的不公平,將會影響爭議當事人的選擇。既然在規則的束縛下被申請人無法通過自己的決策行為實現利益最大化,那么在多次博弈失敗之后,被申請人將直接選擇拒絕合作的策略,以拖延仲裁程序。被申請人因此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將引導被申請人在下次爭議發生時選擇其他仲裁機構,甚至放棄仲裁手段。
因此,從仲裁機構的角度來講,調整組庭程序、保證規則上的基本公正是最優選擇。削弱申請人一方的優勢,應該成為仲裁庭組成程序關注的重點。從這個意義上講,仲裁規則應當盡力尋求當事人真實的意思表示,盡力促進雙方合意的形成,回歸仲裁的基本價值取向。
仲裁庭的組庭程序設置,除了仲裁機構指定之外,還有另外兩種方式受到了學者的關注:一種是“名單法”(list system),另一種是由邊裁選擇首席仲裁員[7]。
(一)名單法
所謂名單法,是指各方當事人編制一份名單,列上3至4名可以接受的仲裁員。之后,這份名單在當事人之間互相交換,以求達成一致[8]。
目前,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北京仲裁委員會已經開始使用這種方式。《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25條規定:“雙方當事人可以各自推薦一至五名候選人作為首席仲裁員人選,并按照上述第(二)款規定的期限提交推薦名單。雙方當事人的推薦名單中有一名人選相同的,該人選為雙方當事人共同選定的首席仲裁員;有一名以上人選相同的,由仲裁委員會主任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在相同人選中確定一名首席仲裁員,該名首席仲裁員仍為雙方共同選定的首席仲裁員;推薦名單中沒有相同人選的,由仲裁委員會主任指定首席仲裁員。”第26條規定:“仲裁庭由一名仲裁員組成的,按照本規則第二十五條第(二)、(三)、(四)款規定的程序,選定或者指定獨任仲裁員。”
《北京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18條第2款規定:“雙方當事人應當自被申請人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15日內共同選定或者共同委托主任指定首席仲裁員。雙方當事人也可以在上述期限內,各自推薦一至三名仲裁員作為首席仲裁員人選;經雙方當事人申請或者同意,本會也可以提供五至七名首席仲裁員候選名單,由雙方當事人在第(一)款規定的期限內從中選擇一至三名仲裁員作為首席仲裁員人選。推薦名單或者選擇名單中有一名相同的,為雙方當事人共同選定的首席仲裁員;有一名以上相同的,由主任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在相同人選中確定,確定的仲裁員仍為雙方當事人共同選定的首席仲裁員;推薦名單或者選擇名單中沒有相同的人選,由主任在推薦名單或者選擇名單之外指定首席仲裁員。”第48條規定:“雙方當事人應當自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10日內在仲裁員名冊中共同選定或者共同委托主任指定獨任仲裁員。選擇獨任仲裁員時,可以適用本規則第十八條第(二)款規定的方式。”
在實踐中,考慮到國外臨時仲裁的存在,名單法有兩種變化形式:當事人提供推薦名單和仲裁機構提供推薦名單。在仲裁機構提供推薦名單的方式中,還存在兩種分支:當事人在仲裁機構提供的推薦名單中選擇信任的仲裁員;當事人在仲裁機構提供的推薦名單中排除不信任的仲裁員。
從規則進化程度來看,內容越豐富、越完善、變化越多的規則體現了人們對其發展可能性和必要性的肯定。仲裁機構提供推薦名單顯然得到了大部分當事人的支持。當事人提供推薦名單盡管為雙方正在尋求的仲裁員類型指向具有幫助意義,為仲裁機構的指定奠定了基礎,但這種方式由于選擇范圍過廣,雙方當事人選擇出共同仲裁員的概率很小。仲裁機構為當事人提供推薦名單,縮小了當事人尋找的范圍,有利于共同選擇的形成。為了排除仲裁機構提供名單的人為因素,部分在線仲裁項目甚至無視仲裁員回避、利益沖突等問題,采用隨機方法[9](rotational method) 抽取仲裁員組成名單以供當事人選擇。
對陌生人的信任程度直接決定著當事人的行為,這是在仲裁機構提供的名單中選擇信任仲裁員與排除不信任仲裁員形成的直接心理因素。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和北京仲裁委員會都采取了在名單中選擇信任仲裁員的方法,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仲裁員本身就是值得信任的群體。國內仲裁均為機構仲裁,《仲裁法》對仲裁員的資質和品德均提出了要求:仲裁員均為品德高尚的專業人士。在名單中選擇信任的仲裁員,意味著仲裁機構提供的仲裁員名單為更符合爭議性質的優秀仲裁員,爭議當事人只有信任與更信任的區別。如果排除不信任仲裁員,意味著仲裁機構提供的名單中含有不符合當事人要求的仲裁員。這些仲裁員之所以被排除,或者是專業原因,或者是道德品質原因。這本身與《仲裁法》關于仲裁員能力與品德的要求不匹配。
第二,組庭的本質是選擇當事人信任的仲裁員。盡管在仲裁實踐中爭議當事人囿于仲裁規則的設置并非如此行為,但這種價值追求本身并未改變。排除不信任的仲裁員,并不意味著直接選擇當事人信任的仲裁員。對于當事人缺乏直接了解的陌生仲裁員,盡管不在排除之列,也無法歸為當事人信任之列,只能作為一種權宜之計。此種情形已經受到仲裁機構的關注,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第6條不僅規定了排除當事人不信任的仲裁員,還規定了當事人應當在排除之后對名冊上的仲裁員進行排序,仲裁機構根據排序確定當事人共同信任的仲裁員,從而完成組庭程序。
第三,在當事人對仲裁員完全不了解的情形下,仲裁機構有義務幫助當事人選擇仲裁員。仲裁機構要求當事人選擇信任的仲裁員,當事人會因此尋找名單上仲裁員的相關背景資料進行比較。相反,仲裁機構要求當事人選擇不信任的仲裁員,當事人會因此尋找這些仲裁員不被信任的原因。相比之下,前一種更為簡單,并增強了當事人對仲裁庭處理爭議的信心。后一種較為困難,只會增加當事人對仲裁庭公正處理爭議的懷疑。因此,選擇信任的仲裁員這一方法是相對合理的,更有利于爭議的合理解決。
(二)邊裁選擇首席仲裁員
這種方式僅適用于三人庭的組成,其基本價值追求從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轉移到了仲裁庭內部的穩定與協調。邊裁選擇首席仲裁員,是指雙方當事人各自委任一名仲裁員,然后由當事人委任的仲裁員共同協商選定首席仲裁員。在我國,由于《仲裁法》規定由當事人選定或者仲裁機構指定仲裁員,并未規定可以由仲裁員代為選擇首席仲裁員,并且為了顯示公平、公正,被選定的仲裁員在仲裁庭組成之前并不愿意過多接觸當事人,因此,這種方法在國內幾乎沒有實踐。
有學者對這種組庭方式給予了極大的肯定,認為邊裁選任首席仲裁員的選任方法是最令人滿意的,因為當事人指定的仲裁員可能對于由他們選定的首席仲裁員的技能和判斷力具有信心,他們也可以將有關情況反饋給指定他們的當事人,通過這種方式確保受委任者可被各方當事人所接受[10]。
筆者認為,這種首席仲裁員選定方式并不能真正解決實踐中的問題。雙方當事人委托選定的仲裁員協商一致選擇首席仲裁員,其實是將自己的權利讓渡給了己方信任的仲裁員。然而,被委托的仲裁員并不了解當事人的偏好,只能根據自己的意愿選擇首席仲裁員。在國際上,這種方式已經造成了一定的后果:由于仲裁員來自不同國家,并不了解其他仲裁員的相關信息,在實際選擇過程中,只能選擇己方熟悉的或者國際知名的仲裁員。這樣一來,不僅造成了當事人經濟上的負擔,而且在一定范圍內造成了“少數精英律師和仲裁員控制國際仲裁”的問題,國際仲裁成了“小團伙”或者“俱樂部”,“國際仲裁群體相對比較小而且相互聯系非常緊密”。仲裁員也被“定義”為某種特定案件仲裁員,被重復選定或者指定[11]。一旦實行該種首席仲裁員選定方式,國內仲裁也將面臨同樣的問題。由于國內仲裁員的報酬均采用價值評估法,知名仲裁員與普通仲裁員的報酬差異并不大,所以知名仲裁員的選擇比例會增加。出于“禮貌”或者“互相信任”等原因,被邊裁選定的首席仲裁員在其他案件中將“投桃報李”,提名該邊裁作為首席仲裁員的候選人。長此以往,知名仲裁員不再愿意被各種低報酬的仲裁案件所困擾,而其他具有“合作關系”的仲裁員則控制仲裁庭的組成,排斥其他仲裁員的進入。
綜上所述,名單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進爭議當事人選擇共同信任的仲裁員,而邊裁選擇首席仲裁員的方式沒有法律依據,無法為當事人選擇直接信任的仲裁員,還可能引起一系列仲裁環境的變化,因此,筆者并不推薦邊裁選擇首席仲裁員的方式。
(三)其他需要關注的問題
從仲裁機構提供的名單中選擇共同信任的仲裁員是筆者更為傾向的組庭方式,然而,在采用這種方式組庭時,還需要關注以下問題:
1.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
當事人意思自治是仲裁效力的來源。如果當事人有明確意思表示,且該意思表示有充分依據,仲裁機構必須予以尊重。因而,當事人協商一致選擇仲裁員,應當作為原則性方法放在“名單法”之前,以強調當事人意思自治。爭議當事人在適用名單法時,享有選擇名單之外的仲裁員、排除名單上所有仲裁員、請求仲裁委員會主任直接指定仲裁員的權利。
2.名單法的修正獨任仲裁員的選定與首席仲裁員的選定程序基本相同,筆者在此不再贅述。在目前的仲裁實踐中,運用名單法選擇獨任仲裁員時,若出現兩個及兩個以上的相同仲裁員,由仲裁委員會主任指定其中之一。該程序無須進行修正。
在適用名單法時,可能出現兩名仲裁員被當事人共同選擇為信任仲裁員的情形。根據現有仲裁規則,仲裁委員會主任將指定其中一名為首席仲裁員,此外的仲裁庭組成人員均由仲裁委員會主任為其指定或者當事人選定。
但是,如何利用雙方當事人共同選擇的另一位仲裁員,發揮這名仲裁員的積極作用?仲裁機構提供候選名單是有依據的,可以結合爭議性質,根據仲裁員的職業、專業、時間安排等因素為當事人提供。當事人的共同選擇應當在仲裁庭中發揮協調當事人利益的作用。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和北京仲裁委員會關于名單法的適用都有前提條件,均為首席仲裁員的選擇和指定,并未對另一名共同選擇的仲裁員予以關注。運用規則合理利用另一名仲裁員,對仲裁庭的合理組成、仲裁庭內部關系的協調、仲裁裁決意見的作出均具有實際意義。
筆者認為,可以對名單法作出如下修正:若仲裁機構提供的名單中有兩名仲裁員被當事人共同選擇,該兩名仲裁員當然成為仲裁庭的組成人員,由仲裁機構在名單之外重新為其指定首席仲裁員。這樣既避免了上述問題的出現,又回避了在仲裁實踐中邊裁一定要傾向于一方當事人的困境。這種方法通過規則調和了仲裁庭內部關系,增加了邊裁之間的共性,在一定程度上也防止了首席仲裁員的傾向性。
綜上所述,在仲裁庭的組庭程序方面,仲裁規則可以表述為:
第 條 三人仲裁庭的組成
(一) 申請人和被申請人應當各自在收到仲裁通知后 天內共同選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員會主任指定一名仲裁員。
(二) 第三名仲裁員由雙方當事人在被申請人收到仲裁通知后 天內共同選定或共同委托仲裁委員會主任指定。第三名仲裁員為仲裁庭的首席仲裁員。
(三) 經雙方當事人申請或者同意,本會可以提供五至七名仲裁員候選名單,由雙方當事人在第(一)款規定的期限內從中選擇一至三名仲裁員作為仲裁庭組成人選。候選名單中有一名相同的,為雙方當事人共同選定的首席仲裁員,雙方當事人各自選定或者委托仲裁委員會主任指定候選名冊之外的一名仲裁員;有兩名相同的,由仲裁委員會主任指定候選名冊之外的一名仲裁員作為首席仲裁員,與當事人一致選擇的兩名仲裁員組成仲裁庭;有三名相同的,由該三名仲裁員組成仲裁庭,并由仲裁委員會主任指定其中一名為首席仲裁員。沒有相同人選的,由雙方當事人各自選定或者委托仲裁委員會主任在候選名冊之外指定一名仲裁員,并由仲裁委員會主任在候選名冊之外指定首席仲裁員。
(四) 案件有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申請人或者被申請人時,申請人或者被申請人應當共同協商選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員會主任指定一名仲裁員。
(五) 案件有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申請人或者被申請人時,經雙方當事人申請或者同意,可以按照第(三)款的規定確定仲裁庭的組成。
第 條 獨任庭的組成
(一) 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由獨任仲裁員審理。
(二) 雙方當事人應當自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日內共同選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員會主任指定獨任仲裁員。
(三) 經雙方當事人申請或者同意,本會可以提供三名仲裁員候選名單,由雙方當事人在第(二)款規定的期限內從中選擇兩名仲裁員作為仲裁庭組成人選。候選名單中有一名相同的,為獨任仲裁員。有兩名相同的,由仲裁委員會主任根據爭議具體情況指定其中一名作為獨任仲裁員。 JS
參考文獻:
[1]張圣翠.國際商事仲裁強行規則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7:118-119.
[2]李登華.論仲裁庭首席仲裁員的確定[G]//商事仲裁:第8集.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 54-56.
[3]費恩·邁德森.瑞典商事仲裁[M].李虎,顧華寧,譯.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 4.
[4]林堅,黃曉紅.農村公共物品多邊治理機制研究[J].技術經濟,2007,(10):59.
[5]Mark Granove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480-510.
[6]Robert J. Aumann.On the Centipede Game[J].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1998,(23): 97-105.
[7]Alon Klement,Zvika Neeman.Private Selection and Arbitrator Impartiality[EB/OL]. (2011-03-31)[2013-06-08].http://ssrn.com/abstract=1800026.
[8]艾倫·雷德芬,馬丁·亨特.國際商事仲裁法律與實踐[M].4版.林一飛,宋連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201.
[9]Shahla F. Ali.What Can the US System of Financial Arbitration Learn from Overseas Jurisdictions?An Initial Responsive Empirical Exploration[EB/OL]. (2012-07-04)[2013-09-20].http://ssrn.com/abstract=2107714.
[10]馬占軍.首席(獨任)仲裁員產生規則論[J].河北法學, 2010, (5): 165.
[11]Natalia Giraldo-Carrillo.The Repeat Arbitrators Issue: A Subjective Concept[J].International Law, Revista Colombiana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2011,(19): 75-106.
On the Misinterpretation and Correction of Procedure for
Forming an Arbitral Tribunal: Based on Game Theory
TAN 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A peculiarity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s that arbitrators are appointed by mutual agreement. In practice, however, the appointment of arbitrators is suffering an undesirable shift from the initial intention of the rules. Instead of choosing arbitrators trustworthy for both, each party is actually excluding its own unwanted arbitrators. The author applies game theory to this paper and discusses both parties behaviors during the appointment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solate game and sequential game theory. List system and “sideline judge” approach are also analyzed, based on which the author offers his own suggestions on the procedure for forming an arbitral tribunal.
Key Words: commercial arbitration; procedure for forming an arbitral tribunal; game theory; list system; “sideline judge” approach
本文責任編輯:邵 海2014年4月第16卷 第2期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Apr.,2014Vol16 No.2 爭鳴與回應
文章編號:1008-4355(2014)02-009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