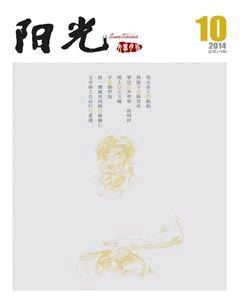當中國商人主宰地球時《廣東十三行史話》之十八:孽海花孟云王
羅三洋
伴隨阿拉伯人的馬蹄和商船,鴉片遠遠超出亞歷山大帝國的版圖,鴉片貿易第一次成為重要的國際經濟活動
作為一種舶來品,“鴉片”這個詞本為音譯,又被譯作“阿芙蓉”、“阿扁”、“阿片”等。它主要由粟目罌粟科的鴉片罌粟蒴果制成,雖然同樣是舶來品,“罌粟”一詞卻是意譯,取其種子形狀類似舀水的器具“罌”,又接近粟米的植物外觀特征,又稱“罌子粟”或“米囊花”。除了蒴果之外,罌粟的其余部分不能用于生產鴉片,而蒴果生長12 天后就會成熟,成熟后也不能用于生產鴉片。所以,要想獲取鴉片,就必須在罌粟蒴果未成熟的這12 天內,用特制的三刃刀具在蒴果表皮拉出口子,刀口的深度必須在1~ 1.5 毫米之間( 刀口太深或太淺都會影響鴉片質量),使含有生物堿的白色乳汁流出,待流出的漿液稍凝固后,將其刮下曬干,即成為尿騷味強烈的生鴉片;把生鴉片反復在熱水中溶解、煮沸、過濾,最終便獲得氣味芬芳的提純物“熟鴉片”。生鴉片和熟鴉片都含有大量致癮性生物堿,具備強烈的鎮痛作用。
鴉片罌粟原產于東南歐,考古研究證實,這種植物早在公元前5000 年的史前時代就已經進入了人類的生活,甚至可能是人類最先培植的農作物品種之一。公元前3000 年左右,西亞的文明先驅蘇美爾人就經常接觸鴉片罌粟,稱之為“快樂植物”。埃及人種植罌粟的歷史也幾乎同樣悠久,鴉片的主要成份——生物堿“蒂巴因”即得名于埃及古都底比斯。古埃及兒童如果過于淘氣的話,父母就會給他們灌服鴉片溶液。此后的中東霸主巴比倫人和亞述人將鴉片分為42 種,贊揚它能夠包治百病,可見他們對鴉片何等熟悉和喜愛。
古希臘人由于地理位置接近罌粟原產地,又長于國際貿易,也很早就了解罌粟。荷馬史詩《奧德賽》稱鴉片為“忘憂藥”,服用者“整天不再掉一滴眼淚,即便他們的父母去世,即便他們的兄弟或親愛的兒子在他們面前被殺死”。公元前5 世紀,希臘醫師開始發現鴉片的上癮作用,并呼吁戒除鴉片。被譽為“醫學之父”的古希臘神醫希波克拉底斯對鴉片持謹慎態度,認為鴉片如果有節制地使用,是很好的止瀉藥、麻醉劑、止血藥、催眠藥,可以治療多種疾病,但并不能包治百病。可是,羅馬帝國時期的希臘名醫蓋侖卻堅信鴉片包治百病,聲稱鴉片可以治愈頭痛、目眩、耳聾、癲癇、中風、弱視、支氣管炎、氣喘、咳嗽、咯血、腹痛、發燒、黃疸、脾硬化、肝硬化、腎結石、泌尿疾病、浮腫、麻風病、月經不調、憂郁癥以及毒蟲叮咬等多種疾病。當時,包括“哲學家皇帝”馬可·奧勒留在內,大批西方人都是蓋侖醫生的信徒。馬可·奧勒留皇帝每天都要服定量的鴉片,他的名著《沉思錄》就是這樣撰寫出來的。
隨著鴉片的使用日益廣泛,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發現它的副作用,這些副作用不僅限于成癮。作為高效鎮定劑,鴉片如果過量服用,會導致心肺功能衰竭,嚴重時會危及生命。公元前183 年,迦太基統帥漢尼拔在被羅馬士兵包圍時,吞服鴉片藥丸自殺,此后鴉片的受害者史不絕書。正由于鴉片及其提煉物嗎啡和海洛因等如果過度服用,都會置人于死地,因此它們又得到了一個共同的稱呼:毒品。
盡管如此,鴉片在古代仍然被普遍視為強身治病的藥材,大多數服用鴉片的人都因此受益,而沒有上癮或喪命。這主要是因為古人不會點燃鴉片吸食,而是直接吞食鴉片,或將鴉片混入蜂蜜、葡萄酒飲用,經過胃酸處理后,鴉片對人體的危害比較有限。
由于波斯人和馬其頓人的擴張,鴉片罌粟被廣泛引種到從阿爾卑斯山脈到帕米爾高原的廣大地區。在亞歷山大大帝死后的一千年內,鴉片罌粟的種植范圍都沒有越出過他的征服區域。伊斯蘭教創建后,鴉片得到廣泛使用,成為“圣戰”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傳染”給了他們的十字軍對手。伴隨阿拉伯人的馬蹄和商船,鴉片遠遠超出了亞歷山大帝國的版圖,傳播到從西班牙到中國之間的廣大土地上,鴉片貿易第一次成為重要的國際經濟活動。
公元10 世紀,阿拉伯世界迎來了其最偉大的醫師伊本·西納,歐洲人稱他為阿維森納。“伊本·西納”的意思是“來自中國”,從這個名字判斷,他原本是個中國人,也許系公元750 年在怛邏斯戰役中被俘的高仙芝部下后裔。伊本·西納是那個時代最博學的人之一,不僅精通中國、波斯和阿拉伯的多種醫書,也系統地研究了希臘和印度的傳統醫學,并且還是亞里士多德哲學的權威,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多部著作正是由于伊本·西納的收集,才得以在中世紀戰亂中保存下來。他傳授給西方人號脈、針灸、拔火罐等中國醫術,堪稱是最早從事中西醫結合的實踐者,其《醫典》是中世紀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世界共同的最高醫學權威著作。但是,伊本·西納醫生酷愛鴉片,而且不守《可蘭經》戒酒令,經常把鴉片混在酒里喝,最終不幸因此喪命。
阿拉伯帝國衰微之后,莫臥兒帝國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逐漸興起,征服了從巴爾干半島到孟加拉灣的廣闊土地。作為伊斯蘭世界的新興力量,這兩個帝國同樣熱烈地擁抱鴉片,其周邊的波斯、阿富汗等國也爭先恐后地推廣鴉片種植。莫臥兒帝國很快發展為全球最大的罌粟種植國,而一位在1546 年周游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法國學者這樣記載他的見聞:“沒有一個土耳其男人不是把最后一塊銅板花在購買鴉片上的。他們在戰爭時期攜帶鴉片,在和平時期也攜帶鴉片。他們愛吃鴉片,因為他們認為這樣會在戰爭中變得更勇敢,更加不怕危險。因此在戰爭期間,鴉片被搶購一空,很難覓得存貨……”就這樣,鴉片幫助土耳其人橫掃中東,攻下君士坦丁堡,一直打到維也納城下。
與莫臥兒帝國出產的印度鴉片相比,土耳其鴉片的嗎啡含量更高,因此廣受熱愛鴉片的西歐人喜愛。土耳其鴉片的最大出口對象,便是后來發動鴉片戰爭的英國,英國則向土耳其出口紡織品,兩國的商貿關系由此日漸紅火。“英國醫學之父”西德納默和伊本·西納一樣酷愛鴉片,因此被稱為“鴉片哲人”。這位醫生公開頌揚鴉片道:“我不由自主地衷心感謝偉大的上帝,他創造萬物,由人類任意享用,還有神奇的鴉片來撫慰人類的靈魂。鴉片不是藥,卻可以防疾治病……沒有了鴉片,藥物也無所作為。明白了這一點,誰都可以妙手回春。”直到19 世紀初,他用鴉片、藏紅花、肉桂、丁香和雪利酒混合配制的“西德納默鴉片酒”都是英國人消費鴉片的主要方式,號稱包治百病。在鴉片戰爭爆發之前,英倫三島本土平均每年要合法地消費20多噸鴉片。據馬丁·布思在《鴉片史》中介紹:在18 世紀,“事實上,每一個英國人在他們生命中的某一段時期都服用過鴉片,而許多人則是經常服用。”印度的征服者克萊武就服鴉片成癮,威靈頓公爵還曾親眼看見英國國王喬治四世服用鴉片。endprint
在基督教和伊斯蘭世界廣泛使用鴉片的時代背景下,中國不可避免地通過國際貿易接觸到了鴉片,絲綢之路也同時成為鴉片之路
亞歷山大大帝死后一百多年,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中西交流掀起高潮,中亞的葡萄、苜蓿、胡椒等作物相繼被引進中國。漢末三國之際,名醫華佗用麻沸散麻醉病人,以便做手術。隨著華佗被曹操處死,麻沸散的配方不幸失傳。好奇的后人對其主要成分多有分析,或以為是原產印度的曼陀羅,或以為是原產西亞的鴉片,或以為是原產中亞的豪麻,未有定論。華佗的醫術與中國傳統醫術頗有不同,歷史學家陳寅恪認為,華佗是一名來華的印度醫生。如果是這樣,那么華佗可能確實接觸過鴉片,并將其用于醫療。
最早記載鴉片的中文著作,可能是成書于公元659 年的《唐本草》:“底也伽,味辛,苦平無毒,主治百病中惡、客忤邪氣、心腹積聚,出西戎。”底也伽這種萬應解毒藥由精通醫術的本都國王米特拉達梯在公元前1 世紀發明,是西方傳統醫學的驕傲,據說含有六百多種成分,其中就包括鴉片。公元667 年,拂菻( 拜占庭) 使者向唐高宗和武則天夫婦贈送底也伽作為國禮,此后這種價值連城的藥物逐漸失傳。不過,通過對底也伽的了解,唐朝人已經愛上了鴉片,于是開始廣泛地在本土推廣罌粟種植。
唐朝中葉學者陳藏器在《本草拾遺》中描述罌粟花說:“罌粟花有四葉,紅白色,上有淺紅暈子,其囊形如箭頭,中有細米。”詩人雍陶在《西歸斜谷》詩中這樣描繪米囊花( 罌粟花) 帶給自己的親切感:“行過險棧出褒斜,歷盡平川似到家。萬里愁容今日散,馬前初見米囊花。”晚唐農學家郭橐駝的《種樹書》也記載:“鶯素( 罌粟) 九月九日中秋夜種之,花必大,子必滿。”由這些記載可知,早在唐朝后期,陜西、四川等地就在種植罌粟了。
與古代西方人一樣,唐朝中國人也直接口服鴉片。五代十國時,南唐的藥典《食醫方》推薦把“罌粟米”與人參、山芋合煮為“罌粟粥”,加姜末和食鹽服用,說可以健胃消食,足見罌粟此時已是藥店中常見之物。
北宋兼并南唐以后,繼承了南唐的廣闊罌粟種植園,并在全國推廣,掀起了全民種植罌粟的熱潮。北宋文豪蘇軾、蘇轍兄弟就經常服用罌粟,還寫詩加以贊美。蘇軾的《歸宜興留題竹西寺》歌頌說:“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鶯粟湯( 罌粟湯)。”蘇轍的《種藥苗》宣傳道:“罌粟可儲,實比秋谷;研作牛乳,烹為佛粥。老人氣衰,調肺養胃……”蘇氏兄弟的這些詩文還透露出,當時的佛教僧人已經普遍地把罌粟作為食物和飲料中的珍貴成分,民間則把它當作養生健體的藥物。
在蘇東坡兄弟看來,罌粟儼然是老幼皆宜的健康食品。當時,持有這種想法的還大有人在。林洪編寫的食譜《山家清供》記載有菜譜“罌乳魚”:“罌粟凈洗、磨乳,先以小粉置缸底,用絹囊濾乳下之,去清入釜。稍沸,亟灑淡醋收聚,乃入囊壓成塊,乃以小粉甑內下乳蒸熟,略以紅面水酒,又少蒸取出,起作魚片。”這里簡直是把罌粟籽當作極受推崇的食料,如此不厭其煩地精細加工,才制作成名菜。除了入藥和食用以外,宋朝人還把罌粟當做觀賞花卉培植,著名學者兼發明家蘇頌在《本草圖經》中記載:“罌子粟,舊不著所出州土,今處處有之,人家園庭中多蒔以為飾。花有紅、白兩種,微腥氣,其實作瓶子,似箭頭,中有米極細,種之甚難。”由此可見宋朝的罌粟產量之大,種植范圍之廣。
也許是因為有“微腥氣”的緣故,罌粟盡管“種之甚難”,但始終無法晉升為高檔觀賞花卉。在宋朝人眼里,罌粟雖然有食用和觀賞價值,但最主要的功用仍是藥材。宋太祖時,翰林學士李昉、劉翰編纂的官方藥典《開寶本草》首先將罌粟列入藥材,尊稱為“御米”,贊揚它“甘平無毒”,主治“丹石發動,不下飲食”。寇宗弼的《本草衍義》進一步闡述說:“罌粟……服石人研此水煮,加蜜作湯飲,甚宜。”所謂“丹石”,通常指的是魏晉時發明的一種興奮劑,其主要成分為:石鐘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因為這五味藥的名字都帶一個“石”字,故合稱“五石散”。作為一種毒品,五石散很容易上癮,一旦停藥,又會產生很大的副作用( 也就是所謂“丹石發動”),而且價格昂貴,自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毒害了很多中國人,其中多半還是高級知識分子。為治療“丹石發動”,人們找了許多藥方,后來發現罌粟最有效,于是尊為特效戒毒藥。殊不知罌粟之所以能治五石散,是因為它本身含有更強烈的上癮成分。唐宋之際,五石散在罌粟的沖擊下,從市場上完全消失了。換言之,五石散走了,鴉片來了,戒毒藥自己搖身一變,成了更可怕的毒品。近代嗎啡、海洛因泛濫的過程,走的也是同一條路:發明嗎啡的最初目的是治療鴉片上癮,發明海洛因的最初目的又是治療嗎啡上癮……
以毒攻毒的結果,就是毒癮越來越大。
除了主治“丹石發動,不下飲食”之外,宋朝醫生還發現,用罌粟治療痢疾有奇效,對痔瘡、肉痿、內熱、咳嗽等疾病也有一定療效。至今中醫仍以罌粟殼入藥, 處方稱為“御米殼”或“罌殼”。罌粟殼和果實、種子也一直被中餐當做輔料使用,火鍋店尤為常見。
宋朝人雖然廣泛種植罌粟,但還沒有掌握割取罌粟果汁,將其加工為鴉片的技術。直到此時,見過真正鴉片的中國人還比較少。但到了宋亡元興之際,從西亞歸來的蒙古遠征軍帶回大批西洋鴉片作為戰利品,很快隨著他們的馬蹄風靡全社會,據說“士農工賈無不嗜者”,迅速把中國傳統的罌粟制品淘汰出市場。元朝也是“鴉片”一詞在漢文文獻里首次出現的時代。由于各個階層人民廣泛食用鴉片,中國人逐漸發現其副作用,元朝醫生朱震享在其醫書《金匱鉤玄》中警告:“鴉片其止病之功雖急,殺人如劍,宜深戒之。”
明朝初年,三寶太監鄭和奉永樂帝之命下西洋,掀起了又一輪中西交流高潮。鄭和自西洋帶回兩種稀有的藥材,進獻給永樂皇帝,其中一種叫“碗藥”,另一種叫“烏香”。其實,“碗藥”和“烏香”不過是鴉片的兩個不同品種而已。
自永樂皇帝之后,明朝皇帝中接觸過鴉片的不乏其人。史載萬歷皇帝“中烏香之毒”,連續二十余年不上朝,頻繁地“令中貴收買鴉片,其價與黃金等”。為滿足自己日益強烈的鴉片需求,萬歷帝發明了礦稅,大肆攤派,導致全國吏治糜爛,百姓暴動,四夷交侵,明朝從此由盛轉衰,鴉片的責任不小。1958 年,考古學家發掘定陵,找到萬歷皇帝的頭蓋骨,經過化驗,發現頭蓋骨中含有嗎啡成分,從而確證了古籍記載的萬歷皇帝癮君子身份。幸而當時的鴉片只是做成丸藥或湯藥吞服,經過胃酸中和,藥力大大下降。否則,萬歷皇帝虛弱的龍體很難撐得住二十多年的吸毒史。endprint
15 世紀末,也就是明朝中葉,長年擔任甘肅總督的王璽由于工作的原因,與穆斯林接觸較多,在其醫學著作《醫林集要》中詳細介紹了鴉片的刮漿、凝縮和煉制方法,是為第一份敘述鴉片生產過程的漢文著作。這時,中國罌粟的種植更加普遍,在部分地區業已成為主要農作物。明末的杰出地理著作《徐霞客游記》這樣記載貴州的罌粟種植景象:“鶯粟花殷紅,千葉簇,朵盛巨而密,豐艷不減丹藥也。”
荷蘭殖民統治模式決定了鴉片產業的畸形繁榮,鄭氏四代統治臺灣23 年,為稅收而放任毒品泛濫,這種短視政策造成致命的惡果
明朝滅亡后,志在反清復明卻屢屢受挫的“國姓爺”鄭成功于公元1662 年占領臺灣,驅逐了島上的荷蘭殖民者。雖然鄭成功很快去世,在臺灣的時間不到兩年,但他肯定多次看到過臺灣當地人獨有的一種風俗:受西班牙人影響,早在萬歷年間,臺灣人就已經開始像印第安人一樣,用煙斗抽來自美洲的煙草;但與大陸居民不同,部分臺灣煙民還喜歡在煙草里拌入一種棕色的膏狀物,共同點燃吸食。任何人一旦養成了這個習慣,都會對抽普通煙草喪失興趣。
這種棕色的膏狀物,就是荷蘭殖民者在爪哇島制造的熟鴉片。與之前將鴉片做成湯劑或丸藥吞服的“生食”法相對,將鴉片點燃后吸入其氣體的方法叫做“熟食”,據說這一“發明”要歸功于某位抽波斯水煙成癮的南洋華人。確實,早期鴉片槍的結構與波斯水煙槍比較接近。南洋華人發現,將熟鴉片同煙草混合后由煙斗吸入肺中,吸食起來的感覺比煙草更加刺激,于是如獲至寶,將熟鴉片和這種新式吸食法一同帶回了華南的家鄉,很快風靡于大江南北。因此,鴉片又被中國人形象地稱為“大煙”。后來,吸鴉片的方式發生了變化,但“大煙”作為鴉片的別名,卻一直保留了下來。
爪哇的荷蘭殖民當局唯利是圖,樂于看到鴉片銷量帶來的利潤,于是鼓勵當地百姓種植罌粟,并推行鴉片專賣制度,第一個鴉片承包商就是南洋華人,名叫王恩安。根據《明會典》的記載,這時的爪哇“烏香”就已成為貢品,可見萬歷帝服用的鴉片可能就是從荷屬爪哇進口的。
1639 年,痛恨煙草的崇禎皇帝下令禁煙,違者處死,吸食熟鴉片同煙草混合的“大煙”也在嚴禁之列。然而,此時的大明王朝風雨飄搖,崇禎的禁令已經難以出北京城,各地政府都需要煙稅,所以對禁煙令陽奉陰違。1642 年,在冀遼總督洪承疇“遼東戍卒嗜此若命”的勸說下,崇禎被迫取消了禁煙令。一年后,洪承疇兵敗降清;兩年后,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禎帝自殺,明朝幾乎與其短命的禁煙令一同滅亡了。
如果說荷蘭的殖民統治模式決定了鴉片產業的畸形繁榮,那么鄭氏祖孫四代先后統治臺灣23 年,卻也坐視鴉片種植和貿易照常進行,從不頒行禁煙令,為了稅收而放任毒品泛濫,這種短視的政策很快就造成了致命的惡果。1683 年,鄭成功舊部施瑯率領清軍來攻,鄭軍僅在澎湖組織了短期抵抗,而當澎湖失守,清朝海軍剛剛出現在臺灣本島海岸邊時,鄭克塽集團即日便像劉禪一樣開城投降,與當年頑抗鄭成功圍攻近一年的荷蘭殖民者相比,相差竟如霄壤。究其原因,主要是鄭軍入臺后普遍抽鴉片,缺乏戰斗力。康熙后期在臺灣任職的多位清朝官員都記載了當地人癡迷于鴉片煙,直至家破人亡的慘象,從這樣的民眾中怎么可能選拔出合格的軍人?
且聽1722 年抵達臺灣的名士藍鼎元如何記載臺灣的鴉片之害:
“鴉片煙,不知始自何來,煮以銅鍋,煙筒如短棍,無賴惡少群聚夜飲,遂成風俗。飲時以蜜糖諸品及鮮果十數碟佐之,誘后來者。初赴飲不用錢,久則不能自已,傾家赴之矣。能通宵不寐,助淫欲,始以為樂,后遂不可復救,一日掇飲,則面皮頓縮,唇齒齜露,脫神欲斃。然三年之后,莫不死矣。聞此為狡黠島夷誑傾唐人財命者,愚夫不悟,傳入中國已十余年,廈門多有。而臺灣殊甚,殊可哀也!”( 此處的“中國”指大陸,證明鄭克塽投降后,臺灣鴉片開始流入大陸。)同時在臺灣工作的清朝官員黃叔敬也有類似的記載:
“鴉片煙,用麻葛同鴨土切絲于銅鐺內,煮成鴉片,拌煙,另用竹筒實以棕絲,群聚吸之,索值數倍于常煙……土人服此為導淫具,肢體萎縮,臟腑潰出,不殺身不止。”
臺灣的罌粟種植業和吸食鴉片風俗并未因荷蘭殖民者的離開而停止,反而在此后繼續發展,1683 年之前的責任應由鄭氏集團來負,之后的責任則應由以鄭氏集團家產繼承人自居、獨占臺灣大部分耕地的施瑯來負。荷蘭殖民者曾經將臺灣的大片耕地劃為“王地”,強迫當地百姓在上面無償勞作,以充稅收,上面種植的作物中必有一部分是罌粟;鄭氏集團繼承了這份豐厚的產業,現在它又落入了施瑯之手。在施瑯統治期間,臺灣鴉片產業繼續蓬勃發展,并隨著兩岸的統一而傳入大陸,在施瑯常駐的廈門傳播尤甚,原因恐怕也在于此。
在“享受”鴉片方面,這一惡嗜隨著荷蘭殖民者的腳步由爪哇而臺灣,最終又伴著清朝統一臺灣而風靡中國大陸。大煙的幽靈,始終與歐洲殖民者在東亞的活動如影隨行。
廣東十三行涉足鴉片貿易很早,當時鴉片貿易是合法的,除非沒有繳納每一百斤鴉片三兩白銀的進口稅,才會觸犯走私禁令
盡管像藍鼎元、黃叔敬這樣的有識之士早已發現了鴉片對中國社會的危害,但清朝最高統治者卻長期對此毫無察覺。康熙統一臺灣之后,清朝初年為抑制鄭氏集團的“海禁”也隨之廢止。于是,把鴉片與煙草混合吸食的“鴉片煙”日益在大陸流行。這時,清朝政府不僅不禁止鴉片進口,反而按照合法藥品向鴉片征收進口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 正式定為一百斤鴉片收進口稅三兩白銀。這么低的稅率與鴉片貿易帶來的豐厚利潤相比,實屬九牛一毛,大大刺激歐洲殖民者發展其南洋屬地的鴉片生產,不斷增加向中國的出口。澳門葡萄牙當局于是開始從南亞和東南亞收購鴉片,再賣到中國大陸,其在中國大陸的主要貿易伙伴當然就是廣東十三行。
廣東十三行涉足鴉片貿易很早,不過,當時的鴉片貿易是完全合法的,除非沒有繳納每一百斤鴉片三兩白銀的進口稅,才會觸犯走私禁令。有時,這種貿易甚至是在將鴉片視為特效藥品的清朝政府催促下進行的。在乾隆皇帝登基之前,中國每年進口的鴉片不過一二百箱( 每箱120 斤),價值三四萬銀元,這對于每年營業額達上千萬銀元的廣東十三行而言,根本無足輕重,因此鴉片貿易并未得到粵海關和廣東十三行商人們的重視。直到1729 年,這種情況突然因為雍正皇帝的一紙禁令發生了變化,鴉片首次成為清朝社會關注的焦點。這一年,內閣學士方苞上書,請求禁止三種對民生有害的經濟活動:一是禁止釀造和販賣燒酒,二是禁止種植和販賣煙草,三是禁止向國外出口糧食。與崇禎皇帝一樣,清朝初期的幾位皇帝都特別討厭煙草,雍正帝也不例外。這不僅是因為他們貴為天子,卻要經常忍受從臣下口腔里吐出的二手煙毒害,而且據說更是因為當時中國人管吸煙叫“吃煙”,聽上去像是“吃燕”,而“燕”是北京的別稱,所以“吃煙”被認為對北京朝廷不利。結果,雍正皇帝同意了方苞的建議,下詔禁止全國百姓種植和販賣煙草。常與煙草混合吸食的鴉片也受到牽連,這份詔書因而被譽為世界上第一部禁毒令。其實,細看當年的原始檔案,雍正皇帝根本就沒有禁毒的打算。endprint
雍正禁煙詔書說:
“興販鴉片煙,照收買違禁貨物例,枷號一個月,發近邊衛充軍。如私開鴉片煙館,引誘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眾律,擬絞監候;為從,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戶、地保、鄰右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如兵役人等籍端需索計賊,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并不行監察之海關監督,均交部嚴加議處。”
按照這一法律,販賣鴉片煙要被枷號并充軍,開鴉片煙館要被判處絞刑,就連鴉片煙館的雇員和鄰居也要挨一百大板,并且接受勞動改造,處罰力度可謂嚴格。不過,千萬別以為雍正帝想要藉此法律禁止鴉片貿易。當年,就有一位不幸的官員誤解了皇帝的旨意。
雍正禁煙令下達后不久,一個名叫陳遠的福州商人從廣東購買34 斤鴉片,準備帶回福建販賣,路經漳州時被查獲。漳州知府李治國按照他所理解的最新禁煙令精神,判處陳遠枷號一個月并充軍。李治國的頂頭上司、老于世故的福建巡撫劉世明聞訊,立即察覺屬下犯了重大錯誤,連忙命令李治國釋放陳遠,并親自給雍正皇帝上奏折寫報告說:鴉片是眾所周知的良藥,是祖國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雍正朝初期大臣年希堯就在所著醫書中多次提及鴉片的藥用價值),只是在與可惡的煙草混合成“鴉片煙”吸食時,才會對人體造成危害。盡管陳遠賣的是純粹的藥材“鴉片”,而不是被最新法律明文禁止的“鴉片煙”,但是由于兩者的名字和成分相近,為了能夠更好地貫徹皇上的禁煙令政策,而不至于讓使百姓誤以為“鴉片煙”已經解禁,他建議將這批鴉片充公,以便給糊涂的漳州知府李治國一個臺階下。
可是素來明察秋毫的雍正皇帝仍然不依不饒,用親筆朱批為鴉片販子陳遠辯護說:
“其三十余斤鴉片,若系犯法之物,即不應寬釋;既不違禁,何故貯藏藩庫?此皆小民貿易血本,豈可將錯就錯,奪其生計?(李治國)妄以鴉片為鴉片煙,甚屬乖謬!”
原來,在雍正帝和劉世明看來,純鴉片屬于“不違禁”的藥材,鴉片販子都是守法的良民,他們購買的鴉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貿易血本”。漳州知府李治國膽敢逮捕鴉片販子,將他判刑并沒收鴉片,涉嫌詔書中嚴禁的“兵役人等籍端需索”,理應被“照枉法律治罪”。
圣命如天,被指責為“故入人罪”(蓄意陷害無辜者)的李治國被迫將沒收的鴉片還給毒販陳遠,并且向后者賠禮道歉。因為不能正確領會皇上的意圖,這第一位查禁鴉片的中國官員終生再沒有得到升遷的機會。
于是,全中國人都知道了如下的事實:
販賣或吸食鴉片與煙草的混合物“鴉片煙”,是犯法的,是要戴枷號的,是要被充軍的,是要被打板子的,甚至是會被當作邪教頭目絞死的;
販賣或吸食純鴉片,則是完全合法的,是有雍正帝親筆朱批作護身符的,任何官員都不敢為此逮捕和審訊你,或沒收你的鴉片。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不難想象:帶有濃烈煙草味道的“鴉片煙”一夜之間在中華大地上絕跡了,癮君子們的煙斗里,現在裝著的是百分之百的純鴉片。而和抽“鴉片煙”相比,抽純鴉片的上癮速度更快,消費量更大,對人體的危害也更劇。盡管如此,雍正皇帝捍衛鴉片販子利益的朱批卻并沒有立即造成嚴重后果。這是因為,傳統的煙斗適合用來吸結構松散的煙草,而不適合用來吸結構緊密的鴉片。吸食純鴉片,需要更加專業的設備,而這種設備在18 世紀初雍正皇帝在位時期還尚未發明。只有少數華南居民將鴉片和麻葛(大麻)混合吸食,但這種做法并未廣泛流行,因為多數中國人不喜歡大麻的味道。所以,雍正皇帝嚴禁煙草貿易,當年的確對鴉片銷量構成了一定的沖擊和限制,就連澳門葡萄牙人也經常為如何賣掉每年從南亞和東南亞進口的200箱鴉片發愁。
就在雍正皇帝禁煙之際,“哥德堡號”等瑞典商船正在向中國航行。粵海關官員看到,瑞典商船上既沒有煙草,也沒有烈酒,于是欣然準許其進口。也可以肯定,瑞典商船上沒有鴉片,因為瑞典本土不種植罌粟,又沒有海外殖民地,無法生產鴉片。但是,英國、法國、葡萄牙與荷蘭等在南亞和東南亞擁有殖民地的歐洲列強則全都很早就涉足了鴉片貿易。盡管英國此時只在印度沿海擁有幾座城堡,一些大膽的船員就已經從印度人那里購買了鴉片,并把它們帶到東南亞出售。由于缺乏銷售渠道,多數鴉片被直接帶到澳門,在那里賣給葡萄牙人,再由他們賣給熟悉的中國商人。直到此時,英國東印度公司自身一直不從事鴉片貿易,因為這種貿易規模太小,而且英國殖民地離印度的罌粟主產區太遠,沒有成本優勢。
公元1773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被莫臥兒帝國授予“ 鴉片專賣權”,1779 年,英國人弗格森在黃埔開設了中國大陸的第一家鴉片專營店
1732 年夏季,英國人首次嘗試在中國銷售鴉片。當時來到黃埔港的四艘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中,“康普頓號”和“溫德姆號”瞞著公司領導,私自攜帶了一些鴉片。據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記載,“由于鴉片在中國價格不錯,致使船長或船員不顧其行為帶來的危險后果,攜帶一些到市場出售。”這已經是雍正皇帝下達禁煙令以后的三年了,英國船員公然在廣州市場上叫賣鴉片,并沒有受到任何阻礙。使他們煩惱的是,十三行商人對他們帶來的西班牙銀元成色不滿,堅持認為含銀量只有93%,而非標準銀元的95% ;此外,英國船員愚蠢地將購買的武夷茶葉與樟腦儲存在一起,導致茶葉全都變了味。返回印度以后,英國船員大肆夸耀自己在廣州賣鴉片獲利的冒險故事,公司管理層對此不以為然。次年(1733 年)5 月25 日,當“康普頓號”和“溫德姆號”再度從南印度的馬德拉斯港啟程前往廣州時,公司管理委員會特別給它們下達指令:
“前時經圣喬治要塞( 英國東印度公司在馬德拉斯的基地) 開來的船只,經常帶來鴉片到中國出售,現在不知在你們的船上是否有這種商品帶往該市場?我們認為,我們有責任(否則恐怕你們不知道)通知你們,中國皇帝最近制定嚴禁鴉片的法令。懲辦方法是,凡在你們的船上發現鴉片,一律沒收,不僅船只和貨物會被充公,而且向你們購買鴉片的中國人也會被處死刑。顧慮及此,必須采取更加有效的方法,防止發生這類不幸事件。為此,你們必須盡可能用最好的方法,在你們的船上嚴密調查和詢問,搞清楚船上有沒有這種東西。如果有,你應該在離開馬六甲之前,將它們從你的船上弄走。無論在什么情況下,不得攜帶、也不準你們的船運載這種東西到中國,否則你們要面臨違反公司命令的危險責任。”endprint
英國東印度公司管理委員會的這份禁止在中國出售鴉片的指示,歷來被當作雍正政府嚴禁鴉片的主要證據,但它與當時的事實并不相符。雍正政府既沒有下達過任何禁止鴉片貿易的禁令,也沒有懲辦過任何鴉片販子,更不要說將他們處死了。盡管當時并無鴉片禁令,鴉片貿易卻并不興旺,因為在中國全面禁止煙草、又缺乏吸食純鴉片專業設備的大環境下,中國民眾對鴉片并沒有多少需求。英國東印度公司無意為了如此小的貿易額使自己陷入危險之中,因此寧愿相信捕風捉影的傳聞,禁止船員在中國出售鴉片。這份禁令得到了較好的貫徹:在此后的半個世紀內,確實很少見到英國船只在中國出售鴉片的記載,以至于后來清朝政府真正開始查禁鴉片時,廣州當局同意:“(英國東印度)公司船被豁免于對鴉片的搜查。”當然,這并不代表英國人就不再涉足鴉片貿易,他們在馬來亞等東南亞地區賣掉鴉片,換成銀元和東南亞特產,再把它們拉到廣州,賣給廣東十三行。向中國輸入鴉片的工作,于是便落到了東南亞華人和澳門葡萄牙人的肩上。
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鴉片貿易態度的真正轉變,發生在1757 年之后。如上文所述,1757 年6 月23 日,克萊武在普拉西奇跡般地戰勝了兵力20 倍于己的印法聯軍,一舉征服孟加拉,控制了這個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罌粟生產地。從此,英國船只上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鴉片。1764 年,英國軍艦“阿爾戈號”因為遭臺風受損,駛入黃埔港修理。粵海關要求像對待普通商船一樣丈量該船,但英國船長不同意,聲稱自己的船屬于皇家海軍,不屬于東印度公司,不是來華做買賣的,船上沒有要出售的商品,不應被丈量。雙方僵持達四個月之久,十三行商人為此受到很大壓力,行商被廣東官員威脅,如果為該船承保,要取締外貿資格并趕出廣州,結果沒有一位敢于承保該船,最后英方讓步。英國東印度公司聽說,該船曾裝載鴉片,懷疑它因此拒絕中國官員丈量,為此進行了詳細的調查。
公元1773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被莫臥兒帝國授予“鴉片專賣權”,這大大激發了公司對鴉片貿易的興趣。經過幾次謹慎的嘗試,對華鴉片貿易被認為確實可以獲得穩定的利潤。1779 年,不隸屬東印度公司的英國人弗格森在黃埔開設了中國大陸的第一家鴉片專營店。受這家商號的成功經營激勵,公司雇員華生中校于1781 年致信印度總督哈斯廷斯,建議將孟加拉鴉片直接運往中國銷售,并由英國東印度公司壟斷,因為他估計,僅在華南每年就能銷售1200 箱鴉片,每箱鴉片平均可以賣到500 銀元,這樣每年就能給公司帶來60 萬銀元的收入。在當時孟加拉鴉片滯銷、廣州市場現貨白銀匱乏的壓力下,公司董事會最終同意,開始對華鴉片出口的冒險。這的確是一種冒險,因為此時,乾隆皇帝的政府確實已經意識到了鴉片的危害,并開始在廣東口岸嚴查鴉片了。這樣,鴉片在中國市場上的銷售情況便與華生中校的預期相差甚遠了。
1782 年,依照哈斯廷斯總督的授權,英國東印度公司派出2 艘商船,載3067箱鴉片東行。船長被告知,盡可能在馬來亞沿岸賣掉這些鴉片,賣不掉的鴉片則拉到廣州出售。不料,其中一艘商船只賣出十分之一的鴉片之后,便在蘇門答臘被法國軍艦俘虜,損失了一千多箱鴉片;另一艘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嫩實茲號”載著1600 箱鴉片逃到菲律賓,從那里開往廣東。“嫩實茲號”原本想像以前的鴉片運輸船一樣,直接在澳門卸貨,但廣州的東印度公司管理委員會卻認為,“應當禁止澳門的船主們購買這樣大量的鴉片,因為在該市的鴉片,除已經售出的以外,至少還有1200 箱”,處于嚴重滯銷的境地。
很顯然,“嫩實茲號”要想在中國賣掉這么多鴉片,只有一個辦法:去找廣東十三行。
【待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