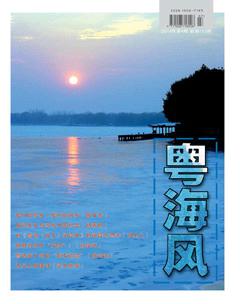從《文學江湖》看臺灣“反共文學”史觀
臺灣作家王鼎鈞的文學回憶錄四卷本,即《昨天的云》(1992)、《怒目少年》(1995)、《關山奪路》(2005)和《文學江湖》(2009)在海峽兩岸漸次出版,以及兩岸讀者在傳媒熱銷大潮下所形成的文學閱讀盛況,使得這份文學回憶錄的生成,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文學事件。四冊巨著,作者以個體經驗的目擊與實感、親歷與反思來挑戰歷史宏大敘述的暴虐粗糲而注入溫柔、悲憫的情愫,輔以點鐵成金般的哲思譬喻、妙語橫出的文字架構,加之文學自敘傳口述、筆抒胸臆而貼近讀者的體裁,在拓寬了這份文學創作的深廣度。文學研究者關于這份文本的研讀、分析,也從作者的文學生涯、創作心史、歷史溯源等多個角度予以展開。通讀王鼎鈞的文學回憶錄,如果將其視為作者最為用心經營的文學工程的話,那么在這個工程項目里作者最為倚重的敘述基石,乃是個體、小我的存在經驗在歷史洪流中的激蕩,以及這種激蕩所帶起的漣漪對歷史敘述的反作用效果。職是之故,筆者以作者親身經歷的50年代臺灣“反共文學”書寫潮流的興起與式微這一文學史階段作為論述切入點,以回憶錄第四卷《文學江湖》中關于這一部分的論述作為比照依據,從回憶錄文本的私密、封閉性中帶出底層敘述與適時主流話語相抵牾之處,將上層強權話語論述中所切割、棄用的文學經驗還原,獲得迥異于千人一面的文學史固態敘述模式的現場報導,揭示讀者在以往文學閱讀和理解中所習焉不察的文學細節。
一、 文學與歷史之間的細節互補:回憶錄文本的文學史向度
法國學者菲利普·勒熱訥在《自傳契約》里曾經明晰地點出,在回憶錄中,作者表現得像是一個證人,“他所特有的,是他的個人視角,而話語的對象則大大超出了個人的范圍,它是個人所隸屬的社會和團體的歷史”,回憶錄作者給予當代事件、給予歷史本身的比重經常要比作者個性的比重大得多。[1]的確,《文學江湖》雖然書寫的是個體經驗,但作者的視閾并不畫地為牢,而能由己及人,推而廣之,寫出時空機緣所帶給社會的一種“水在瓶中”的定型。如高華所論述的那樣,“《文學江湖》一書,既是為歷史做見證,也給我們啟示和教益,讓我們知道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在過去的20世紀所經歷的痛苦和所懷抱的夢想、希望”。[2]王鼎鈞回憶錄的沉重,是個體經驗與歷史進程的天人交戰,以及這種焦灼的對峙關系所造成的斡旋空間,著眼是在“小人物”對“大歷史”的參與度上。王鼎鈞以邊緣性的角色(流亡中學生、憲兵成員、解放軍俘虜、報社主編等身份)親身參與歷史進程,具有感性的親身經驗;書寫這段經驗的時候,作者已經身處美國,具有離散的書寫經驗,是一種“寫在家國以外”的反躬自省,因而難能可貴。
文學與歷史之間的那種糾葛而紛擾的關系,由是在《文學江湖》中一再搬演。蘭克在《歷史科學的特性》中指出,歷史敘述兼具科學與藝術的雙重性格,因而文學敘事能評介一己的敘事孔道,而參與歷史敘事。文學絕不是對歷史事件的簡單還原或者貼身摹寫,而能借由述者主觀經驗的參與,來揭示具有普遍性的歷史內容,或者展現個體經驗對歷史事實的一己之見。往昔文學史論者多半對“系統”“連貫”“完整性”有著過分的仰賴,這樣的仰賴可能導致在文學史的敘述過程中強調排他性,以期完成連串線索之論述,對史料的其他側面重視度不足。正如邱貴芬援引福柯的觀點認為:“福柯強調不連貫、斷裂的考古學,并非完全否定歷史進程中有因果關系和連續的成分,而是認為不連貫與差異和連貫一樣重要,必須納入歷史敘述當中。傳統歷史敘述最大的弊病在于將所有歷史里的斷裂和差異化約為循次漸進、連貫而成的發展流程。”過分追求“周密”的體系構成,可能無法呈現文學場域里多重結構和活動有時重疊、有時沖突矛盾的狀態。[3]對于50年代臺灣“反共文學”的興起與式微這一文學現象,兩岸意識形態光譜各有不同的文學史家通過比對適時的政令、文學團體活動、文學獎勵、文學作品刊行等等文學制度情況,雖然得出不同的文學史結論,但這些結論卻都吊詭地共享著一些文學史敘述特性;而這些結論的得出,毫無例外都是仰仗、依賴文學上層組織活動的話語論述,沿著這些論述自上而下地爬梳材料、得出一條明晰的歷史線索。那么,被這條文學史明線所舍棄的枝蔓部分是否有它的價值?這些枝蔓被舍棄是因為它雜蕪還是因為它不合敘述連貫?枝蔓部分能否重新找回而對原有結論貢獻出異質且可供參考的聲音?《文學江湖》作為一份精彩的回憶錄文本,它里面富含的文學細節都出自作者的親身體驗,這些細節與文學史主線敘述中或有抵牾、或有修正,其實不妨都視為對文學史主線的一種補充;回憶錄文本個體經驗書寫的自我閉鎖式結構,以及作家情感認知在側寫人物時的投入情況也使得考鏡事件源流、理析完整細節并無十分必要,而不妨以“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的態度坦然接受文本本身。而關鍵則在于《文學江湖》以其書寫、存在,挑戰了單線敘述的文學史認知狀況,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份回憶錄文本就自有其永恒之光,值得細細研讀。
二、文學(史)敘述中“反共文學”形塑的“大環境”
按照臺灣文學史書寫所共享的“潛規則”來看,以十年為限度來進行臺灣文學的梳理劃分,是眾多臺灣文學史的操作策略。是故,50年代的臺灣文學,在經歷了1945—1949年光復以后的短暫調整,以一個嶄新而完整的面目浮現在研究者眼前。無論稱其為“風暴中的新文學運動”(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1991),還是“反共戰斗文藝淪為反現實主義逆流”(呂正惠、趙遐秋:《臺灣新文學思潮史綱》,2002),在表明了將50年代的臺灣文學作為一段相對獨立的文學史階段的合理性。以何種線索來把握這個階段,是(文學)史家下筆的關鍵。由是,“反共文學”的題眼,就幾乎成了50年代臺灣文學的統攝關鍵字。40年代后期國民黨來到臺灣后,反思既往,檢討文藝戰線上的失利,基本看法是之前“國民政府從未把力量集中在文學領域”;如計璧瑞指出的那樣,“國民黨對文藝工作的忽視,具體而言就是缺乏方針政策、工作方法簡單和經費短缺;表現為組織動員能力差,沒有建立一個思想統一、行動有力的文藝組織機構,更談不上建構與國民黨意識形態和統治機構相對應的文藝體制”。[4]將前所未及之處加強補足,就成了此時臺灣官方機構話語論述的當務之急。
研究者在審視50年代臺灣文學場域活動的時候,順著官方構建這套體系的痕跡,首先就會注意到前所未有的、由政治權力機器所主導的各種類型文藝運作。無論是“中國文藝協會”“青年寫作協會”“婦女寫作協會”,還是“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這些文藝運作當中最重要的訴求,就在于建立一種可以迅速、有效率地將“上層旨意”以文學運作方式傳達到涵括臺灣各行各業、隨時可以進行意識形態宣傳與社會思想動向捕捉的文學/文化體系。在戒嚴體制的高壓控制下,如何“純潔化”作家隊伍、對文學背景多有不同的各個作家進行嚴密有序的篩選、控制乃至使用,并通過這種純潔化后的作家隊伍及對其的文學動員,來實現政令的文學化軟性傳播、思想戰線的形塑與鞏固等重要政治動員,就成為這套體系建立與完善的應有之義。“反共文學”的提出,顯示出臺灣當局將40年代后期解放戰爭失利以來的敵對情緒帶動到臺灣島內,冀望以文學宣傳激勵跟隨來臺的大眾,給予其虛幻的“反攻希望”;與此同時,“反共文學”的搖旗吶喊實際上也試圖撫平乃至遮蔽臺灣光復初期來臺的大陸接收權貴與一般臺灣本省人之間業已激化的文化矛盾,通過強調“反共/反攻”大業,要求大眾忽略文化場域中的其他次要矛盾,以利于統治需要。由是,在文學史的觀察中,50年代的“反共文學”書寫,就成了這個階段政治力運作下文學生產的最為顯著的特點。文學史既定的敘述線序,也大多沿著“反共文學”主題的萌芽(50年代初期)、深化(“文協”“文獎會”的成立)、泛濫(“戰斗文藝”的提出、文學創作實績的蜂起)、跌落(文藝政策的調整、現代主義文學的興起)等文學史“生長階段”來展開。
如應鳳凰所觀察到的那樣,雖然“國民黨文學史書”“臺灣本土派陣營之文學史書”“大陸左派陣營之文學史書”對50年代“反共文學”的觀察體認各有不同,[5]但三者都有共享的結論,“其一,兩邊都認為“反共文學”的藝術性很低,或者根本沒有藝術價值可言。其二,都認為其形式僵化或公式化,同質性太高,是政治的附庸”。[6]通過對照既有文學史論述對于“反共文學”生產的“大環境”研究,筆者也同樣注意到相關論述中的共性很多,對于“反共文學”在官方政治力加持下大環境中的塑形,已產生了近似固態的文學史敘述模式。首先,各種文學史毫無例外地點出了在這樣的文學生產大環境中,“反共文學”的生產蔚為大宗、盛況空前、霸占文壇。這種盛況由文學評獎所帶動,使得這個主題的創作產量空前;同時借倚文學傳媒如報紙副刊和文學出版,更增益其聲勢,“文獎會維持了七年,1956年年底結束,每年于元旦、五四、十月十日、十一月十二日定期舉辦,前后共舉辦十七次,七年間共有三千多人投稿,作品近萬件,入選者給予高稿酬或獎金”;[7]“有關戰斗文藝的理論和創作,蔚成一大風尚。各報副刊和文藝刊物,都競相發表此類文稿”;[8]其次,在既成的文學史論述中,這種書寫的熱潮毫無疑問源自于受政治力機器運作以及文學制度(文藝社團、文學評獎)的保駕護航,這種體制內的保護、鼓勵誘發了作家全員的創作激情,“官方的文藝獎金制度,在荒涼的年代鼓勵不少知識分子與軍中官兵投入寫作的陣營”,[9]“若非這十年國民黨機器介入文壇的程度,比其他時候都深而廣,文藝政策也不會一再成為50年代文學史關注的焦點”;[10]最后,就文學實績而言,研究者對這段文學創作藝術成就的保留意見非常集中,葉石濤指出此階段大陸來臺作家把持文壇,配合“黨國宣傳”做出文學闡釋,這十年的文壇因此“白色而荒涼”;[11]陳芳明更在此基礎上直指文藝創作價值的匱乏,反映出作者的心靈創傷,“在這個制度下,是官方文藝政策順利進駐作家的心靈,并且也使作家對于支配性的政治體制產生依賴”。[12]凡此種種,諸多論述固然可以給后來者重溫這一段文學史事實時以清晰的邏輯思路、順暢之發展線序;但與此同時,它對研究主題本身所造成的刻板化印象,也在整齊劃一的敘述中同步誕生。以上這些意識形態光譜不同的文學史,它們所帶出的敘事鏈條,以及所共享的價值判斷,是否和文學動員中的運動軌跡完全嚴絲合縫?在50年代文學場域生成的“大環境”中,是否存在創作主體——作家因個人經驗而對“大環境”的權力運作有所反作用的“小生態”?這些都必須返歸適時的文學現場,通過《文學江湖》這個文本,或能窺探一二。
三、從《文學江湖》自傳文本窺探“反共文學”生產的“小生態”
如前所述,50年代的臺灣文壇,由于官方意識形態的倡導以及對文學發展方向的有意識導向,興起了一股“戰斗文藝”的書寫。而這種書寫的集中表現形式,乃是所謂的“反共文學”的創作。在文學史的敘述中,這種文學類別的生產被目為“泛濫一時”,當仁不讓地占據著文學場域中最為重要的中心位置,而當時移事往,現實環境丕變,這種文學潮流則被后來的現代文學、鄉土文學所取替。追溯1950年代的臺灣文學,文學史對這一段文學潮流的描述大致若此。
《文學江湖》在“十年燈”“十年亂花”兩部分,以親身經歷直接梳理50年代“反共文學”的來龍去脈。作者彼時交游文藝界,列名“中國文藝協會”發起人、任職“中國廣播公司”、參加文協小說創作組、為各大報刊撰稿,確為適時文壇要角。親歷50年代文壇,深悉“反共文學”的起與興、衰及落,作者始能有自己的判斷。王鼎鈞對這一階段的文學書寫,重現了文學史敘述中因過分強調連貫、整體而遮蔽掉的部分。他有心讓讀者注意到,文學史“一以貫之”的宏大敘事,在歷史長河中披沙排金的過程中,可能疏忽掉的細節部分。這些細節曾因不合乎主潮的運行軌跡而被排擠為一朵拍死在岸邊的浪花,而借由文學歷史親歷者的細膩筆觸,讀者得以知曉這一段往事的隱情或雜音,獲得拓展這一段文學史思考和理解的可能性。
對“反共文學”生產所謂的“盛況”及其實情進行剖析,是《文學江湖》以親歷者對文學史敘述提出的一大質疑。要員張道藩領銜的“中國文藝協會”,在文學史的論述中對于“反共文學”施以領導,似乎是發號施令即一呼百應的“官衙”,如陳芳明指出:
……從1950年到1960年,可以說是中國文藝協會的全盛時期,國民黨的文藝政策與活動方針,都是透過這個組織而得以實現。在這十年期間,中國文藝協會主宰了臺灣的文壇。
就內部而言,該會舉辦各種文藝研習輔導活動,培養小說、攝影、美術等等人才;并舉辦各種定期文藝社會活動,提供作者與讀者有對話交流的機會。在重要的節日,該會還主辦各種文藝活動,以配合官方預定的政策。當時,所有外省作家都成為文藝協會的成員。組織之龐大,超過文學史上任何一個時期。[13]
以上述論述為代表,在文學史家的論述中,50年代臺灣“反共文學”的生產盛況是由“文協”領導而產生的,其掌握文壇全部資源,通過各種運作使所有外省作家集聚一堂、戮力同心。首先,“反共文學”之“盛況”到底如何,這種“盛況”是如何生成的?其次,“反共文學”的參與者——作家,是否真的全員參與?作家是否有選擇權,能否對這個議題敬謝不敏?如果決定參與“反共文學”創作,其文學活動是不是有益無害,是幫助其累積文學資本的絕佳途徑,還是也有政治風險的畏途?這些問題,文學史家語焉不詳,則必須求助于回憶錄文本的細密記錄。
史家縱論“反共文學”書寫云蒸霞蔚,到底情況如何?王鼎鈞的個人回憶里,坦言這股潮流的發展其實借助了媒體的力量夸張了聲勢,回憶錄里點破其聲勢宏大的妙竅,原來是“主持反共文藝運動的人看上了報紙副刊這輛順風車,報紙的銷數超過文學期刊幾十倍,“反共文學”上副刊,不脛而走。早期“反共文學”的質量都不高,給人的感覺卻是聲勢浩大,可以說是副刊的功勞”(頁85);而這種繁榮的興起另有玄機,“當時倡導‘反共文學,用‘千金市骨之計,國王愛馬,以千金買千里馬的遺骨,于是四方爭獻寶駒上駟。提倡反共的文學作品(或者說,按照黨部的規格提倡反共的文學作品),先有‘求,再求‘好”。隨后,官方通過先刊載作品,然后緊接著發表文學評論的辦法,“和聲回音”力捧符合意識形態要求和具有“反共”意識的文學創作,“這樣做,預期給讀者大眾這樣的感覺:排場聲勢如此,作品豈能等閑”(頁85)?于是,“反共文學”包裹著盛譽、挾持著力捧,走在官方鋪就的金光大道上,在沒有反對聲響的贊許中獨享著文學潮流的頂尖。“反共文學”的聲勢浩大,原來也不過是官方手制的虛假繁榮。
而“反共文學”運作的基石——“文協”的作用,在王鼎鈞的觀察里,其實也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大。“后來的人有一個印象,‘反共文學壟斷了所有的發表園地。其實以張道公之尊,挾黨中央之命,各方面的配合仍然有限”“《中央日報》號稱國民黨的機關報,它的副刊正正經經的文章,簡簡單單的線條,干干凈凈的版面……它冷靜矜持,從未參加集體暗示”(頁86)。就連1954年張道藩完成《三民主義文藝論》原稿,發表之后“中廣”公司也未濫用公器為之制作特輯“踵事增華”。在文學史中,官方背景的“文協”之受到矚目,主要在于史家通過把握上層機構的權力運作體系,來順流梳理體系下面文學活動概況的文學史處理方式。文藝運作誠然通過政策的出臺、獎懲的實施、創作實踐方向的導引等等方面加以操作,但在操作運行的過程中這個論述主體會遭遇到作家個體乃至作家小群體的反作用力,使得這個政治運作力大打折扣甚至大為變形。在臺面上,的確所有的外省作家都成為了“文協”會員,但他們的文學活動的“小生態”,即對“反共文學”創作的參與度、認可度才是探看他們對這個文學議題真實心態的依據。從《文學江湖》來看,這個問題有重新解讀的必要性。王鼎鈞自言“50年代,臺灣興起‘反共文學,那時我拿不動這樣大的題材,沒有作品,只有心情”(頁82)。這個情況其實并非孤案。作家特別是文協成員作家,對于“反共文學”的態度其實相當多元,他們并非毫無疑問、竭心盡力參與書寫熱潮,“反共文學”的書寫其實也并非一本萬利毫無危險性。王鼎鈞指出,“臺灣在50年代號稱恐怖時期,政府對文藝作家百般猜疑,而作家多半以對現實政治離心為高,兩者互為因果”,是故兩者之間其實充滿曖昧關系,作家對待“文協”所組織的活動,不少人其實陽奉陰違:
國民黨對于拒絕回應“反共文學”的作家并沒有包圍勸說,沒有打壓排斥,他只是不予獎勵,任憑生滅。那年代,只有作家因“寫出反共作品”受到調查(因為他反共的“規格”與官方制定不合,或分寸火候拿捏不準),并無作家因“沒有反共作品”而遭約談。(頁86)
最后,黨部掛帥的“反共文學”究竟有沒有成就?應當如何認識乃至重新認識它的價值?文學史家與文學作家之間的分歧可以預期。文學史家云,“這種文學作品的誕生,基本上與國家權力脫離不了依賴的關系。作家心靈向權力靠近,向政府交心表態,使得文學作品全然失去了批判的能力。不僅如此,作家的思考等于是向權力體制開放,隨時可以接受干涉與干擾”;[14]更嚴苛者則言“‘反共文學大鍋菜式的同質性(公式化)、虛幻性和戰斗性等反文學主張,是它的致命傷,所以盡管它霸占了整個臺灣文學發展的空間,文學的收成還是等于零”。[15]而王鼎鈞雖然并未直接參與“反共文學”的書寫,但他仍主張不妨以“同情之理解”來看待這一份臺灣文學的遺產。他認為“反共文學”的生命力不在其意識形態的撥弄操控抑或非文學化的書寫模式,而在于它以創作實績延續廢止日語后的臺灣文學創作的那段空窗期,“從文學史的角度看,‘反共文學延續創作行為,填補空隙,承先啟后。往遠處看,它替后世作家保存了許多素材”。其次,“反共文學”的書寫,也是啟發原本以日語寫作的臺灣本省作家,磨礪中文語言文學能力,重新出發的重要材料。“‘反共文學傳達的訊息,臺灣作家并不喜歡,但是文學的學習觀摩者應該可以把內容和形式分別對待。那時中國30年代的新文學作品列位禁書,本省作家無可取法,反共也許討厭,文學技巧尤其是語言,那是天下公器”。[16]更何況,“反共文學”中并非全然是粗制濫造之作,亦不乏經典。張愛玲的《秧歌》、姜貴的《旋風》,如今都是文學研究者的必讀經典。
四、結語
實如孟悅所言,“歷史規定我們,規定著我們的話語,而又是我們以自己的話語宣布著歷史的規定。歷史借助或利用我們完成它偉大的故事,而又是我們記錄和講述著歷史,把它變成我們的敘事”。[17]文學史現場的復雜局面,實在無法用單線平面來粗草勾勒。就50年代的臺灣文學來講,一直以來被目為書寫主潮的“反共文學”,在《文學江湖》的回憶里,其實是浮夸的空中樓閣,并無堅實的讀者基礎,甚至連許多體制內的作家都對參與這項寫作不甘扈從,這多少提點讀者理解歷史/文學史書寫的“暴力”。
誠然,文學史的著眼之處,是文學場域生產的“大環境”,其書寫邏輯自上而下,從關注政治機器對文藝的運作情況入手來勾勒文學史線條。在敘述活動進行的過程中,對主線、核心的過分倚重和強調,如本雅明在《講故事的人》所預見的那樣,使得“可交流的經驗不是更豐富而是更匱乏”。[18]而透過回憶錄文本對個人隸屬的社會與團體歷史的主觀介入與盡心書寫,那種歷史現場感得以筆墨的方式鮮活續存。從作家回應“反共文學書寫”這個文學小生態系統出發,通過對讀文本,讀者可以反思自己對于這一段文學史的認知:在用心感受這種文學敘述魅力的同時,未必一定要依據文學文本來修訂歷史敘述,但卻能明晰地認識到在歷史敘述中,文學言說自有其發生的孔道;并以文學所獨到的創造性特質,為歷史“大敘述模式”投下精彩變量。《文學江湖》即是如此一本具有巨大歷史深度的文學文本。回憶錄的書寫形式,通過取舍、拼接、剪裁人生素材,展示出作家個人實感經驗與文學形式之間的完美融合。個人的人間行旅在歷史長河中實在太過短暫,可是生命長河生生不息,能將一葉文學的扁舟置放之上,或者就能夠依憑文學的魅力獲得歷史的永恒。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現當代文學制度史”子課題“臺灣、香港地區:特定時空下的文學制度”研究成果,項目批準號11&ZD112
[1][法]菲利普·勒熱訥著,楊國政譯:《自傳契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4頁。
[2]高華:《讀王鼎鈞的〈文學江湖〉:冷戰年代一位讀書人的困窘和堅守》,《思想》雜志第18期,臺北:聯經出版,2011年5月。
[3]邱貴芬主編:《日據以來臺灣女作家小說選讀》,臺北:女書文化,2001年版,第4—5頁。
[4]計璧瑞:《張道藩與國民黨的文藝政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年第1期。
[5]在“文學史如何批判/書寫反共文學”這個議題上,應鳳凰指出,國民黨文學史書將“反共文學”視為“表現一種志士爭自由的時代精神、作家親身的血淚經驗”;臺灣本土派陣營之文學史書則指稱其“形式僵化,主題教條化,墮落為政治的附庸,是沮喪與仇恨的夢囈,和本地民眾的現實生活脫節”;大陸左派陣營之文學史書直言其“顛倒歷史是非,歪曲現實生活,只是國民黨的宣傳工具,掩飾失敗真相,是麻醉與逃避的文學”。參見應鳳凰著:《五十年代臺灣文學論集》,臺北:春暉出版社,2004年版,第52—55頁。
[6]應鳳凰:《五十年代臺灣文學論集》,臺北:春暉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頁。
[7][15]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出版社文化出版部,1991年版,第72頁、第75頁。
[8]尹雪曼:《中華民國文藝史》,臺北:中正書局,1976年版,第87頁。
[9][12][13][14]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280頁。
[10]陳建忠等著:《臺灣小說史論》,臺北:麥田出版,2007年版,第115頁。
[11]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志社,1987年版,第88頁。
[16]王鼎鈞:《文學江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初版,第89頁。
[17]孟悅:《歷史與敘述》,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初版,第2頁。
[18] [德]本雅明著,張旭東等譯:《啟迪:本雅明文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96頁。
作者信息:馬泰祥,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臺港暨海外華文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