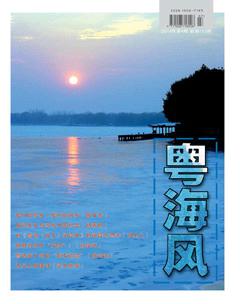我們為什么要去曲阜
干春松
一、曲阜曲阜
曲阜,對于一個研究儒學的人而言,是座“圣城”。而我每次來到這里,總是會涌出一種十分復雜的情緒。
這些年有很多機會可以“朝圣”,但我卻一直很少來。其中原因也難以言喻,有時候則是對規模太大、儀式感太強的活動心生畏懼,比如國際儒聯或孔子研究院的世界儒學大會,就令人望而卻步;有時則是源于意識形態的諸多限制,比如尼山論壇,因為他們“拒絕”比較有創新意義的儒家學者出席,同時也愿意吸納許多并不從事儒學研究的人參與。所以,我也跟著沒了興趣。
要說我也并不是那么嚴苛,而是屬于“中庸”之人。但從一個研究者的角度出發,我的確更愿意去開一些有明確問題指向的會議,這些會議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偶爾也會在廣州出現。比如《開放時代》的專題會議和曾亦老兄籌辦的會,都很有質量。
不過,曲阜就是曲阜,這所“圣城”有不可替代的地方。我研究的每一個問題,幾乎都與這個地方相關,如果紹興是我身體上的故鄉的話,曲阜或許就是精神上的家園,而且這種感覺愈發強烈。
我第一次“朝圣”曲阜,是陪同湯一介和龐樸兩位先生。當年一路上聽龐公講述他“文革”期間在曲阜整理孔府檔案的往事,一起走在嶧山小道。可是,如今兩位先生的身體都愈發令人擔心,他們或許再不能完成一趟曲阜的“旅行”,而我,則或許應該趁自己還走得動的時候,常來這里,看看那些石頭,那些山水,體悟孔子的靈感。因為他的堅持、他的理想,都源自這里。
二、“南孔”和“北孔”
這次去曲阜,主要是為了籌拍中央電視臺的紀錄片《孔子》,作為找素材的前采準備,撰稿組準備開赴曲阜和衢州。
許多人或許會問,遠在浙江的衢州跟孔子有什么關系嗎?清朝兵部尚書李之芳《清康熙衢州重修孔氏家廟碑》云:“孔氏之家廟者遍行天下,唯曲阜衢州耳。”這就是說,天底下有許多孔廟,但是家廟卻只有兩處,一處在曲阜,一處在衢州。
那么,為什么“萬世一系”的衍圣公除了在曲阜之外還存在家廟呢?事情的原因還必須追溯到中國歷史上的戰亂。大略地說:1127年,在著名的“靖康之恥”之際,宋朝在跟女真族的戰爭中,那位喜歡畫畫寫字的皇帝宋徽宗被擄,而趙構被擁戴為宋高宗,被迫南渡建立南宋皇朝。1128年,這個流亡的王朝在揚州祭天,孔子的48代孫孔端友陪祭。后來,南宋定都臨安,孔端友也跟隨南下,并被賜家衢州。這樣,就有了“南孔”,而孔端友的弟弟則只好留守曲阜。
至元十九年(1282年),南宗在衢州已歷經五代衍圣公,而元朝在統一中國之后,令孔子第53代嫡長孫孔洙奉詔入覲,元世祖要求他其載爵回故里曲阜承祀。孔洙認為,衢州已有5代墳墓,若遵皇上詔令北遷,自己實在不忍離棄先祖的墳墓;若不離棄先祖墳墓,又將有違圣意。孔洙表示,母老乞南還,愿將自己的衍圣公爵位讓給他在曲阜的族弟孔治世襲。這樣衍圣公的封號就讓位給留在曲阜的后裔。
由于這個事件,造成了孔子族譜上的很多問題,因此,前些年已故的朱維錚先生就說過他不怕得罪孔子后裔,一定要堅持曲阜之譜系為假的說法,他在《東方早報》撰文說:“我是研究經學史的,很重視家譜族譜之類史料。以前我常說,如果血親聯系無法證明,那么任何譜系就都難免有偽造的嫌疑。史書上明明白白記載著孔子的嫡系,到他的二十世孫孔融被曹操滅門,就中斷了。孔子說過‘夷狄之有君也,不如諸夏之無也。建立金朝的女真權貴痛恨此說,攻打北宋時到曲阜就放火燒了三孔。當時跟隨宋高宗南逃的人群里有孔子的族裔,就是遷居浙江衢州的‘南孔。稍后金朝海陵王突然想到要尊孔,就在民間拉出一個人封作衍圣公,于是‘北孔就續起族譜了。這樣的歷史在蒙元又重演。有歷史記載可證。”
當然,這段話里也有很多的史實的問題,但此處可以暫不考證,需要略微說一句的是,這次去曲阜孔林,發現一則材料,即朱維錚先生的老師,經學史研究的老一輩學者周予同先生,曾經在北師大紅衛兵譚厚蘭去孔林挖孔令貽墳墓的時候,被“指示”從上海速到曲阜,去“陪挖”。
周予同先生的經學史研究,大約是把經學當作“博物館”的材料來研究的,所以,他一直主張要分清“真孔子”和“假孔子”,但是不知為何選擇他去挖墓,這個背景我不甚了解,反正朱維錚是由著“真孔子”和“假孔子”來討論孔子的血統的。
三、孔廟、孔府和孔林
1992年第9期的《讀書》上曾發表了《孔林片思》一文,很受人關注。我自己覺得,費老之所以晚年關注“文化自覺”的問題,或許與他晚年重走江村,關注農村的發展有關。其中關于孔廟,他說:“這次到了孔廟我才更深刻地認識到中國文化中對人的研究早已有很悠久的歷史。孔子講‘仁就是講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講人與人之間如何相處。孔子的家族現在已經到了七十六代了,這說明中國文化具有多么長的持續性!“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要破壞孔廟,群眾不讓,被保護了下來。為什么老百姓要保護它?說明它代表著一個東西,代表著中國人最寶貴的東西,這就是中國人關心人與人如何共處的問題。”
的確,“三孔”的存在,在某種意義上是中國文化持續恒久發展的一個重要證據,雖然歷史上的每座城池都基本會遭到異族的侵略和來自內部的破壞,但是,對于曲阜的爭議卻很少。因為,曲阜的建城史雖然與魯國的故城有關系,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曲阜,大約是圍繞著孔子死后,因弟子守孝,被人仿效而逐漸形成的。
費老說中國人關心“人與人如何相處”的問題,也是說到了關鍵處。儒家素來“借天道明人事”,核心是關心人與人、人與社會的事,而不太關心死后的世界。雖然“慎終追遠”,但核心還在“民德歸厚”,“神道設教”。所以梁漱溟先生說中國文化早熟,很快就走出了信仰,進入了理性主義的時期。沒有發展出西方社會中教會化的宗教。當然,中國沒有發展出教會化的宗教一事,可以有很多種意見,也不好用好不好來評判。但是,關注人事,則無疑是儒家文化的特點。難怪黑格爾要說看儒家的書,沒有哲學味,只有一個道德格言而已。
要說孔廟,各地的建制都類似。而對于曲阜,我最喜歡的是大成殿的石柱,那上面雕刻的祥云和龍紋,雖然是一種孔子地位的象征,但是,我依然會覺得,當陽光透過這些鏤空穿出來的時候,會給人帶來一種無比溫暖之感。
這次去時,孔府正在修繕,我們通過文物局的工作人員介紹,實地觀察了古建筑修繕的過程,在“詩禮堂”邊,他們一邊介紹詩禮堂的一些典故,一邊介紹古建筑修繕的一些規定。這個“詩禮堂”當然是后起的建筑,但其原委也來自于孔子教孔鯉學詩習禮,并留下“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這樣的話。
“三孔”這樣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所有的修繕活動都是要報上級批準的,尤其彩繪的修繕更要做特別的工作,在新繪之前,要把舊彩繪的拓下來。這是一道程序。
有一位修繕工人祖上三代一直在孔府工作,擔任古建修繕工作,他說以前曲阜人都以在三孔工作為榮,理由一方面是因為三孔是曲阜的最著名的景點,同時人們對孔子抱有敬意;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這個工作有保障、福利不錯。但是他也“坦承”,由于收入的減少,現在在“三孔”工作已經不再具有從前的吸引力。
詩禮堂的后邊則是魯壁,我們只能通過被腳手架掩住的空隙,想象漢代魯壁損毀露出舊書的情境,進而想象這個關乎古文和今文的故事,在歷史的蒼茫中像謎一樣存在。
我們這次趕在清明節去曲阜,還有一個原因是要觀摩孔氏聯誼會的清明祭祖活動。
清明的前一天,我們采訪了一位修族譜的老人,他也是聯誼會的負責人之一,年逾八旬,身體健朗。他給我們出示了收集孔氏后裔的表格。他介紹說,最新統計姓孔的人已經有四百多萬。
不過,這次了解到,竟然孔子的后人也有在西藏和青海生活的,甚至有些孔氏后裔的長相已經趨近于藏族人。前一陣看景軍寫的《神堂記憶》,他提到甘肅孔氏后人的生活變遷,也感覺不論生活如何變遷,總有一種特殊的精神將孔氏后裔凝聚。
孔林是曲阜埋葬孔子后裔的公共墓地,最初孔子就埋在這里,進而流傳下來關于子貢和其他弟子的著名故事。但是,這里的許多碑在“文革”時期都被砸斷了,包括孔子的墓碑也難以逃脫損毀的命運。孔子和孔鯉、子思的墓排列在一起,成犄角之勢,按旁聽導游的說法,是“攜兒抱孫”,孔鯉和子思的墓碑后面立著刻有二世組和三世組的小碑,各地孔裔族人,在祭拜完孔子之后,會繼續在二世祖三世祖墓前行禮。
四、尼山和東野村
尼山,是孔子的誕生地,大約在距曲阜城30公里的地方,原先屬于泗水,現在劃歸曲阜。
最近幾年因為尼山文明對話的活動,所以尼山變得比較知名。尼山書院,最初是為了教育孔子家的后裔而建立,書院建有一座觀川亭,據說孔子就是在這里浩嘆“逝者如斯夫”,但現在看來,河水很少,大約也已經流動不暢。
去尼山,夫子洞才是關鍵。
夫子洞又名坤靈洞,天然石室,位于尼山孔廟東南崖下,相傳為孔子誕生處。《闕里志尼山》載:“溪流而南,其上為坤靈洞。”坤,雌性之義,靈,精靈。相傳孔子的母親顏徵在曾在此祈禱并于尼丘山而生孔子。孔子出生后,其父叔梁紇嫌其貌丑陋,棄于山上,此地今名紅草坡。傳說正巧一只母虎過此,將其銜入洞中乳養。故名“坤靈”。
當然關于孔子出生,主要的爭議點不在是否他父親嫌其丑陋,而是關于野合的傳說。野合之事,史有明傳,《史記·孔子世家》,開篇說“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意思是說“叔梁紇(孔子的父親)與顏姓的女子野合,于是生下了孔子”。但是野合的解釋很多,網上可以查到的就有比如:中國古代禮儀認為結婚生育的合適年齡,男性應該在16至64歲之間,女性應該在14歲至49歲之間。凡是在這個范圍之外的都是不合禮儀的,孔子的父親叔梁紇迎娶顏徵(該字讀zheng,陰平)在時已72歲,故稱之為“野合”。 又有說顏徵在屬賤民階級,叔梁紇卻是士大夫,迎娶于禮不合,故稱“野合”。 亦有指司馬遷只是說叔梁紇和顏徵在于野外交合(這是一種古代習俗),故稱之“野合”。所以,這個事情是一種古代禮儀還是其他,難以斷定。另據《孔子家語》記載: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于顏氏,顏氏有三女,小女徵在從父命為婚。大約是要把這個事情瞞過去的。
夫子洞旁邊還有一個新的書院,叫尼山圣源書院,是一群儒家學者建立的,以前的院長是牟鐘鑒先生,現在的執行院長是山東大學的顏炳罡。這次恰好碰上顏炳罡和我的朋友趙法生在尼山中學談論開設論語課程的事,順便了解到趙法生和顏炳罡一直在尼山附近的一些村子進行講學活動,并對當地的村風民俗起到了改善的作用。
他們帶著我們去了一個叫東野的村子,這個村子相對還比較貧窮,村民的房子上都印著《論語》里的句子,墻上還畫著二十四孝圖。
趙法生說,他因為深感農村的道德潰敗,比如東野村發生過兒媳婦在路上直接打婆婆耳光的事,以及老人給孩子蓋了房子,而自己卻只能住在四面漏風的老人屋的等等情況,故而作為山東人的他便想通過自己的講學活動來改變。最初的講學活動很艱難,因為村民本身有農活,不愿抽時間,其次他們也不太相信這樣的講學活動能帶來什么實際境遇的改善。因而起初幾次,他們為來聽的村民準備了毛巾、肥皂之類的日用品,以吸引村民。但幾次之后,村民們逐漸從《三字經》《弟子規》等一系列道理中,查找出了自己的問題,逐漸改變了他們的生活行為。
據村支書說,他如果說要召集會議,在村里的喇叭里喊半天也沒人來,而現在只要聽說有人來講課,村民就很踴躍,所以村支書往往把他要開的會議放在講課前。
民間講學活動,是儒家的傳統。在南宋,晚明一直很盛行,雖然那時的講會活動更為多樣,但是考慮到現在的儒學活動主要集中在大學里,主要以研究的形式展開,而村里的講學活動則是從重建日常生活開始,我想,儒家的生活力,更多應該來自這樣的實踐活動。
分別之際,趙法生說要我今年去給那些村民講一次,我答應了,但是,我講什么呢?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