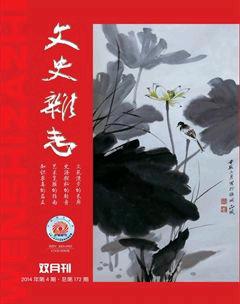從吳濁流小說看臺灣地區知識分子的尋根意識
趙元堯
對于初讀中國臺灣地區文學的大陸人來說,實在產生不了像臺灣作家吳濁流先生的小說中頻繁出現的類似文化認同之類的困惑;不僅如此,很多人甚至驚訝于如此一個理所當然不用思考的問題居然會困擾臺灣人這么久。這大抵是因為我們對于中國文化的歸屬感是一出生便有的,也可以說是這幾千年來一代代傳承、從未割裂的,我們的“根”是唯一且不變的。無論祖國是落后還是繁榮,我們的民族與文化認同都不會有絲毫的動搖。再來看臺灣地區,由于近代時局的變換,關于認同的問題一直不斷地困擾著一代又一代的臺灣人。為此,許多知識分子都在苦苦追尋答案。
一
總的來說,中國臺灣地區近代以來出現的認同情結、尋根意識當與兩個主要的因素有關,一是政權的更迭,二是獨特的地理位置。臺灣的近代歷史絕對不能忽視的就是日本對其長達半個世紀的占領與殖民,它在文化和現代化的方方面面對臺灣產生了難以想象的影響。
甲午戰爭(1894—1895年)以來,日本侵略者一直在臺灣地區大力推行所謂同化(實則為奴化)教育,誘引臺灣人去做“真正的”日本人。可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在本質上的對立,和臺灣地區一直以來的殖民統治的高壓氛圍,使得成長于這一時期的臺灣年輕人處于一種認同的迷惘之中。他們既接受了在當時相對現代化的日本式教育,體會到現代化的種種好處,可是又不斷地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侵略者的壓迫和失去“根”的失落。而隔海相望的祖國大陸縱使有風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卻也因那一片海洋而被隔絕。
與此相應,在日本統治時期,臺灣文學也經歷了好幾次明為文學的論戰,實為文化認同的論戰(除了新文學發展的萌芽期主要為單純改革語文的那次論戰外)。“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臺灣的新文學到底應該使用哪一種語言寫作呢?是祖國大陸的白話文(北京話文)、臺語還是日本語?首先在語言的使用上,作家們就要進行痛苦的抉擇。到底是把臺灣文學放入中國文學的大體系中,還是將之剝離出來,在當時還只是一個關于文學本土化問題的論爭。不過,隨著日本侵略者在政策上的變化(全面推行“皇民化”政策),文學的創作便只余以日本語文為工具的選項了,文化上的“根”漸被混淆了。而后在光復初期,來臺接收的國民政府又管理不力,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導致了“二·二八事件”(1947年)。原本期待光復卻被現實潑了冷水的臺灣人對待外省、大陸、政府的態度更加微妙。70年代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得以恢復,許多臺灣人的自我認同問題也因此變得更為復雜。
二
而以《亞細亞的孤兒》一書道盡日本統治時期臺灣人身份模糊、迷失處境而出名的吳濁流先生(1900—1976)可謂是經歷了近代臺灣地區最重要的兩個時期:日據和國府。正是以他為代表的作家們將臺灣人的這種認知的彷徨、迷失和不斷的尋根放入到文學創作之中,才讓我們讀到一代知識分子對祖國寶島臺灣命運的深刻思考。
關于我要討論的主題,在先生的筆下主要有兩種臺灣人的形象:1.努力卻仍得不到與日本人同樣待遇、在所謂同化中沉淪的知識分子(如《功狗》里的洪宏東、《水月》里的仁吉);2.御用紳士(《陳大人》、《糖扦仔》等)。
先說所謂同化吧。成長于日本統治時期的知識分子,即便從小就接受完全日式的教育,對日本的“認同”也多半是矛盾與痛苦的。因為無論他們如何學習日本文化、日本的生活方式,他們也永遠只能是次等公民,永遠得不到與在臺日本人相同的待遇,更不可能成為如侵略者所許愿的“真正的日本人”。
在吳先生的書中就有許多這樣的描寫:“二等車是玉蘭很不容易坐的,他覺得身份忽然高起來”,“當時日人對臺灣人動輒就處笞刑”,“你們是野蠻人……你們這樣的清國奴如何配作日本國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其實,這種不平等本身就是日本侵略者維護殖民體制的根基所在。它對底層人民是精神與文化的折磨,對知識分子更是一種宿命性的悲劇。不少知識分子就是在這樣的打擊中由迷惘走向了沉淪與毀滅。
在《水月》中,主人公仁吉就是這樣的知識分子,“抱負很大,也有很高的理想”,現實讓他不得不到制糖會社做雇員,但是因為臺灣人的身份,“這十五年間他雖然對‘會社有過不少貢獻,但‘會社卻從來也沒有改善過他的待遇……仍然是個雇員……制糖會社雖然很賺錢,只是對臺灣人這樣刻薄……”小說的結尾是無奈而且悲傷的——仁吉突然忍無可忍地對妻子說:“蘭英,蘭英,我要去東京。”妻子卻流著淚說他夢還未醒,“可是他少年時代所抱的理想,他所憧憬的世界,他的美麗的夢,縱然已經過了十年二十年,還是那樣美麗地蕩漾在心頭”,這種無可為的悵惘和對現實的無奈,實在令人嘆息。
再說“御用紳士”吧,他們其實是一些面對殖民者的壓迫、歧視而自我作踐,心靈變異的特殊人群。他們不僅在文化上認同日本,在很多時候還傍依殖民者而充當壓迫同胞的角色。
《先生媽》里面的錢新發立志要做一個“真正的”日本人。他還視說臺灣話、穿臺灣衣的母親為“眼中釘”,不愿母親到客廳接待客人。“日本政府許可臺灣人改姓名的時候,他更怕落后,立刻把姓名改為金井新助,并且掛起新的門牌,同時家族開始了穿‘和服的生活……同時又建筑純日本式的房子。這個房子落成的時候,他喜歡極了,要照相作紀念。”他和妻子、孩子已全然日本化了,穿和服、彈日本琴、住日本房子、吃日本料理,整日里大談所謂日本精神以及如何做日本人。
在母親明確留下遺囑說不可以請日本和尚的情況下,他在母親死后仍然大張旗鼓地辦了一場日式的盛大葬禮。他的形象與王昶雄先生《奔流》中的臺灣人伊東春生的形象不謀而合——伊東春生里里外外都完全看不出是臺灣人,甚至在母親的葬禮上未流一滴眼淚。他們即是被侵略者夸贊的那一部分所謂“歸化”日本、甚至成為“皇民化”典范的臺灣人。
《陳大人》中的陳大人,和《糖扦仔》中的糖扦仔則比假心假意對人的錢新發之流更為可恨。陳大人不僅靠做“御用”警察在鄉里作威作福,還貪污、剝削,無惡不作,直至弄到悲慘可笑的結局也還不悔悟,對同胞仍是大罵“巴迦野郎”……而在鄉里有權有勢的糖扦仔在看上女學生月英之后資助她上學,又多方“關照”她母親的面店,最后奸污了不愿嫁給他的月英,將其逼死。(在《泥沼中的金鯉》中也有類似情節。)陳大人、糖扦仔的形象,充分地表現了日據時期所謂“體面人”(實為奴才)沐猴而冠的丑態。他們越受到日本人的歧視就越是加倍地鄙視、折磨和自己一樣的位于底層的臺灣人,并且賦予自身這種行為以“日本化”的合理性,完全忘記了自己的民族屬性,根本拋棄了自己的文化母體。這種心靈的扭曲與猙獰,既可惡又可悲。
三
日據時期的臺灣人,從主流來看,一直盼望能早日光復,回歸祖國。這在知識分子群體中尤為如此。吳濁流先生在二戰期間曾去過祖國大陸,只是他所見所感與他的想象并不符合。連年的戰亂讓大陸的現代化進程停滯,戰火波及處是滿眼的凋敝。
而戰后早期接收臺灣的國軍形象的不堪也令歌唱光復的臺灣人失望:“隊伍連續的走了很久,每一位兵士都背上一把傘……有的挑著鐵鍋,食器或鋪蓋等……(玉蘭)她內心非常難受,可是有日人在旁的地方也不愿示弱……雖然所得到的外觀不是什么好的,可是心里總有說不出的滿足感……好像被人收養的孩子遇上生父生母一樣,縱然他的父母是個要飯的……”(《波茨坦科長》)
當國民政府任命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司令陳儀領兵入臺后,這里的治理腐敗不堪,走私猖獗,物價飛漲。國民政府接管的行政機構、醫院、法院等全部辭退了不會說國語的臺灣人,很多人失業,且飽受從大陸來臺的軍民的歧視。這之后便發生了“二·二八事件”,成為臺灣人和外省人心中永遠的痛。
在這樣的背景下,在吳先生的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中,主人公胡太明便以一個在認同上始終迷惘的臺灣青年形象出現在讀者眼中。他在臺灣當教員時喜歡上日本女同事久子,但卻被久子以身份不同拒絕了。他之后在日本留學,以為可以提高身份,卻照樣受到日本人的歧視,回到臺灣后還是失業。而當他到大陸謀職時,也遇到比異族歧視更為尷尬的情形與矛盾,以至于他要隱瞞自己臺灣人的身份。之后他還經歷了入獄、戰爭,一切的理想都沒能實現。他輾轉各地,最后在悲憤中精神崩潰。
胡太明作為小說主人公的一生,反映的是作為小說作者的吳濁流先生等為數不少的臺灣知識分子對自我認同的迷茫、彷徨與探索。這是一種在流亡中的嚴肅思考,是一種由認同危機生發的尋根意識。
在以吳濁流為代表的臺灣地區作家筆下,這種由內在的流亡而產生的流亡文學(或范圍更大的臺灣文學),其主人公的精神多因內心對“根”的疏離而異化,在找不到出口之后,往往會走向毀滅性的結局(如失蹤、出走、瘋狂、死亡等),這樣的結局或可能在今天的現實中真正發生。這無疑給當今臺灣地區的年輕知識分子一個值得鄭重考慮與嚴肅回應的警示。
參考文獻:
1.《吳濁流選集》小說版,臺北廣鴻文出版社1966年12月出版。
2.吳濁流漢詩集《風雨窗前》(其中附錄《先生媽》《陳大人》),苗栗文獻書局1958年5月發行。
3.吳濁流中篇小說《波茨坦科長》,臺北學有書局1948年出版。
4.傅恩榮譯、黃渭南校閱吳濁流小說《亞細亞的孤兒》,臺北南華出版社1962年6月出版。
5.王昶雄中篇小說《奔流》,載《臺灣文學》第3卷第3期(1943年),后收錄于《臺灣小說集》,大木書房出版。
對于初讀中國臺灣地區文學的大陸人來說,實在產生不了像臺灣作家吳濁流先生的小說中頻繁出現的類似文化認同之類的困惑;不僅如此,很多人甚至驚訝于如此一個理所當然不用思考的問題居然會困擾臺灣人這么久。這大抵是因為我們對于中國文化的歸屬感是一出生便有的,也可以說是這幾千年來一代代傳承、從未割裂的,我們的“根”是唯一且不變的。無論祖國是落后還是繁榮,我們的民族與文化認同都不會有絲毫的動搖。再來看臺灣地區,由于近代時局的變換,關于認同的問題一直不斷地困擾著一代又一代的臺灣人。為此,許多知識分子都在苦苦追尋答案。
一
總的來說,中國臺灣地區近代以來出現的認同情結、尋根意識當與兩個主要的因素有關,一是政權的更迭,二是獨特的地理位置。臺灣的近代歷史絕對不能忽視的就是日本對其長達半個世紀的占領與殖民,它在文化和現代化的方方面面對臺灣產生了難以想象的影響。
甲午戰爭(1894—1895年)以來,日本侵略者一直在臺灣地區大力推行所謂同化(實則為奴化)教育,誘引臺灣人去做“真正的”日本人。可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在本質上的對立,和臺灣地區一直以來的殖民統治的高壓氛圍,使得成長于這一時期的臺灣年輕人處于一種認同的迷惘之中。他們既接受了在當時相對現代化的日本式教育,體會到現代化的種種好處,可是又不斷地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侵略者的壓迫和失去“根”的失落。而隔海相望的祖國大陸縱使有風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卻也因那一片海洋而被隔絕。
與此相應,在日本統治時期,臺灣文學也經歷了好幾次明為文學的論戰,實為文化認同的論戰(除了新文學發展的萌芽期主要為單純改革語文的那次論戰外)。“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臺灣的新文學到底應該使用哪一種語言寫作呢?是祖國大陸的白話文(北京話文)、臺語還是日本語?首先在語言的使用上,作家們就要進行痛苦的抉擇。到底是把臺灣文學放入中國文學的大體系中,還是將之剝離出來,在當時還只是一個關于文學本土化問題的論爭。不過,隨著日本侵略者在政策上的變化(全面推行“皇民化”政策),文學的創作便只余以日本語文為工具的選項了,文化上的“根”漸被混淆了。而后在光復初期,來臺接收的國民政府又管理不力,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導致了“二·二八事件”(1947年)。原本期待光復卻被現實潑了冷水的臺灣人對待外省、大陸、政府的態度更加微妙。70年代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得以恢復,許多臺灣人的自我認同問題也因此變得更為復雜。
二
而以《亞細亞的孤兒》一書道盡日本統治時期臺灣人身份模糊、迷失處境而出名的吳濁流先生(1900—1976)可謂是經歷了近代臺灣地區最重要的兩個時期:日據和國府。正是以他為代表的作家們將臺灣人的這種認知的彷徨、迷失和不斷的尋根放入到文學創作之中,才讓我們讀到一代知識分子對祖國寶島臺灣命運的深刻思考。
關于我要討論的主題,在先生的筆下主要有兩種臺灣人的形象:1.努力卻仍得不到與日本人同樣待遇、在所謂同化中沉淪的知識分子(如《功狗》里的洪宏東、《水月》里的仁吉);2.御用紳士(《陳大人》、《糖扦仔》等)。
先說所謂同化吧。成長于日本統治時期的知識分子,即便從小就接受完全日式的教育,對日本的“認同”也多半是矛盾與痛苦的。因為無論他們如何學習日本文化、日本的生活方式,他們也永遠只能是次等公民,永遠得不到與在臺日本人相同的待遇,更不可能成為如侵略者所許愿的“真正的日本人”。
在吳先生的書中就有許多這樣的描寫:“二等車是玉蘭很不容易坐的,他覺得身份忽然高起來”,“當時日人對臺灣人動輒就處笞刑”,“你們是野蠻人……你們這樣的清國奴如何配作日本國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其實,這種不平等本身就是日本侵略者維護殖民體制的根基所在。它對底層人民是精神與文化的折磨,對知識分子更是一種宿命性的悲劇。不少知識分子就是在這樣的打擊中由迷惘走向了沉淪與毀滅。
在《水月》中,主人公仁吉就是這樣的知識分子,“抱負很大,也有很高的理想”,現實讓他不得不到制糖會社做雇員,但是因為臺灣人的身份,“這十五年間他雖然對‘會社有過不少貢獻,但‘會社卻從來也沒有改善過他的待遇……仍然是個雇員……制糖會社雖然很賺錢,只是對臺灣人這樣刻薄……”小說的結尾是無奈而且悲傷的——仁吉突然忍無可忍地對妻子說:“蘭英,蘭英,我要去東京。”妻子卻流著淚說他夢還未醒,“可是他少年時代所抱的理想,他所憧憬的世界,他的美麗的夢,縱然已經過了十年二十年,還是那樣美麗地蕩漾在心頭”,這種無可為的悵惘和對現實的無奈,實在令人嘆息。
再說“御用紳士”吧,他們其實是一些面對殖民者的壓迫、歧視而自我作踐,心靈變異的特殊人群。他們不僅在文化上認同日本,在很多時候還傍依殖民者而充當壓迫同胞的角色。
《先生媽》里面的錢新發立志要做一個“真正的”日本人。他還視說臺灣話、穿臺灣衣的母親為“眼中釘”,不愿母親到客廳接待客人。“日本政府許可臺灣人改姓名的時候,他更怕落后,立刻把姓名改為金井新助,并且掛起新的門牌,同時家族開始了穿‘和服的生活……同時又建筑純日本式的房子。這個房子落成的時候,他喜歡極了,要照相作紀念。”他和妻子、孩子已全然日本化了,穿和服、彈日本琴、住日本房子、吃日本料理,整日里大談所謂日本精神以及如何做日本人。
在母親明確留下遺囑說不可以請日本和尚的情況下,他在母親死后仍然大張旗鼓地辦了一場日式的盛大葬禮。他的形象與王昶雄先生《奔流》中的臺灣人伊東春生的形象不謀而合——伊東春生里里外外都完全看不出是臺灣人,甚至在母親的葬禮上未流一滴眼淚。他們即是被侵略者夸贊的那一部分所謂“歸化”日本、甚至成為“皇民化”典范的臺灣人。
《陳大人》中的陳大人,和《糖扦仔》中的糖扦仔則比假心假意對人的錢新發之流更為可恨。陳大人不僅靠做“御用”警察在鄉里作威作福,還貪污、剝削,無惡不作,直至弄到悲慘可笑的結局也還不悔悟,對同胞仍是大罵“巴迦野郎”……而在鄉里有權有勢的糖扦仔在看上女學生月英之后資助她上學,又多方“關照”她母親的面店,最后奸污了不愿嫁給他的月英,將其逼死。(在《泥沼中的金鯉》中也有類似情節。)陳大人、糖扦仔的形象,充分地表現了日據時期所謂“體面人”(實為奴才)沐猴而冠的丑態。他們越受到日本人的歧視就越是加倍地鄙視、折磨和自己一樣的位于底層的臺灣人,并且賦予自身這種行為以“日本化”的合理性,完全忘記了自己的民族屬性,根本拋棄了自己的文化母體。這種心靈的扭曲與猙獰,既可惡又可悲。
三
日據時期的臺灣人,從主流來看,一直盼望能早日光復,回歸祖國。這在知識分子群體中尤為如此。吳濁流先生在二戰期間曾去過祖國大陸,只是他所見所感與他的想象并不符合。連年的戰亂讓大陸的現代化進程停滯,戰火波及處是滿眼的凋敝。
而戰后早期接收臺灣的國軍形象的不堪也令歌唱光復的臺灣人失望:“隊伍連續的走了很久,每一位兵士都背上一把傘……有的挑著鐵鍋,食器或鋪蓋等……(玉蘭)她內心非常難受,可是有日人在旁的地方也不愿示弱……雖然所得到的外觀不是什么好的,可是心里總有說不出的滿足感……好像被人收養的孩子遇上生父生母一樣,縱然他的父母是個要飯的……”(《波茨坦科長》)
當國民政府任命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司令陳儀領兵入臺后,這里的治理腐敗不堪,走私猖獗,物價飛漲。國民政府接管的行政機構、醫院、法院等全部辭退了不會說國語的臺灣人,很多人失業,且飽受從大陸來臺的軍民的歧視。這之后便發生了“二·二八事件”,成為臺灣人和外省人心中永遠的痛。
在這樣的背景下,在吳先生的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中,主人公胡太明便以一個在認同上始終迷惘的臺灣青年形象出現在讀者眼中。他在臺灣當教員時喜歡上日本女同事久子,但卻被久子以身份不同拒絕了。他之后在日本留學,以為可以提高身份,卻照樣受到日本人的歧視,回到臺灣后還是失業。而當他到大陸謀職時,也遇到比異族歧視更為尷尬的情形與矛盾,以至于他要隱瞞自己臺灣人的身份。之后他還經歷了入獄、戰爭,一切的理想都沒能實現。他輾轉各地,最后在悲憤中精神崩潰。
胡太明作為小說主人公的一生,反映的是作為小說作者的吳濁流先生等為數不少的臺灣知識分子對自我認同的迷茫、彷徨與探索。這是一種在流亡中的嚴肅思考,是一種由認同危機生發的尋根意識。
在以吳濁流為代表的臺灣地區作家筆下,這種由內在的流亡而產生的流亡文學(或范圍更大的臺灣文學),其主人公的精神多因內心對“根”的疏離而異化,在找不到出口之后,往往會走向毀滅性的結局(如失蹤、出走、瘋狂、死亡等),這樣的結局或可能在今天的現實中真正發生。這無疑給當今臺灣地區的年輕知識分子一個值得鄭重考慮與嚴肅回應的警示。
參考文獻:
1.《吳濁流選集》小說版,臺北廣鴻文出版社1966年12月出版。
2.吳濁流漢詩集《風雨窗前》(其中附錄《先生媽》《陳大人》),苗栗文獻書局1958年5月發行。
3.吳濁流中篇小說《波茨坦科長》,臺北學有書局1948年出版。
4.傅恩榮譯、黃渭南校閱吳濁流小說《亞細亞的孤兒》,臺北南華出版社1962年6月出版。
5.王昶雄中篇小說《奔流》,載《臺灣文學》第3卷第3期(1943年),后收錄于《臺灣小說集》,大木書房出版。
對于初讀中國臺灣地區文學的大陸人來說,實在產生不了像臺灣作家吳濁流先生的小說中頻繁出現的類似文化認同之類的困惑;不僅如此,很多人甚至驚訝于如此一個理所當然不用思考的問題居然會困擾臺灣人這么久。這大抵是因為我們對于中國文化的歸屬感是一出生便有的,也可以說是這幾千年來一代代傳承、從未割裂的,我們的“根”是唯一且不變的。無論祖國是落后還是繁榮,我們的民族與文化認同都不會有絲毫的動搖。再來看臺灣地區,由于近代時局的變換,關于認同的問題一直不斷地困擾著一代又一代的臺灣人。為此,許多知識分子都在苦苦追尋答案。
一
總的來說,中國臺灣地區近代以來出現的認同情結、尋根意識當與兩個主要的因素有關,一是政權的更迭,二是獨特的地理位置。臺灣的近代歷史絕對不能忽視的就是日本對其長達半個世紀的占領與殖民,它在文化和現代化的方方面面對臺灣產生了難以想象的影響。
甲午戰爭(1894—1895年)以來,日本侵略者一直在臺灣地區大力推行所謂同化(實則為奴化)教育,誘引臺灣人去做“真正的”日本人。可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在本質上的對立,和臺灣地區一直以來的殖民統治的高壓氛圍,使得成長于這一時期的臺灣年輕人處于一種認同的迷惘之中。他們既接受了在當時相對現代化的日本式教育,體會到現代化的種種好處,可是又不斷地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侵略者的壓迫和失去“根”的失落。而隔海相望的祖國大陸縱使有風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卻也因那一片海洋而被隔絕。
與此相應,在日本統治時期,臺灣文學也經歷了好幾次明為文學的論戰,實為文化認同的論戰(除了新文學發展的萌芽期主要為單純改革語文的那次論戰外)。“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臺灣的新文學到底應該使用哪一種語言寫作呢?是祖國大陸的白話文(北京話文)、臺語還是日本語?首先在語言的使用上,作家們就要進行痛苦的抉擇。到底是把臺灣文學放入中國文學的大體系中,還是將之剝離出來,在當時還只是一個關于文學本土化問題的論爭。不過,隨著日本侵略者在政策上的變化(全面推行“皇民化”政策),文學的創作便只余以日本語文為工具的選項了,文化上的“根”漸被混淆了。而后在光復初期,來臺接收的國民政府又管理不力,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導致了“二·二八事件”(1947年)。原本期待光復卻被現實潑了冷水的臺灣人對待外省、大陸、政府的態度更加微妙。70年代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得以恢復,許多臺灣人的自我認同問題也因此變得更為復雜。
二
而以《亞細亞的孤兒》一書道盡日本統治時期臺灣人身份模糊、迷失處境而出名的吳濁流先生(1900—1976)可謂是經歷了近代臺灣地區最重要的兩個時期:日據和國府。正是以他為代表的作家們將臺灣人的這種認知的彷徨、迷失和不斷的尋根放入到文學創作之中,才讓我們讀到一代知識分子對祖國寶島臺灣命運的深刻思考。
關于我要討論的主題,在先生的筆下主要有兩種臺灣人的形象:1.努力卻仍得不到與日本人同樣待遇、在所謂同化中沉淪的知識分子(如《功狗》里的洪宏東、《水月》里的仁吉);2.御用紳士(《陳大人》、《糖扦仔》等)。
先說所謂同化吧。成長于日本統治時期的知識分子,即便從小就接受完全日式的教育,對日本的“認同”也多半是矛盾與痛苦的。因為無論他們如何學習日本文化、日本的生活方式,他們也永遠只能是次等公民,永遠得不到與在臺日本人相同的待遇,更不可能成為如侵略者所許愿的“真正的日本人”。
在吳先生的書中就有許多這樣的描寫:“二等車是玉蘭很不容易坐的,他覺得身份忽然高起來”,“當時日人對臺灣人動輒就處笞刑”,“你們是野蠻人……你們這樣的清國奴如何配作日本國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其實,這種不平等本身就是日本侵略者維護殖民體制的根基所在。它對底層人民是精神與文化的折磨,對知識分子更是一種宿命性的悲劇。不少知識分子就是在這樣的打擊中由迷惘走向了沉淪與毀滅。
在《水月》中,主人公仁吉就是這樣的知識分子,“抱負很大,也有很高的理想”,現實讓他不得不到制糖會社做雇員,但是因為臺灣人的身份,“這十五年間他雖然對‘會社有過不少貢獻,但‘會社卻從來也沒有改善過他的待遇……仍然是個雇員……制糖會社雖然很賺錢,只是對臺灣人這樣刻薄……”小說的結尾是無奈而且悲傷的——仁吉突然忍無可忍地對妻子說:“蘭英,蘭英,我要去東京。”妻子卻流著淚說他夢還未醒,“可是他少年時代所抱的理想,他所憧憬的世界,他的美麗的夢,縱然已經過了十年二十年,還是那樣美麗地蕩漾在心頭”,這種無可為的悵惘和對現實的無奈,實在令人嘆息。
再說“御用紳士”吧,他們其實是一些面對殖民者的壓迫、歧視而自我作踐,心靈變異的特殊人群。他們不僅在文化上認同日本,在很多時候還傍依殖民者而充當壓迫同胞的角色。
《先生媽》里面的錢新發立志要做一個“真正的”日本人。他還視說臺灣話、穿臺灣衣的母親為“眼中釘”,不愿母親到客廳接待客人。“日本政府許可臺灣人改姓名的時候,他更怕落后,立刻把姓名改為金井新助,并且掛起新的門牌,同時家族開始了穿‘和服的生活……同時又建筑純日本式的房子。這個房子落成的時候,他喜歡極了,要照相作紀念。”他和妻子、孩子已全然日本化了,穿和服、彈日本琴、住日本房子、吃日本料理,整日里大談所謂日本精神以及如何做日本人。
在母親明確留下遺囑說不可以請日本和尚的情況下,他在母親死后仍然大張旗鼓地辦了一場日式的盛大葬禮。他的形象與王昶雄先生《奔流》中的臺灣人伊東春生的形象不謀而合——伊東春生里里外外都完全看不出是臺灣人,甚至在母親的葬禮上未流一滴眼淚。他們即是被侵略者夸贊的那一部分所謂“歸化”日本、甚至成為“皇民化”典范的臺灣人。
《陳大人》中的陳大人,和《糖扦仔》中的糖扦仔則比假心假意對人的錢新發之流更為可恨。陳大人不僅靠做“御用”警察在鄉里作威作福,還貪污、剝削,無惡不作,直至弄到悲慘可笑的結局也還不悔悟,對同胞仍是大罵“巴迦野郎”……而在鄉里有權有勢的糖扦仔在看上女學生月英之后資助她上學,又多方“關照”她母親的面店,最后奸污了不愿嫁給他的月英,將其逼死。(在《泥沼中的金鯉》中也有類似情節。)陳大人、糖扦仔的形象,充分地表現了日據時期所謂“體面人”(實為奴才)沐猴而冠的丑態。他們越受到日本人的歧視就越是加倍地鄙視、折磨和自己一樣的位于底層的臺灣人,并且賦予自身這種行為以“日本化”的合理性,完全忘記了自己的民族屬性,根本拋棄了自己的文化母體。這種心靈的扭曲與猙獰,既可惡又可悲。
三
日據時期的臺灣人,從主流來看,一直盼望能早日光復,回歸祖國。這在知識分子群體中尤為如此。吳濁流先生在二戰期間曾去過祖國大陸,只是他所見所感與他的想象并不符合。連年的戰亂讓大陸的現代化進程停滯,戰火波及處是滿眼的凋敝。
而戰后早期接收臺灣的國軍形象的不堪也令歌唱光復的臺灣人失望:“隊伍連續的走了很久,每一位兵士都背上一把傘……有的挑著鐵鍋,食器或鋪蓋等……(玉蘭)她內心非常難受,可是有日人在旁的地方也不愿示弱……雖然所得到的外觀不是什么好的,可是心里總有說不出的滿足感……好像被人收養的孩子遇上生父生母一樣,縱然他的父母是個要飯的……”(《波茨坦科長》)
當國民政府任命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司令陳儀領兵入臺后,這里的治理腐敗不堪,走私猖獗,物價飛漲。國民政府接管的行政機構、醫院、法院等全部辭退了不會說國語的臺灣人,很多人失業,且飽受從大陸來臺的軍民的歧視。這之后便發生了“二·二八事件”,成為臺灣人和外省人心中永遠的痛。
在這樣的背景下,在吳先生的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中,主人公胡太明便以一個在認同上始終迷惘的臺灣青年形象出現在讀者眼中。他在臺灣當教員時喜歡上日本女同事久子,但卻被久子以身份不同拒絕了。他之后在日本留學,以為可以提高身份,卻照樣受到日本人的歧視,回到臺灣后還是失業。而當他到大陸謀職時,也遇到比異族歧視更為尷尬的情形與矛盾,以至于他要隱瞞自己臺灣人的身份。之后他還經歷了入獄、戰爭,一切的理想都沒能實現。他輾轉各地,最后在悲憤中精神崩潰。
胡太明作為小說主人公的一生,反映的是作為小說作者的吳濁流先生等為數不少的臺灣知識分子對自我認同的迷茫、彷徨與探索。這是一種在流亡中的嚴肅思考,是一種由認同危機生發的尋根意識。
在以吳濁流為代表的臺灣地區作家筆下,這種由內在的流亡而產生的流亡文學(或范圍更大的臺灣文學),其主人公的精神多因內心對“根”的疏離而異化,在找不到出口之后,往往會走向毀滅性的結局(如失蹤、出走、瘋狂、死亡等),這樣的結局或可能在今天的現實中真正發生。這無疑給當今臺灣地區的年輕知識分子一個值得鄭重考慮與嚴肅回應的警示。
參考文獻:
1.《吳濁流選集》小說版,臺北廣鴻文出版社1966年12月出版。
2.吳濁流漢詩集《風雨窗前》(其中附錄《先生媽》《陳大人》),苗栗文獻書局1958年5月發行。
3.吳濁流中篇小說《波茨坦科長》,臺北學有書局1948年出版。
4.傅恩榮譯、黃渭南校閱吳濁流小說《亞細亞的孤兒》,臺北南華出版社1962年6月出版。
5.王昶雄中篇小說《奔流》,載《臺灣文學》第3卷第3期(1943年),后收錄于《臺灣小說集》,大木書房出版。